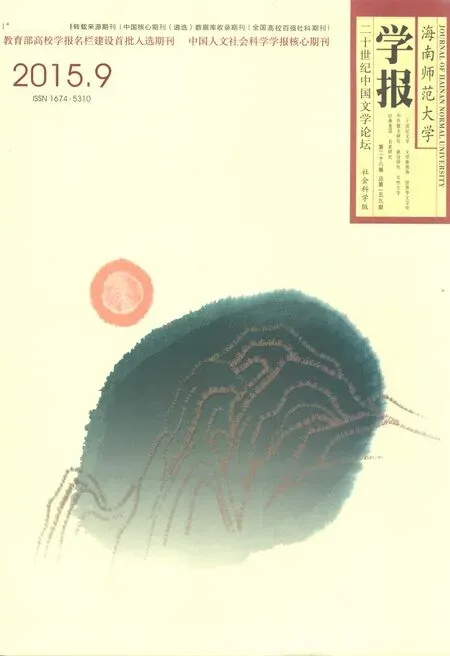“你”是“我”的眼——杜青论
姚则强
(韩山师范学院 诗歌创研中心,广东 潮州515633)
人心和世事,堆放一堆杂物
晒来晒去,从没有改变
我们经过树林、楼丛、人群
说不清曾有多少次兴奋和渴望
也说不清曾有多少次悲伤和绝望
生活的机器运转无常。亲爱的
我不想说明什么,只是想告诉你
天天注视相片,并时时微笑
这是件痛苦的事情,我却乐意
把这种痛苦视同幸福
——杜青《微笑》
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从事很多不同的艺术样式,或者一个作家什么体裁都写,会不会不专一。我想,其实艺术是相通的,就像艺术与哲学是相通的一样。在尝试了多种体裁,甚至不同的艺术样式后,杜青似有“烦恼”地在一本名为《一粒沙上的大海》的诗集后记中向我们袒露心迹。
“当然,我没有说出心中更重要的秘密,那就是,我热烈地爱上了小说,但心中却一直感恩着诗歌。”在写作上,应该说杜青是从诗歌这个门径出发的,之后才逐渐涉足小说等文体。而且,我非常认同她对于诗歌的这种认识,“诗歌像是我的母亲,我必须把母亲安顿好,才能安心地踏上新的路途。写诗至今,时近七年。七年来诗里诗外,我似日行千里的马,在自己思维的草原上驰骋,不论是诗歌语言、技巧和思考都无时无刻地在变化之中。诗歌在变化,我在成长,我的生活似乎就是因诗歌而喜悦、为诗歌而存在。”[1]数年以前,当我也在摸索诗歌的门径的时候,曾在阴暗的路上探索多时,后来才隐约地感到诗歌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相遇相知。而且我们可以“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周瓒语)看到世界和人生的很多被遮蔽的面目。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豁然醒悟,感到原来世界可以以这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作为诗人和画家的杜青,她那独特的诗歌观念让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你是我的眼》,里面有这样的唱词:“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这是一种神谕式的传递过程,世间万物通过“光”,在诗人和画家的“眼”里呈现出来,又通过诗人的诗句和画家的画作“映射”在读者的面前。如此,“光”便是诗人和画家之“眼”、诗人和画家通过“眼”发现了世界;其作品又成为读者之“眼”,透过线条、颜色和语词,呈现了万象的纷繁。
可以这么说,诗歌是杜青的“眼”,让她懂得了“看”的哲学。哲学或者佛教并不以常人的眼光看世界,在常人的眼里“有”是众生之相,是物质世界,而这在佛家看来恰恰是“无”。因为佛教引导我们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和心灵的宁静。哲学和宗教超越了常人的目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看”世界。“你”是“我”的眼,这个“你”当然是就杜青的诗歌写作而言的。杜青是幸福的,正如她在《微笑》中写的,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凝视给她带来了痛苦,但这个痛苦的凝视的过程却让她无比幸福。
一、世界被赋予了“光”
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人类需要光,眼睛需要光,诗歌和绘画一样需要光。杜青不仅写诗,而且善于绘画。一些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光和影的技法最早被命名为“光感画法”,这对于她来说一定不陌生。在杜青的许多诗歌中都有对光的独特感悟和表达,似乎她的诗歌世界从此有了光,当光把世界打亮,世界才可能被看清。
这是一首直接用《光》为标题的诗歌:
光穿过千山万水,穿过
一拨一拨人群和我的身体
你随时就可以将我擭走
或者随时将我放回原处
在擭走与放回之间
请将脚步放轻些,再轻些
体恤鸟儿清晨飞出,要穿越
密布的荆棘,才能回到夜晚
也许,诗人就是那只从清晨飞出的鸟儿,她要穿越“密布的荆棘”才能到达光的另一面,找寻一个栖息的地方。在杜青的诗歌中,总有一种在擭走与放回之间的痛感。“你随时就可以将我擭走/或者随时将我放回原处”,而这施行擭走和放回的“光”时而是有形可见的光线,时而则借以指代无形的时光。奔波的“鸟儿”许是太累了,所以才请求“光”——“请将脚步放轻些,再轻些”。光影的变换与时光的流转成为同构,而日常生活的艰辛与奔波、凡常人生的风尘与流离,却呼唤着宁静的甚至诗意的栖居。
在杜青的另外一首名为《我的到来》的诗歌中,她写到:“我的到来比秋天迟了/大海把所有的光线收拢”,光的出现,让诗人更看清了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相遇,“我看到另一个太阳/于你的前额升起”。这首诗中,同样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了“鸟”的隐喻,而且与“光”(光亮/时光)形成某种象征的同构。“水鸟将光亮一点一点衔来/擭走了草的重量/我知道 时间即使含在它嘴里/秋天同样拒绝它的存在”。诗中表达了对遇见的执着,从相遇开始就预示着别离的痛感。在“秋天”这个既意味着萧瑟又象征着收获的季节,“草”成长的苦涩被擭走,时光的流逝被忽略,而光亮在一点点地到来,这真真是在瞬间体会永恒。
仅有三行的《天色暗下来》,光亮再一次与时光对应。
天色暗下来,大片大片的红树林
暗下来,我的生活暗下来
许多事物再也回不到从前
光亮慢慢消散的时候,大片的红树林暗下来,而“我的生活”也便暗下来。在光的背后,时光再一次成为绝对的胜利者,而生活、生命却等待着命定的无望的失败。“光”的流逝和消散,对应着光阴的不再,诗人发出了深深的感慨。在“光”照之下,许多事物在成长、在消亡,那大片的红树林仿佛因为天色暗下来而悄悄消失在眼前。这所见的事物,就在“光”影之下浮沉。回到从前,怀念如雨、如光,自然万物已经在时光的裹挟中袭来。“阳光碎成一地/许多人都在,以前见过的/后来再也见不着的人,都在/在阳光抵达,足迹来不及抵达的地方/等你。”(《一地阳光》)在光影的背面,生命折射出多棱的色彩,但却那样难以把握,如同沙泄指缝。在时光的背面,诗人用诗意的相遇在做着抵抗。诗人知道在时光的河流之中,总有那个人在“等你”,一种不期而遇的遇见,在“阳光抵达”的地方,也许人们都不曾到达,但依然有心灵的相遇了。
在迎来光亮、抵抗时光的象征物中,杜青选中了“向日葵”。“一场雨水过后/向日葵就开了,吃着光/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
如果你家的向日葵
每一棵都独一无二
我家的向日葵也独一无二
如果你一个人的江湖独一无二
我的人生际遇也独一无二
一阵风吹起
你家的植物和我家的植物
都垂着头。风再吹起
你的鬓上和我的额上,雪一样白
奇怪,你和我变成了同一个人
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同一个人
——《向日葵》
这种向阳的植物,似乎一直在追随阳光的去向。好比日晷,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眺望,阳光俯仰的角度恰恰是标明光阴的流转。像大地上的向阳植物向日葵,“你”、“我”也在经历相同的时光的雕刻,从东到西、由生至死。每一个人生的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又都如此雷同。这首诗歌之中,“风”起到了时光流逝的暗示作用,“一阵风吹起”、“风再吹起”,时间的沙漏不受控制,如同风的来去一般,或者江河的奔流。作为植物的向日葵“垂着头”,说明时间从白天转到了夜晚,而人生的对应性则在雪白的鬓发得到印证。在披上“光”的世界上,在时光的交汇之中,“你”和“我”又何尝不是来自同一的“共同体”。仿佛这世间的万物都同源而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杜青可贵的发现,在光的指引下发现了诗意的世界及其同一性。
杜青在接受阿翔访谈时,谈到诗歌与人的关系,“诗与人的关系就像空气与人的关系。我们不写诗时,诗依然是存在的,它无声无息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之中和之外。我们写诗时,是我们发现了诗,而不是创造了诗,诗通过我们的思维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存在,被更多的人阅读,感觉。”[2]我想,每一次诗意的发现都是一次诗人与世界、与自己的相遇,一种不期而遇。仿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是来采菊的,而南山就在那里,“见”或者“不见”都在那里,这个“悠然”体现了人与世界和谐之中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更多的来自诗人内心宽广而无限的诗意自觉,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所以,杜青说“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了诗”,而不是“创造了诗”。
这种发现的一个诱发点便是“光”的交汇,一边是诗歌之“光”打亮了周围的世界,一边是诗意的目光与之相遇。《交汇》一诗这样写道:
一束光自西厢射出,与东厢射出的
另一束光在院子里交汇
像萍水相逢的我们,灵魂出窍
在半夜的空中。但一碰面
又分道扬镳。一束光在旷野中
消失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匹马的蹄音
再也听不见了,我们各自回顾
来路已经没入夜色
“光”各自射出,在“萍水相逢”中相遇,然而也只是打一个照面,仿佛于千万年之间、于千万人之中,“我”与“你”的相遇,没有别的,只是轻轻地道一句:“噢,原来你也在这里。”(张爱玲语)诗人用马蹄声来比喻相遇之后的“分道扬镳”实在万分贴切,而且似乎表明了从相遇到分离的某种宿命感。在“消失的时候”,“我们”只能望着彼此在奔驰的红尘中的背影,而且“望尘莫及”,已然找不到来时的路。
杜青诗歌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打亮、加光,如在黑暗的世界,她取来镜像的前提是要有“光”,如同摄影中的光影效应,读来倍有真切的质感。
二、诗意凝视下的现实人生
仅仅只是世界被打亮了还不够,还应该有一双凝视的眼睛,才能看见现实之中和现实之外的人生。只有当目光凝视,世界和人生才在凝视的时光中停顿下来,人才能发现其中隐藏着的和被遮蔽了的丝丝纹理,以及内在的复杂而清晰的结构。并且在阅读的背后,我们能清晰可感地发现,那凝视的双眼正期待热烈的回应。
凝视无边的黑
黑暗似乎也落了下来
屋里有了风和光
尘埃扬起,纸屑飘动
——《适应》
摆动,雨下起来
两片叶子粘合成一片
像漆黑中的两个人
当猫的瞳孔眯成一道横线
风消失了。两片叶子
两张脸,多么陌生
——《陌生》
同为画家和诗人的杜青,似乎深谙画与光的相互作用,更深刻领会着绘画开启的并接续着“看”的传统。作为一种观看方式,凝视是诗人的目光投射和深刻关注。如果说画家杜青对世界的凝视与观察是对于外在世界的光的研究,那么诗人杜青正是在凝视与想象中探究世界内在的灵魂互通。
在凝视之中,诗人发现了凝视之外的世界,即“看”创设了意义。“凝视”,作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黑暗”被赋予了动感,甚至提供了一个生命的场域。“夜晚宛如白昼/一只惊慌失措的蝙蝠/东飞西撞”,或者,这蝙蝠是真有,抑或这蝙蝠就是现实的诗人自己。如何去适应这样一个日常以外的世界甚至自己,诗人有自己的理解。静静地凝视这个世界,不仅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和自己,还能发现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关联。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所论述的,人与人无法是两种关联状态,一种是“我—他关系”,一种是“我—你相遇”。“我—他关系”是人和世界相分离的异化关系,他人作为“我”的客体,是“我”要征服的对象,“我”和他处在敌对位置;而“我—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主体,“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来接近“你”。[3]
在现实人生的背景里,诗人通过“凝视”完成了“我—你相遇”的关系的确立。在粘合的两片叶子,仿佛“漆黑中的两个人”,他们那样紧紧地依偎抵御着黑暗,然而,诗人是那样富有技巧而又不露痕迹地告诉我们,光阴的无情与现实的无奈——猫眼,作为时光流逝的象征意味是那样的浓烈,而风在预感和暗示着光阴变幻的同时,还为两片叶子的存在状态提供了一个变换了的场域。于是,两张脸,在岁月神偷实施的伎俩下变得“多么陌生”。在巨大的现实面前,人往往是无力的、脆弱的,面对现实,或者诗人选择了放下。我们都是滚滚红尘中的匆匆过客。
生命像一条河流突然腾空而起
在你逗留过的城市降落
一条直线的弯曲部分,被裁剪出来
寄存在你的身体上
一截与我的日常生活无关的线段
只是一只手
拨开人群和时间的河流
送走一个与日常毫无关联的秋天
——《线段》
一堆乱石中的宇宙
石缝被无限放大,我们是
显微镜下细菌,在巨人的手里
看见了我们的忧伤,看到两个人
一粒米的距离,要付出一生
——《距离》
生命是向上帝借来的一段时光,我们一直在用减法生活。生命的长河如同一部电影,在这长河里,每一次相遇仿佛就像这部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城市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空间,提供了诗意的想象可能,并作为记忆储藏的器皿,不时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打开。在凝视生命的时刻,一个一个的片段看起来与眼前的日常生活无关,好似荧幕里面别人的生活与苦难。相遇的时光被现实一次次地剥离,成为孤立的片段,痛与不痛与“日常生活无关”,而那被裁出的“线段”也只是留存在残缺的记忆里面。
于是,相比于宇宙时间,生命时间如此的有限,甚至是微弱的晨星。当诗人凝视这宇宙中的乱石,“石缝被无限放大”,于是“看见了我们的忧伤”。平凡而渺小的两个人,就算只有相距“一粒米的距离”,也还是“要付出一生”。这首诗让我想起了顾城的《远与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所谓的距离,不过都是相对而言的,现实的距离也许是一粒米,而心灵的距离则难以测量,更多的则是内心的感受。
生活于现实人生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幻,很多时候我们都来不及,时间却关上了门。在一首《生活》里面,“家、办公室、画室、城市”等等,都以“笼子”的形象出现,“囚禁身体的,也囚禁心灵”。在现实生活中,诗人也许遇到过阻难和困苦,然而只有当内心强大,世界才有可能被拯救。“内心的空虚,还没有灭绝”,尽管“我想说的生活,上了咒语”。生活的网,布满牢笼与禁锢。黑夜真的恰到好处地出现和到来,这在生活以外,如同上了咒语。泥土与城市,城市与人,人的爱与悲,这些事物,也都见过,最后,那孤独的一个人会开始想念,没有太多的特定选择,意识里的游走,如何即可,怎样都行。
诗意凝视下的现实人生,也许都在现实之外。“关上门,背靠老槐树/内心枝叶无存,照见一张老脸”。(《人间的脸》)时光像一道闸门,起合的瞬间或者放出光亮,或者隔绝光线。一切似乎都在赶场,这一出戏完了就要谢幕下场,下一幕谁又能料到是何种情形?
三、在光阴背后“望”故乡
诗人一直在去乡的路上。这语调特别有老海德格尔的范儿。然而乡关何处?这个问题似乎无解。哲学家会在现实无从下手的情况下告诉我们,向你的内心去追问吧。在我看来,杜青是用感恩的心在回答这个诗歌母题的。杜青《诗意生活》一文中坦言:“我爱上诗歌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读诗写诗,日夜以诗为伴为趣,写诗似乎已成为我心头的瘾,瘾即是病。我把写作和画画都当作病,无可根治的病,只能不断地写和画,才不会难受。以前这病还不至于害得太厉害,可以三天捕鱼四天晒网般的写写涂涂,现在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了,倘若一段时间不写不画,我就觉得难受了,就像发病了无药可治那样难受。有时,一首诗完成,我会很感动,自己被自己感动,这种快乐是物质或爱情无法代替的。生活中,诗歌仿佛是我的朋友、我的仆人、我的上帝,永远不会抛弃我,永远耐心地听我倾诉,消解我内心的茫然、无奈、苦楚与恐惧。”
如果我们的出生地是祖先漂泊的最后一个驿站,那么我们的故乡又在哪里?在诗人笔下,那故乡仿佛是在光阴面前照见自己。
一滴水遇见河流,变成河流
遇见光,就被光穿越
一滴水,一个流落民间的王
孤独地隐回自己不安的心
它穿越光,穿越自己
却怎么也穿越不过一个人的眼睛
——《一滴水》
“遇见”其实是透过“光”与自己相遇,或者融进众人的大河,或者回到自己孤独的内心。一滴水在这里那么的渺小,仿如世间人海中的一个诗人,显得那么次要,又绝决。用凝视的角度来抒写一滴水,一滴水或者无法穿越一个人的眼睛,只能被观看、凝视,一旦穿越了也许将是一滴泪水。对于一滴水来说,她是否正内心孤独地期待着“一个人的眼睛”呢?
尽管如此,杜青的诗歌创作依然是快乐而幸福的。因为在时光的背后,隔着“光”的河流,杜青可以远远地“望见”故乡。在《微笑》中,杜青写道:
人心和世事,堆放一堆杂物
晒来晒去,从没有改变
我们经过树林、楼丛、人群
说不清曾有多少次兴奋和渴望
也说不清曾有多少次悲伤和绝望
生活的机器运转无常。亲爱的
我不想说明什么,只是想告诉你
天天注视相片,并时时微笑
这是件痛苦的事情,我却乐意
把这种痛苦视同幸福
在与阿翔的对话中,杜青这样回答关于童年的话题,“也许是对远方的向往,让我生活得津津有味。其实我们对童年保持清晰的记忆,我想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所坚持,只是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内心比较单纯,把事物储存起来,没那么容易忘记而已。童年是过去,如果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不管是苦是乐,它总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东西回味起来会激动也正常呀。”[2]
“幸福”来自于与曾经的时光的相对观照。把痛苦的事情视同幸福,这当然有生活的无奈在其中,更多的则是诗人“放下”的精神状态的表达。曾经的生活、生命都已经留在光阴里,悲伤与绝望都是徒劳的,因为“生活的机器运转无常”。然而杜青看透了这一切,“天天注视相片”就是一个足以明证的细节。相片将时空定格,犹如画家的画作和诗人的诗句,可以供我们在日后阅读和回味。曾有过的时光成为内心的“琥珀”,喜怒哀乐、相聚或者别离,在时间的背后,相片提供了“看”的创造,旧梦历历,仿佛打开了穿越时空的“虫洞”,让我们在现实的痛苦中回到过去,回到令人难忘的“故乡”。曾经一切在诗人的眼前,如今却只在相片里。尽管时空不在,然而相片却在眼前。在“注视”之中,看与被看,“故乡”就在眼前,这个过程痛并快乐着。
杜青说,“写作、绘画与我,不可分割。它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的,在诗人那里,凝视的双眼通过“光”将世界打亮,世界被赋予了光亮。由此而照进现实人生,照进诗人的暗夜和梦乡,世界就在眼前。对于读者的我来说,杜青写诗作画,杜青就是我的“眼”,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谢谢杜青!
[1]杜青.后记[M]//一颗沙上的大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
[2]杜青,阿翔.阿翔与杜青访谈录[J].诗歌月刊,2008(8).
[3]〔德〕马丁·布伯.导言[M]//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