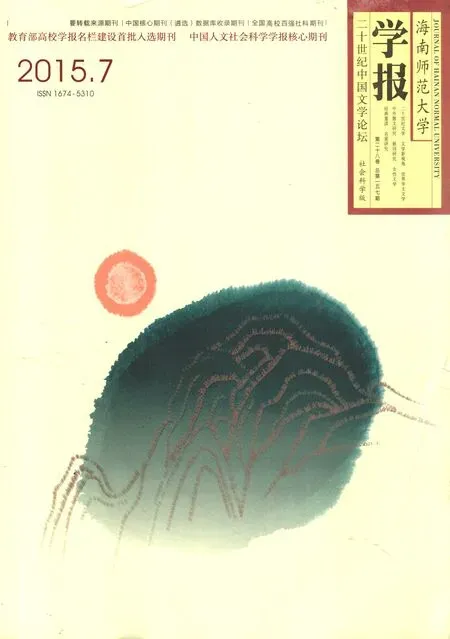为文学正名 为批评定位——评贺仲明《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
朱献贞
(1.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2.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文学,在我们这个实用理性和相对主义泛滥的时代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即使文学生产的能力在不断翻倍增长——上世纪80年代年产千儿八百部长篇小说人们就惊呼不已,在当下一年发行近万部长篇作品(包括网络)也早已司空见惯;但即便如此,这也无法改变它在人们心目中败落的地位。文学成了文学圈自娱自乐的“行为艺术”,尽管人们知道文学创作还依然存在,但似乎那只是遥远天际一道与己无关也并不亮丽的风景线,偶尔的关注也完全是因为个别的文学炒作事件引来的短暂一瞥。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文学生活现状。同样令人沮丧的是,与文学创作相伴相随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曾经一度扮演着引领文学创作和大众文学欣赏的重要角色,甚至在一些特殊的年代充当政治批判的大棒,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说明它具有不可忽视的威力。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新生代作家们就公开指责当代文学批评“拙劣”与“落后”。他们声称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毫无指导意义,批评家缺乏足够的艺术敏感和才智,甚至嘲讽批评家“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是“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认为作家是批评家的衣食父母,二者之间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1]这种指责虽然有失公道和过于情绪化,但我们的确看到了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开始走向了“断裂”——自说自话,谁也不理谁。而普通读者呢,他们的文学阅读是那么的任性,只是跟着感觉走,喜欢轻松感性的阅读,不愿做费神的理性思索,他们对文学批评也基本视而不见,尤其对一些晦涩缠绕的学院批评更是感到厌烦,惟恐避之不及。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批评本身的反思也经常成为各种媒介的热点和年度流行话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双重危机。
面对这种危机,有责任心的学者开始了有深度的系统思考,他们的一部部(篇)著述都做着思考文学当下命运和提升当下文学批评质量的努力。在这些奋进者中,就包括了著名评论家贺仲明教授。他在努力推进着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同时,也对文学批评本身和文学本体投注了极大的热情。2014年作为“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之一的《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重建》,涉及内容只注出页码)一书,汇集了他近些年来对文学本体和批评自身思考的部分研究成果,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贺仲明教授文学理论论述的缜密深切,而且也深深感受到他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现状的担忧和担当。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重建》鲜明的问题意识
贺仲明教授的《重建》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鲜明的问题意识。他紧紧抓住了当前我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批评家勇于面对危机敢于直面现实的表现。
在《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一文中,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十几年以来,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的特性”,“人们不再对文学有热爱和信任”,“作家们缺乏对文学的敬畏和奉献精神”,“社会大众对文学的普遍冷漠”;近些年来文学自身也严重地丧失了“对人类生存的深层关切”,无法“为人类提供美好的精神家园”,文学自身精神内涵特质的丧失与文学精神的高度平庸化和文学角色的宗教奴仆化,合力促使文学“严重地丧失了信仰的位置”(第105—107 页)。这充分说明作者对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危机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和迫切的责任担当。在作者看来,这种文学信仰的危机感,正是当前社会精神状况的折射和缩影。《重建》指出,中国社会在最近十几年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信仰危机,精神被放逐,虚无主义占据文化的舞台,物质崇拜和金钱崇拜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社会伦理和道德严重失范,思想文化杂乱无序,人们找不到精神的出路,也无力思考生存的信念。“文学信仰危机源于这一全民性的信仰匮乏,它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匮乏”,文学的虚无和精神溃散,“加速了精神文化的崩溃”。
这绝不是作者耸人听闻的大话。文学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化的产物,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是当下的文学却丧失了它的艺术认识价值和掌握世界的功能,甚至有批评者严厉地指出,当下的文学创作远远低于生活本身,文学所展示的魅力远没有生活本身精彩。[2]如此看来,文学陷入被大众冷漠的境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仅如此,大量低俗平庸的文学创作既是这个精神虚无缠身的时代的畸形儿,它又是新“谬种”产生的温床和社会病毒的传播者。这些年来见诸报端和各种媒体的社会病态,已经引起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国家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和宣传,以及对文艺创作的低俗化的严厉批评和对健康文学创作的提倡,无不表明我们时代存在严重的精神信仰问题。
文学信仰的丧失固然有着时代的社会原因,但自身质量的低下和创新动力的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重建》的《当前中国文学到底缺什么?》一文中,贺仲明以长篇小说为例分析了当下文学自身的缺失,这包括艺术上的粗糙简陋、生活反映上的简单狭隘和虚有其表、文学思想性的缺失和浅薄。在作者看来,当前创新意识不足和创作态度的浮躁造成了文学艺术上的粗陋,“自我重复、技术粗疏和简单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叙事上的漏洞、情节上的破绽、语言的僵硬板滞,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第91 页)而作家割裂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和缺乏对生活现象的富有穿透力的揭示以及对深入生活缺乏自觉性,导致了“作品叙述上的不合理,情节上的虚假感”;作家缺乏深层的超越历史思考和剖析社会现实的思想勇气阻碍了作品对历史深层真实的揭示和对生活本身的亦步亦趋。
针对文学创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面临的信仰危机,贺仲明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指责和埋怨上,也没有丧失对文学的信仰和信心。他一面呼吁人们要重拾文学信心,因为对文学的信心实质上也就是对人文的信心,对精神的信心:“我以为,无论在任何时代,人的存在都绝不可能只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精神是人类生存更重要也是更根本的所在,是人之作为人的本质价值。所以,文学的形式可能会发生演变,但其生存绝对不会随物质文化的发达而消亡。”(第109 页)在呼吁的同时,他也给出切实的路径和方法:文学始终要坚持美学价值、人性关怀和理想精神,这是文学拥有自信的前提(第98 页);作家应该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不让文学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要寻求文学的理想主义方向和超越精神。
《重建》的问题意识同样表现在对文学批评现状的认识和热切关注方面。
在《论当前文学研究的内部生态》一文中,贺仲明教授指出,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生态总体上呈现出严重的不足,文学研究内部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之间存在较严重的脱节和冲突,没有形成和谐与相互促进的关系。”(第57 页)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文学研究内部原因主要在于,一、文学批评受制于商业文化和行政干预,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二、文学史家存在过强的文学史权力意识,排斥个性化文学批评;三、文学研究内部生态最严重的问题是文学理论建设的薄弱,这与本土精神的缺失和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实践有关。这些问题和原因,使文学价值变得混乱、文学思想变得肤浅、文学研究功能和影响力丧失。为了改变文学研究内部这种不健康的生态,贺仲明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加强文学研究伦理的建设,二是要有文学理论本土化意识,三是要加强文学研究界之间的合作。这些都是中的之论,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文学文化批评是一种将文学视为社会文化整体之一部分、采用文化视角研究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范式,它源自西方文化研究和人类学批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界中发展起来。这种方法既促进了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带有自身的理论局限,那就是在具体操作中,文学性研究往往被忽视或只是陪衬。在《重建》看来,这种排斥文学性的文化批评,“使文学批评的文化化走向了极端和单面化”,它对文学艺术性分析很少,“根本不谈论文学审美性,不以文学审美标准进行文学价值评判,其中充斥的,只有文学的社会或政治功能,只有从经济、政治或文化角度对文学各种文化内涵的审视。”因此,《重建》提醒批评界文化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不能过分扩大范围,更不能将其与文学批评混淆,文学批评应该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感染力。
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个范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后者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之一;后者包含前者,它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它在深度和理论化上要求更高。二者之间不应互相排斥,当然也不能混淆。但是,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文学研究还未完全摆脱批评化特征,而更有甚者当下批评的一些不良倾向也渗入文学研究中来。针对这一现象,贺仲明在《去批评化:对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中,指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改善当代文学研究现状的两个重要原则——“历史性原则”和“文学与学术主体原则”。这是非常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应该引起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二、为文学正名,为批评定位:《重建》对文学的正本清源
“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其暗含的命题是“文学的信仰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信仰什么样的文学”。这必然涉及“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因为不理清何谓文学,就必然缺乏重建文学信仰的依据。同时,也只有首先搞清楚了“文学是什么”,我们才有判断什么样的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依据,也就是说,才可以以“文学”的方式为批评定位。显然,《重建》的作者非常明白这种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首先,何谓文学以及文学的属性。
在贺仲明看来,“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中以美为基本要素、以语言为承载体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具有知识性、教育性、娱乐性等多重功能,但是,最基本的,却是审美。审美赋予文学以独立个性和存在基础。”(第9 页)这种看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
马克思在阐明理论掌握世界方式的特点时,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3]这就是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四种掌握方式。文学当然就是人类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中的一种。马克思还认为,“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成东西的。”[4]那么文学更是如此,更是以美为基本特征和要素。
《重建》认为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提出的文学的“虚构性”“创新性”“想象性”等基本特征,体现了以美为特征的文学的个性和本质。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文学以美为特征,并不只是说表现形式即语言形式是美的,而且其思想也是要“以美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文学思想独立价值的重要前提。”(第9 页)这也就是说,文学一种以美的方式理解把握世界的,包括形式和思想。
当然,文学的本质虽然与“美”(审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真正搞清楚文学的本质,就必须懂得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只有理解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才真正明文学的审美特征。因此贺仲明在《文学与生活关系在考量》一文对这两者做了理性的分析。他认为要理解两者的关系必须坚持“二元性”,即要正确理解生活与文学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文学与生活的差异”;“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应该认识生活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关于第一点,贺仲明指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构(尤其是叙事类文学),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反映,而是充分渗透了作家的心灵和情感,是作家对生活的提炼和再创造。……作家绝对不是拘泥于生活,停滞于生活,而应该是不被生活所局限,以想象力和思想力对生活进行提升,使之具有更高远关怀精神,表达出对生活更深远的思考。”(第52 页)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贺仲明认为要把握这几个原则,第一生活是文学最基本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来源,作家的想象力要立足生活。第二,文学的价值、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时代的把握能力以及生活面是否宽广,决定这一个作家思想艺术高度。第三,文学的价值体现也与生活有直接关系,文学要承担一定的现实责任,有表现生活和反映生活的义务。(第53—54 页)
基于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性的“二元性”理解,文学的本质才能看得更清楚:“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建构。……从根本上说,文学世界是人类借助想象形式对现实世界感悟和超越的结果,它的内在精神动力是人类对现实的不满足,其基本内核是一种乌托邦想象。”(第101 页)在这个基础上,贺仲明总结出文学的自我个性,第一,文学是以肯定人类生命和明确的人文关怀为前提。第二,文学是以美为基础的。第三,文学比一般信仰更为宽容和理性。(第102—103 页)
其次,“文学批评”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定位“文学批评”。
那么,什么是“文学批评”?在贺仲明看来,“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艺术,是美的体现。”即文学批评具有思想创造性和形式美感。这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有自己的独立追求和个性,“真正好的文学批评是创造性思想和艺术表达的结合,其内在精神是智性的美。”另外,好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由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带来的雍容美,而其批评的对话式原则又体现出文学批评的人文之美和谐之美。(第15—17 页)
而要保证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和美感特征,就必须首先要保证批评的自由,因为,“自由,是文学批评的根本灵魂。”(第19 页)这既包括批评的精神,也包括批评的形式上,文学批评不应该受制于其他因素。
搞清楚了什么是文学和什么是文学批评,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确立文学批评的标准。《重建》指出,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要在内容和艺术两个大的方面着手:从思想内容上看,文学批评要坚持“深刻性”和“前瞻性”,即作家或作品在对人、对人类生存命运、对民族时代的命运和历史的关注上是否做到了前瞻性和深刻性;而艺术形式的评价标准要坚持圆熟性和创新性。另外,还有坚持批评的标准与多元化相统一的原则。(第32—35 页)这个标准就是审美标准与多元化原则。
“文学批评的角度可以多样化,如从文化、心理、社会、政治等,都可以评价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和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寻找出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批评角度都不能离开审美的角度,也就是说,审美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审美视野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视野。”(第9 页)这也就指出了文学批评的基本定位,它不同于其他的批评而是要坚持审美或者说“美学的”原则,但是它又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批评,它必然要与文化、心理、社会、政治等等因素相联系,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另一个原则,即“历史的”原则。
三、理论与实践的相得益彰:《重建》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实践
《重建》一书虽然是一系列文章的结集,但绝不是任意的拼凑,而是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匀称的框架结构。
这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为“文学的理论视野”、第二辑为“文学现象与思潮扫描”、第三辑为“作家与思想”。从这种分布结构来看,该书遵循了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分类,即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5]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主要侧重文学的一般规律、一般原理和文学本质的研究。显然,《重建》第一辑就是如此,它分析归纳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含义和基本要求,这属于文学本体研究,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详细分析。“文学史研究”主要在于以文学的审美标准和历史原则来分析文学现象或思潮的文学史价值和思想史意义。《重建》第二辑分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缺陷、当下文学精神信仰缺失问题、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文学现象和新时期知青小说的文学史地位、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技术化思潮、1990年代以来小说的浪漫主义思潮、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势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主流文学”“底层文学”“女性文学”等思潮的发展变化。而“文学批评”是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下,以文学品鉴为基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它更注重共时性分析,即分析同时期或时代的不同作家作品的具体创作问题,注重文本内部研究。《重建》第三辑收入了莫言、张承志、韩少功、张炜、贾平凹、毕飞宇、陈希我、黄咏梅等当代作家论或作品论,对我们了解这些作家创作的基本情况很有帮助;同时这一部分还收入了有关现代文学中的“人类之爱(爱的哲学与革命之爱)”“国民性批判”“知识分子道德”等文学思想问题研究论文。
第二辑“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和第三辑“作家与思想”,正是立基于第一辑中严密的文学批评原则和文学本体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批评美学原则的坚持,对多元方法的包容,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同情的理解”,无处不在实践着他的“美学的”与“历史的”批评观念。但三者之间又相互支持,第一辑的内容对第二、三辑的内容在方法论上看是一种理论指引,反过来说,第二、三辑的研究和批评实践又在佐证和夯实着第一辑中的批评理论和文学理论。这样使著作的三部分既显得“泾渭分明”又相互包涵彼此联系,整体上显示出扎实严密的理论功底和精彩纷呈的赏鉴美感,可谓相得益彰。相信读过此书的人,既可以学到丰富的文学批评或研究的理论知识,也可以得到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惊喜。
[1]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J].北京文学,1998(10).
[2]张光芒.当下文学远低于生活[J].东岳论丛,2012(2).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4.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 卷[M].程代熙,等,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26.
[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