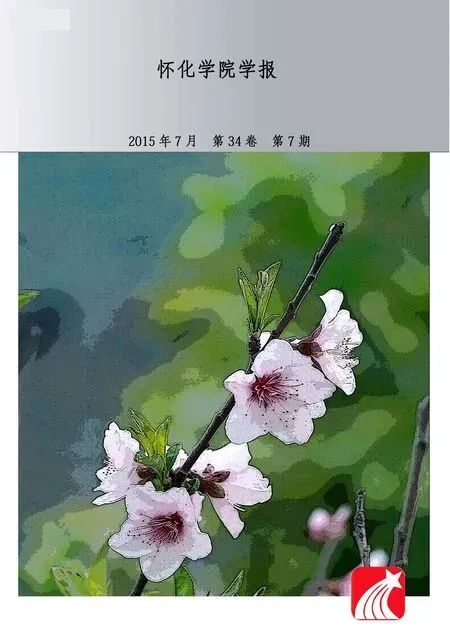乡土文学疆域的拓展
——解析向本贵《凤凰台》的文化内涵
莫百颂
(怀化学院 教务处, 湖南 怀化 418000)
乡土文学疆域的拓展
——解析向本贵《凤凰台》的文化内涵
莫百颂
(怀化学院 教务处, 湖南 怀化 418000)
苗族作家向本贵擅长写乡土小说。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对湘西这片乡土地域进行了“鸟瞰式”的描写。在其长篇小说《凤凰台》中,他从哲学、宗教、文化等层面对“乡土中国”及其流变史这一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主题进行了全新的思考与拓展,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书写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艺术文化命题。
向本贵; 《凤凰台》; 乡土文学; 文化内涵
向本贵是近年来在文坛上颇受关注的一位苗族作家。曾以长篇小说《苍山如海》摘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而声名鹊起。之后笔耕不断,写出了数部以乡土为题材、颇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凤凰台》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向本贵擅长写农村题材的小说。这与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并且有着丰富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密不可分。由于长期在农村工作、生活,对农村生活的观察体验更是独到深刻。怀着浓浓的乡土情怀,他用饱蘸情感的笔触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反映乡土原貌的大作。在他的作品里,他不仅仅局限在写地域的民俗、风土人情和个人的乡思、乡愁,更是立足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验和把握,力求从哲学、宗教、文化流变上来进一步开拓乡土文学的疆域。《凤凰台》所蕴含的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作者在乡土文学疆域开拓方面的成绩,这一成绩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考察。
一、透视乡土生活的辨证眼光
作家的作品,常常反映着作家的人格,也常常反映着他的哲学思想。孙犁说过:“哲学是艺术的思想基础、指导力量。凡艺术家,都有他自己根深蒂固的哲学思想,作为他表现社会、展示人生的基础。这就是一个艺术家或作家的人生哲学”[1]。向本贵凭籍对生活深刻、独到的体认和感悟,运用深沉凝炼的笔触和酣畅严谨的哲学思辨能力,把《凤凰台》写得极富哲理意味。《凤凰台》不论在小说主题的开掘上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表现出作者透视乡土生活现实的独特的辨证眼光,显示出作者自觉地运用矛盾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分析问题的思想痕迹。《凤凰台》写长工出身的复员军人刘宝山回到家乡凤凰台任基层干部,一心带领乡亲们“吃饱肚子”、“住上瓦房”,历经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折腾了二十多年,越折腾越穷,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活活饿死。直到改革开放后,凤凰台农民“吃饱肚子”、“住上瓦房”的两大愿望才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小说既是声讨极左路线的檄文,也是唱给改革开放的赞歌。在这部小说中,向本贵没有掩盖矛盾、刻意去粉饰太平,而是以一分为二的辨证眼光看待这一历史和事件。他一方面积极“为农民叹苦经”,力图为农民仗义执言,写出了极左路线带给农民的痛苦,另一方面深入到农村文化传统的弊端,从更深的文化层面剖析了农民身上固有的文化缺陷和人性的弱点,从而进入到鲁迅称之为“疗救国民性”的历史文化层面。
《凤凰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着一分为二的辨证哲学。小说没有将人物形象简单化为“高大全”或一文不值,而是采用矛盾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塑造人物形象,用辨证的眼光把人性的闪光点和劣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从而更好的反映出人的原初本性和精神面貌。如对地主分子田大榜的塑造,没有将他简单化——非奸即恶。在向本贵笔下,田大榜具有中国农民的典型特征:勤劳、俭朴、保守,但又不失农村有产者的狡黠。在作品中,向本贵是这样写田大榜身上所固有的农民保守性和对土地的依恋情结的,写他崇尚“农耕传家”,只认“做阳春才有饭吃,读书当不了饭”的死理,不仅亲手扼杀了儿子田中杰读书的命运,还企图让儿子的悲剧在孙子身上重演。在他眼里,只有那一亩三分地,所以最后当他连自己的田地也不保,被孙子田耕的新楼房强行所占时,他那一直恪守的、甚至身体力行践行着的“农耕传家”思想被彻底的颠覆了。田勤占地建房的“不孝”,给视地为命的田大榜狠狠地抽了一巴掌,打碎了他的“农耕传家”梦,也击垮了他灵魂深处恋土情结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很快就疯死了。向本贵对这一情节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在现代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剧烈冲击,以及在这冲击下农民身上天生所具有的传统文化面临蜕变的痛苦经历。在作品中,向本贵还这样写到了田大榜的狡黠:他通过立契约借钱给穷人的卑鄙手段夺去了很多农民的田地,刘宝山就是这样沦落为他家长工的。为了让一家人在运动中少受惊吓和折磨,他竟然以牺牲女儿的青春为代价,把他嫁给当时凤凰台的带头人周连生,制造了一场毫无感情基础的悲剧性婚姻。对儿子受到的残酷折磨,他“漠不关心,冷眼相待”,目的也是为了全家在运动中不至于遭受牵连。至此,田大榜已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异化了。一些人之常情的东西在这特定的时代里田大榜却不能拥有,更不敢拥有。他作为人、作为父亲的面孔越来越模糊了。作为地主的他,曾经在凤凰台主宰过一切的一切,而如今的地主帽子,却又掩盖了一切的一切。这里渗透了多少与闹剧式的政治运动孪生的无奈和忧怨,又有多少无辜的生灵成为了政治铁蹄下的牺牲品呢?该小说的价值之一也就在于通过地主田大榜作为父亲在这特定历史时期对自己子女的这种前后变化,深刻地揭示了农民在特定时期的生存挣扎,他的畸变也正是社会的畸变,无论有多少政治理由,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资格去指责田大榜为求生存所做的一切,因为他只不过是社会政治巨变无辜的承受者,他有理由从本能的保命需要出发,抛弃在别人看来是人之常情的东西。这种保命哲学任何人无权加以指责,因为它是弱者的最后的护身符。但向本贵没有将田大榜这一形象简单化,他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田大榜勤劳、俭朴、善良的一面上,从而使得这一文学形象更加饱满丰韵,更加贴近人物的本初面貌。田大榜起早贪黑,勤作不辍,为了攒积家业,他要求全家光着身子睡觉,怕“穿着衣服睡觉把衣服给磨破了”;他舍不得花一碗米去给儿子治病,说“一碗米的稀饭我们四口之家能当一餐饭”;他从三十岁起就一直打着单身,不再娶女人,原因是“多个人吃饭划不来”,他的家业就是靠勤劳和俭朴建起的。他也善良,始终牢记毛主席要他“多做善事,少做恶事”的教导,平时对自己的长工亲似一家,对穷苦人也不像作品中的另一个地主恶霸王启中那样残忍刻薄,而是对他们的命运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同情,以至在后来如潮般的运动中免遭杀手。他曾在饥荒年月把平时攒积的粮食分给乡亲们度荒,救下了不少人命,而自己的儿媳却被活活饿死。在战争年代,当共产党部队经过他家乡的时候,他还主动捐出了四十块大洋来支援革命。作者通过这种既剖析“外王”又讴歌“内圣”的一分为二的眼光,把主要人物田大榜的两面性体现得淋漓尽致,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对农村有产者“非奸即恶”的书写,从而更好地完成了对农村有产者的形象塑造,开拓了乡土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新领域。同样,对刘宝山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也是采用此法。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刘宝山,思想觉悟高,劳动积极肯干,工作热情主动,始终站在人民的前列,为民请命,鞠躬尽瘁。他不仅放弃了留在部队里的机会,而且也放弃了去县里做干部的美差,主动留在凤凰台,带领乡亲们走致富之路。但作者并没有将他简单化为“高大全”,而是以辨证的眼光透视这个人物身上的道德和情感、经历和行为。写他绝非圣贤,一生为情所困,一直游离于数个女人的情感之间,以致后来他没让自己的女儿刘玉进城去做纺织工人,而让一直令他内心愧疚的女人伍爱年之女孙红梅去了。这一举措,既直接导致了女儿婚姻的不幸和最后被车撞死的人生悲剧,也交织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它既是真诚关心伍爱年的反映,也是刘宝山企图用这一行动来赎还自己多年来对伍爱年所背负的过重的情债的体现。对曾经破坏过他和田玉凤爱情并砍了他一刀的田中杰的多次发难,一斗再斗,这不仅仅是情字上结下的过节,更主要的是他没有逃脱农民狭隘的思想局限性所致。更见原始人性的是他还用谁也想不到的办法报复了玷污他的妻子的男人孙少辉——强迫孙少辉之妻脱裤就范。这种恶毒的报复心理是人的劣根性的体现,是人性弱点的使然。即使一个思想水准高尚的人,也难逃脱人性之恶的宿命,这也许是作家看到的乡土生活的另一面。向本贵正是站到了哲学的高度,用一分为二的眼光审视乡土,以巧妙的笔触写出了乡土生活的新貌。
二、浓厚的因果报应观
佛教思想对中国乡土社会影响很深。而对中国乡土大众影响力最大的是佛家的因果报应说。这一佛教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作者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向本贵在小说《凤凰台》中,就用较多的笔墨从佛教因果报应的角度审视了中国乡土的历史变迁,并在因果报应法则支配下去安排人物的命运,表达个人对乡土历史的认知。孙少辉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向本贵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表明了作者塑造乡土人物的价值尺度。这个讨米出身的孙少辉,好吃懒做,贪恋女色,思想落后,生活作风败坏,是个典型的无赖。他常用“饿死人,干部要负责”的话或动辄就要去讨米,给领导脸上抹黑来要挟干部,逼他们处处为自己开“护照”。他放浪成性,整天在女人身上打主意。连自己的小姨子也不放过。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给自家多发粮食,还借为穷人家多分些粮食的手段换取穷人子女和自己睡觉。他毫无人性,先以红薯米为诱饵骗取了“醒”女人的身子,后又将红薯米做成的饭抢吃去一大半;在饥馑之年,他跟自己的儿子抢饭吃,致使小儿子成为凤凰台第一个被饿死的人。他异常恶毒,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依仗乡长贾大合这一后台,为非作歹,随意制造事端。在数九寒天里,逼田中杰和韦香莲下河洗澡,之后还用风车车他们。其手段残忍狠毒,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让读者感到欣慰的是,向本贵在小说里巧妙地让这个多行不义的家伙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仅被临死之前的韦香莲咬去了一只耳朵,还因缺了一只耳朵在班房里备受欺凌。更为快意的是,在人民都过上了幸福日子的时候,他依然是流落街头的讨米汉,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印证了佛家恶因必得恶果的报应原则。同样,淫棍一条的乡长贾大合,命运虽不如孙少辉那样不幸,但也同样遭到了报应。他虽然根正苗红,但思想觉悟极差,阶级立场不坚定,而且工作作风粗暴。他利用乡长职务这一权势,淫乱女人无数。他在位期间,还干了无数违背政策的事情。这样一个混迹于人民政府内的衣冠禽兽、道貌岸然的家伙,自然没有好结果,不仅落了个永远不能搞女人的阳痿,而且连自己的女人王美桂也保不了。与之相反的是地主田大榜,因一生谨记毛主席“多做善事,少做恶事”的教导,结果在诸多的政治运动中都能活命闯关,没像其他作恶多端的地主被人民政府法办。这种作为新型人生哲学的因果报应思想,从理论上把因果律、自然律和道德律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作品中不仅论及到了人的道德观、生命观、生死观、命运观和来世观,还体现了作者对现世的关切和对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怀。《凤凰台》就是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剖析,阐释了乡土大众对因果报应原理的领会,以期唤起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使人们认识到善恶报应皆因自己而为并“思前因与后果,必修道而行仁”[2]96。如此,将多年形成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的政治评判和道德说教转为一种宗教的道德自律和自醒,从而开拓出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境界。
三、凝重沉厚的现实文化流变
在《凤凰台》这部小说里,向本贵把犀利的目光还落到了文化流变的层面上。面对与改革开放并行发展的精神颓废这一现象,他毫无保留地予以暴露。他把乡村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问题、城乡交叉地带的不安和骚动以及在时代大转型时期农民的恋土情结和文明对人类灵魂的污染一一予以展示,并对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后现代信息文明的大碰撞所带来的文化裂变给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思想观念都造成的根本性的颠覆作了大胆的披露。小说写到最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凤凰台农民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家户户有饭吃,有酒喝,农民不再固守在一亩三分地上,开始抓经济、向“钱”看。孙红梅用肉体换金钱、出卖自己青春的行为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在凤凰台本就不太平静的生活中再度掀起了惊天骇浪。作者正是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对人性的沉沦进行广而深刻的文化批判,以入木三分的现实文化审视力揭示了人性普遍意义的存在价值及其令人触目惊心的被物质所戕害的过程;田勤、刘相与丁有金等政府要员扯不清的权钱交易关系;吴春香和丁有金婚姻的破裂以及刘相、周莹离婚后在事业上依然走向联手合作,是挣脱旧思想藩篱、思想解放的体现;还有田勤一开始就违背长辈意愿的买车跑运输和后来强行在爷爷的田地上建起了新房的“不孝”,既是对“农耕传家”思想的否定,又是对“无商不活”思想的张扬;更让人震惊的是,伍爱年和瓦匠的大胆相爱,是对乡土传统的直接宣战,是反对人性压抑、争取真爱的有力一搏,这一切都是当下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面对此,作者在这里提出了大胆的责问: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人性历史性的失落?也正因为作者对人性有着高度的关怀,使得他所写的这部乡土小说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品,他要表现的是一种“大地道德”、“大地情怀”。是在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写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交叉地带中的农民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反思城市文明对人类灵魂的污染,考察人性闪亮的东西,对正处在急剧文化嬗变中的中国当代农民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关怀。这种对人类自然本性的触及使其文学艺术穿透力也随之加深。在小说快要结尾的时候,向本贵还对政治和经济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不协调的国情进行了剖析,对解决中国当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提高国民素质,健全法律制度,改革现行体制,提倡树立信仰和民族精神”等一系设想。向本贵以一个乡土作家的身份对农民的命运进行了叩问和探讨,以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对民族命运进行了自觉而深刻的思索并提出了终极追问,深化了这部作品的主旨,使其思想性有了更高的体现。
可见,扎根在乡土文学大地上的作家向本贵,以其严谨的思辨和开阔的视野对乡土文学不断地进行反思和开掘,在理性地对乡土文化进行梳理和扬弃上,又不断追求新的视点和突破口,力求乡土文学和现代文化的完美结合。作品《凤凰台》正是以超越的历史视野,囊括社会的襟怀,庖丁解牛般游刃于凤凰台社会的这一肌体上,写出了其历史递变、生活血肉、社会风情,特别是写出了各种不同人物命运交织的纵横人生,从而把乡土文学的创作推向了更高的历史文化层面。
[1]孙犁.尺泽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2](释)印光.印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On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Local Literature——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PhoenixPlatformby Xiang Bengui
MO Bai-song
(HuaihuaUniversity,Huaihua,Hunan418008)
The Miao nationality writer Xiang Bengui is good at writing the village novel.In most of his novels,he gives a“bird’s eye”description of this piece of land in the west of Hunan.In the novelPhoenixPlatform,faced with the subject of long-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about“Chinese village”and their flowing deformatio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religion and culture,he carries out the brand-new thinking and opens up an exhibition to provide a new art culture preposition about the writing and studying of Chinese local literature.
Xiang Bengui;PhoenixPlatform; local literature; cultural connotation
2015-04-29
莫百颂,1979年生,男,怀化麻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I247
A
1671-9743(2015)07-007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