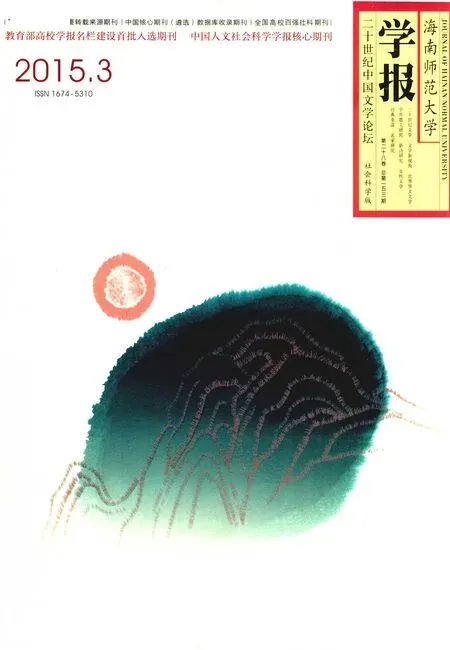龚鹏程对《中国小说史略》批评之探析
赵 旭
(沈阳大学 文化传媒学院,辽宁 沈阳110044)
《中国小说史略》上起先秦神话传说,下迄近代谴责小说,本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后几经修订成书。其著述与修订的过程,体现着鲁迅严谨的治学态度,凸显出作为小说家的鲁迅的小说史观。
此书问世之后,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如蔡元培认为《中国小说史略》“已打破了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1],并在1936年鲁迅逝世后所作的挽联中特别提出“著作最严谨,岂徒中国小说史”,显然他把《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了鲁迅学术精神的代表。胡适在1928年6月5日作《〈白话文学史〉自序》认为: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2]
郭沫若则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3]160。建国后,学术界更是将《中国小说史略》奉为圭臬。鲁迅之后出现的小说史著述不少,在资料占有上和研究方法上较之《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体例和叙述上仍然未能超越其框架。
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学者龚鹏程的《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小说文学学科建立的精神史》①此文为2005年6月24日北京大学“中华文化的诠释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后发表于《文化月刊》2006年第1期,并收入其《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360 页。,通过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分析,“重新研究鲁迅小说研究中的盲点”,[4]356尤其对鲁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质询,认为其存在缺陷。此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对鲁迅小说史观进行更全面客观的审视和反思,并对当代中国小说史学科的理论构建产生有益的启示,自有其学术价值。本文不揣冒昧,对龚鹏程所论鲁迅知识结构存在缺陷的问题加以探析。
一
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是件难事。龚鹏程也承认“天下书本子之多,真是浩如烟海。每个人因其精力与与兴趣之限,均仅能择选某一小领域去读”[4]334。不过,龚鹏程以“古之博大真人”和“方今学林之独行者”自许,认为“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什么都要研究”[4]总序1,而且自言:
我自己就淹贯四部,博涉九流、兼综三教。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自夸自炫,其实一点也不。以我之鲁钝,做到这一步,也不过就花了三几年工夫。在我大学时期,便已把国学诸领域大抵摸熟了,掌握了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此后不过渐次精修,并与西学新学相孚会、相激荡、相印发而已。[5]自序1
他对学者的知识结构非常看重,甚至认为陈寅恪“只是一肚皮印度知识无处张皇,故于史册小说中去捕风捉影罢了”[5]231,所以对鲁迅的质询也是能够理解的。
鲁迅学识渊博,“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籍,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3]161这是公认的事实。龚鹏程也承认“鲁迅确实是阅读范围广泛。而若再考虑到他除了文献书本子以外,还摩挲金石、版刻、图录等等,更是要令人赞叹不置了”[4]334,但同时又指出“鲁迅是位文学史家,并不只是一位随兴读书的作家而已”[4]335。“文学史家在论列文学史的发展变迁轨迹时、在讨论文学大趋势时,总揽全局实在就非常重要了。”[4]335在龚鹏程看来,鲁迅有着“偏畸的阅读习惯”,缺乏宏观审视的角度,具体表现为“比较意识也很薄弱”,“论文学时,绝少比较各体文,也绝少参会着讲。那就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参会或比较的知识基础,故亦无此视域,以致放过了许多可以比较或参会的论题”。而“缺乏这样的能力或视域,就是光做小说也是做不好的”[4]336。而且进一步指出鲁迅“切开了整体文学史,孤立地谈小说。在谈小说时,往往也是孤立地谈那一类小说”[4]337。
平心而论,鲁迅的知识结构确有不够完善之处。郭沫若就曾指出鲁迅对于先秦古物“不大致力”,而且鲁迅的力量“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3]161。鲁迅对此也是承认的,他最初将油印的小说史讲义定名为《小说史大略》就不是简单的谦虚,而是清楚地意识到此书在知识结构上存在着不足。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文献所限。鲁迅在1923年10月7日所作《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就明言:“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6]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书籍文本的获得是有较大难度的,如第十二篇曰:
书为宋初所藏,多佛经,而内有俗文体之故事数种,盖唐末五代人钞,如《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则在伦敦博物馆,《伍员入吴故事》则在中国某氏,惜未能目睹,无以知其余后来小说之关系。[6]87
因为文献难寻,其知识结构存在缺漏和错误也在所难免。鲁迅在1924年3月3日所做的《后记》坦承:
其第一篇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讫。已而于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陈忱,字遐心,为《<后水浒传>序》考得其事尤众;于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第一编知《说唐传》旧本题庐陵罗本撰,《粉妆楼》相传亦罗贯中作,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6]265
而且,随着文献不断被发现,知识不断被更新,先出著述中的结论不断被修正也是正常的。因此鲁迅在1930年11月25日作的《题记》中言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而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大器完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6]265
此番言语虽有谦虚成分,但其中的遗憾之意也是明显的。
第二,精力所限。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有其机缘的。他当初去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也是机缘巧合,因为这本来是周作人接下的工作,后来发现不好做,便推给了鲁迅。“这件事的重要,在于促成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一学术名著的产生。鲁迅虽然一向注意研究中国小说,但如果不是有教课的需要,也许不会想到要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吧。”[7]据周作人回忆:
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马虎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8]
鲁迅的踌躇,很重要的原因是考虑到备课需要耗费太多精力。可是周作人打了退堂鼓,鲁迅只好接了这门课。而他又是极为认真的人。在已经有了《古小说钩沉》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等参考资料的基础上,他也并不满足,还是积极备课,其备课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编著了《小说旧闻钞》,如1926年8月1日的《序言》所言:“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移写。”[9]序言
1935年1月24日的《再版序言》更是描述了其编写的辛苦:
《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煮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难也,颇亦珍惜。[9]再版序言
这足见其付出的心血精力。此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而且当时纷乱社会环境也不能保证其安心著述。如其在1924年3月3日的《中国小说史略·后记》中所言:“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6]265
过多的“他事相牵”,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不过,鲁迅对此书也是很尽心的。从1920年起陆续油印编发共17 篇的《小说史大略》,到内容扩充至26 篇铅印的《中国小说史略》,直到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版修订本。15年的时间里,鲁迅做了多次增订修改,使之从知识结构到理论体系都渐趋完善了。
二
龚鹏程在质询鲁迅的知识结构缺陷问题时,特地指出鲁迅的小说史“没有参会或比较的知识基础”[4]336,“切开了整体文学史,孤立地谈小说。在谈小说时,往往也是孤立地谈那一类小说。”[4]337
龚鹏程指出“中国小说的特征乃是说唱文学,整个小说均应放在这个说唱传统中去理解”[27]338,但鲁迅却有意识地“规避了一个中国小说明显的特征:韵散间杂”[4]337,“把所有名为词话的东西几乎全都撇开了……乃彼刻意为之。因为自己不懂,就扫而弃之”[4]339,“谈《三国》而不说三国戏,谈《水浒》也不说水浒戏,谈《西游记》仍不说西游戏,谈《红楼梦》还是不说它跟戏曲的关系”。认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优点固多,然此正为其膏肓之所在”[4]339。
诚如龚鹏程所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并没有对小说发展的轨迹做出全面立体的论述,但这不单纯是知识结构的缺陷,而且与鲁迅对小说史学科的认识和著述《中国小说史略》的具体教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的确,鲁迅“其实知道这中间的问题,也明白大家的想法”[4]337,他并未忽视小说的说唱文学传统,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在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中都照顾到了小说与说唱艺术的关系。其备课之用的《小说旧闻钞》中就收集了不少说唱文学资料,而且在其他论著中也对此问题有所补充,如《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中说:“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诗;别一小本则题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0]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更是只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不提《大唐三藏取经记》,可见鲁迅并非如龚鹏程所论:“连《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他也刻意采用日本德富苏峰成篑堂藏的本子,因为只有那个本子叫做《取经记》。”[4]339此外,鲁迅对民间文学,包括民间说唱文学的重视,近年来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此不赘述。
鲁迅没有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小说的说唱文学传统加以详述,这的确是有意而为之的。首先,这与他对小说史学科的本质看法相一致。他在1923年10月7日的序言中说: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6]序言
鲁迅要著述的是与“中国文学史”不同的中国小说的“专史”,而说唱文学传统虽然对中国小说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小说本身。龚鹏程所言古代小说与戏剧的“共生互长的关系”[4]340固然存在,但毕竟不能混为一谈。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虽然在内容上与《西游记》有相似之处,“目连故事及戏剧,跟西游故事及戏剧相因相承”[4]341,但这只是存在着源流关系,可以同源但却是异流。小说与戏剧之间虽然有着复杂的关系,但小说的发展还是有自己独立的系统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力图为中国小说史描绘出一个独立的发展轨迹,还是有其合理性的。而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更是贯彻了这个“专史”的思路,力图“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6]268。
其次,还要考虑到《中国小说史略》的教学性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毕竟首先是一份讲义,而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感受到其口语特点。而且,是面对大学生的讲授。按照周作人的记载,当时北京大学对鲁迅的课程安排是“小说史,二小时,周树人”。因课时的限制,似乎也无法在课堂上有太多的展开。因此鲁迅在诸多单篇文章中对相关小说问题做了论述,如《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和《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补充,只是受时间和环境限制不适合在课堂上讲授罢了,这个对于高校教育来说,是很正常的,不能单纯地将之视为知识结构的缺陷。
这里需要提出来的是顾颉刚对鲁迅的批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后,顾颉刚对其评价一直不高,不仅在1926年告诉陈源《中国小说史略》是对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小说部分的抄袭,从而引起陈源和鲁迅的纠纷,而且还在1942年公开评价说:
周树人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最初亦有贡献,有《中国小说史略》。此书出版已二十余年,其中所论虽大半可商,但首尾完整,现在尚无第二本足以代替的小说史读本出现。[11]
“小说史读本”这个评价显然是带有轻视态度的。这个态度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顾颉刚以史学研究者的身份对文学教育者的鲁迅产生的不理解。这一点,早有学者论述过:
这一重研究而轻教学的立场,使顾颉刚对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类从课堂讲义脱化而成的学术著作缺乏起码的认同与敬意。在顾氏看来,这类著作不过是常识之汇集,虽有稳健博洽之长,却不利于研究者个人创见的充分发挥,学术含量不高,亦难免空疏之弊,且相互间在体例及论述上均大体相沿,视之为粗陈梗概的教科书“读本”尚可,而难以企及严谨的学术著作的理论深度……而将《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相类同,否定其原创性。[12]
但鲁迅本人却很看重教育者这个身份。在讲堂上,把授课内容作为表达自己观点的载体,这与他改造“国民性”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为了授课的需要,鲁迅参考了大量的著作,当然也包括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而作为一部教学用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并未严格按照学术著作的标准给出注释。而顾颉刚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轻视,恰恰就是因为其本为教学而著的动机。
当然,鲁迅也一直在努力提高《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性,此书从1920年起陆续油印编发,共17篇;后经作者增补修订,由北大印刷所铅印,内容扩充至26 篇,题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这次铅印,颇具意义:
在《史略》版本的流变过程中,从油印本到铅印本是改动最大的一次。铅印本之后的各版本,只存在作品及相关史料的增补和论述文字的修改,小说类型的划分和命名至此基本确立。[13]
此后的15年中,鲁迅付出了巨大心血,对《中国小说史略》进行多次修订,最终,达到的效果就是“一部《中国小说史略》,用于讲坛则是讲义,供同行阅读则为专著,在讲义和专著之间自由出入,从而有效地弥合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学术落差”[12]。但即使这样,在学术性不断提高的同时,其供教学所用的特点依然存在。这是不容忽视的。正因为《中国小说史略》的教学性质,所以它不必追求周密完整的体系,只要能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小说发展线索,能够自圆其说即可。
三
总的看来,龚鹏程所言鲁迅小说史著述中知识结构的缺陷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但却不能强求完美,因为这样的完人是不存在的,即使是以“博大真人”自许的龚鹏程自己也不能。知识结构,只能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去追求完善,鲁迅先生终生都在努力践行着。而且,我们应该从一个全面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述。这部著作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而首先是一份供教学使用的讲义,虽然后来有过比较认真的修订,但其供教学之用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书中浓重的口语化表述色彩就是明证。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浓厚学术性的教材。其著述必须要符合课堂教学要求,顾及到受众群体、课堂环境和教学时间,不能求全、求大,只要能够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小说的发展线索,并能够自圆其说,从而使学生受到一定的启发并进而领悟创作技巧就足够了。而鲁迅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
要将小说史论述周密本来就不容易,例如龚鹏程本人提出用“不可究诘的进程和宇宙秩序建构的原理”[14]的“天命”观来“说明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原则和意义取向”[15],论述中国小说的发展,但他的小说史论也是细碎片段的,直到目前也并没有成体系严密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史。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管是作为榜样还是靶子,都将在未来的讨论中不断推动中国小说史学科理论构建的发展与进步。
[1]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C]//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三十年集.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47:卷首.
[2]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M]//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
[3]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M]//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龚鹏程.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小说文学学科建立的精神史”[M]//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龚鹏程.国学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50.
[8]周作人.自传[M]∥知堂回想录.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367.
[9]鲁迅.《小说旧闻钞》序言[M]//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0]鲁迅.坟[M]//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37.
[1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2:118.
[12]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J].鲁迅研究月刊,2008(5).
[13]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J].鲁迅研究月刊,2007(1).
[14]龚鹏程.神话与幻想的世界:人文创造与自然秩序[M]//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7.
[15]龚鹏程.中国小说研究的方法问题[M]//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