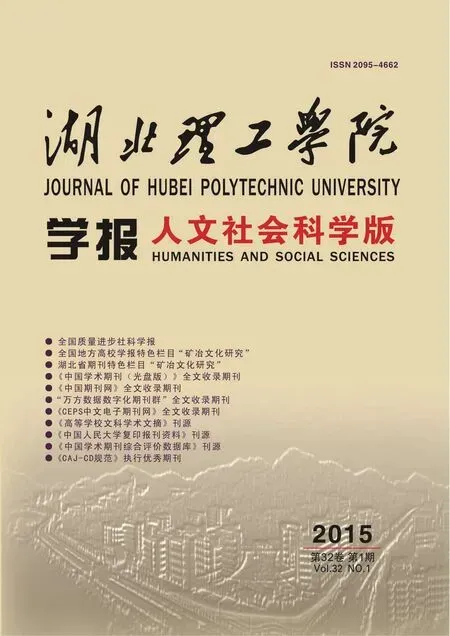休闲审美范畴略谈*
陆庆祥
(1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休闲审美范畴略谈*
陆庆祥1,2
(1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休闲审美是以一种美学的生命情怀观照人类休闲活动,从而提升休闲的审美境界。闲情即“休闲感”,具有这种休闲感的人,会在心中升起想去休闲的冲动与愿望;闲趣意味着在休闲当中主体自我获得了审美情趣或审美趣味;闲适昭示了一种审美境界,它是生命意义的获得,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是本真自我的回归。人类的休闲审美活动正是由闲情而闲趣,进而上升为闲适的境界,这既是中国古代休闲审美文化的智慧,也对现代人类的休闲文化有着普适的借鉴意义。
休闲审美;闲情;闲趣;闲适
笔者曾多次撰文提出,休闲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化[1]。从“休闲”的字源意义上看,“休”与“闲”的造字伊始便与自然有着紧密的关联,“休”为人倚在树木边休憩,而“闲”则与树木或月亮有关,从字面意思即可看出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亲近的关系。而“闲”,则更从诗意的生存角度(“门中窥月”毋宁说是一种悠然诗意的心境)让休闲具有了一种精神现象学的深度。人向自然的回归,从根本上揭示了休闲的本质。人在自然化的休闲体验中,必然通向的是审美之境。审美化的休闲也是本真意义上的休闲,以审美来嫁接休闲,可以避免休闲滑入异化之途,从而提升休闲的质量;而休闲进入审美,则可以把美学引入日常生活。于是,“美的休闲”与“休闲的美”就是休闲研究必须要面对的两个话题。张玉勤曾提出“休闲美系统”一说,即审美自由作为前提条件,审美情趣是核心意蕴,审美体验为桥梁中介[2]。这就确立了休闲审美研究的一个基本宏观框架。为此,笔者相应提出休闲美系统之下的三个范畴:闲情、闲趣、闲适,以对应于休闲美系统中的审美自由、审美情趣与审美体验,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闲情
人类的现实生命活动,本质上都是由情感的冲动引起的。若没有情感的引发,人也不会主动地去寻求一种活动。闲情也即“休闲感”,具有这种休闲感的人,会在心中升起想去休闲的冲动与愿望。这种发自内心的冲动促使主体去寻找一些特定的活动来发掘生活的意义,去展现个性的自我。闲情当是休闲活动发生的前提,它是主体在排解掉诸多主客观的纷扰,摆脱了外界强加给内心的压力而获得的心无羁绊的心理活动。
闲情之所以是休闲活动的前提条件,主要在于闲情之“闲”。“闲”既有“防范”之意,又有娴静之意。表面看来,两者意思相差甚远,其实在古人看来,真正健康的休闲情感在娴静的基础上,还必须要有“防范”、“闲正”的一面。宋朝的倪思曾说过:“‘寻思百计不如闲’、‘未老得闲方是闲’、‘又得浮生半日闲’,皆昔实欲闲而不能,羡闲而未遂者。闲豈易得哉?然古人制字闲适与防闲之字同,盖有深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君子居闲虽不至如小人之无所不为,然亦多恣意于声色杯酒者。是以贵于以礼防闲也。”[3]这种观点虽不能代表古代休闲活动的实际,但其中反映出来的理性主义精神确实对古人的休闲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理解古代乃至现代人类的休闲活动时,对于“娴静”与“防范”也必须进行辩证的理解。正是因为闲之“娴静”意,休闲情感才具有一种超然自由的审美意味;同样正是由于闲之“防范”意,休闲之情感才不至于恣意无度,而是在合理的法度之内享受自由的趣味。
闲情作为一种情感,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种情感是由主体之“闲”带来的。闲作为人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为主体的心境,是主体在摆脱了外在物质与文化环境的压力下而获得的情感态度。当闲情在人的心中产生的时候,人的精神就会出现一种“虚空”状态,此即庄子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 ),这种“虚空”是心灵泯灭掉过多欲望后所达到的萧然自适的心理情境,它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寻得能体现自由的活动。当这种寻求自由体验的情感冲动,适逢主体拥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而“参与”到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活动中去时,休闲活动便展开了。
闲情是休闲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正如李渔所言:“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4]134从下面两首诗反映出来的古人休闲活动中,也可见闲情对休闲的重要:
酒醒欲得适闲情,骑马那胜策杖行。天暖天寒三月暮,溪南溪北两村名。
沙澄浅水鱼知钓,花落平田鹤见耕。望断长安故交远,来书未说九河清。
(徐夤《酒醒》)
官散有闲情,登楼步稍轻。窗云带雨气,林鸟杂人声。晓日襟前度,微风 酒上生。城中会难得,扫壁各书名。
(姚合《早夏郡楼宴集》
从诗中看出,诗人在获得可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后,因闲而生情,由情而思遣,因遣而假物以扩展、寄托、驻留,这就生成了诗人的一段休闲时光。
二、闲趣
闲趣是休闲的特性表现。我们似乎习惯了用“自由体验”或“自由时间”等来描述休闲的特征,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不仅体现在休闲活动中,人类的其他活动如审美、道德乃至求知活动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体验到自由。当然,在休闲活动中,自由的体验也是较为明显的表征,但休闲中的自由体验,毋宁说更是一种“趣”的体验。以“趣”来描述休闲,更能突出休闲的娱乐性与游戏性,章辉博士更是认为休闲之趣关乎个体的自我实现①。
“趣”是中国古代被广泛运用的美学范畴,见用于艺术审美、自然审美、生活审美、工艺审美中。“在人生意味的探索中,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以‘趣’为要素的相当完整的审美生态系统,说明人生可以全方位地寻求与创造生命之美与生活之趣。”[5]魏晋时期,“趣”被用于人物品藻,又伸展到艺术品评领域,被用以谈诗论画。宋元以来,以趣味表征诗歌审美特征的用法得到大力推动。最有名的属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到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时之“趣”,多为一种古典的雅趣,重含蓄,尚情味,反映了文人特有的心灵意境。至明清,“趣”的运用更加广泛。随着明清市民意识的上升,俗文学的发达,审美理想的变化,“趣”也带有了更多的可爱、活泼、好玩等感官享受、俗世快乐的色彩。袁宏道对趣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
(《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近人谈“趣”最多者为梁启超。他主张人生的“趣味主义”,把趣味作为根本的人生态度②。
较早将闲与趣连在一起的是南朝沈炯:“矧幽庭之闲趣,具春物之芳华”(沈炯《幽庭赋》)。至唐宋,闲中之趣更是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倾心。白居易:“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闲意》),“闲气味”即指“闲趣”。为何弃忙就闲?闲的趣味性特征最能满足士人活泼而又纯洁、率性而又高雅的心灵需求。宋代以降,士人对闲趣的欣赏与追求更加普遍,葛立方“官冷有闲趣,花开无世情”(《九日庆善示诗次韵》);“多少幽闲趣,吾方事退潜”( 韩琦《孟冬朔日祀坟》);“悟上还重悟,得得真闲趣。收住身中无价真,岂逐人情去”( 谭处端《卜算子》)。到明朝袁中道论闲趣时说:“夫人生闲适之趣,未有过于身在砚北时亲韦编者也”(《砚北楼记》)。可见,闲趣并非纯主观的审美趣味,它是在主体闲情观照下,在具体的客观活动或事物中呈现出来的情趣意致。它是由一片无挂无碍、尘虑尽消的心境所唤起。闲情是闲趣得以呈现的前提条件,而闲趣的呈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对“幽庭”、“江湖”、“韦编”等诸事或诸物的赏玩与体受时呈现的。
我们说的“闲趣”并非专指文人之趣,也非梁启超所谓的“趣味主义”之趣。前者之趣多指文人艺术家精英式的赏玩,带有技术性、艺术性的涵养,不是一般平民大众都能具备的。后者之趣又太过广泛,它不仅指闲暇之趣,也指劳动、工作中之趣,人生无处不充满了“趣”。而“闲趣”之特殊性在于“闲”字,指的是人在劳碌生活之后,在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而于其中获得盎然的趣味。此时,闲趣的呈现便意味着主体进入了休闲的生命状态,闲趣是休闲活动的特性,由趣而入闲,进而引发主体闲适的休闲境界。
三、闲适
存在主义休闲观认为,休闲是成为人的过程。如果说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活动中闲趣的不断生成,那么闲适则是对这一闲趣进行享受的心理评价。适与不适是主体在与外界的对话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反应,最终也体现为主体所能达到的心境。适,作为一种肯定性的评价,是主体对休闲活动的认可,反之如果不适,则意味着休闲质量的降低。
闲适之适渊源有自,最早推崇适的境界的是庄子。庄子哲学尚自然无为,恬淡寂寞之说,追求的正是“自适”的人生境界:“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庄子·齐物论》),又“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庄子认为要达到“适”的境界,需要做到齐万物、一生死、忘是非,最高的“适”的境界是身处适中而不自知。
庄子哲学是古代休闲美学思想的滥觞,这种以“忘”的无为哲学为主导的自适境界,本质上就是对“闲适”的描述。上文我们指出,闲是人从外在的文化环境压迫束缚中解脱出来、对自适心境的肯定,休闲活动最终所追求的其实也就是一种闲适的境界。林语堂说,中国人是最懂得悠闲的民族。事实证明,受庄子哲学精神的影响,闲适的境界已经成为后世文人所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人生状态。陶渊明对采菊东篱的隐士生涯的持守自不必说;白居易提出“中隐”的处世方式,无非也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适境界,他的诗集中大量的闲适诗便是证明;北宋邵雍也是闲中求适的能手,请看他的《闲适吟》:“春看洛城花,秋玩天津月。夏披嵩岑风,冬赏龙门雪。”花、月、风、雪,都是四季之趣,趣中有真乐,邵雍正是从看似平常的闲情逸趣中觅到了人生适意之境。
在闲趣的驻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闲适那种平和、淡远以及娴静的特征,这是有着鲜明的东方古典式的休闲意蕴,也一样可以看作是现代人类休闲的必要内涵。现代西方休闲理论界提出“畅”的范畴,以表达休闲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峰体验”。 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i.Csikszentmmihalyi)认为:
畅是一种感觉,当一个人的技能能够在一个有预定目标、有规则约束并且能够让行为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做得如何之好的行为系统中,充分地应付随时到来的挑战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这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没有心思注意与此无关的事,也不考虑别的问题。自我意识消失,甚至意识不到时间的存在。能让人获得这种体验的活动实在是让人陶醉,人们总想做这件事,不需要别的原因,也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会产生什么后果,即使有困难、有危险,人们也不在乎[6]12。
著名休闲理论家杰弗瑞·戈比进而认为:“在我们提到的种种概念中,必须加上‘畅’(flow),正如心理学家奇克森特米哈伊所定义的那样,畅是一种可以在‘工作’或者‘休闲’时产生的最佳体验。”[6]21不可否认,“畅”这个范畴的确能够表述在休闲过程中所达到的境界,“畅”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提出的“闲适”有着类似的成分。比如“畅”与“闲适”都有“忘我”的特征,都有一种心情愉悦地做某种事情的心理冲动。然而,“闲适”与“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有着鲜明的不同。
首先,“畅”并没有上升到人生本体的高度,仅特指个体在从事某项活动或投入到某种事情中时,由于难度的适中,一时的兴趣,在主体身上产生的一种乐此不疲的心理体验。而“闲适”在用来描述休闲活动时,更是体现为人生的理想境界。范仲淹在体验休闲时认为“度日无客,公事绝稀,甚闲适也,不谓劳生亦有此遇”(范仲淹《范文正公尺牍》)。“闲适”与“劳生”相对,而显然闲适是更令人向往的境界。若说休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的生命活动,那么是“闲适”而非“畅”更能够表达这种活动的意义与价值。
其次,“闲适”表现为平和娴静的风貌,而“畅”则是努力地去“做”某事,这固然是兴趣盎然,但终究是一种“动”。皮普尔曾认为休闲有三种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理智的态度,是灵魂的一种状态……休闲意味着一种静观的、内在平静的、安宁的状态;意指从容不迫的允许事情发生”;第二,休闲“是一种沉思式的庆典态度”;第三,它与“努力”直接相反[7]14。休闲作为人类一种生命活动,总体上呈现出的就是皮普尔所说的平静状态,而闲适无疑是对这种平静状态的最好描述。畅则更多地体现为人在进入自我实现状态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极度兴奋的喜悦心情。“极度兴奋”是容易疲劳的,因此“畅”这一概念并不能很好地表述休闲的最佳体验。
最后,闲适作为休闲活动中的“高峰体验”,它是有节制的狂欢;而从“畅”的概念描述上,我们看不到这种节制,更多地是个体陶醉于外物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说闲适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话,畅则仅是“随心所欲”。前者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即体现为“自由的必然性”,而后者则是“盲目的自由”。我们看陆游一首《闲适》诗:“饮酒不至狂,对客不至疲,读书以自娱,不强所不知。一窗袖手坐,往往昼漏移,初非能养生,简事颇似之。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柴门傍野水,邻叟闲相期。”诗中所体现的闲适意境,是平和宁静的,也是非常理性而又节制的。这种休闲之境应是最能得休闲之真谛的。
四、小结
本文主要是立足于中国休闲审美传统展开对休闲三个范畴的试析,并试图寻求中国特殊的休闲审美经验的普世性价值。林语堂先生早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懂得悠闲的民族;现代休闲学的发起者于光远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休闲“是将休闲与文化结合得最完美的典范之一”[8]。致力于休闲学研究的马恵娣女士同样认为,中国古人“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隐居生活,都普遍存在‘闲’之境界”[8]。笔者认为,休闲审美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而鲜明的传统,它不仅是日常经验层面的放松身心的简单活动;古人更是从人生本体的层面,即形而上的层面去理解休闲、实践休闲。从对“休”与“闲”的词源意义的考察,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休闲审美正是在与政治、宗教、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多种领域的博弈中展现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休”指向了一种从公共领域退归于私人领域,并在当下自我生命的片刻生存中寻求一份自然与宁静;而“闲”指向了不同于职业化与道德化的另一种人生境界,并且蕴含了古人对生命的形而上的本体思考。
从词源学角度得出的休闲审美内涵又体现在“闲情、闲趣、闲适”中。闲情即休闲感,它是一种审美情感与审美态度,其特点既有心无羁绊、摆脱压力束缚的自由感,同时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我规范。当人能以一种自由的心态从容面对闲暇甚或是工作时,他便很容易进入自得自在的休闲之境。闲趣意味着在休闲当中主体自我获得了审美情趣或审美趣味。而闲适昭示了一种审美境界,它是生命意义的获得,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是本真自我的回归。人类的休闲审美活动正是由闲情而闲趣,进而上升为闲适的境界,这既是中国古代休闲审美文化的智慧,也对现代人类的休闲文化有着普适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 参见章辉《南宋休闲文化及其美学意义》,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04-106页。
② 参见方红梅《梁启超趣味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 郑明,陆庆祥.人的自然化:休闲哲学论纲[J].兰州学刊,2014(5).
[2] 张玉勤.休闲的审美蕴藉[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3] (宋)倪思.经鉏堂杂志[M].邓子勉,校点.沈阳:辽宁出版社,2001:45.
[4] (明)李渔.李渔随笔全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7.
[5] 邓牛顿.趣——国人的审美生态系统[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6] (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康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7] 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8] 于光远,马恵娣.于光远马恵娣十年对话[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陈咏梅)
On Leisure Aesthetics and its Categories
LUQingxiang1,2
(1Normal College,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Huangshi Hubei 435003;2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9)
From the etymological point of view, leisure makes people retreat to the whole self and the fidelity .Leisure aesthetics can help people go out of business and try to enter into a meaningful state. Leisure passion is a kind of impulsion or desire that can spur people to leisure. Leisure interest means that leisure subject can develop aesthetic taste. Leisure coziness leads to a aesthetic state which mean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fe value. Human leisure aesthetic movements are just from leisure passion to leisure interest , then rise to leisure coziness state. This is not only leisure aesthetic wisdom used in antiquity, but also a great wisdom for modern times.
leisure aesthetics;leisure passion;leisure interest;leisure coziness
2014-1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自然与超越:宋代休闲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2CZX073。
陆庆祥(1983— ),男,讲师,博士,华中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休闲学、美学。
10.3969/j.ISSN.2095-4662.2015.01.005
G122
A
2095-4662(2015)01-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