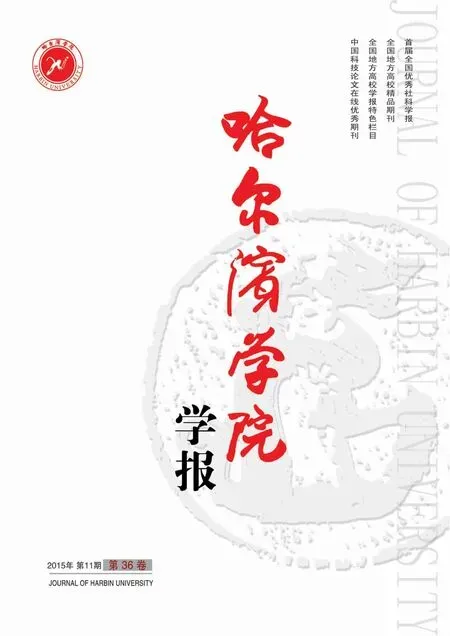从散居族裔批评解读莫里森的小说《爱》
刘 星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一、散居族裔批评
莫里森的小说以黑人的流散经历为主题,[1]其小说改变了西方经典文学中现代小说的定义。小说《爱》引入了黑人创伤后应激障碍,反映了其现代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的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表现为反复出现闯入性的创伤性体验、持续的高警觉和回避”。[2]在创伤事件中,“人为蓄意的创伤对个体的创伤影响最严重。”[2]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造成了非洲黑人族裔散居现象,也给他们带来了心理创伤。族裔散居是指,“某一种族由于外部力量的强制或自我选择分散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情形。”[3]奴隶贸易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跨大西洋的贩奴船。在贩奴船上发生的暴力事件被历史学家、小说家以及艺术家所记载。种族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给非洲裔美国人带来的贻害在莫里森的小说中多次被反映出来。
二、小说中的“警头怪”
小说《爱》的开篇以叙述者L的口吻讲述了一个“警头怪”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久远,甚至在叙述者的妈妈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从海里窜出来伤人的警头怪仿佛是吃人的鲨鱼,但它伤害的对象是有选择的被认为有过错的女人和小孩。当灾祸降临,黑人妇女和小孩受了伤而得不到解释的时候,人们就只好说是“外来的邪恶在作怪”,并加罪于他们自己的“疯狂”。[4](P3)例如,梅是个穷得吃不饱的牧师的孩子,她安分守己,甘于奉献。在她成为柯西的儿媳后,成为了柯西家的奴隶,把柯西的需求凌驾于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之上,替柯西管理着酒店。就在她付出了全部艰辛和努力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柯西的认可,反而要将一切管理权拱手交给一个比自己女儿还小的新婚婆婆。对于梅来说,没有安全感,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在女儿只有五岁时,疾病夺去了她的丈夫。女儿青春期还不到,52岁的公公娶了女儿的同龄小伙伴。梅担心女儿受到不良影响,就把女儿送走并希望她不要再回来。L注意到梅后来变得十分敏感,特别是小新娘来后,梅就有了偷窃癖,甚至小到一支笔。最后终于精神失常。梅的女儿刚开始不能理解自己的母亲,最后才明白“梅心中的那个世界永远在倾颓,在那里她的地位永远受到威胁”,[4](P104)因此随时都需要保护自己。当梅出席柯西的葬礼时,一定要坚持戴头盔以免受到外来的攻击。给梅带来精神创伤的事件除了公公的再婚,还有后来的二战、民权运动。她认为这一切都威胁到了她的地位和身心安全,所以每天保持高度警惕,一直持续到她生前的最后一刻,这实际上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
梅是普通黑人女性和母亲的代表,她的种族的祖先经历了与自己的家乡及亲人相分离的悲伤与苦痛,这已经成为他们的集体潜意识。从他们的祖先被贩奴船载着经过中间通道时,警头怪就已经出现了。到后来,警头怪以各种形式与身份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除了奴隶主,警头怪还可以是白人警察博斯·丝克的儿子,他利用父亲的职位,提高酒店的保护费。警头怪也可以是想侵犯朱妮儿的所长,诬陷朱妮儿使她又当了三年的犯人。在每个事件中,黑人女性始终是受害者,在白人的价值观下却被冠上了“不检点”的恶名。
三、非洲散居民族的爱神
小说中能与警头怪抗衡的女性不多,除了L,被赋予了魔力的美丽女性是凌霄。她是非洲爱神的象征,凌霄正如她的名字,跟宇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征服海的节奏,牵引月亮,这里暗示着散居民族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物理位置的回归,而是文化认同上的回归。在当时的美国司法体制下,适合黑人的地方除了边缘地带就只有两个地方:少管所和监狱。朱妮儿的人生轨迹就说明这点。朱妮儿在少管所一直是模范生,假如这次不出“差错”,也会顺利离开。作为反叛男权性暴力的发言人,朱妮儿正要离开少管所就被判了三年的监禁。她的叛逆使L联想起了凌霄。后来柯西的女儿和她的玩伴只要谈到比较危险的事情就会想起凌霄。虽然凌霄迫于生计只能从事卑贱的职业,她却得到柯西的偏爱,在去世之后和L的鬼魂一起守在柯西的墓碑前,哼唱爱的曲调。
四、结语
非洲裔美国黑人的祖先在经历了跨大西洋的旅行后,被割断了和非洲大陆、非洲民俗宗教的联系。幸存的美国黑人在心理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这种创伤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影响他们的后代。在莫里森的小说里,创伤性应激障碍是小说人物的常态,而黑人女性和儿童尤其是受害者。小说《爱》中的柯西是其他几个女性人物悲剧的来源,自从他娶了孙女的玩伴,他的家庭就逐步走向瓦解。《爱》中除了L和凌霄,其他人物行为上几乎都有些怪异,这也折射出心理的畸形。L和凌霄代表着这场心理创伤的幸存者,她们将通过共同哼唱,来哀悼逝去的人,为受过创伤的人疗伤。
[1]董晓烨.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评莫里森的小说创作[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4).
[2]杨智辉,王建平,等.蓄意创伤受害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应用心理学,2006,(2).
[3]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莫里森.顾悦.爱[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