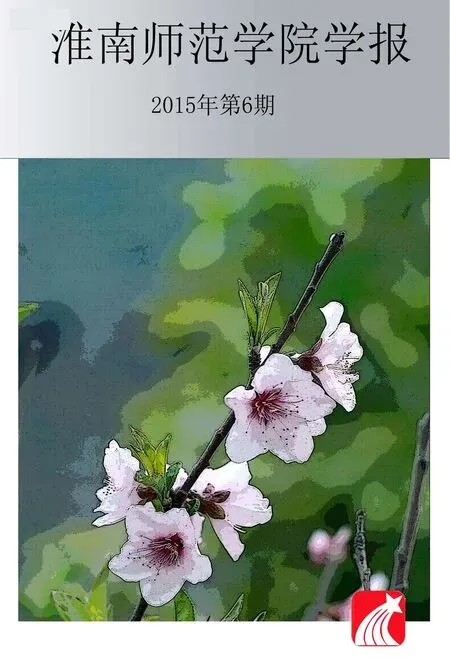从《看虹录》看沈从文的都市叙事和想象
程振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从《看虹录》看沈从文的都市叙事和想象
程振兰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随着《看虹录》《摘星录》版本问题的考订,沈从文1940年代的爱欲书写小说再次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这类小说是沈从文早期湘西书写和都市书写的延续和变异,其中包含了沈从文对于都市建构的设想。从《看虹录》这种都市爱欲书写的文本中来看沈从文对于神性的重构。其中包含着对于社会公共自由的追求,对于自然道德的建构,以及通过对于物的热衷,具象与抽象结合完成“美的造物”,从而将身体和情欲转化为一种诗意性的,具有抽象性的与艺术有关的美的生命形式和审美。
沈从文;《看虹录》;爱欲;都市;神性
一、沈从文爱欲小说研究状况
近年来,沈从文小说佚文的发掘为沈从文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研究方向,裴春芳女士对《看虹录》《摘星录》版本流变的考订再次激起了研究者对于沈从文1940年代这组曾经被斥为“色情”小说的兴趣。有研究者从其相关的情感经历进行考证,力图指证这几篇“新爱欲传奇小说”带有作者自叙传性质,认为这是沈从文与妻妹张充和的隐秘情事,关于这一说法引起了一些争议,我们暂且不说这一考证是否有着充足证据或是仅仅只为作者的奇想抑或纯粹出自猜测。考据者挖掘史料的不倦的精神以及佚文的发掘对沈从文研究的推进是值得肯定的,而沈从文在1940年代这组爱欲小说中主角是否为沈从文和张充和的争论仅仅只能作为文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谈,相信研究者不倦怠地对沈从文佚文的查找以及资料的发掘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找出其中某些不为人知的艳情传奇故事,而是为了更好地去推动沈从文研究,是为了给沈从文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域,是为了更真实地走近沈从文,更好地理解他。从另一方面来看,关于沈从文1940年代爱欲小说的争论也足以让我们注意到这种爱欲体验小说在沈从文的创作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那么,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这种曾经被称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品与沈从文当时的思想究竟有何关系?
纵观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其在1940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他仍在继续湘西世界的书写,但是这里的湘西世界已经不同于传统牧歌式的乡村,另一方面他此时期的写作转向了抽象深奥的内向性书写,且爱欲传奇小说都是发生在都市之中,而这又区别于之前的关于都市题材小说的写作。另外此时期他不单单创作小说,杂文和散文的数量明显增多,而这类文体涉及到很多社会现实问题,如女性、战争、性、政治、文学等,那么为何一向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会在1940年代逐渐舍弃湘西牧歌写作而创作了一些发生在都市的私人色彩浓重的内向性的作品呢?1940年代依旧处于抗战时期,尽管左联解体,左翼文学却得到了有力的发展,很多作家在1940年代选择了批判现实的写作,如冯至在1940年代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纯文学的哲学命题的探讨逐渐被现实批判的文学写作所替代,卞之琳写出了《慰劳信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那么沈从文的涉及社会问题的杂文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何沈从文在抗战时期的写作却转向了抽象的和都市中内向性的爱欲体验书写呢?当时也正是因为这些爱欲体验的小说创作,沈从文被郭沫若批判为“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许杰也对沈从文的这类小说进行了批判。暂且搁置沈从文与郭沫若之间的论争详情及私人恩怨,从这种批判上足可以看出在战争年代沈从文的爱欲小说似乎“不合时宜”,且其创作被冠以“反动文艺”之名,那么此时沈从文的思想状况是如何的呢?从其创作状况上面也许可以窥见其思想变化的一些端倪,换句话说,沈从文思想状况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在其创作之中的,本文拟从《看虹录》来看沈从文对都市的想象,从而更好地去理解沈从文的思想发展情况。
二、“神”的重构——对生命本体的坚持和公共自由的追求
《看虹录》以“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的一种生命形式”为副标题,在第一节之后又以“神在我们生命里”作为结束,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生命和神。那么沈从文所要表现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命形式呢?这个“神”又是什么呢?
1940年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作为中国文化精英聚集地的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更是有着空前的民族危机意识,对于战时中国的重建进行了自己的努力,如《战国策》杂志即是在此种情况下创办的,“战时重建是刊物的基本宗旨”①张森:《沈从文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而沈从文也在此时进行了自己的“神”之重造的思考,沈从文的“神”不再像《从文自传》中所言的湘西地区人人信神、敬神这种有神论的宗教性质的信仰,沈从文的“神”的重造主要集中为对生命形式的探索。沈从文在40年代对于生命形式的探究已经不同于30年代对于人性美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的思考。《看虹录》中作者在一种抽象意味和具有隐喻色彩叙述中描绘了一对没有具体名姓的青年男女在“镀上一种与世隔绝的颜色,酿满一种与世隔绝的空气”的都市小屋之中发生了一场同诗与火有关的暧昧的情爱故事,这显然不同于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强烈的40年代的社会氛围,这种生命形式是不同于生活形式的。他在《烛虚》中就已指明多数人只具“生活”的状态:
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平时如此,即在战时,自然还是如此。生活下来俨然随时随处都可望安全而自足,为的是生存目的只是目下安全而自足。②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43页。
沈从文认为这种人“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在1940年代战时情况下,他来到昆明,看到了大后方人性的沉沦,希望通过对生命形式的探讨和神的建构来重造民族文化和民族人格,期望人能够“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③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9页。。可以看出,沈从文所说的生命形式是超越了人基本的生物性的存在,从“抽象思索”中去探求生命意义,进行对“神”的重造。
《看虹录》一共由三节组成,这三节在叙事结构上似乎并不是一气呵成的,第一、三节用的第一人称“我”,而第二节用第三人称叙述,似乎是穿插进入,第一、三节中的“我”似乎是处于现实之中,缅怀着“在想象的时间下失去了色和香的生命残余”,第二节中的“客人”却处于强烈的爱欲体验之中,似乎一个现实中人做了一场别有意味的梦,在梦中身体的美完全呈现,最终达到了生命的神性。由此可以看出,似乎这些爱欲体验仅仅在虚幻的梦中才能够发生,现实生活中是无法达到生命的神性的,这也就意味着“神”的重造这一任务的艰难。值得注意的是,《看虹录》这种完全着眼于男女主体间私事的叙说看似与公共世界中的生活并无联系,而插入“梦”的叙述模式却将现实与爱欲体验联系起来,这易于让人联想到1940年代的社会现实,当时的社会注重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大众”似乎在逐渐取代“个人”,《看虹录》中爱欲体验出现于“梦”中,似乎就是意味着个人在集体之中的隐没,这也就表明了沈从文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不管是繁殖的急剧增长还是这一过程的社会化(即社会或集体的人一类代替个人成为过程的主体),都不能消除(生命显示于其中的)身体过程或劳动活动本身经验的严格、乃至冷酷的私人性”④[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页。。这其中也就蕴含了沈从文对于政治、社会问题的观点,这种观点一方面延续着沈从文在30年代时期对公共自由建设的坚持,另一方面发展了30年代的思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看到了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巨流一方面被‘暴政的罪行’,另一方面被‘自由的进步’推波助澜,狂飙突进,两方面又不免相互激荡,一直运动和反运动既无法达到平衡,也无法相互擎肘和牵制,而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汇聚成一股‘进步的暴力’,不断加速奔涌向同一个方向”①[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7页。。1940年代左翼文学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我”逐渐融入“我们”的革命热潮之中,沈从文试图通过“神”的重构来找到美好的生命形式,“名誉、金钱,或爱情,什么都没有,那不算什么。我有一颗能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还可以完全实现它”②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3页。在《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中沈从文既看到了重庆的“特务世界”也看到了昆明的腐败堕落的扩大,“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③同②,第128页。。所以在战时沈从文依旧关注着被忽视的人的审美丰富性的体现和重构,这正好跟其当时的杂文形成呼应。
三、女性身体的描摹——对情欲的映射和自然道德的建构
沈从文在努力用诗意的表达,去参与公共自由的空间,而“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历来为文学家所倾心描画,从楚辞中披薜荔的山鬼到当代身体写作,透过女性身体在空间世界中的投射,“试图穿透,表现甚至创造的精神世界”④吴治平:《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可见,空间世界的女性身体与精神的描摹是不可分割的,沈从文也善于通过不同空间的女性身体描画去彰显精神世界的表达。同样,《看虹录》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女性的身体形态,但是此时的身体书写已经不同于早期都市绅士或太太们无爱肉体的放纵,《看虹录》中的身体是跟母鹿的身体、百合花的姿态、雕塑的样态联系在一起的,这其中形成一种爱欲的映射,对于女性身体的情欲的表达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叙说,这与沈从文早期湘西健康爱恋表现主要是通过“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相互文。那么此时沈从文爱欲小说中关于身体的变化究竟说明了他关于“神”的怎样的重构?关于身体叙述从鲁迅开始并不缺乏,早期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中头发作为一个被观看的对象,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并夹杂着政治色彩;郁达夫的《沉沦》中身体同样作为一个被言说的对象承载着主体对于国家落后的痛苦,可以看出身体已经不再成为具体的身体,而是承载了某种文化、政治以及精神内涵。在《看虹录》中,沈从文将男子对女子身体的凝视放置在一种诗意的氛围之中,而火炉又为这种氛围加上了温度,绘有粉彩花马的窗帘以及书信中的内容的呈现都带有一种唯美的色彩,此时的身体和情欲已经在这种美中升华,身体不仅仅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还成为了叙说主体,与文学,艺术以及色彩等共通并形成一种抽象形式的美,“身体已经成为了‘意象’,具有融具象与抽象为一体的功能,经过抽象了的身体,既保留粉灵动生命的体温和色泽,又呈现出形而上的生命意义”⑤李蓉:《论“身体”在沈从文四十年代创作中的审美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正如他在《水云》中所言:“最奇异的是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说毫无情欲,只有艺术。我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⑥同②,第117页。由此可以看出,身体和情欲在这里已经被转化为一种诗意性的,具有抽象性的与艺术有关的美的生命形式和审美,那么自然道德形式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解志熙老师校注《沈从文佚文废邮再拾》中《梦和呓》讲到对绿百合的爱受到社会限制,“一般人喜用教育、身分,来测量这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关乎性的道德”。可以看出绿百合花有了一种人的隐喻色彩,我们姑且不去猜测这是否为张充和的象征,用绿百合的隐喻其实并不是很难理解,沈从文在《看虹录》中即已经用百合花和女性身体联系起来,所以绿百合花也是有着身体和爱欲的隐喻色彩的,是具象和抽象的统一,而这爱欲的承载体——身体,是无关乎教育,身份的,而人恰恰用这些来衡量道德程度,这样就会无法体味由身体抽象出的美与爱。关于身体和性的写作这种思想承续了沈从文早期湘西和都市写作,早期湘西传奇写作中,沈从文就对湘西健康人性和健康女性进行书写,如在《萧萧》《边城》等篇目中对于湘西世界中健康女性感情生活进行了描写,童养媳的萧萧并未被浸入猪笼,单纯的翠翠因美的歌声而对傩送生发朦胧的情感,他们的情感世界并没有受到道德、名分等的压制。而都市男女中绅士、太太们受到所谓道德、身份等的约束,以至于形成一种“阉寺性”特点,但是这种阉寺性却受到尊重,“这个社会的道德也即是在虚伪中,压制中,被伪君子和无性感的女子所污渎”。与早期不同的是,沈从文在《看虹录》中似乎是将两者进行了结合,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描写了都市男女之间的情爱,这里面身体、情欲依旧是生命本体的生发,其中又融入了沈从文对于现代境遇的思考,《看虹录》中第一节写到“我”在读一本奇书,而第二节似乎就是奇书之中的内容,是关于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之间美好的爱欲故事的,这个男子或许就是“我”,或许仅仅为书中的角色,这样男子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假如是“我”,那么男子似乎是在现实之中对于过去或者幻想的某种缅怀,对过去纯真的爱欲和美的情感的释放,达到生命神性的怀念,也恰好说明了现在的状况即是爱欲受到道德、身份、名分等的压制,现代社会的种种限制是无法达到神性的,而对于神性的建构即是对于未来的一种设想。假如男子仅仅为书中的角色,那么“我”“依然活在一种有继续性的荒唐境界里”,而书中是另一种梦的形式,另一种生命形式,现实和梦幻之中呈现出巨大的张力。正如作者所言:“我体会到‘生存’唯一事情,此外一切‘知识’与‘事实’,都无助于当前,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由此可见沈从文所追求人的自然道德形式是一种完全出于生命本体的,并不受到世俗教育、社会制度、家庭、身份及一切生活、习惯等束缚的,与文化、艺术的美紧密结合的真实的人,丰富性的人的生命形式。
四、“物”的诗意栖居——“美的造物”的构想
《看虹录》是沈从文栖居于文化想象的空间的创造,这样就使他的关于社会问题和道德认同的认识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看虹录》中对于都市男女情爱故事书写并不同于曾经的新感觉派笔下的男女出入于灯红酒绿的现代大都市,摩登女郎被五光十色的镁光灯包围,或者是男女过着纸醉金迷的写实的生活。而沈从文表现的似乎是一种湘西乡下人发生于都市的情感故事,男女之间的情爱故事似乎是一首触动人内心深处,可以激起最深的感情,舒缓、细腻且徐徐进行的音乐,他们的故事发生在一间并不大但是温馨而多彩的房间里,他们的情欲也被屋内燃烧的火炉点燃而释放温度,有着小马图案的窗帘将他们与外界隔开,似乎他们的时间停滞在那个房间之中。《看虹录》中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对于周围环境的渲染上还有对于“物”的书写上,第一节中写了“我”随梅花清香的引诱走向“空虚”进入了小院子;第二节中写了男女在小屋中发生的事情,其中又穿插了雪中猎鹿的故事,女子在火炉边读的信中也出现了大量对于雕刻、百合花等物的描写,就连对身体的描绘也融入了物,“展露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肉体,竟是一片光辉,一把花,一朵云”。为何作者如此热衷于对于“物”的表达?沈从文在早期的湘西世界书写中就对物进行了描写,如《丈夫》中对河水、船的描写,《边城》中对翠翠生活自然环境的描写。人以物的形式存在于自然之中,与物并呈,这样人的生命本体的存在与物达到了融合。这样看来《看虹录》中出现对于物的热衷描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时候的对于物的书写同早期湘西世界中对于物的书写形式一样吗?
《看虹录》中的物并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周围环境以及物的书写,还有“梦”中物的书写,想象出来的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真实的都市风景还是作者想象出来的风物似乎都与男女结合在一起,这里的物的呈现有早期那种以物观物的方式,让物自行地呈现出来,如第二节对于小屋中环境的描写:“近窗边朱红漆条桌上,一个秋叶形建瓷碟子里,放了个小小黄色柠檬,因此空气中还有些柠檬辛香”,这样用物自身的表达从而发现人的生命本体性特征。除此以外,物既是审美对象也是审美主体,物跟人并不是从属关系,它们成为了人的一种隐喻的表达,如女人和百合花,“百合花颈弱而秀,你的颈肩和它十分相似。长颈托着那个美丽头颅微向后仰。灯光照到那个白白的额部时,正如一朵百合花欲开未开”,这样人的主体性也呈现了出来,达到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结合,从而实现了人和物之间的双重的美的呈现,故而“我手指发抖,不敢攀折,为的是我从这个花中见到了神”。《看虹录》中还有对于雕刻的描绘,雕刻已经融合了艺术家的生命和尊贵情感,所以“在我面前那一个仿制物,倚据可看到神的意志与庄严的情感”,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将从都市男女新的爱欲体验中的抽象出来的美扩大到一切物,从而完成了美的造物,从而进一步重造神性。
综上可以看出,沈从文在1940年代都市爱欲小说中蕴含着沈从文对神性的重构的思想,而这种神性的重构其实是他对都市的理想生活的一种想象,一方面依旧是坚持着湘西牧歌时期的生命本体的自然呈现的状态,另一方面有别于左翼文学的主流,将笔触伸向被遗忘的爱欲故事,展现出人的主体性的存在,重新唤起在现代社会中沉沦的爱和美的生命形式,从而实现神性的重构,神性扩展到一切生命之中,而这种生命形式不仅仅是爱欲,这种生命形式是在公共自由的社会中,在并不受到世俗教育、社会制度、家庭、身份及一切生活、习惯等所束缚的自然道德形式下,重新发现生命中与艺术、文化紧密相连的爱与美,这恰好和他在《一个理想的美术馆》中提出的用艺术建构民族、国家的设想相契合,“这些人若能把文化二字看得深刻一点,明白国家重造社会重造的工作,决不是当前所见如彼如此的表面粉饰宣传所可见功,还得作更多的设计,而艺术所影响到民族感情的丰饶和民族自信心的加强”①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8页。,这显示出沈从文在对都市的构想中对于文化、艺术、人的丰富性的重构的重视。
Shen Congwen's urba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mirrored inKan Honglu
CHENG Zhenlan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versions ofKan HongluandZhai Xinglu contributed to researchers' interest in Shen Congwen's lust-themed novels written in 1940s.That kind of novels continued but changed Shen's earlier narration of Xiangxi and cities and revealed Shen's idea of city construction.This paper discusses Shen's construction of divinity through analyzing the kind of novels like Kan Honglu which is mainly about city lust.Pursuit of social public freedom,constructing of natural morality,and love of things are included.
Shen Congwen;Kan Honglu;lust;city;divinity
I207
A
1009-9530(2015)06-0071-05
2015-08-11
程振兰(1989-),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