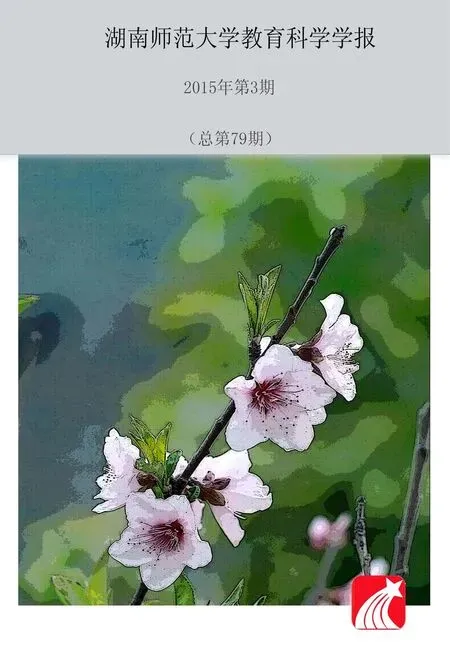论中古大学的科学研究及其特点
徐超富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中古时期即中世纪。因为中世纪是希腊文化衰落、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困、科学技术文化起色不大的一个比较黑暗的时代,尤其是前500年。因此,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贫乏而单调,对于科学研究也同样如此,无论其氛围、活动还是其成果都十分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整个中世纪,一部好的,甚至是原创的、品质上乘的科学著作一直创作于大学之外”[1]。由此也可以想象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之状况。由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有时空重叠,我们拟把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的科学研究情况一并纳入其中进行讨论。于是,中古大学科学研究就可分为非“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在今天所认定的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前的大学科学研究)、今天所说的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科学研究。
一、中古大学科学研究:历史考察
1.非“中世纪大学”
非“中世纪大学”是指今天人们认可的中世纪大学之前的中世纪高等教育机构。这里主要考察拜占庭帝国及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大学。在425年创办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几度兴衰,几度沉浮,直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在1 000 余年里,它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学术的中心,是世俗文化与教会文化相互渗透、对立斗争不断、博弈长期并存的互摄并包之所。君士坦丁堡大学创办初期,拥有20 名文法学者,并拿政府俸禄。哲学学者斯蒂芬纳、哲学家与数学家利奥、哲学家领袖普塞洛斯等学者先后在此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君士坦丁堡大学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探索真理和发现真理的人。从这一教育目的来看,探索真理就意味着要进行科学研究,显然,科学研究业然成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学者学术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拜占庭时期,法学教育与研究也十分活跃。当时著名的贝鲁特法律学校的法学研究,对积淀法学智慧和成就法典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此外,由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热衷于立法活动,推出了一系列法典,如《查士丁尼法典》、《法理汇编》与《法令新编》——《民法大全》。由于学校厚重的法理研究和社会广泛的法律践行间的良性互动,使法学理论与实践在当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阿拉伯帝国极盛时期,阿拔斯王朝非常重视科学事业。一方面,启用从罗马帝国遭受基督教迫害而来的希腊学者,直接继承和光大希腊文化与学术;另一方面,把从拜占庭那里获得的许多希腊典籍翻译为阿拉伯文。在9~10世纪的大翻译运动中,希腊学术与文化得以在阿拉伯帝国第一次复兴。
在公元830年,在巴格达创办了智慧馆——赫克迈大学,这个智慧馆与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的缪塞昂学园类似,设有两座天文台、一座翻译馆和一个图书馆,是当时的学术和翻译中心。赫克迈大学除传授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等学科外,还主要以翻译、教授、研究科学知识著称。首任校长撒赖姆曾留学希腊,把许多希腊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且还亲自前往巴尔干半岛古希腊一带搜集古代的学术著作,丰富了学校藏书。著名数学家花拉子模曾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并从事管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阿拉伯人在吸收了印度和希腊人的数学成就之后,创造了有自己特色的数学,特别是代数,花拉子模是阿拉伯数学的开创者。花拉子模闻名于历史的工作是写就了一部论印度数字的书和一部《复原和化简的科学》,将印度的算术和代数介绍给西方,使之成为今日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他在天文学上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了托勒密的体系,写了一部《地球形状》,而且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巴格达的大翻译运动使阿拉伯人很快掌握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日后西方借阿拉伯文献复兴希腊文明奠定了基础。
公元988年,哈里发阿齐兹在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建立了一所正式的学校——爱资哈尔大学。大学除教学外,还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法蒂玛王朝,埃及在文学——《一千零一夜》、医学——《医典》、天文学——译著《至大论》、数学——译著《几何原本》、历史、哲学等方面出现了许多著名学者,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显然,我们既可想象当时大学科学研究的盛况,又可直观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
2.中世纪大学
中世纪大学指现在普遍认可的博洛尼亚大学之后所创办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一批大学。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和大学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大学的内在机制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像大学科学研究就开始从宗教、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向自然科学领域发展。
从11世纪开始,欧洲十字军东征,进行了长达200 多年的宗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十字军从东方带回了东方文明、阿拉伯的科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并把当时西欧尚未知晓的哲学、医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一翻译运动从11世纪中期开始,到12世纪后期达到高潮,并持续到13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当时的最重要的两个翻译中心。意大利得益于地缘优势,它与拜占庭商务交往密切,而且许多人既懂阿拉伯文又精通希腊语;西班牙曾被阿拉伯人统治,后倭马亚王朝于1085年才被推翻,不少基督教学者得到了大批阿拉伯文的古希腊文献。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文化、学问与科学的吸收、消化和改造,大学担当主角并不辱使命地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翻译运动导致了欧洲的第一次学术复兴。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学主要是教师型大学,而且以神学、逻辑学、道德哲学、心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天文学、数学研究见长,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巴黎大学教授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1274)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不仅教学出色,而且他的科学研究成就——经院哲学取代了教父哲学,他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他把理性引进神学,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而且,实现了由天启信仰向理性判断的思维习惯或模式的转变,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牛津大学首任教长(1214年)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它不仅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翻译、评注,而且对神学、光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著述,如在光学方面,他对折射与反射、颜色、视觉和彩虹的几何学等问题都有研究,并写就了《论光或形式的起源》,而且以他为代表(还如约翰·佩克汉姆(约1230~1292)、威特罗(约1235~1274))推进了13世纪光学的发展。同时,他开创了牛津大学数学科学的新篇章,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对数学及自然科学的发扬光大及其科学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的学术影响,不仅在生前非常显著,而且在身后更是显赫。
在14世纪20~70年代,牛津大学出现了一批所谓“牛津计算者”,其奠基人就是唯名论的逻辑学家约翰·比里当。在动力理论方面,他对强力运动或抛射运动的解释下了一个定义,并被巴黎大学奥雷姆的尼古拉斯所接受。这一场学术的开端起于托马斯·布拉德沃丁的《均衡论》。托氏试图用一种新的数学工具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物体速率的观念并进行定量计算。这一新的思想启发了牛津大学默顿学舍学者们的思维,即寻找运动与变化的数学法则。巴黎大学奥雷姆的尼古拉斯在吸收牛津计算者的成果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图解计算方法,即实现了以一个定性的公式进行定量解释的目的。在14世纪和15世纪,这些成就通过意大利的大学和西班牙的大学得以传播与扩展。而且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共同创造的许多数学方法与力学术语,被16世纪的伽利略所运用。
在中世纪,巴黎大学的神学学术中心地位不仅是不可撼动的,而且在其他学科如在文法研究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实现了由古典文法(11世纪前)转向诗体文法(12世纪)并向推理文法(13世纪)的升华与发展。推理文法大约于(1270~1300)诞生于巴黎大学的文学院。
近代实验及其倡导实验科学精神的先驱罗吉尔·培根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与研究,于1267年写就了三部著作:《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并发出了中世纪未曾有过的声音,认为人们之所以常犯错误,在于对权威的过于崇拜;囿于习惯;拘于偏见;对有限知识的自负[2]。
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学主要是学生型大学,而且以法学、医学研究见长。在1500年之前,医学学术中心依次主要在萨勒诺大学、博罗尼亚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如帕多瓦大学的学者阿巴诺的彼得(卒于1316年),除教授医学、哲学和占星学外,他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在天文学和占星学方面都有专著,特别是他把教学所得融入到自己在巴黎大学多年的研究成果之中,撰写的《调整哲学家与医学者之间的差异》,对意大利大学的医学院产生的巨大影响长达数个世纪之久。中世纪后期涌现出的医学方面的大批手稿和作品,主要是大学医学教授的贡献。特别是1300年世纪之交,法国蒙彼利埃大学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一道掀起了直接研究盖伦著作的热潮,同时,对希波克拉底著作的评注也是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最富有活力的、最出彩的一部分。
3.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科学研究主要是人文研究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繁荣”。人文主义在大学的兴起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因此,大学里的人文研究也是意大利大学先行一步。意大利著名学者加斯帕里诺·巴兹查先后在帕维亚大学(1403~1407)和帕多瓦大学(1407~1421)教授文法、修辞学和道德哲学,同时,他对西塞罗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人文主义在16世纪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和作出了贡献。在帕维亚大学(1431~1436)和罗马大学的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洛伦佐·瓦拉,他不仅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如《优雅的拉丁语》和《辩证法的辩论推理》等著作,而且还大胆地尝试使用新方法——历史批评的方法对文本进行阐释,即根据作家的语言和环境的理解来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无论是著作还是方法都对后来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就受到了其方法论影响。人文研究与教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其薪金待遇窥见一斑。1432年佛罗伦萨大学,人文教师薪金224 个佛罗伦萨基尔德,哲学教师160个基尔德,医学教师150 个基尔德,民法教师130 个基尔德。15世纪末希腊语教师薪金高的可达400 个基尔德。在人文研究过程中,他们始终避免不了要涉及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因此,天文学在那个极富生命力的时代也爆发出了自己的活力。
发起天文学领域革命的哥白尼,曾先后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和研究医学、法律和神学,但他对天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情有独钟,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539年写出了天文学史上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系统论述了他的日心地动学说。出生于丹麦贵族的第谷13 岁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14 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日食的观察,由此一发不可收,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天文学的成就,发现了新星等新天文现象,经20 多年观察,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观测资料,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而充分的佐证史料,天空立法者法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曾作为助手就从中获益不少。可以说,没有第谷持续20 多年的观察,没有第谷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谷的许多新发现,成就不了所谓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开普勒先求学于法国图宾根大学,从那里了解了哥白尼学说,并成为哥白尼的坚定拥护者,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并担任数学和天文学讲师,他在进行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探索天体运行的规律(即开普勒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并出版了《宇宙图景之谜》、《哥白尼天文学概论》、《宇宙的和谐》和《新空间几何》。随着椭圆的引入,他给希腊古典天文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近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先后在比萨大学和帕多瓦大学任教并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写就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两门新科学》、《试金者》等著作。伽利略在科学研究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在科研方法上尝试了实验与数学结合的方法,在天文学方面,利用自己改进的望远镜发现许多新天文现象,捍卫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在动力学方面,发现摆的等时性,提出合成速度的概念,等等。
在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方面,西班牙大学相比其他欧洲大学也是比较出色的。可以说,西班牙是当时数学、星相学教育与研究方面的卓越中心。因此,欧洲不少学者不畏艰辛穿越比利牛斯山来到这里学习、访学和研究。一方面,它是当时的古希腊和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中心,近水楼台;另一方面,在那里有像阿威·罗伊一样的一批杰出的自然哲学家。
1527年被任命为德国的巴塞尔大学医学教授帕拉塞尔苏斯(1493-1541),他是一个炼金术信奉者,但他拓展了炼金术的概念——包括了一切化学过程;他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引进矿物质作为药物——医药化学的肇始。作为当时世界的医学中心——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医学院,不仅注重教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维萨留斯医学博士、威廉·哈维医学博士、法布里修斯医学博士等),而且还结出了累累学术硕果——血液循环、输卵管等发现。
1543年当哥白尼的关于宇宙《天体运行论》出版之时,另一部关于人类的《人体结构》的杰作也诞生了——公开出版了。《人体结构》一书的作者维萨留斯曾就读于巴黎大学,因对盖伦学说错误之处的批判,与教授们发生了争执,在1537年毕业时,巴黎大学医学院并未授予他学位。后来,意大利帕多瓦大学考虑到维萨留斯在解剖学方面的成就,授予他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该大学解剖学教授。
中世纪盛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医学院只是照本宣科地讲述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医学著作,根本不关注医学实验,针对当时医学教学的弊端,维萨留斯在教学和研究上注重实验,并亲自动手,通过具体的解剖,研究人体结构,根据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特点,划分了人体的骨骼系统、肌肉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内脏系统和脑感觉器官七大系统,绘制人体解剖图用于教学,还指出盖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医学错误达200 多处。其实,在宗教桎梏下,人体解剖是不允许的,只能是冒着风险进行解剖,而且死尸尤其女尸极其难找,曾出现过医学学生掘墓偷尸的情况。
还如1559年获帕多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于1565年成为该校的外科教授法布里修斯,他不仅自己勤奋科研出版了《论静脉瓣膜》,而且还培养了血液循环理论的创立者哈维——这样杰出的学生。哈维任牛津大学教授、生理学家,实验生理学的先驱——近代生理学之父,著有《心血运动论》、《论动物的生殖》等著作。它不仅生前把自己的心血献给了医学事业,而且逝世前立下遗嘱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给牛津大学发展医学科学。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上层内科医生的教育一直在大学进行,因此,许多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理论的重大成果都是在大学里诞生的。不仅如此,大学里的医学教育与科学研究还催生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如植物学、药物学和化学等都是在大学里发展起来的。
16世纪的大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书籍印刷出版机构的大量成立以及大量书籍的出版发行。其实早在15世纪,大学里就出现了学者型的出版商。如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人文教师纪尧姆·费雪,在1470年,他与同事海恩林一起,建立了索邦神学院的出版社。还如先后在罗马大学和费拉拉大学从事人文研究与教学的阿尔都斯·马努提修斯,在1490年,他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出版机构。为了出版经校勘的希腊经典著作,他集聚了一大批希腊学者和教师。其中不少就是大学教师,他们一边教学,一边研究,还一边从事书籍出版。
二、中古大学科学研究的特点
中世纪前半期(5~10世纪),西欧文明极度衰落,古希腊罗马文化几乎消失殆尽,处于一种极为“粗野的原始状态”。而度过了500年最黑暗年代之后,从11世纪开始,欧洲从漫漫长夜中渐渐苏醒。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十字军东征带回东方文明和古希腊及阿拉伯的文献与学术精神,欧洲学术才开始得以兴起。就大学科研而言也呈现出一种新气象,涌动出一定的科学研究活力,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更是甚之。由于在世俗性文化以及科学发展的影响下,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和实践,以及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派别的教育实践活动迅速发展,大学教育不仅出现新的局面,而且大学科研也呈现出一定生机。总体而言,中古大学科学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有如下六个方面。
1.研究文化的宗教性
中世纪尤其是11世纪罗马教廷成为西欧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之后,宗教昌盛,事事处处都要受到宗教束缚甚至禁锢。也就是说,宗教神学渗透到中世纪社会的方方面面,钳制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上至皇帝陛下或国王下至黎民百姓,甚至上至联邦政府或市政当局下至各种行会组织,无不受教会的渗透或干涉,无不经受宗教精神枷锁的羁绊。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对于学术,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教性。中世纪大学的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四个学院,不同地区、时期或不同的大学其地位有一定的此消彼长,但总体而言神学院地位最高,尤其是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崇高地位一直没有哪所大学撼动过。由于神学地位高,学者向往之也就是情理中的事,这种向往就是当时强烈的宗教文化所致。如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自然哲学家、论意志自由的作家托马斯·布拉德沃丁,他就撇开自然科学转向神学,英国天文学者和数学家——沃林福德的理查德(曾制成的天文钟在16世纪前鲜有能与之匹敌),曾说“后悔自己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学科上而忽视了神学”[1]。此外,我们考察研究文化的宗教性还可以从当时印刷的著作即可窥见一斑。1501年以前印刷的近30 000册古版著作中,将近50﹪的是圣经的各种版本、宗教祈祷书、每日祈祷书和其他宗教书籍;近30%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早期,以及当时的文学作品;近10﹪是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著作[1]。这其中不乏大学学者的作品。这种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学学术研究的宗教取向。教父哲学的始祖圣·奥古斯丁说过,世俗的学问至少要以合适的方式为基督教的发展服务。因此,无论自然哲学,还是人文学科,其语词言说时常表现出神学化,其话语方式时常表现出宗教化。多明我会一位教师曾抱怨说:“研究形而上学的人却总是谈论神学方面的知识内容。”[1]当然,中世纪末或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勃兴,人文主义的研究内容也进入许多大学人的视野,大学的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不过,人文主义取向的宗教研究也包括其中。
2.研究对象的文献性
对古典文献研究,一直是中世纪学术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些文献包括古希腊罗马的文献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等,阿拉伯文献,以及希腊化时期的注释与评注等。在医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对盖伦《医术》、希波克拉底《箴言》、阿维林纳《医典》等古典著作的研究,并不断地推出其研究成果——评注或评议。像盖伦著作的研究热潮,大约在1300年前后10年同时出现在博洛尼亚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的。总之,欧洲的中世纪是知识生产相当贫乏的时期,在自己未能产出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幸亏发现了古希腊罗马的文献典籍、阿拉伯的学术宝藏和东方文明。对于历史文献典籍,一般是先翻译,后研究,再评注。可以说评注也是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方法。评注的对象既有历史文献,又有当时学者的成果,但主要还是历史典籍。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西塞罗、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贺拉斯等人的著作,这些既是大学教学的材料,又是研究和评注的对象。另一个研究的内容就是《圣经》以及查士丁尼的法典的评注与阐释。培根曾谴责大学及其科学研究:这些地方人们的研究禁锢在某些作家的著作中,如果任何人对他的看法持有异议的话,他就会受到排斥并作为一个暴乱分子和革新者而接受审判。从培根的批评语词中看到了研究关注的对象——典籍文献;从培根的批评语音中听到了研究中翻阅文献的沙沙声。
3.研究内容的广泛性
研究内容除传统学科“七艺”以及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外。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这种发展要求人们从多方面去研究,如对贵重金属的追求促进了矿物学与化学的发展;机械的早期使用促进了机械学和力学的发现;力学研究的深入又进一步发展了数学;伽利略落体、抛物和振摆三大定律的发现,又进一步发展了物理学;生物学及生理学开始建立的同时,人们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并提出了有关学说,等等[2]。总之,这时期,除高扬人文主义,打击神权,讴歌人的力量,复兴古希腊文学与艺术外,自然科学研究广泛而深刻,在探索大自然奥秘的过程中,也充分显示了人的巨大的主观能动力量。其研究内容已开始扩展到地理、物理、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而且,每所大学的研究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在16世纪,意大利大学关注植物学和自然历史;西班牙大学注意力在“新世界”——新大陆里发现的动植物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数学研究成就斐然;帕多瓦大学和莱顿大学引领新科学发展。因此,大学除了对传统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外,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已大大地拓宽和拓展了。一言以蔽之,大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了,更加广泛了。但是尽管如此,此时的科学研究仍然受宗教神学精神的干扰和控制,甚至扼杀,如对伽利略著作的查禁和罗吉尔·培根的迫害就是例证。
4.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从11世纪起,十字军东征带来了大量的古希腊以及阿拉伯的文献,经过翻译,不少学者大开学术眼界。首先进入学者视野的是古希腊文献和阿拉伯文献,如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学术遗产,以及阿拉伯医学文献等。特别是托马斯·阿奎纳把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神学进行结合,并把理性引入神学发展为经院哲学以来,坎特伯雷的安瑟伦(卒于1109年)试图综合理性与信仰并著有《见证信仰的知识》,该书奠定了他的“经院哲学之父”的地位,在唯名论与唯实论的长期争论中,无论争辩,还是著书立说,一般都是借用逻辑学进行形而上学思辨的。思辨不仅是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中世纪整个学术活动的常用方法。在神学方面,早在12世纪就有人把文法和修辞知识应用于神学研究中去,试图使神学精致化即科学化。在中世纪具有实验性质的科学研究也时有发生,像阿尔扎切尔研究天文学仪器——天体观测仪——赤道仪,用于测量行星的位置,罗吉尔·培根曾“苦涩地抱怨说他自己的大笔钱被迫花费在他的实验上”[1]——说明当时实验研究是存在的。此外,在法学方面,出现了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照本、比较读本民法和教会法的比较,教会法与《圣经》的比较,格拉蒂安的《教会法汇要》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教令集》的比较,寻找和指出其相似或一致之处。可见,除了以思辨法为主外,还有注释评注法、零星实验法、观察法、比较法等多种方法并存。
5.研究形式的组织性
尽管中世纪研究形式主要还是个体性,如像神学、法学和哲学,特别是对各种古典文献的注释、评注与评论,个体研究是其研究的主要形式。但在医学方面,其组织形态上出现了初具雏形的集体研究“单位”,如大学里出现了植物园、人体解剖室。1544年比萨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建立了植物园,帕多瓦大学和荷兰的莱顿大学分别于1595年和1597年建造了会堂——解剖手术室。15世纪初以来,社会上出现许多私人性质的学术聚会。1454年,人文主义者里努奇尼(1419~1499)在家里建立了第一个学术协会。1462年,在佛罗伦萨成立第一个仿建组织——菲奇诺的“柏拉图学园”。16世纪下半叶这些组织遍布欧洲地区。尽管这些组织是在大学外,但有不少的大学学者参与了这些组织的学术活动。因此,他们的研究形式体现了一定的组织性。
6.研究发展的非均衡性
总体来说,各种学问的研究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世纪,神学及其研究都是属于统领地位的。此外,逻辑学在中世纪大学中也是一门处于非常重要地位的学科,它的教学(讲座与辩论)与研究也是相当活跃的,直到14世纪中后期,逻辑学发展到了当时水平的顶点。文法的发展经历了由古典文法(11世纪前)转向诗体文法(12世纪)再发展到推理文法(13世纪),即1300年以后,文法的发展基本上就停止了。始于14世纪前期牛津大学的、并源于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和他的学生们数学及自然科学传统的自然哲学(主要指物理学)的内在发展,直到14世纪中后期,似乎也达到了当时的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度。随着其地位不断地得以提升,自然哲学的辩论与研究在中世纪大学里也开始热了起来。教会法的教学与研究在中世纪也是相当抢眼的,特别是在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更是如此。总之,各学科研究总是此起彼伏并不均衡。以现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类来看,人文科学研究比重最大,如文法、修辞、逻辑、文学、诗学、道德哲学等;其次就是社会科学,如民法、教会法等;再次就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
[1]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M].张斌贤,程玉红,和震,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2]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2 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