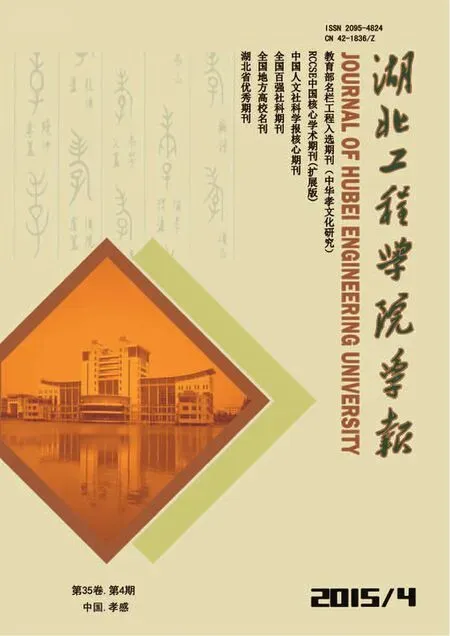诬陷的文学阐释
——北宋怀古诗祸评议
张劲松
(贵州大学 科技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4)
诬陷的文学阐释
——北宋怀古诗祸评议
张劲松
(贵州大学 科技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4)
北宋怀古诗祸常起于政治对手之间的相互构陷。这种构陷的特征多缘于私人的恩怨,而这种私怨又卷入文人政治的特殊环境和中期党争的斗争漩涡中。怀古诗祸的发生形成了一个阐释运动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陷害者对文本的曲解成为怀古诗阐释中的他释,他释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政治影射的契合点。被陷害者的辩解又成为一种独特的自释。他释和自释构成了怀古诗特有的一种文学解释现象。它的价值意义在于通过这个交替的话语释放,既联结了政治的影射习惯,也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全面敞开。
北宋;怀古诗;诗祸;诬陷;文学阐释;政治影射
宋代是典型的士大夫王朝,重儒业科举,故文化繁荣。士大夫涵养其间,常以诗文自娱。然文人政治亦因此有可虑者,即文祸难免发生。太祖虽有不杀大臣之誓言,但若因诗文得“讪谤”之罪,轻则降职失官,重则下狱远窜蛮荒之地。如北宋早期的邱濬因诗遭贬官,中期苏轼的“乌台诗案”等。而因作怀古诗而出现的文祸亦在此间出现。最著名的有李淑的周陵诗案和蔡确的车盖亭咏郝处俊案。历史的阐释和被政治联系的解释及影射式的分析在此显示出怀古诗传播中的特殊的生存状态。即历史一直被一只隐蔽的手——文人政治的性格所解释与戏弄。
一、宋代怀古诗案祸起之端
宋代文人因作怀古诗遭祸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多因“私隙”而被人告发,并非朝廷宰执的政治方针,突出表现为个体的政治报复行为。二是既杂有私怨,又被卷入北宋文人政治的特殊环境,特别是中期新旧党争的漩涡中。
李淑虽是北宋最早因作怀古诗被落职的士大夫,但因私怨被人告发的却是更早的孙仅。孙仅,字邻几,真宗咸平元年(998)进士。“仅性端悫,中立无竞,笃于儒学,士大夫推其履尚”[1]29册卷三〇六10101。只是孙仅比较幸运,因君主的阅读趣味而躲过一劫。此事不见正史,唯欧阳修《归田录》载之甚详。
孙何、孙仅俱以能文驰名一时。仅为陕西转运使,作《骊山诗》二篇,其后篇有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时方建玉清昭应宫,有恶仅者,欲中伤之,因录其诗以进。真宗读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骊山”,遽曰:“仅小器也,此何足夸 ! ”遂弃不读,而陈胜、禄山之语卒得不闻,人以为幸也。[2]一编五册
此节所记“有恶仅者,欲中伤之”,应是能够接近他的同僚或相识之士大夫。欲以此诗作为对皇帝建玉清昭应宫的讪谤之罪。只因真宗不太欣赏其诗,评其“小器”故无耐心续读后篇“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之句,遂能平安无事。“中伤”者与孙仅的个人恩怨,《归田录》语之不详,但很可能也是出于私怨。欧公隐去中伤者之名想是有所忌讳。而发生在仁宗庆历八年(1048)的李淑怀古诗《题周恭帝陵》之祸,其起因于“私隙”的脉络却很清楚。据魏泰《东轩笔录》云:
李淑在翰林,奉诏撰《陈文惠公神道碑》。
李为人高亢,少许可与,文章尤尚奇涩。碑成,殊不称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为二韵小诗”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恳乞改去二韵等字,答以已经进呈,不可刊削,述古极衔之。会其年李出知郑州,奉时祀于恭陵,而作恭帝诗曰:“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纔三尺,犹认房陵平伏来。”述古得其诗,遽讽寺僧刻石,打墨百本,传于都下。俄有以诗上闻者,......仁宗亦深恶之,遂落李所居职,自是连蹇于侍从,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3]二编八册23-24
陈文惠公就是陈尧佐,“文惠”乃其谥。尧佐尝拜相,以太子太师致仕,是北宋著名大臣。李淑撰其神道碑而不称其功德反谓之仅能为小诗,暗含讥讽,遂引起陈家的怨恨。对于此事,宋人诸家所记情节大抵相似。惟陈述古《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为“会淑尝作《周陵诗》,有‘不知门外倒戈回’之句,国子博士陈求古者,尧佐子也,因上淑诗石本,且言辞涉谤讪”[4]7册卷一六五3972。《宋史·李若谷传》附《李淑传》亦记为“在郑州,作《周陵诗》。国子博士陈求古以私隙讼其讥讪朝廷,除龙图阁学士,出知应天府”[1]28册卷二一9742。陈求古应为陈尧佐另一子。李淑撰词之所以对陈尧佐不恭,也有个人的私怨。据《儒林公议》载:“淑怨尧佐素不荐引,虽纳其润赂,文有讥薄之意。陈子哀诉,求为改削,淑终不从。”[5]一编五册132李淑,字献臣,乃李若谷之子,“年十二,真宗幸亳,献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赋诗,赐童子出身”。[1]28册卷二一9741淑警慧过人,又“博习诸书”,但为人却有点问题,比如他对宋郊的暗算就有点不光彩。
初,宋郊有学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国姓;而‘郊’者交,非善应也。”又宋祁作《张贵妃制》,故事,妃当册命,祁疑进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问之,淑心知其误,谓祁曰:“君第进,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倾侧险陂类此。[1]28册卷二一9741
《儒林公议》也记其“自负文藻,急于柄用,众恶其阴险,每入朝则搢绅为之不安”[5]一编五册132。可见,恃才自负,加之器量的狭窄,就很容易被官僚们视为“阴险”。故陈家掇取周陵怀古一诗加以曲解陷害,朝廷中就没有人为其辩解,宦途遭遇“连蹇”。李淑因此落职,大概不久又复为翰林学士。但在仁宗皇祐三年(1051)九月周陵怀古诗案又被旧事重提,遂遭到包拯等的弹劾而罢职:
谏官包拯、吴奎言:“淑性奸邪,尝乞侍养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养, 又复出仕,有谋身之端,无事亲之实。作《周三陵诗》,语涉怨愤,非所宜言。”[4]7册卷一七一4113
李淑曾为翰林学士,侍从二十年而官不显,表面上看来是怀古周陵诗惹的祸,实则是因为个性的问题与他人结怨,遭人陷害。不过,毕竟宋代对士大夫的宽厚政策,淑未遭太重的责罚,只是落职而已。相比较而言,卷入了北宋新旧党内耗的蔡确,其命运就惨多了。宰相蔡确在哲宗元祐四年(1089)夏遭旧党陷害远贬新州,也是因《夏日登车盖亭十绝》中的一首钓台怀古诗被人诬陷而致。蔡确的诗祸,一方面源于跟他人的恩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深深卷入了党争的漩涡。以笺释怀古诗的方式陷害蔡确的是知汉阳军的吴处厚。吴氏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立场,只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利益摇摆在新旧党之间。他诬告陷害蔡确,主要还是出于个人私憾,同时借机取悦正对旧党官僚虎视眈眈的新党执政者。关于吴处厚与蔡确结怨之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邵伯温《辩诬》云:
吴处厚者,尝从蔡确为山陵司掌笺奏官。处厚欲确以馆职荐己,而确不荐用,由此怨确,故缴进确诗。士大夫固多疾确,然亦不直处厚云。[4]17册卷四二七10317
而《宋史》本传所记则更详:
始,蔡确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笺乞怜,确无汲引意。王珪用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知安礼与珪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密遣达意救亶,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珪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珪为永裕山陵使,辟掌笺奏。确代使,出知通利军,又徙知汉阳,处厚不悦。[1]39册卷四七一13702
可见,吴、蔡二人的私怨是早已结下的,埋下了日后的车盖亭诗案的伏笔。蔡确在元丰间为神宗朝宰相,乃新党之人。元祐初旧党全面掌权,目之为“大奸”,黜之外州。而吴处厚正是看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采用沈括当初对苏东坡诗的曲解方式对之进行政治陷害,开告讦之风,取个人之利。其具体的陷害过程,北宋文人多数语焉不详。直到南宋王明清才有详细生动的描述:
其后,持正罢相守陈,又移安州。有静江指挥卒当出戍汉阳,持正以无兵,留不遣,处厚移文督之。持正寓书荆南帅唐义问固留之,义问令无出戍。处厚大怒曰:“汝昔居庙堂,固能害我,今贬斥同作郡耳,尚敢尔耶!”会汉阳僚吏至安州者,持正问处厚近耗,吏诵处厚《秋兴亭近诗》云:“云共去时天杳杳,雁连来处水茫茫。”持正笑曰:“犹乱道如此!”吏归以告处厚,处厚曰:“我文章蔡确乃敢讥笑耶?”未几,安州举子吴扩自汉江贩米至汉阳,而郡遣县令陈当至汉口和籴,吴袖刺谒当,规欲免籴,且言近离乡里时,蔡丞相作《车盖亭》十诗,舟中有本,续以写呈,既归舟,以诗送之。当方盘粮,不暇读,姑置怀袖。处厚晚置酒秋兴亭,遣介亟召当,当自汉口驰往,既解带,处厚问怀中何书?当曰:“适一安州举人遗蔡丞相近诗也。”处厚亟请取读,篇篇称善而已,盖已贮于心矣。明日,于公宇冬青堂笺注上之。后两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司户,至侍下,处厚迎谓曰:“我二十年深仇,今报之矣。”柔嘉问知其详,泣曰:“此非人所为。大人平生学业如此,今何为此?将何以立于世?柔嘉为大人子,亦无容迹于天地之间矣。”处厚悔悟,遣数健步,剩给缗钱追之,驰至进邸,云邸吏方往阁门投文书,适校俄顷时尔。先子久居安陆,皆亲见之。又,伯父太中公与持正有连,闻处厚事之详。世谓处厚首兴告讦之风,为搢绅复仇祸首,几数十年,因备叙之。先人手记。[6]三录卷一
这是记载蔡确被陷害的整个过程的最有价值的文献。然历代党争研究者多视而不见。长期以来,旧党一直将蔡确、章惇、邢恕、黄履等人呼为“四凶”,虽逐之外州,然仍不放心,正欲加之罪而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在蔡确讪谤诗案前,旧党正收集章惇所谓“劫持”州县“强市田产”之罪证。[4]17册卷四二四10261而吴处厚所上笺释的蔡诗,正合旧党心意,故刘安世、安焘、吴安诗等旧党官僚纷纷上疏,要求高老太后对蔡确“正典刑”,严厉诛罚。虽然朝中一些士大夫对于这种告讦之风也有不满,如彭汝砺等担忧“今缘小人之告讦,遂听而是之,又从而行之,其源一开,恐不可塞”。[4]17册卷四二五10278但出于捍卫集团政治利益之目的,旧党不惜鼓励“小人之告讦”。以“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4]17册卷四二七10323,将蔡确远贬新州安置。
古代文祸,并非少见的现象,但北宋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士大夫的王朝,文人政治是主体,因此还没有出现像后来清代那种带有种族恐怖和压迫的文字狱。也就是说,至少在元祐党禁之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文祸。北宋的文祸多为个体性质,当然其中也夹杂有政治斗争方面的因素。文人之间因私怨而对一些作诗文政治性的阐释,以达到诬告陷害之目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联系政治的阐释方式构成了解释宋代怀古诗的一个特殊方面。
二、政治目的的双向言说——他释和自释
北宋诗人怀古诗遭到“曲解”的过程,其实属于政治阐释的一个部分。北宋怀古诗祸发生后,一般会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往往由他人构陷的话语和自我的辩解两个部分组成。这就实际上构成了传释活动的他释和自释。两者合一正好组成一个由外而内的阐释过程。李淑和蔡确因怀古诗被特殊地关照和笺释的过程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先看李淑怀古诗被构陷时的解释话语。检宋人关于李淑诗的被谗话语,大致相似。《渑水燕谈录》所记较略:
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曰:“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垅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陈文惠薨,淑奉诏为墓志。淑言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陈之诸子请易之,淑不从,乃言其诗谤太祖。落淑侍读学士。[7]二编四册卷七
这里只记了陈家言其“诗谤太祖”。虽嫌简略,却是历史影射式的政治解释。李淑诗到底所“谤”何事?邵博《闻见后录》所记陈家的话语就详细多了。“陈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诗》于石,指‘倒戈’为谤。上亦以艺祖应天顺人,非逼伐而取之,落淑学士。”[8]卷一七136按宋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虽以和平的方式获得天下,但将士“倒戈”拥赵是政变成功的关键。*陈桥驿兵变,看似突然,其实是赵匡胤等精心策划的。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载兵变前太祖一家都住在定力院,就是为政治变化所做的准备。五代王朝的更迭基本上是靠军队的“倒戈”方式获得成功。可参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宋朝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第65-66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而李淑的“不知门外倒戈回”诗句却暗示了赵家天下的某种暴力获得的非法性,这是对李淑诗构陷的核心理解。其实这恰好是赵家的最大忌讳。因为宋朝国祚一长,士大夫就千般美化赵氏夺帝的合理性。*古代士大夫对于王朝和皇位的合法性是以时间来衡量的。朝代长的一般都被文人极力美化,短的就目为篡位。除了陈氏子弟的这种别有用心的话语,叶清臣的解释也是如此。据魏泰《东轩笔录》云:“俄有以诗上闻者,仁宗以其诗送中书,翰林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3]二编八册卷三24叶氏之言代表了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赵氏帝位的理想化解释。“揖逊”是类似禅让的儒家温柔,而“倒戈”暗示了残酷的权力斗争。故当李淑诗上达朝廷,”下两制及台谏官参定,皆以谓引喻非当,遂黜之。淑累表论辨,不报,因请解官侍养,许之”。[4]7册卷一六五3972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到的李淑“累表论辩”,乃是他对周陵怀古诗的自释。但李氏没有详载其辞。查北宋文献,惟邵博《闻见后录》载其片言话语:
淑上章辩《尚书》之义,盖纣之前徒,自倒戈攻纣,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经术,待之如初。宋内翰祁曰:“白公云‘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其献臣之谓乎?”献臣,淑字也。为文尤古奥,有樊宗师体。[8]卷一七136
李淑以《尚书》之义,以自释其诗。意在说明“倒戈”不是“武王伐纣”乃是军队“自倒戈”,非赵氏所谋,暗示赵氏皇权获得的正义性和人心所向。对于这种阐释大概连皇帝也是理解和认同的,故有所谓“待之如初”。但李淑终究因此诗而在仕途上严重受挫。解析李淑怀古诗解的关键是对“倒戈”的理解。他人之释的契合点即构陷之语谓之诬蔑赵家以武力夺帝位,而李氏的自释认为赵氏皇统乃人心所向。在他释和自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变动的张力,关键是看解释者的政治目的何在。
蔡确车盖亭郝处俊怀古诗的情况与李淑相似,但却卷入了党争的政治风波中。政治意图的影射式的阐释更为明显。据史载吴处厚是这样解释郝甑山怀古诗的: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此一篇,讥谤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笺释之。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时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天子治阳道,后治阴德,然帝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谪见于天,下降灾于人。昔魏文帝着令,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尽用仁宗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尽极孝道,太母保圣躬,莫非尽极慈爱,不似前朝荒乱之政。而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借曰处安陆人,故思之,然《安陆图经》更有古迹可思,而独思处俊,又寻访处俊钓台,再三叹息,此其情可见也。臣尝读《诗·邶风·绿衣》,卫庄姜嫉州吁之母上僭,其卒章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今确之思处俊,微意如此。[4]17册卷四二五10271-10273
与陈家陷李淑不一样,吴氏是精心准备,仔细阅读,认真笺释蔡确怀古诗的。因此,虽是构陷之语,然掘发的历史源泉确是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此诗之深意。蔡确此诗所以能触怒太皇太后高氏,乃是吴处厚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历史的政治的理解之契合点。这就是唐代武后和高太后垂帘听政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史语有“昔魏文着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9]7册卷二〇二。这是摄政的高老太后最为忌讳的。梁焘得到吴处厚的笺释弹劾蔡氏亦云:
今确乃思慕处俊,自见其意,以谓太皇不当临朝听政,作为流言,惑乱群听,阴怀奸宄,动摇人心,以为异日诬诞之基。其为悖逆,无甚于此。[4]17册卷四二五10274
吴处厚告讦成功乃因其笺诗能体味到时代的政治气息,把握了元祐旧党和高太后的政治心理。高太后听政尽用旧党,罢废神宗新政,逐蔡确、章惇等新党大批官僚。文人政治陷入严重内耗,朝野气氛一直紧张,高太后和旧党宰执对在野的神宗朝士大夫时刻警惕。吴处厚因私怨告发蔡确怀古诗中用郝处俊尝谏不可逊位武后之典以隐射当朝高太后。这不仅激怒时刻担心新党翻覆的执政的旧党官僚, 而且恰好触到了高太后的痛处,她以“山可移,此州不可移”的坚定,遂用文彦博之谋远谪蔡确至新州。[10]二编六册我们再看蔡确的自辩自释:
臣以涢溪旧有郝处俊钓台,因叹其忠直,见于诗句。臣僚谓臣以涢溪讥谤君亲,此一节中伤臣最为深切,须至缕缕奏陈。处俊,唐之直臣。父子夫妇之间,人所难言,而上元中,高宗令其子周王等分朋角胜为乐,及欲传位于武后,皆为处俊论议所回,故臣诗因叹其上元间有敢言之直气。今臣僚乃摘取处俊谏传位皇后事,言臣意在讥谤,其诬罔可见,一也。且又其事绝不相类,伏惟太皇太后,神宗维子,皇帝维孙。夫以祖母之崇、圣德之盛,故先帝遗诏,以社稷为托,保佑嗣君,乂安宇内。盖先帝托子于圣母,同揽万机,即非唐高宗欲传位之比也。臣僚辄敢妄引此事,牵合以资其说,其诬罔可见,二也。 元丰八年春,先帝服药,臣与诸执政在禁中御床下受诏,请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先帝登遐之日,于福宁殿奉遗诏,太皇太后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同行听断,退而就资善堂参议垂帘仪制,奏禀施行,则是太皇太后听政诸事,臣皆预焉。岂有身预其事,而自为议谤,其诬罔可见,三也。又将臣诗句中一“思”字,却引《邶风·绿衣》诗“我思古人”,刺州吁之母上僭事以为说,且经、史、毛诗“思”字至多,其所言思古人、思君子、思贤之类,有不胜其多,乃独引此一篇,盖其意在中伤臣,而不自觉其言之乖悖也。伏惟太皇太后以帝之祖母垂帘听政,而辄无故引唐高宗欲逊位与皇后,及州吁之母以妾僭夫人事迹,展转附合以为说,上渎圣听,莫甚于此。以此论之,孰为不恭,孰为非所宜言也?[4]17册卷四二六10301-10302
蔡确的自辩说明了自己作诗的思想动机及其诗意。他还指出吴处厚“摘取郝处俊谏传位皇后事”,以“绝不相类”的“牵合”,自己“身预其事,而自为议谤”诬罔自己等三点疑问,并对“思”的意思作了解释。其实旧党也意识到吴处厚以私怨释蔡诗的目的,如彭汝砺和范纯仁等,但旧党出于稳固政治利益的需要,对于可能引发的告讦之风作了很好的辩解,如梁焘所言:
其以告讦之风不可长而责处厚者,是亦不然。所谓告讦者,等辈之间,苟快怨愤, 摘其阴私,以相倾陷,伤败风俗,诚为不诫。至于自纳罪恶,凌犯君亲,忠臣孝子忠义切于上闻,不当妄引告讦,以为比拟也。况法所不加,义所不制,欲以何名议罪处厚?如谓告讦之风犹不可长,则如确悖逆者其可长乎?告讦之长,不过倾陷一夫一家,悖逆之长,至于危乱天下,岂倾陷之害可忧,而危乱之祸不恤耶?[4]17册卷四二六10285
梁焘还认为,通过朝廷大臣对蔡确诗态度,可以“尽见在廷之臣内怀向背,即是非邪正于是分明”。[4]17册卷四二六10858可见蔡确怀古诗案其实给了旧党政治上清洗新党又一次机会。故同情蔡确的彭汝砺、曾肇等人皆被贬谪。属新党的邢恕、章惇又遭惩罚。李淑和蔡确的怀古诗均遭到读者的阐释(以构陷为目的),他们自己也分别有自释的话语辩解,这恰好组成了一个双向的解释和理解。政治的动机带来了对作品理解的深入,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阐释价值。
三、北宋怀古诗案阐释对话的价值意义
在北宋怀古诗案的过程中,构陷者的笺释与被陷害者的自辩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传释的流程,形成一个完整的传释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一窥文学作品的作者传意和读者释意的有趣的文化现象。古代的文人,在一般情况下明确以文字或口头话语来解读自己作品的并不多,而作品多为读者的解释和理解。在怀古诗祸中,由于陷害的因素,作者被迫主动地回应读者(构陷者)的解读,同时,为洗清自己,他们对作品所传之意均作了详细的自释。于是构陷者的解读和被陷害者的自释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当下”的传释对话。对于怀古诗的深意的理解,自释和他释均有重要的阐释价值,一是他释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按照历史可能对当下的影响来理解文本,即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这种发掘深意的解释在怀古诗案中屡见不鲜。二是文本的自释者在自辩中的话语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最可能接近文本原意的途径。毕竟由作者亲自出来解释自己诗词创作的心态对于读者来说是很难得的,尽管自辩并非绝对能代表文本的真意。
首先,他释挖掘了文本深意,特别明显的是李淑诗和蔡确的怀古诗都没有直接涉及的史事和“深意”都被构陷者延伸出来。特别是吴处厚对蔡确郝处俊怀古诗的解释更为全面认真。蔡诗虽是怀古,但如其自辩所言的“但叹郝处俊忠直,而不曾指事”。[4]17册卷四二六10304南宋胡仔尚赞其“殊有闲适自在之意”,政治倾向并不明显。但吴处厚却以私人之隙,以政治的嗅觉将其联系到武后事,其动机固在报私怨,但他确实是以一个“读者”的角度,对蔡诗作了政治性的阐释。他的这种“笺释”证明了一个真理性的论断:“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11]211。如果说吴氏从蔡诗笺释出“忠言直节上元间”乃指郝处俊谏高宗勿逊位武后事情还不算惊人的解释,那么他以为蔡诗意在“讥谤”当朝太皇太后高氏则可谓“再创造”。因为他找到了一个解读的联系点——武后弄权临朝(含有执政的非正当性)和当下的高太后的垂帘听政的相似性。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影射般的符号学意义的释义,它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比如高太后摄政的不合法性,违背神宗改革等。这种比附想象戳到了当权者的软肋。以此而言,蔡确的新州之祸几乎是注定的。
其次,作者为洗清自己的自释一定程度上传递了文本的原意和当时的创作心态。如果按照加达默尔的说法,“诠释学的工作就是要重新获得艺术家精神中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将使一部作品的意义得以完全理解”。[11]172-173那么,北宋怀古诗祸逼迫作者自己站出来解释文本,这无疑是将解释趋向“出发点”了,如李淑对“倒戈”的解释。蔡确在辩解上元间“忠节直言”事云:“然则臣云上元间者,上元年中所谏事皆是,而臣僚乃略去谏周王分朋事,而独指陈传位皇后事。”[4]17册卷四二六10304此亦可见蔡诗怀古郝处俊意在临场的感叹,故不指事。不过,李、蔡的自释并不一定就是作品最终的“出发点”。因为“创作某个作品的艺术家并不是这个作品的理想解释者。解释的惟一标准就是他的作品的意蕴,即作品‘意指’的东西”[11]250。其实无论他释还是自释,理解都是在似有似无之间。蔡确感叹郝处俊,说他没有一点潜意识的贬谪的伤感是不可能的。这与新党指控苏东坡“乌台诗案”讽刺新法道理一样。且蔡确遭陷后有异常之态,其“离安陆,复遣亲吏取去诗牌,洗涤刮劘,靡有存者”。故刘安世责之亦有理:“使确之诗意别无诋斥,虽刻之金石,固自可信;惟其内怀觖望,志在谤讪,有歉于心,惧或流播,故令毁撤,欲以灭口。”[4]17册卷四二六10305-10306当然蔡氏毁去诗板不一定就是心虚的表现,毕竟对文字祸端的恐惧,早有如东坡那样的前车之鉴。但这依然是不能绝对排除其诗的政治含意的。元祐间东坡遭御史贾易劾其曾作诗庆贺神宗驾崩,情况与蔡诗相似,两人在遭构陷后的行为亦相似,如贾易所责云:
书于杨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从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4]18册卷四六三11055
东坡“内不自安”最有意思,也许是担心被读者误解,故有“换诗板”,“倒先后之句”和自明作诗之由等举动。但不论怎样,都与蔡确当年的心态表现是一样的,都是担心诗句被作政治性的解释,特别是被那些特殊的读者所理解。但我们依然有理由不能完全排除蔡确和东坡诗句中也许含有一种内心难以明言的“深意”,即便他们“确实”没有这样想。因为对怀古诗“所指”意味(包括是否讥讽时政等)的索隐是没有边际的。假如把古人身临其境、怀古浩叹的表达看成一种复杂的文化符号行为的话,那么“理解,或解释的对象是能指,它的目标却是意义”。[12]79故无论蔡确如何辩解其诗不曾有指事,依然难以躲过一场诗祸。因为构陷者是按照政治这个“目标”进行解读的。蔡确贬谪安陆,而郝处俊墓即在州境,怀古自然成为迁臣骚客寄托抒发政治失意的郁闷情感的一种方式,而蔡氏的不够谨慎终为自己招来祸端。据《麈史》载,庆历中,孙之翰知安陆,本欲为郝处俊撰文立碑,但“会温成张氏方以修媛宠贵,之翰畏谗,终不立,议者或讥其太忌”。[13]一编十册卷中孙之憾之所以小心谨慎,是他清楚文字阐释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密性。“诗的讽谏功能出自比兴手法,自身本来就含有‘寄托遥深’与‘穿凿附会’的内在悖反,阐释的差距与恶意的诬陷相结合,为文字狱的出现提供了可能。”[14]果然蔡确诗为仇人所释,指向的就是高太后的听政,遂贬新州而卒。
怀古诗案中的构陷者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解释诗句,存在曲解是难免的,但同时也是对作品含义的一种特殊的发掘。被陷者的自释让我们理解到文本的很多真意,但同时为了逃避陷害,他们也不会将最真实的含意完全倒出,自释者所考虑的气死并非在还原文本的原点上,而只是撇清自己,与构陷者针锋相对。也许将自释和他释合二为一,理解能够更为全面。但无论怎样,作品没有最终的解释。北宋怀古诗案是一个阐释的双向的对话,是在一种政治目的很强的特殊状态下对作品的阐释。构陷者和作者组成了一个对话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极具文化解释的意义,它存在于阐释和诬陷的缝隙之间。这个过程也生动地告诉我们,“客观的释义只是一个梦想”。[12]126怀古作品本身指向某个“历史”的价值符号,释义者确能将它无限延伸,产生更加丰富的意义。
[1]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欧阳修.归田录[M]//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251-252.
[3] 魏泰.东轩笔录[M]//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田况.儒林公议[M]//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6] 王明清.挥麈录[M].上海:上海书店,2009:185-186.
[7] 渑水燕谈录[M]//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76.
[8]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3:6375-6376.
[10] 王巩.随手杂录[M]//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61-63.
[1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2]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13] 王得臣.麈史[M]//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56.
[14]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0.
(责任编辑:李天喜)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False Accusation: Inquisition of Poem Singing for Historic sites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Zhang Jingsong
(TheDepartmentofTechnologyandScience,Guizho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4,China)
Imprisonment of poets for writing about historic cites was often due to the interactive false accusation between political opponents. Such false accusation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officials’ personal resentment which was involved in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s of literati politics and the intermediate-term struggles between parties. Imprisonment of poets for writing about historic cites formed a circulation of interpretation during which the person who accused others interpreted the text from an absolute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the key of the misinterpretation lied in the integrated point of political mapping. The explanation from the accused became a unique self-explanation or self-defense. Hence the misinterpretation and the self-defense became a kind of literary phenomenon for composing poems about historic sites. And its significance lied in that the alternate discourse release was not only linked to the political mapping, but also realize the spreading of the meaning in the text.
North Song Dynasty; poem singing for historic site; explain themselves; interpretation of egoist
2015-04-08
张劲松(1970- ),男,四川三台人,贵州大学科技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I207.22
A
2095-4824(2015)04-00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