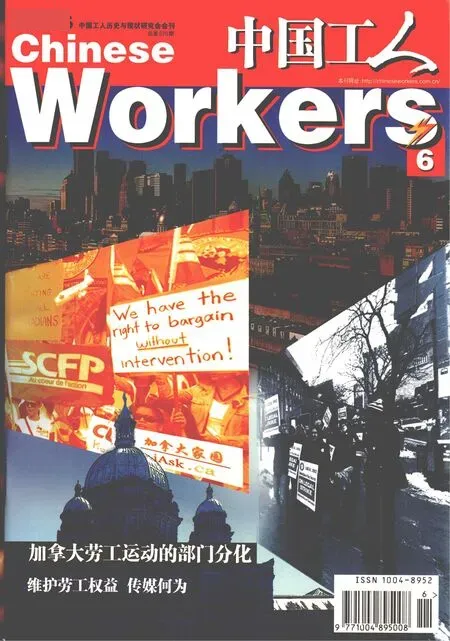维护劳工权益,传媒何为?——对五个青年工人代表的同题访谈
●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张玉洪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劳工的权利状况不容乐观。突出的表现是近年来劳工维权的集体行动频发,在表现形式上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如上访和“罢工”等。还有一些工人则以终结个体生命的方式进行抗争。
与之相伴的是,信息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影响。对劳工来说,在互联网出现前的信息社会里,他们是被报道的对象;而在网络社会,他们既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
那么,劳工的权利意识与维权意识是否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有关?他们对当前不同类型媒体在维护劳工权利方面的表现有何评价?对于让媒体积极发挥维护劳工权利的作用,他们有什么建议?
2 014年12月,我就上述疑问对五个有代表性的青年工人进行了同题访谈。
我选择的五个访谈对象,有60后、70后,也有80后;有的是全国知名的维权人物,有的则是NGO的组织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曾经或仍是底层的工人,为劳工维权鼓与呼,是名副其实的行动者。

张海超:1973年生,河南人。“开胸验肺”维权者。从2004年4月份开始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工作,到2007年10月份离开,共工作三年半时间。期间得了尘肺病,但职业病法定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下的诊断却属于“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即有尘肺表现。2009年6月,在多方求助无门后,他不顾医生劝阻,执著地要求“开胸验肺”,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病”。全国媒体大面积报道其人其事。2009年9月16日,张海超证实其已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各种赔偿共计615000元。
此后,他开始四处奔走致力于公益事业,寻救患尘肺病的病友。他还成立了网上工作室,对外发布自己的最新动态,对需要维权帮助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导。

吕彦武(笔名:红别民工):1985年生,甘肃古浪人。初中毕业后,从2003年开始出门打工,先后在饭店、石棉矿、塑胶厂、鞋厂、电子厂工作过。现在是公益机构干事。在《中国工人》杂志和个人博客发表了大量反映劳工生活的文章。

黄才根(浙江永康小小鱼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部负责人):1975年生。江西人。从1998年起,先后在福建、上海、广东等地工厂从事过制造业工人,一直到2007年离开广东到浙江永康打工,至2008年8月因工受伤而维权才结束打工生涯。2009年初,成立永康“小小鱼劳工服务部”以来,已先后与志愿者一起为上万名工友做过法律咨询、职业安全培训等服务。2012年7月,有报道称两年半来,他先后免费帮助上千名打工者,讨回1000多万元工伤赔偿款。

钟光伟:1973年生,陕西人。2006年,经村里人介绍到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云岗镇竹林寺煤矿打工近一年,得了矽肺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2010年9月,他用微博讲述自己的遭遇和维权经历,得到网友的声援和帮助(如捐款)。也有网友专程从北京等地前往山西看望钟光伟一家。 在2010年11月3日的微博里,钟光伟表示,他已经拿到赔偿款27万元。这笔钱,除去欠下的债和看病的钱,几乎所剩无几。

张志强:1967年生,四川人。走上法庭讨薪的中国农民工第一人,农民工利益代言人、中国十大法治人物,参与了《劳动法》维权和《农民工问题》领域的调研和立法讨论,非政府法律咨询组织“打工之友”建立者。1984年开始打工生涯,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广州和北京等地打工。2003年为讨要被拖欠的120元工资开始走上法律维权道路,后开始义务帮助其他打工者法律维权,并于2007年创立“打工之友”,同时开始关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
访谈者:在工作中,是否曾有过权利被侵害的情况?若有,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或二者兼有?
张海超:我在工厂工作的三年多当中遇到过延长上班时间、克扣劳保用品、各种借口被罚款等不公平待遇。精神层面的是厂里每天以不近人情的厂规给每个工人洗脑,让每个工人宣誓。
吕彦武:打工,可谓是权利处处受侵害。不签劳动合同、不参加社会保险、超时加班不给加班费、被拖欠工资、做不好事情挨主管的骂等等。
黄才根:在打工生活中,自己的劳动权利受到侵害是件很寻常的事,如强制超长时间加班(月工作超400小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法定休假日、受到工伤企业不予赔偿等,强制冒险作业、被辱骂和殴打的事也有遇到过。
钟光伟:企业老板知道我们农民工家里很穷,急需我们打工挣来的钱维持家用,他们为了取得暴利,无论工作环境还是工资报酬方面都很苛刻。有些矿企给农民工精神上施加了超人的压力。
张志强:有。主要是物质和经济损失,同时也有精神伤害。
访谈者:当权益受损时,常用的做法是什么?是否有效?
张海超:当权益受损时的做法是实施停工、怠工等,因为停工、怠工的工人并不齐心,所以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带头者均被开除。
吕彦武: 可以说,当自己权益受损时,我常用的做法就是沉默。曾经因为社保和工厂打过一次官司,但拖的时间很长,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直播过,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黄才根:在2008年工伤发生前的打工生活中,如遇到拖欠工资时,一般会先与企业主沟通、据理力争,如无果,纠集一帮老乡暴力追讨也有过。
2008年发生工伤后,因企业主拒绝支付医疗费用,为了维权,向企业主沟通过,也向当地工会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执法部门求助过,还向工作地的县、市两级多家媒体寻求过帮助,但都无任何作用。
钟光伟:当我们农民工意识到自己权益及身体受到伤害时,想用法律找回一点尊严,可这一点尊严成了奢望浮云。常常是企业方耍无赖,职能部门相互推诿,把我们农民工当皮球踢。
在法律程序上,有效证据都要我们受害者自己提供,难度可想而知:企业会搬石头砸自己脚吗?企业方知道我们农民工没经济实力,更耗不起时间。有些农民工在干活期间受伤或因工作患病,为找回合法权益把命都搭上了,都无法找回一点合法权益,所以有些农民工只能忍气吞声,只能放弃讨回那比登天还难的合法权益。
张志强:第一,本能的反抗;第二,思考一下;第三,制订行动方案;第四,实施行动;第五,抗争到底;第六,书写结案报告,对外发布。
如果说效果,我认为80%以上都有效。
访谈者:工作中的权益知识,主要是从何处知道的? 从法律书籍,还是报刊、互联网?
张海超:工作当中权益方面的知识大多是从互联网上了解到的,也有少部分是从法律书籍上了解到的。
吕彦武:互联网。
黄才根:2008年工伤发生前我基本属法盲。工伤事故发生后,为了维权,我购买了几本劳动维权的书籍,又学会了上网,在网上搜索相关案例来参考。
钟光伟:我们农民工文化浅,无自我防护意识,在自己权益受到伤害时只能摸石过河。
张志强:1997年至2001年,我购买了书籍,自学法律;后期进行了实践并巩固。
访谈者:从个人经验来说,你觉得媒体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有用?如果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海超:从个人经验来说,媒体对于维权的作用还是挺大的。主要的作用体现在能对相关部门和用人单位起到督促和舆论监督作用,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监督他们公正地处理事件。
吕彦武:说实话,媒体对个体权益的维护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一,像拖欠工资、不买社保这类事情,就是你去爆料,也不会引起注意的,因为这些事情太多了,吸引不了眼球;第二,利用新媒体,比如微博,但粉丝太少,转发几下,根本引起不了人的关注。就算引起了关注,对个人权益的维护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当然,近年来,一些案件,比如说罢工,利用新媒体引起了一些关注,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个不具有普遍性。
黄才根:我认为,一些媒体已市场化,为了追求发行量和收视率,他们一般不会太多关注劳动争议,这是其一。其二,一些媒体要接受新闻审核,相关题材难以刊(播)出。当然,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是例外的,好像也只有都市报会报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和自媒体给工人维权带来些许改变。如从地方到中央的相关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网站,网站设有投诉、监督、举报窗口,我们遇到权利受侵又维权受阻时,可以通过这些窗口反映诉求,其效果还比较好。另外,利用微博维权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还是没有上述投诉效果好。
钟光伟:被侵权的农民工也有通过互联网最终维权成功的,但很显然不是每个受害农民工都有那么幸运。
张志强:非常有用。可以说,让公众了解真相,就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和扩散与传播,并从中获得一定法律知识或者维权技巧。也增加或者增强了社会评论、加大或者加强了公众的参与度与知情权。还留下了第一手资料,或者说是后期的证据,以及榜样、标本,值得借鉴和学习。
访谈者:从个人观察来说,你觉得媒体在维护劳工群体的权益方面表现如何?党报、都市报、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哪个更符合你的预期?
张海超:从这几年的个人观察,我认为媒体在维护劳工群体权益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在多个群体事件或者典型案例中,都市报或者互联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都市报和互联网更符合我的预期,多起事件的首发都是都市报和互联网。
吕彦武:我只能说是互联网。
黄才根:都市报、网络、政府部门网站。
钟光伟:大部分媒体在劳工维权方面的确出色,他们按照实际情况讲出农民工的心声和遭遇。电视、互联网如新浪微博和一些报刊表现不错。
张志强:互联网、电视表现好些,其次是自制宣传品和设计活动表达或者表演。
访谈者:在你看来,目前是否有真心为劳工群体伸张正义的媒体?若有,可否举例?若无,可否列举原因?
张海超:我个人看来,目前为劳工群体伸张正义的媒体屈指可数,比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工报》等媒体不错。它们在多起劳工集体事件中为工人呐喊,让外界了解到了事实真相。
吕彦武:也有劳工群体自己创办的媒体伸张正义的,比如《劳工互助网》《城边村》等。说实话,现在我都不指望其他媒体为劳工说话,我觉着还得靠劳工自己。一些劳工和关注劳工的人,注册了微博、微信公众账号,开始自办劳工媒体为劳工发声了,比如《尖椒部落》《锤子之声》等。
我也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主要发我自己的文章和身边的工友们写的东西。
黄才根:都市报、网络、政府部门网站。
钟光伟:《新京报》、 @邓飞、@王克勤。
张志强:有,但我认为几乎都是点到为止,无法确认谁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访谈者:你觉得如何才能让劳工群体工作和生活有尊严?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张海超:我个人认为,让劳工群体工作和生活得更有尊严的前提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应有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权益。只有了解到这些应有的权益后,他们才会在没有享有时去争取,去抗争。比如,以前很多工人不知道用人单位应当为每一位劳动者缴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保。当知道这是应该享有的权利时,他们就会通过投诉、举报和罢工等行动来争取。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应该把事实报道出去,起到好的舆论监督和推动作用。把工人成功争取到合法权益的事件予以跟踪报道,这样好让其他劳工更多地了解自己应有的权益,学习争取权益的策略办法,增加可行性。
吕彦武:一是劳工自己权利意识的觉醒,二是可以建立真正维护劳工权益的NGO,三是大力倡导劳动文化。
我还是更看好互联网的作用。让更多的工人了解互联网,使用互联网,让工人为自己发声。
黄才根:一人8小时工作的报酬就能满足一家人的生活支出,这就是体面。劳动没有尊卑,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全社会尊重各阶层劳动者的人格,无歧视;全社会尊重各阶层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尊严。
钟光伟: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职责,对老百姓不苛刻打压,实事求是办事,才能使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看到希望和公平正义。
媒体只有按照事实情况报道,才能起到监督作用。
张志强:我个人认为,要想真正活得有尊严,劳工“三权”不可少。
媒体应深入追踪报道,而且一定要独立,还要有帮助劳工的责任和批评地方政府的勇气。此外,应该提出独到或者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推动改革。
通过对五位青年工人的同题访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
第一,在工作中,劳工权利受损是常有的。它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如薪酬,也是精神层面的如自由、尊严。
第二,在权利受损后,要夺回应得的权益是非常难的,有时可能用非常手段包括暴力。
第三,对媒体的作用,多是认同的。不过大多认为网络媒体和个别都市报表现更佳。
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从访谈结果来看,劳工的权益知识来源,主要是图书和互联网。因为信息的海量性、互动性和可搜索性,网络实际上成为一个免费、开放的知识库和咨询平台。
因此,对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来说,如何借助新兴的网络平台,传递与劳工权利相关的政策信息、相关案例,以及提供在线咨询等服务,应是工作的着力点。目前,一些工人报刊的网站和一些劳工NGO的网站都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受访的五位青年工人大多认同媒体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帮助,但对除个别媒体外的传统媒体表现并不满意,更认同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类媒体如新浪微博和自媒体如劳工网站、论坛等。
对劳工权利的维护来说,传媒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即时、全面地报道劳资关系的变化?如何将劳工作为社会有机构成的一部分来再现?如何充当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预警器和安全阀?
对相对弱势的劳工阶层来说,通过亲友、老乡、劳工NGO等个人关系网络进行自我赋权当然是一个重要途径,但作为社会公器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更应对劳工的赋权与平权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