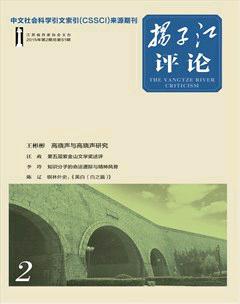基督徒的爱情:罪的深渊与神性之爱
陈振南+刘亚
北村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先锋作家的身份进入文坛,在他的文学实验室里创作出《黑马群》、“者说”系列等作品。但随后北村陷入“叙事的迷津”,一度失语,“信主前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我开始真正失语,连聒噪的热情也消失殆尽了。在我的内心深处已经厌倦了后现代主义那种将一切都平面化的写作方式,甚至有一种想回到现代主义梦想里的愿望,可我找不到回去的路。”a北村发生在1992年的受洗归入基督这一精神事件,使他接受了新的精神资源,与之前的先锋创作相比,他的创作有了釜底抽薪式的改变。他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追求不同,而是他吸收的宗教文化资源改变了他的创作。他围绕着爱情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并持续不断地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度思考和书写。北村所接受的宗教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对北村的爱情叙事具有决定性影响。北村吸收的宗教文化资源既包括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资源,还包括接续犹太信仰传统进行创作的犹太裔作家辛格作品中的犹太教文化资源。下面将从北村的基督信仰及其创作观,罪的深渊和圣爱的降临,辛格“具有神圣性的英雄”的引导这三个方面来追溯北村爱情叙事异质性的成因。
一、北村的基督信仰及其创作观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作家受到诸多流行思潮的影响,创作流派纷呈。80年代后期初入文坛的北村同样吸收外国文化资源,解决自己遇到的精神困境。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人丧失了终极信念之后的心灵的空虚和痛苦,并在卡夫卡、加缪、尼采、博尔赫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那里寻找出路。北村时而“逃亡”,时而“聒噪”,最后丧失了“聒噪”的热情,真正“失语”,这些都能在北村前期的先锋创作中寻得轨迹,但这都是北村在绝望和迷惘之时痛苦的文学实验。他坦言,“一批批评家对我小说的形式先锋性津津乐道,他们无视我的心灵,这个事实令我心酸”b。北村在1992年之后的一篇文章里对当代文学的批评真实地展示出当代文学对人们心灵的无视以及对各种流行思潮十分热衷的原因,“当今中国文坛却充满了只有感觉而没有感动的作品,连外在遭遇的命运的感动都消失了,而那些能让人在良心深处产生巨大震撼的作品几乎荡然无存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原因很简单:人放弃了神给他定的边界,作家也一样。放弃人格的唯一结果就是产生动物的感受,苍白的文学,里面似乎什么都有,动人的故事,优美的语言,缥缈的文风,唯独没有心灵的质量,这就是它不会让人感动的原因。”c
诗人海子的自杀事件彻底粉碎了北村对文学的全部幻想。他和他的妻子不为任何外面的事物,平静地解除了婚约,至此他持续不到几年的婚姻彻底破裂,他曾经视为具有超越性的爱情理想也幻灭了。这些把北村的心灵和精神逼上绝境。诗人之死、爱情之死、精神荒芜呈现出艺术、爱情和人自身的局限性,但北村还未找到自己具有永恒性的生存根基,直到1992年北村与基督信仰相遇,他找到了自己丧失的终极信念。基督道成肉身的救赎使北村恢复了与“永恒之你”的关系,个体之“我”在现时与“永恒之你”相遇,这是一种“充盈纯全的关系性存在”d。北村在此地找到了诗意栖居所。
北村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信仰基督的作家,受洗归入基督的精神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观。北村与基督教文化资源产生精神共振,以致他用异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眼光来思考关于生存、死亡、爱情等主题,将神性维度引入当代文学。罪与苦难、爱与救赎成为北村作品重要的主题。在文学道路的发展和信仰过程的经历中,北村在学着应该如何同时做一个基督徒和作家。
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耶稣基督。三年后的今天可以见证说,他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这之后我写出了另一批小说《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和《水土不服》等作品。我对这些作品没什么好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e
北村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打量这个堕落世界,由此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并且这些作品都与他吸收的信仰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评论者认为北村作品的布道意味太浓重,但北村如此解释他的创作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我承认自1992年以来我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一个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变化,同时我也承认这种变化跟我得着一种信仰具有紧密的关系。其实这是很好理解的,人心里怎样思量,他的行为便怎样,既然我的价值观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连我的生活细节都随之改变,我的小说发生改变又有什么奇怪呢?”f北村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已然把创作当成一种无法与他的基督信仰割裂的使命,这是区别于他之前的创作,也是异于其他当代作家的。不管是阅读北村的作品或是创作谈,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北村的基督信仰与他的创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并且是他创作转变的最主要的动因。
北村皈依基督信仰之后的创作观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神格的介入。神格象征着一种终极之光,是一种终极信念。其实,北村在1990年《文学自由谈》期刊第2期上曾发表一篇文章《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距离1992年的皈依基督信仰这一精神事件还有两年时间。在这篇文章中,北村已经意识到精神和信仰在小说创作中的缺席“预示着整个小说发展的荒原”g。“在目前中国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看不到这种一以贯之的终极之光,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种道德感,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民族忧患意识等等,就是难以看到他对存在的特殊敏感、对人类生存原痛苦的敏感和对生命的终极体验。即使在一些新潮作家身上,我们也只看到了经过伪装的对生命与存在的认识,如果究其独在的精神领土,就可能发现那是一片不毛之地。”h当时北村对中国8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现状进行的批评无疑是深刻而又有长远见识的。80年代中后期,一些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已经放弃了终极价值,在小说创作的形式上不断实验和创新,创作的形式本身成为了创作的内容,最后只能陷入精神荒原之中,没有能力继续进行实验以及在创作内容上深刻。北村环视诸多小说流派,“寻根文学”、“新潮小说”和“后新潮小说”,均没有窥见终极信念以及作家对一些终极命题的态度,浪潮汹涌般的文学创作昭示着作家精神世界的无主和混乱。但北村当时虽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但他并不理解终极信念的具体内涵以及该如何在自己的创作中引入终极之光,并且能够在小说叙述层面避免陷入技术主义的泥淖。
北村在1990年发表《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之后又创作了《孔成的生活》这一中篇小说,《孔成的生活》写的是迷津中孔成的生活,迷津是一个困境,人在其中行走,看似是具有超越性的跋涉,其实只是生命的沉沦。孔成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他的建筑理想具有常人无法理解和进入的超越性,但他陷入生存的迷津之中,无力构筑他的理想国,最后走向了自杀的结局。这一次写作只能说明北村在思想观念中意识到文学艺术需要神格的介入,即一种终极信念的介入,但就像孔成一样,北村仍无法把握终极信念的内核,那只是一个缥缈的诱惑和概念,北村依然无法走出他生命的迷津,更无法在创作中有突破与更新。北村皈依基督信仰这一精神事件直接影响了北村的生命以及他的创作。虽然在北村的叙述中,他信主的事实是如此的短暂和神秘,但这与他之前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洞悉、对艺术迷津的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算是后来他皈依基督的一种预示和铺垫。基督信仰使得北村之前一直无法参透的终极信念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并且他明白了终极信念与人的存在以及文学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曾经一度在迷津中沉沦的生命如今在终极信念的光照下找到了走出迷津的出口。
“神格的介入”统摄了北村1992年之后的创作。北村认为“对于作家来说,在终极信念之光的照耀下,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写作、写什么以及怎么写,这四句话是同一句话”i。因此,在北村创作的爱情小说中同样有着终极信念之光的光照,并以人间爱情的残缺性的揭示和人类对神性之爱的渴望表现出来。人间爱情的残缺性内容包括人们丧失了爱的能力,拥有的爱是自我的、易逝的、有限的;神性之爱则恰好相反,是舍己的、永恒的、无限的。北村诸多爱情文本都有对人间爱情残缺性的表现,《伤逝》中爱情的错乱,《玛卓的爱情》中玛卓在追求理想的爱情时丧失了生活的能力,《周渔的喊叫》中人们在生活中丧失了爱情,《强暴》中敦煌和美娴之间脆弱的爱情,《鸟》中把人间爱情想象成宗教之后的幻灭。除了挖掘人间爱情的残缺性之外,北村同时也在作品中构建爱情理想,《长征》里吴清风对吴清德超越肉体、时空、其他任何障碍的爱情,具有神性之爱的特性。短篇小说《苏雅的忧愁》写了苏雅对待爱情的深刻自省和主动担当,是一种理想的爱情。《望着你》中的五环和维林经过种种感情波折、苦难之后的和好,是深刻的纯美爱情。凡此种种,都与北村创作时神格的介入息息相关。基督信仰内化为北村持守的终极信念,北村借终极之光的照耀更深刻地揭示了人间爱情的残缺性及其原因,并在创作中引入神性之爱,小说人物没有被爱情困境淹没,而是在破碎中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并积极地、舍己地去爱。至此,神格的介入标志着北村创作将“现代汉语诗学中的基督宗教话语跃升为现代汉语基督宗教诗学”j。
北村皈依基督信仰之后的创作观呈现出的第二个特征是心灵写作。终极信念为北村的创作提供了超拔的视野,能越过现象把握人们的心灵,他借此透视人类爱情的困境并引入具有永恒性、无限性的神性之爱。心灵写作则是北村在终极之光照耀下的创作立场。“我不过是站在良心的立场上写作,描述在路上的苦难和尴尬,但并不是说我本人是绝望的。正如有光就意味有暗一样,你若退出光明就必进入黑暗。今天站在光的地位向黑暗注视,但不意味着接受它,而是给它一个良知的态度。”k“良心的立场”和“良知的态度”使终极信念不被事实暗夜淹没和取代,人间爱情的困境不只是由于物质的匮乏或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乃是根本源于人类自身的罪和自我中心。北村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有了对人类情感残缺性的犀利剖析,而不是如同池莉的“不谈爱情”,以此来逃避爱情困境。北村自己曾坦言他越来越感到做一个作家的困难了,并非是对技巧修炼知难而退,而是作家的心灵为此忍受煎熬,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l这正是北村坚持心灵写作的真实感受。
北村的爱情小说使人们感到强烈的不适感,他不允许他笔下的人物徜徉于物质层面、社会层面,而是进入人物的心灵层面。这些人物似乎都在自虐式的自我搏斗,有着诗人哲学家的气质,困扰他们的不再是物质的匮乏,对爱情的追求更没有停留在对身体欲望的满足和享乐层面,而是充满着对完美爱情的渴望但又有丧失爱的能力之后的沮丧和绝望。《玛卓的爱情》中刘仁和玛卓的爱情困境不在于物质的匮乏,刘仁出国也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的一种心灵的逃避,早在结婚那天,他就不能对玛卓说出“我爱你”三个字,爱的能力早已丧失,只好通过外在物质来表达他的爱情。当玛卓自杀之后,刘仁再也无法逃避爱情的困境并且无力解决,因此他也绝望地把车开向大海,走入死亡。敏感而又理想的玛卓对理想爱情有着强烈的渴望并一直坚持和寻找,这也是导致她自杀的根本原由。但玛卓爱的是她的爱情理想,她并没有切实地关心身边的丈夫、孩子,她不会做菜、做饭,对一个妻子应该尽的本分满不在乎,甚至多次请刘仁帮自己撒谎来逃避自己上班的责任。小说深入人物心灵内部,人物心中对爱情的向往、在困境中的挣扎和绝望都得到了深刻的描述,并且这种困境并不是由于外在阻力、刘仁或玛卓单方面的过错造成,没有完全忠诚的一方或是彻底背叛的一方,而是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一起必然会遭遇的困境。
另外,北村将人分为灵、魂、体三个层面这一神学观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使其创作陷入一定的困境之中。灵包括良心、直觉和交通(良心就是“是非之心”,凭是非的原则,叫人们感觉到什么是神所看为正确的,什么是神所看为错误的。直觉叫人们直接感觉神的意思,而不必凭借什么事物。交通叫人们和神来往相交)。灵和体相结合才有了魂,包括人的心思、意志和情感。体就是肉身,是人与这物质世界往来的部分。北村坚持的三元人论在他的小说和文章中都能找到类似的论述。三元人论高举灵,怀疑魂,贬抑体,坚持灵是属上帝的;魂是属尘世的,人的心思、意志和情感都已堕落。由此,北村作品中呈现出两种倾向与三元人论有关:一是文本在解决人们遇到的爱情困境或生存困境时提供的出路具有一种神秘和不可知性,并且不愿对神学观念进行文学转化。“信仰是不在逻辑里面、推理之中的,正如我们呼吸、生气不要经过逻辑推理一样,他是灵里的故事,是个奥秘”m,这句话表明了北村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北村观念中的灵是独立并超越于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的,与其说北村不愿对小说模式化的结尾进行美学转化,还不如说持这种神学观的北村已经不能对此进行调整,这已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与他的神学观紧密相联。但即使信仰是灵里的故事,信仰也并不等同于文学艺术,北村的这一主张与文学的美学原则是相冲突的。二是三元人论认为魂和体是堕落的和属尘世的,即人的理性、意志、情感、欲望都是衰败的,思想黑暗、情感颓废、意志消沉。由此而来的创作观念就是人没有信仰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北村爱情小说的主人公在遭遇爱情困境和爱情理想的幻灭时会走向绝望和自杀的原因之一,北村忽略了基督教神学中的普遍恩典,即人固然犯罪堕落了,但人身上仍有上帝的形象和光芒。这两个倾向将在下面探讨北村爱情小说创作的困境时继续深入。
王晓明先生曾说:“对二十一世纪文学的期望应该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说:希望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小说里面能够看见灵魂,能够读到灵魂的颤动。”n北村的创作已经显露出对人类灵魂的刻画和描写,并且已带给读者心灵的颤动。北村文学创作的突围与他个人的基督信仰之间存在的关系已是不言而喻的。
二、罪的深渊与神性之爱的降临
北村对爱情困境的书写、对人间爱情宗教幻灭的揭示、对爱情乌托邦的构建离不开他对罪和爱的重新认识。《圣经》是基督教的正典,被基督徒认为是上帝的话语,《圣经》中对罪和爱都有深刻的论述,这些来自《圣经》的启示无疑更新了北村对人自身的罪和人间爱情的认知,并且影响了北村的爱情书写。“罪”在希腊原文中的本义是射箭偏离目标,没有射中靶心,即人本是受造者,却以创造者自居,背离上帝创造人类的旨意,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再是以上帝为中心,把本应该属于上帝的荣耀归给爱情、艺术等。人从罪而来的自我中心是人间爱情困境产生、爱情宗教幻灭的根源。
人的自我中心导致了人的情感具有残缺性,情感的残缺性致使爱情困境的产生。《圣经》中对人类罪的描述为北村提供了关于人性的真相,他对爱情困境的书写不仅是爱情悲剧的呈现,更是关乎人性的悲剧。许多当代作家都有关于爱情主题的创作,他们书写的爱情可能只是一种政治隐喻;或是爱情的终极性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取代,人只要好好过日子,不谈爱情成为解决困境的虚假出路;或只追求身体欲望的满足而忽视爱情更需要灵魂的参与。但北村的爱情书写是以人性的缺陷为出发点,深入爱情内部透视人间爱情的困境,这无疑使北村的爱情书写具有超拔的深刻性。他是基于普遍的人性来透视普世爱情,并不是追随当下的流行思潮而创作,也不是只关注当下的困境,他的创作具有一种终极性。
北村创作的爱情悲剧与人的自我中心有关。离开上帝之后人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人既没有爱的内容,也缺乏爱的能力。”o美国学者欧文·辛格在其著作《爱的本性》中总结了古往今来关于爱的评价,认为爱的本质是一种积极的评价,一种吸引和欣赏。爱的实质在于给予和奉献,而绝不是要求和索取。p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提出,“成熟的爱”应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而绝不是“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q。北村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所拥有和投入的情感显然都悖离了以上这些真正的爱的本质——他们都是在“自爱”而非“他爱”,是占有而非给予;是情欲的满足,而不是甘心乐意地承担责任;是试图按自我意愿改变别人,而不是尊重他人依照其本来面目接纳对方。
中篇小说《长征》中陶红式的爱即是缺乏爱的内容的情感,陶红通过武力抢回吴清德,打烂了吴清德的情人吴清风的下身。陶红与吴清德一辈子相互折磨。陶红的爱是自私的、占有式的,充满了妒忌,爱的本质是舍己,但他对吴清德的爱情早已丧失了这一本质。长篇小说《我和上帝有个约》中刘春红对陈步森的爱是畸形的,她有强烈的占有欲,想要控制陈步森。当这种控制失败后,竟然拿自己的孩子出气,将孩子放到水里,孩子不幸被水冲走。在陈步森入狱之后,她之所以竭力为他的案子奔走,更多的是出于恐惧和愧疚。后来她才终于明白,“她其实没爱过陈步森,即使说她爱上过他,后来也没有继续。刘春红终于明白,爱一个人,不是索取和要求,不是占有,而是了解对方,尊重对方,并舍己奉献给对方。”r小说中教授陈三木的荒谬理论被他的女研究生情人一点点拆穿,即“人可以同时专一地爱上两个人”。理论只不过是陈三木不道德的借口,并用它粉饰自己的出轨行径。陈三木式的爱情只不过是自我和情欲的满足。他既不爱他的妻子,也不爱他的学生千叶。
罪同时也是人间爱情宗教幻灭的原因。《圣经》认为人是受造物,是为了荣耀造物主而活,但罪却使人自己设定活着的目的和意义。爱情和艺术都被人们赋予了宗教意义,活着只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得不到理想的爱情就深感人生是无意义的,以致走向绝望甚至死亡的处境,人受造本不是如此,缘木求鱼注定走入绝境。另外人间爱情本身不具有永恒性、专一性、神圣性的特点,根本无法承载人类生命的全部重量,如果把生存的意义寄托于爱情,爱情和生命都会崩溃。超尘、玛卓、康生皆是因爱情理想遭到摧毁而走入死亡之地的可怜人。
北村的爱情叙事除了让人们看到爱情困境的真相和爱情宗教的幻灭之外,还有对爱情乌托邦的建构。北村所构建的理想之爱显然是受到《圣经》中爱的观念的影响。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段经文中描述的爱情正是人间爱情所欠缺的,北村构建的爱情理想正是对人间爱情的一种补足。
北村认为爱是具有完全性和永恒性的,北村在小说《长征》和《望着你》中有对这种理想之爱的建构。吴清风对吴清德的爱情已超越肉体和时空的限制。吴清风对吴清德的爱情与陶红相比是更为炽烈、纯粹的。吴清风为了爱放弃了家庭、财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惜万里长征寻找吴清德的下落,只为看一眼心上人并送上一张照片和一首诗,表达自己永恒不变的爱。吴清风的爱具有惟一性、持久性。《望着你》中维林和五环两人在经历重重人生的磨难、情感的挫折之后终于重新牵起对方的手,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们在大学相爱,“因为夫妻两人原是一体,妻子是丈夫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s就订下爱的誓约,相约要一生相守。但当他们工作之后,金钱渐渐腐蚀了他们的爱情,两人莫名其妙地成为了陌生人直至分开。后来他们又都因为欲望、金钱、寂寞的原因和其他人进入恋爱和婚姻的关系。但他们在经过破碎的人生之后又再次重逢,埋藏在心底的爱火重新点燃起来,不同的是如今他们学会了彼此珍惜、包容、相信,他们的爱情结局是凄美而动人的。五环因为煤气中毒意外死去,他们的婚礼和葬礼一同举行。
但人何以从没有爱的能力到恢复爱的能力,北村似乎没有将这一过程书写出来。北村在《活着与写作》中曾谈到:“我想如果这世上有真爱,那一定不会有眼泪的,也不会死人。但非常遗憾,人没有爱,因为爱是具有完全性和永恒性的,所以爱是神的专利。人只有残缺的情感,这就是离开神性之后的人性的缺陷。人既没有爱的内容,也缺乏爱的能力。”t也就是说,在北村看来,爱是唯有神才能拥有和给予的,犯罪堕落的人本身是无法拥有神性之爱的。北村构建的爱情理想只是告诉读者真正的爱应该是这样,但情感具有残缺性的人类本身该如何重新拥有爱的能力去真正的爱着,这仍是北村爱情叙事需要突破的。否则北村的爱情叙事容易在两种模式中摇摆,一是放大人们的爱情困境,易走向绝望; 二是在构建爱情理想时容易陷入“缺少价值内涵的爱情至上”u这一处境中。
三、艾·辛格“具有神圣性的英雄”的引导
北村的爱情叙事不仅吸收了基督教文化资源,而且还受到接续犹太教信仰传统进行创作的犹太裔作家艾·辛格的影响。艾·辛格是美籍犹太裔作家,有特殊的宗教背景,他的父亲、祖父都是拉比——犹太教会众的信仰领袖、精神导师。辛格从小就浸泡在犹太教文化传统之中。尽管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但他创作中有着深厚的犹太教信仰传统和宗教情怀。他的父亲说他是无神论者,但他自己表明他信仰上帝。v不过,辛格的上帝观不同于犹太教信仰中的上帝,“超常的天赋和与生俱来的独立思考习惯,是形成辛格独一无二的上帝观和创作观至关重要的因素”w。总之,辛格的写作与他的犹太教文化资源有着无法分离的血浓于水的关系。
艾·辛格于1978年秋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品很快被译成中文,影响了许多新时期作家,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更是得到极大推崇。北村对《傻瓜吉姆佩尔》同样是推崇备至,他的文章《十读》中的第七读就是推荐辛格的这篇短篇小说。文章中列举的前面几读分别是《圣经》 《复活》 《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世界一流文学作品,可见该短篇小说对他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分量是何等之重。他说:“我认为《傻瓜吉姆佩尔》是现代文学史上惟一成功地描写英雄的小说。因为现代社会只有这样的英雄,英雄一到现在就是吉姆佩尔,他就是英雄,因为他相信一切应该相信的,背负一切应该背负的,忍受一切应该忍受的,最后他享受他的果实:快乐一切应该快乐的。他是英雄,因为他是良知的代表,忠诚的象征,英雄是具有神圣性的,吉姆佩尔身上就有这种神圣性,像忠诚、忍耐、爱、宽容,相信这些神圣要素都是简单的,所以人叫吉姆佩尔为傻瓜。我至今还为辛格用短篇写出巨著而百思不得其解。”x不仅如此,北村还在一些采访中谈论辛格,对辛格的文学成就作出极高评价,“辛格是二十世纪伟大的专注于描述人类灵魂境遇的少数作家之一”y。北村还表示他对辛格作品的喜爱,“我很喜欢辛格的小说,他总是能以很小的篇幅、简洁的形式表现很深的主题,他的几千字、一万字的小说,别人可能觉得非要写长篇,他用温和朴实的语言就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有着纯洁灵魂和坚定信仰的人物。”z另外,也有论者如塞妮娅认为“北村是中国作家中风格最像艾·辛格的人”@7。如此看来,不管是评论家的评价抑或是北村自身的观点,辛格之于北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并对北村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北村的创作也是间接地受到犹太教文化资源影响。
“具有神圣性的英雄”即出自《十读》中北村对吉姆佩尔的评价,吉姆佩尔的身上有忠诚、忍耐、爱、宽容等神圣性的品质,这是英雄身上所必备的神圣性的内容。辛格说:“我笔下的人物,尽管不是那种在世界上起重要作用的大人物,但也并非微不足道,理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有个性的人,有思想的人,历经折磨的人。”@8吉姆佩尔正是这样的人物,他渺小但并非微不足道。尽管他的一生充满被欺骗、被侮辱等等不幸,但他按照他自己的信念生活,成为北村眼中的现代英雄。正是吉姆佩尔这一“具有神圣性的英雄”典型对北村的创作有着切实的引导。北村认为辛格专注于描述人类的灵魂境遇,这同样适用于辛格对吉姆佩尔的塑造。辛格用很短的篇幅以几个片段来写吉姆佩尔的一生,他在讲关于吉姆佩尔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以故事为依托来透视主人公的灵魂境遇。
如果以尘世大多数人的标准来衡量傻瓜的一生,那么吉姆佩尔的一生就是一个笑柄。邻人对他的欺骗和侮辱,妻子埃尔卡对他的背叛,使他有足够的理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吉姆佩尔并非没有动过要反抗和报复的念头,他曾想过要离开小镇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他曾考虑是否要和妻子离婚,他曾试图报复小镇上的邻舍,只是信念之光的射入使他能够承载一次次的欺辱,一次次的背叛,心灵受到的戕害。信念概括起来很简单,就是爱、宽容、饶恕、相信、忠诚等内容,但它们不是空洞无聊的口号,吉姆佩尔是在苦痛之中真实地与信念相遇,并且信念促使他做出恰当的选择,没有被人世的纷扰与人性的暗夜所淹没和影响。不仅如此,当吉姆佩尔依靠信念生活的时候,他深刻地体验到信念之光的真实、信念强大的力量,他灵魂深处因着信念的介入而生发出对人的爱、怜悯和饶恕,而不是愤怒和报复。有一天晚上,吉姆佩尔从面包房回家,发现妻子身边躺着另外一个男人,为了不使孩子受惊,他没有发怒、大喊大叫,而是默默地回到了面包房。只此一个细节足以看见吉姆佩尔所持守的信念带给他的悲悯和爱的力量,足以温暖冰冷和充满谎言的人世。
吉姆佩尔对他妻子埃尔卡的爱情也令人动容。埃尔卡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还带着一个私生子,走路一瘸一拐的。众人强逼他娶埃尔卡,他们决心要把吉姆佩尔当作笑柄。不过,吉姆佩尔决定娶埃尔卡的真正原因不是出于众人的强迫,而是他认为结婚如果对埃尔卡来说是很好的话,那么他也是愉快的。吉姆佩尔拼命赚钱养活妻子孩子。当拉比建议他和妻子离婚时,他很伤心,他思念妻子和孩子,这是发自心底的爱。在生活中谁都可能会犯错,他以此宽容妻子并依然爱她。妻子离世前再次告诉他一个真相,孩子们都不是他的,但傻瓜并没有对妻子心生恨意,而是常常思念妻子,埃尔卡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并且是荣光焕发般的圣徒模样。吉姆佩尔在婚姻中持守爱情,一生忠诚、忍耐、饶恕并用恒久的爱来爱妻子和孩子,即使受到背叛和伤害。因为他坚信爱和宽容比背叛和伤害更真实、更有力量。
辛格的创作接续了犹太文化传统,永恒古老的信仰传统是他创作的价值支点,这一信仰资源使得辛格具有“命名”的能力,能把握人的轴心——灵魂。皈依基督信仰之后的北村的创作与辛格的创作有共同的追求,即回到自己的信仰传统,重新找回“命名”的能力,进而描述人类的灵魂境遇。北村在辛格的作品中看到了文学的本质以及文学应有的样式。他对辛格的高度评价显示出他对辛格创作的认同以及他个人的创作方向。辛格塑造的“具有神圣性的英雄”为北村的爱情叙事提供了两个方面的资源:一是如何描述人类的灵魂境遇,尤其是在爱情之中如何描绘;二是北村在作品中塑造出“具有神圣性的英雄”。如果说基督教文化资源使得北村的创作具有两个特征,即“神格的介入”和“心灵写作”,那么辛格的创作则为北村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典范和借鉴,即如何在创作中接续信仰传统并借此描绘人类的灵魂境遇,塑造出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傻瓜吉姆佩尔”以及英雄如何用具有神圣性的爱承载爱的困境。
北村个人对基督教信仰资源的吸收、《圣经》中阐释的人类罪恶的深渊和神圣之爱的降临、辛格“具有神圣性的英雄”的引导是北村爱情叙事异质性的来源。若不分析北村爱情小说与宗教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对北村的创作有同情性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更不能认识到北村爱情叙事的可贵性。
【注释】
a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作家》,1996年第l期。
b同上。
c北村:《信仰问答》,《天涯》1996年第3期。
d[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6页。
e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f林舟:《苦难的书写与意义的探询——对北村的书面访谈》,《花城》1996年第6期。
g北村:《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2期。
h同上。
i北村:《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2期。
j唐小林:《论北村的基督宗教诗学》,《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
k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l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m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作家》,1996年第l期。
n王晓明、铁舞:《向二十一世纪文学期望什么》,《上海文学》1995年第5期。
o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l期。
p[美]欧文·辛格:《超越的爱》,沈彬等译,《爱的本性——从柏拉图到路德》 (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0页。
q[美]艾·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页。
r北村:《我和上帝有个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s北村:《望着你》,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t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l期。
u齐宏伟:《以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世界的苦难和苦难的世界——从〈长征〉看北村的心灵写作》,《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1期。
v[美]艾·辛格:《艾·辛格的魔盒——艾·辛格短篇小说精编》,亚伯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w傅晓微:《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x北村:《十读》,《青年文学》1999年第8期。
y北村:《生活在异乡的精神家园坚守者——与北村谈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及其它》,《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11期。
z北村:《信仰问答》,《天涯》1996年第3期。
@7塞妮娅:《重塑中国文学精神》,《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
@8[美]艾·辛格:《艾·辛格的魔盒——艾·辛格短篇小说精编》,亚伯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