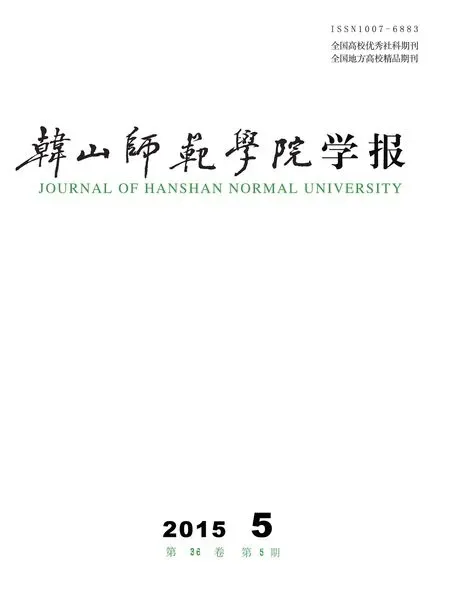文化创伤与侨批记忆
曹亚明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文化创伤与侨批记忆
曹亚明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西方学术界主要把文化创伤理论运用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反右运动和文革的反思,但将文化创伤理论与侨批记忆进行互相阐释还是一种新的尝试。文化记忆是保存经验与知识的储存器,而侨批档案正是一种具有意味的民间“文化形式”,也是保存侨民生存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储存器”。侨批所记载的并非仅仅是侨民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中国移民群体的创伤记忆。因此,直面侨民历史,反思文化创伤,是我们当前华侨研究和文化研究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文化创伤;文化记忆;侨批;侨批记忆;创伤叙事
引言
“批一封,银两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克苦做,猪仔哩着饲。待到积有钱,猛猛归家来团圆。”这是一首流行于民间关于侨批的歌谣,里面甚至还掺杂了不少潮汕方言,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批”是我国东南沿海区域方言对“信”的称呼,“侨批”则是自清代以来在广东、福建、海南、广西沿海侨乡出现的一种民间文书,它是由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亲人的侨汇凭证和书信的结合体。侨批历经清末、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涉及侨居地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侨乡社会、文化、经济等发生重大变迁的见证,也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记忆遗产。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从经济史来看,侨批可与徽州学的“契据”、“契约”媲美,其价值相等。[1]“依笔者看,侨批不仅可与徽商的契据契约媲美,侨批同样可与被称为‘中国银行之父’的晋商的‘钱庄’、‘票号’媲美,尽管规模和范围远不及晋商的‘钱庄’、‘票号’,但从地域经济史的角度看,侨批业却有独到的特色。”[2]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际侨批学术会议的影响下,侨批研究已经逐渐由民间私藏开始走向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研究视角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以往对于侨批的研究比较着重于金融或历史等领域,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悄然兴起,对于侨批文化的研究也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可以说,2013年“侨批档案”被录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侨批研究由民间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开启了侨批文化研究发展的新阶段。总体来说,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新理论的尝试将是下一阶段侨批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因此,作为一种尝试,本文试图将西方学术界的文化创伤理论与来自中国民间的侨批记忆进行互相阐释。
一、记忆的碎片
弗洛伊德对于创伤的解释是:“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3]创伤是引起持久病变的身体损伤,或能导致情绪异常的精神打击,既包括生理创伤或身体创伤,又包括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侨批文书中有很多关于创伤的叙事,无数封饱含血泪的侨批文书其实就是海外华侨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的真实写照。尽管都是碎片式的零散记忆,但依然能让我们想象出他们在漂泊生活和战乱祸患中所遭遇到的心灵与精神的创痛。
“一船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驰过七洋州,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能回还。”听着这首悲伤的民间歌谣,我们能深深体会早期中国移民的痛苦与无奈。早期的海外移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生存不得不飘洋过海、辟地以居。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的109年间,由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很多人出外谋生、避祸。此外,当时东南亚各国长期对出入境很少限制,不少华人被诱骗或劫掠到海外当劳工。因此,出现了几次移民出国的高潮。移民分两种类型,一类是延续以往的历史传统,由旅外乡亲牵引或由专做移民出洋生意的“水客”引带的自由移民,另一类则是以“青单客”、“猪仔”等形式被拐骗、输送到东南亚殖民地的契约劳工移民。严歌苓小说《扶桑》的女主人公扶桑就是当年成千上万地被拐骗到海外的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对于侨民在海上的经历,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在他们的温和与乖顺中,成百上千的年轻女奴被运载来了。他们温和地处置一路上死去的女奴,安详地将无数尸体抛进海洋。”[4]由于路途遥远,饥寒交迫,还未抵达彼岸就病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当然,更多的还是自发去海外谋生的自由移民。但是,即使最终顺利抵达彼岸,要在异国他乡立足谋生也异常艰辛。饿死、病死、惨遭折磨致死者层出不穷,因此南洋各地都有义山和公墓收殓在海外死无葬身之地的苦难乡亲。义山还留下对联:“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付流水;想做座山,无回唐山,终老尸骨归义山。”不少老华侨至死终未能“猛猛归家”与亲人团圆,不少老华侨凄苦无告,最终葬身异乡。
依据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C·亚历山大的界定:“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5]11作家严歌苓非常关注百年来海外华人的文化创伤体验,《扶桑》这部小说就是以一个第五代移民的叙事视角展开中国第一代移民的创伤叙事。在翻阅了美国旧金山档案馆里160册有关圣弗朗西斯科唐人街的史料后,她凭着敏锐的感受力和文化血缘上的天性,用充满传奇色彩的笔调还原了一个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夏天的故事。而她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移民的历史记录,作者凭着卓越的想象力在记忆的碎片中从文学的角度还原早已湮灭的历史,充满了叙事的张力和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在严歌苓充满张力的创伤叙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东方妓女扶桑在东西方文化隔阂与冲突中的悲哀,还有弥漫在整个创伤叙事过程中充满漂泊感的弱势民族的悲哀。但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样的创伤叙事远远不及侨批记忆那般真实可靠。新加坡侨胞陈应传在海外执教多年,他写的侨批令人心酸动容,“奔波十余载,尚赤手空拳,未得酹愿”,本应多寄批款回家乡让母亲购买新谷,无奈力与心违,便在寄给母亲的批信中写道,“非传不知家中之痛苦,奈命生如此,惟有昂首问天叹息而已”。[6]191“昂首问天叹息”的又何止陈应传一人,千千万万的侨民都通过侨批向亲人讲述了他们在海外生存的艰辛和内心的创痛。侨批文书中的这种创伤叙事虽然简短,甚至零碎,不像严歌苓的小说笔调那样凄美和神奇,但是我们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最真实的创痛。旅泰侨胞杨捷从赚到第一笔血汗钱后,首先想到的是要赎回卖出去的苦命女儿。他寄出五万元国币给妻子,在侨批上留下附言,嘱咐她收到批后“至切赎回吾女回家”[6]232。短短几字,字字锥心。从旅泰侨胞曾哲坤的侨批我们还发现,不少侨民为了不让家乡亲人担心,并不想在侨批中提及自己当时所处的苦境,实际上是他对于创伤性经历的一种压抑。后来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他才不得不在1955年5月4日寄给母亲的批信中吐露实情:“儿本家信不要说话,无奈母亲爱儿心切,来书常问何种职业,现在不得不贡献一切过程,儿自旅暹至今,生活真恶劣,其苦难言,每逢失业时期,食宿无着,这凄凉的事,不能尽诉。近来儿的职业,忽得忽失,没有固定,致不敢奉告,一面又恐母亲见信,为我担忧,故此迟迟不复,请希原谅,情长纸短,余容后申,顺颂。”[7]53令人惋惜的是,不少侨批原件并没能完整保留下来,但是凭着侨批档案中记载的这些“记忆的碎片”,我们不难想象当初海外侨民所遭遇到的精神创伤是何等深重。
简·奥斯曼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是他将集体记忆的概念引入了文化领域。他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中说:“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①参见Jan Assman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No.65,1995年第125-133页。他认为“文化记忆有固定点,一般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并称之为“记忆形象”,这些节日、仪式、诗歌、意象等,形成了“时间的岛屿”,在日常的交流中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文化记忆是一个享有共同文化的群体对自己经历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本身又是这个文化能够保持其凝聚力、持续存在的结构力量。集体经验正是通过文化型构而结晶为文化记忆。因此,文化记忆是保存经验与知识的储存器,一个群体从这种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而侨批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意味的民间“文化形式”,也是保存侨民生存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储存器”。
侨批记忆不仅能反映当年中国侨民在海外谋生的景况,也能通过侨眷回批一览中国侨乡的历史变迁,通过侨眷们的血泪控诉,还能还原历次战争中中国侨乡的生活场景。尤其在战争和政治动荡期间,侨眷们生活更是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创痛。沦陷期间,寄批受阻,使家乡的侨眷生活贫困交加,抗战胜利后又开始内战,侨乡百姓苦不堪言。陈氏写给丈夫锡泰的回批中这样描述:“自沦陷以来批信断绝,天涯海角无从相叙,念念。良人客居异地,劳瘁风尘,务当贵体调摄,努力加餐为祝……数年以来,万物腾贵,免想而知,家无寸土之遗,内无一钱之存,衣服一介费尽,株守苦海,以待天下升平,朝夕祷祝。日夜忧愁,谁料复员以来,乃竟自三月一批而又断绝,是何也?望乞示知。现潮汕各界早造失收,日难度三餐,人人失业,去年幸有吾母家颇丰裕,才能寸丝看待。现吾母家境亦困难,一无所出,惟望信到之日速速批银寄来,以免饥寒之忧,是所为盼。”[8]117家无寸土之遗,内无一钱之存,由于生活困苦,忧愁过度,又因为担心批银断绝的女儿宜家,锡泰的岳母甚至眼睛都因此而失明了,陈氏急切期盼丈夫能按时寄批银回来救急,“以减尔岳母之愁”。1945年12月初三,林坚颂在写给远在新加坡的孙子林展开的回批上这样写道:“久不通音,皆缘日寇之乱,弹指于兹,将十载矣。正思念间,忽接寸丹,开缄展阅,欣悉吾孙旅居平安,殊慰迈怀。家中及诸亲戚邻友均托安康,祈勿远介耳。所询家乡情状,因自寇军登汕,苛政如云,布乱潮线,断绝阡陌。屠杀劫夺,种种罪行,无恶不作,谈此苦况,情似叻坡,百物日贵,粮食断绝,甚至俺乡乏供、饥饿,皆靠土产以压腹饿,塘(唐)中局面,笔亦难歌,惟俺之用均属园货,勤耕力锄,以助供养,幸得无虞,屈延于今。日寇坠沉投降,我国山河重新如斯。束缚形况,人民殊足以尝雪伸,敌寇伐倒,四海通津。值逢鸿便,接来佳音,满怀告慰者而乐欤。思吾孙可观四路捷通,祈从速收拾回塘(唐)以慰老迈之望,而可仰足以奉侍父母,俯以畜妻子。”[8]97-98澄海莲阳林荣年于民国卅五年(1946)七月初四写给新加坡的侄儿林思曾的回批中描绘了一幅日本践踏侨乡的悲惨画面:“现在饥荒严重,米贵如珠,遍地皆是。余自莲阳湖港上乡尾陈学校本春歇事之后,入息断绝,生活岌岌,诚恐饿殍,惨状难述。今环境迫逼,上下为难,苦极苦极……惟物价高贵,月间银项至切多寄者为最要。乡中自失陷后流离死亡,十室九空,疮痍满目,失业者众”,一句“苦极苦极”,却道不尽其中的万重苦难。[8]103
可见,侨批比一般意义上的家书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家庭书信,更是中国侨乡百多年来与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发生广泛联系的文献见证,是“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文递播为外象,以心心沟通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的一种流动型、综合性的多层次文化形态”[9],是人类的一种集体记忆遗产。从侨批这一独特的知识储存中,海外华侨和侨眷乃至于他们的后代都能获得关于这一群体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侨批与侨民的各种民间仪式、宗族信仰等融合而成“记忆形象”,形成了“时间的岛屿”,让我们得以在虚空的时间之流中重现百年来的中国侨民海外拓殖史,还原中国侨乡民间生活场景。
二、文化创伤的建构与反思
有人认为20世纪的文化是“后创伤文化”,而20世纪的中国移民显然承受了更为复杂和更为沉重的苦难与创伤。杰弗里·亚历山大的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主张,文化创伤是被社会文化所中介、建构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自在事实。一个事件只能在持续的文化网络和意义解释系统中才能被经验、解释、建构为创伤,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需要反思能力和道德勇气的行为。[5]11“创伤理论”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当时研究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的学者们提出来的。西方学者已经非常成功地把文化创伤理论运用于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国学者也已经开始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反“右”运动和“文革”的文化反思。
文化创伤首先是一种强烈、深刻、难以磨灭的、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未来取向发生重大影响的痛苦记忆。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涉及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到群体认同。李小龙从美国回到香港接拍第一部电影《唐山大兄》便是很好的例证。这部电影的主人公郑潮安是由熟人带到泰国谋生的自由移民。冰厂的工友陆续被厂长和老板残酷杀害,郑潮安一人赤手空拳与泰国当地恶霸激斗,为工友们报仇雪恨。当郑潮安目睹工友们被残忍杀害的惨状之后,在河边坐了很久,可见他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到底是逃回老家还是去寻仇的两种选择中犹豫了很久。最终,郑潮安把包袱丢到水中,毅然决定复仇。李小龙在这部影片中以一敌十,凭着迅猛犀利的三脚回旋连环踢、凌空飞脚以及高亢的啸叫等极具个性魅力的武打获得了观众们的极力追捧,使这部电影创下当时香港有史以来的最高票房纪录,高达319万港元。李小龙的功夫表演使观众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与快感,但是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与狂欢式的迷狂,还是来源于对同一文化群体和族裔的认同。
文化创伤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涉及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到群体认同。这创伤的承受者可能是个体,但它必须“在群体意识上”发生作用并极大地改变了群体的身份认同。最终郑潮安选择留下来复仇是因为他在“群体意识”上产生了身份认同,工友们的苦难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难,而是群体性的苦难,他们的受难经验是整个族群的共同命运。但是,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通过个人暴力的复仇和杀戮是否能得到修复和抚慰呢?
严重的文化创伤是全人类共同的受难经验,从而对于文化创伤的反思和修复,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而不只是个别灾难承受者的事情,也不只是承受灾难的某些群体、民族或国家的事情。[10]海外移民的家眷往往留在国内,不少华侨新婚之后就远渡重洋,很少有机会回家,只有通过侨批上的文字来倾诉心中的牵挂与思念。从旅暹侨胞曾哲坤写给妻子的侨批,我们可以看出夫妻隔海相望的“忧闷”和痛苦:“久别念念,我为家庭环境困迫,亦为一家老少温饱着想,无奈抛别慈母妻儿漂流异国,许久未能欢叙一堂,心中忧闷难堪。况且此次又闻家母年老身体不快,我不能在侧侍奉,不孝可知。贤妻在家敢烦你在劳动之余代我朝夕招待家母,劳神之处有日酬谢,家务小儿亦望你代为调理培养。另者,我真对不起你,若缓唐中生活转佳亦决回国,定不敢累你代我操劳。”[7]44华侨在海外谋生,除了夫妻不能团圆,还不能享受天伦之乐。有位老华侨在侨批中给刚刚出世的孙女起名的时候抒发心中怅痛:“但恨两地远隔,含饴无从,心中甚为黯然。每观他人之子,而想及自己之儿孙,心中实有怅痛!何以造物者如此刻薄,令我抱无限痛苦而不释。”[8]418让海外华侨在精神上遭遇创伤的不仅仅是海外谋生的艰辛、妻儿隔海相望的相思,还有对于老父母的愧疚之情,这种“生不能尽养,死不能尽哀”的痛苦在林汉松的一封侨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马来亚华侨林汉松的母亲于民国二九年(1940)因病去世,他在批信中写道:“接来信内报,吾母于月之初九夜寿终,恶耗传来,五中俱碎。但上月接吾母信,云身得病,使吾甚为惊忧,想不到一病即与世长辞,此家门之不幸也。今后不能再见亲颜,为人子者,岂不悲乎?哀之父母生吾哺劳,生不能尽养,死不能尽哀,不能亲侍膝下,亲视含殓,子职有亏,罪孽深重。本想回家奔丧,皆因天涯远隔,况又身边如洗,两手空空,幸此次有颜坤、学祖叔、成声叔并亲戚诸人帮理,死生铭刻。”[8]377身居异地的高德能非常孝顺,在得知父亲逝世的消息之后“泪夺眶出,一时眼花缭乱,痛哀如焚。念兄离家三载余,爹爹病既不克在家奉侍汤药,爹爹临终弥留之时又不能亲受听遗言”[6]229,深深自责,甚至抱憾终身。事实上,这样的创伤叙事在侨批文书中比比皆是,这些文字记载的并非仅仅是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中国移民群体的创伤记忆。
事实上,中国文化最博大精深的部分不在正史官文,而是深藏于民间的野史文化,它与史官文化相对应、对立、始终互渗却又相对独立。因此,寻找中国文化记忆的根源,还需从民间文献中去挖掘;寻找华侨文化记忆的源流,也有必要从侨批这一独特而宝贵的民间文化记忆宝库中去寻找。也许只是零星、片段的记录,或是残篇尺牍,但是,这才是饱含侨民侨眷血泪的具有生命温度和文化气息的文字和图景。通过文化记忆的视角进行侨批研究,能从这“时间的岛屿”穿越历史,重现已流逝的海上贸易繁华景象,还原侨乡民间生活场景,也能够从对侨批的身份征用中呈现并反思当今中国社会的构造和倾向。作为对话的记忆具有把人类凝聚在一起的力量,群体的生命可以通过这种记忆得到恢复,摆脱孤立,逃脱百年孤独的宿命。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社会文化会为记忆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个体的记忆必然置身于这个框架,特定的记忆能否被回忆起或以什么方式被回忆起,都取决于这个框架。这个框架使得某些回忆成为“能够进行回忆的回忆”,某些则被作为“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不正确的回忆”被打入冷宫。[11]那么侨批文书中所记载的这些“文化记忆”是“能够进行回忆的回忆”还是“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呢?不同的创伤叙述往往能够建构起受害者和受众之间的不同关系。由于伤害事件的发生和对伤害事件的叙述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在伤害事件发生之时,伤害故事的大部分读者(受众)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或者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因此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5]24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从人类普遍价值的角度反思,把中国移民所受到的伤害看作对全体中国人乃至于整个人类的伤害,广大受众才能建立起对于受害者的深刻而普遍的认同,才能体验到这种伤害是对整个人类尊严的侵犯,当然也是对自己的伤害。这样的创伤叙事才能使广大公众不会把中国移民的受难者“他者化”,不会觉得它已经过去。因此,如何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把侨批创伤记忆建构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文化创伤,把中国移民的创伤建构为和每个人有关的共享的创伤,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结语
文化创伤是一种强烈、深刻、难以磨灭的,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未来取向发生重大影响的痛苦记忆。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文化创伤还指向一种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因为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有人认为移民的历史是边缘化的,移民的记忆也是边缘化的,更多的人认为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但是严歌苓显然不认同这种说法,她在《主流与边缘》一文中指出,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正是因为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流。”①参见严歌苓:《主流与边缘——〈扶桑〉序言》,大众日报2000年6月22日。同样,凝聚在侨批之中的文化记忆也是不应该被边缘化的,我们有义务承担这样的责任,直面侨民历史,反思文化创伤,传承华人移民的这份色彩浓烈的文化记忆遗产。
[1]饶宗颐.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潮学讲座[J].潮学通讯.2000(12):34.
[2]吴二持.侨批文化内涵刍论[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84-88.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7.
[4]严歌苓.扶桑[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47.
[5]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C]//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王炜中.潮汕侨批论稿[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3.
[7]王炜中.潮汕侨批档案选编(一):上册[M].汕头:潮汕历史文化中心,侨批文物馆,2011.
[8]沈建华,徐名文.侨批例话——真实的原始记录[M].香港:中国邮史出版社,2010.
[9]陈训先.论侨批的起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3):76.
[10]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2011(5):10.
[1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8-69.
Cultural 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Overseas Remittance
CAO YA-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the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s mainly applied to the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while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lso applies it to the reflec⁃tion on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ut few people got it related with the studies of Overseas Remittance.It is a new attempt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trauma theory and memory of the overseas re⁃mittance.Cultural memory is a reservoir storing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while overseas remittance file is a kind of reservoir,a folk cultural form saving overseas’living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Over⁃seas remittance describes not just their personal memory,but all Chinese immigrants’traumatic memories.Hence,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our current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to face the history and reflect cultural trauma.
cultural trauma;cultural memory;overseas remittance;memory of overseas remittance;traumatic narration
K 106
:A
:1007-6883(2015)05-0100-06
责任编辑 温优华
2015-04-03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记忆视角下的潮汕侨批文书研究”(项目编号:14YJC850002)。
曹亚明(1978-),女,湖南常德人,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