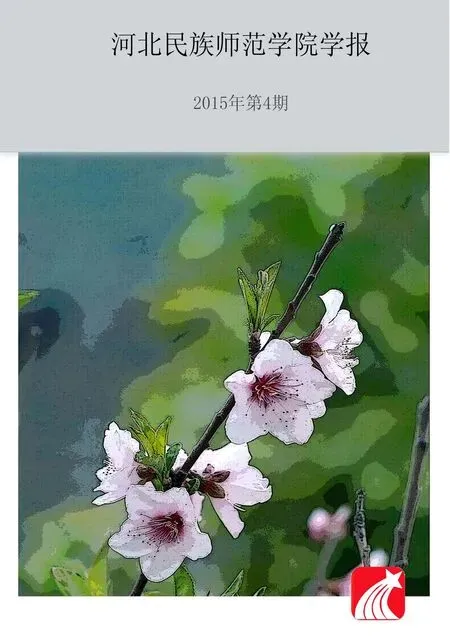生命体验的张力
——徐玉诺散文诗的梦幻抒写
李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生命体验的张力
——徐玉诺散文诗的梦幻抒写
李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现代诗人徐玉诺在现实的苦难里执着于爱与美的生命本真的追求,自觉地创作了不少散文诗著作,并在散文诗的世界里致力于梦幻的营构。其“梦幻”类作品的思想、形象与诗人的现实生存经验互涉,由此彰显了诗人生命体验的张力。
徐玉诺;散文诗;梦幻;生命体验;张力
徐玉诺(1894-1958)是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重要诗人之一,同时也是早期散文诗的开拓者之一。他的散文诗创作主要集中于20年代,其大部分散文诗作品被收入《将来之花园》。徐玉诺追求爱与美的主题,致力于建构梦幻般的理想家园,其梦幻类的散文诗著作是徐玉诺在现实的困境与理想的虚无之纠结中所呈现的生命体验的张力。诗人在生的苦闷与个人潜意识底对自由创造之欲望的张力中凸显跃进的生命力。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精神底活力具了感觉底的各样形状而出现的就是梦”,“那幻想,那梦幻,简而言之,就是藏在自己的心中的心象”。[1]本文将梦幻界定为梦境及与梦的特质相似的幻想、想象、回忆和无意识的思绪。自散文诗的引进和创作开始,有不少作者在散文诗的世界里致力于梦幻的抒写,诸如鲁迅、冰心、徐玉诺、高长虹等。鲁迅是20年代散文诗梦幻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散文诗集《野草》整体上是一部梦的著作,以《秋夜》入梦,以《一觉》出梦,遵循了梦的结构。梦幻对鲁迅而言,更多的是一种修辞策略和表现方式;而对徐玉诺来说,梦幻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更是其追求的一种生命主题、超越于现实的彼岸世界。在其梦幻般的花园中,徐玉诺建构的并不是单纯的美与爱的宇宙,同时还映射着现实的苦吟及诗人复杂的人生体验,从而生成一种生命体验的张力美。本文着重以梦幻类的散文诗为例,从梦幻的主题思想、梦幻者形象及诗人现实生存经验等方面进行思考与探讨。
一、思想的遁逸:理想的建构与现实的摧毁
身处20世纪之交的徐玉诺,深刻体会到社会制度的昏暗、兵灾匪祸的残忍,百姓的流离失所、生死无常。诗人不堪忍受现实的苦难对其生命和记忆造成的负重,试图在精神上开拓一片远离现实与苦难,只保留爱与美的生命本真的梦幻花园。他的梦幻花园是对现实的否定与超越,但又无法真正脱离现实的束缚,他的思想与生命一边幻想着乌托邦的超越,一边又受着现实与记忆的负重,两者形成张力。正如西谛在《将来之花园》卷头语中所写:“虽然在《将来之花园》里,玉诺曾闪耀着美丽的将来之梦,他也想细细心地把他心中更美丽,更新鲜,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组在上边;预备着小孩子的花园。但挽歌般的歌声,却较之朦胧梦境之希望来得响亮多了”。[2]1-2现实苦痛的隐射与生命本真的瞻望以对立统一的方式交织缠绕在梦幻花园之中。
(一)现实与幻境间的游弋
20年代的徐玉诺正处于年轻气盛之时,他满怀热血与理想,积极参与“五四”等各种爱国运动。20年代初,徐玉诺参加河南学生运动,并成为河南学生运动的学联理事。随后,河南学生运动的失败使他意识到现实的黑暗,单靠一腔热血和激励的反抗无法改变残酷的现状。至此,徐玉诺由现实的直接战斗转向文学梦的间接反抗,并于1920年以第一篇短篇小说《良心》的创作步入文坛。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社会时局的变化,徐玉诺对黑暗现实的体验愈加深入,单从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已无法寻求慰藉,唯有从梦幻世界中寻取解脱。为此,诗人在文学的世界里,一边唱着现实的挽歌,一边抒写着梦幻的甜美。
在现实与幻境的对立结构中,徐玉诺的思想经历着束缚(现实的负重)——超越(梦幻的建构)——坠落(现实的摧毁)的艰难历程。诗人在梦幻的畅游中体验着自然界的美丽、自由与纯真,但梦境过后又流露出对自然美景的依恋、对现实的厌恶。他渴望“虚幻的平安”,但又不堪忍受虚幻过后的沉痛。他幻想着“一步”踏入和谐美丽的梦幻世界,但又流露出对现实中“我总是一步一步的走着”的无奈与辛酸,如《一步》;他不堪忍受现实的负重,渴望拥有一双能够帮他挣脱现实、寻得超越的“梦中鞋”,能够在林梢、白云和微风间翔游,但又怕云过风去之后,“空留林梢思悠悠”[3]80的惆怅与孤独,如《旅客的仓山前·轻歌二首》。诗人在《现实与幻想》一篇中对现实与幻想作了形象的比喻,“现实是人类的牢笼,幻想是人类的两翼”,[2]55-56人类无论怎样挣扎,都将“脱不出牢笼”。梦幻与现实是徐玉诺思想世界的两大阵营,诗人想远离现实的牢笼,认为现实的“铁钉鞋”和“水上鞋”都无法摆脱现实的荆棘与泥泞,唯有穿上“梦中鞋”翱翔于梦幻的云间,方能获得安逸,但幻想的羽翼终归要受到现实的打击,难免遭遇梦幻坍塌的危险。弗洛伊德曾言:“梦是愿望的满足”[4]114,现实的苦闷与懊恼对徐玉诺的精神造成极大的创伤,潜意识中被压制的愿望无法在现实中获得实现。通过无意识的梦境和幻想,诗人内心欲挣脱现实的愿望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但梦终有苏醒的一天,无论梦幻建构得多么别致,在现实的炮火面前终究是昙花一现。可见,诗人的思想由现实遁入梦幻,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无解。
(二)记忆与忘却的反复
“记忆是一切痛苦罪恶丑陋等等的泉源”,[2]113现实的不幸留给诗人的多半是苦痛的记忆。为此,诗人认为没有记忆就没有苦痛,欲抛开苦痛的记忆,建构自由与美的梦幻世界。“假设我没有记忆/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3]96(《杂诗三》),诗人从记忆的层面上揭示人类止步不前的根源:人类是受着自身所创造的记忆的牵绊。
记忆对诗人而言,不单是我们所理解的回忆,更是自我的世界中因一部分受着外部世界的控制和压抑而不得释放的创伤。从而,诗人憎恶记忆,不惜认为记忆的滋味多半是苦涩的,如《记忆》;羡慕没有记忆的海鸥,认为海鸥是“宇宙间最自由不过的了”[3]89,如《海鸥》。诗人追逐着梦幻世界中无记忆的微风、小草、小鸟、蝶等美好事物,想借此获得记忆的忘却。但诗人又无法真正摆脱记忆,记忆时常化身为一些苦痛的意象潜入梦幻中,侵扰因暂时的忘却而获得的安宁。如《花园里边的岗警》中的“岗警”凝结了诗人对现实小人物苦忍的记忆,《谜》中的“我”融入了现实中诗人漂泊的记忆,《燃烧的眼泪》中的“旷野”与“坟墓”倾注了诗人对家乡兵匪灾难的记忆。此外,诗人有时又努力拾掇记忆,如对故乡、亲人及儿时童年的回忆,诗人因受了现实中回忆之苦,试图在梦幻中寻求记忆的美好。如《故乡》中构建的故乡之景,《小孩子》中的小孩子的念想,何尝不是诗人追逐的记忆。由此,诗人在记忆——忘却——记忆的循环反复中经历着梦幻的建构与消解。
二、梦幻形象的建构:向往与反抗
徐玉诺在梦幻世界的体验中主要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诗人、孩子、歌者、智者等形象;另一类是权势者、疯人、劳苦者等形象。身处战乱时代的诗人,在现实的压抑与内心的渴望中游弋。前一类形象寄托着作者对纯真、自由、理想的向往,后一类形象隐射着现实对生命灵魂的扭曲。诗人痃痖曾说过“徐玉诺是一个真的不能再真的人,他的痴与狂,来自对文学艺术的狂热、执着,对理想世界的执着。他的笑与闹,是对这变异世界、失序社会的反讽”。疯人、权势者、劳苦者的形象建构是作者对现实变异世界的反讽与控诉。这两类形象的塑造可以看作诗人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他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将自己建构成孩子、歌者等充满阳光与纯真的形象,致力于美与自由的生命本真的追求。正如他在《将来之花园》中作为孩子的代言人,为他们精心编织花园之梦;一方面又不满现实的重压,以劳苦者、疯人的角色揭露和控诉社会的黑暗。徐玉诺对形象建构的过程体现了他内心两股精神力量的形成过程,正如弗洛伊德曾言:“在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两种精神力量(亦称倾向或系统)作为梦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一种构成梦所表达的愿望,而另一种对这个梦愿望实行检查制度,由此造成梦的歪曲”。[4]135可见,孩子、歌者等形象是诗人对理想愿望的开拓与追求,疯人、劳苦者等形象是诗人对现实的防御与对抗。
徐玉诺自小生活在农村,切身感受着农村的美丽风光,同时又亲眼目睹底层人民生活的穷困与坚韧。因此诗人在他的梦幻王国里一边描绘着温馨的画面、旖旎的风光及光鲜的人物形象,一边又揭示了劳苦者的生存困境,两种画面、两类形象交织在一起,彰显张力的维度。《春天》中的“小鸟”、“花牡丹”、“小草”、“春风”、“小孩子”、“小牛”、“小孩子”与“失望的哲学家”、“倦怠的诗人”[3]87两者对立,打破了春的和谐,揭示了一切的美与平安都是虚幻的。“失望的哲学家”和“倦怠的诗人”是作者心底的写照,他执着于理想的建构,同时又困于现实的无望,从而流露出失望与倦怠的情绪。《花园里边的岗警》将牡丹、小鸟、青年男女、诗人及画家的悠闲、欢快与守园的岗警进行对照。岗警疲倦而冷枯的心境、为生计发愁的窘迫与前者的悠然闲适形成对立,梦想的美丽侵染了现实的苦痛,人类的苦味最终侵入梦幻的甜美中,由此突显人类生命的困顿与生活的坚忍。
徐玉诺曾如此感慨:“人生最好不过做梦/一个连一个的/掩盖了生命的斑点”(《小诗》),[2]11他希望在自我的世界里建构孩子、歌者等形象,远离生活的斑点,能在纯洁、本真的梦幻世界里自由歌唱,但现实的磨难、兵匪的抢掠、流离失所的苦痛又使他不得不建构疯人、劳苦者等坚韧与反抗的形象。两者的形象建构既是诗人对生命主体的观照,也是诗人现实体验的方式,两者的对立统一彰显了诗人精神的无限张力。
三、生存的体验:寻路与梦中的皈依
徐玉诺身处五四时期的动乱时代,他将近大半生都过着漂流四海的游子生活。自1923年3月开始,徐玉诺由郭绍虞介绍在福州英华书院任教,1923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兼任《思明日报》编辑,1925年5月中旬,又由厦门返回河南开封,并筹办《豫报·副刊》,1925年9月应冯友兰之邀到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任教,1926年2月辞去中州大学教职,到洛阳省立第四师范大学任教,随后七八年里又辗转于吉林毓文中学、淮阳河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信阳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山东曲阜师范学校等地任教。在此期间,徐玉诺主要从事与教学相关的工作,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有时甚至一年换三、四个地方。这种在路上的漂泊状态既是徐玉诺的现实经历,同时又是他生存体验的复现。徐玉诺的友人周作人在《寻路的人——徐玉诺君》一文中说过:“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他的似乎微笑的脸,最令我记忆,这真是永远的旅人的颜色”[5],徐玉诺的漂泊人生正是一个寻路的旅程,他的寻路生涯历经着这样一个历程:现实中寻路——梦中的寻路——梦中的皈依(生命的本真),其寻路的生命哲学由形而下的寻路和形而上的寻路两部分构成。
(一)流离与怀乡:旅人的归梦
徐玉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徐营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仅有一两间牛屋、两三间草房和几亩荒地,生活极为清苦。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徐玉诺目睹了兵、匪、地主对中原人民的迫害,目睹了战乱给家乡带来的生灵涂炭的惨状,再加上自身居无定所的漂泊经历,诗人的心中流露着对平安之“家”的渴望,对自由与美的向往,诗人在现实中无法寻得此路,只好转为梦中寻觅与建构。梦是自身愿望的满足,身处异乡的诗人受异乡之景的视觉刺激而生发怀乡的情结,于是在梦中寻找故乡的皈依。如《故乡》中,诗人由现实的雨滴声、白马奔腾的大海而引发对故乡的思念。故乡的图画已被现实之景遮蔽,唯有梦里寻觅:母牛与牛犊在小平原上沉静静地吃草的情景;“我”与小弟无言地摆弄着小石的画面;小河绕桑田,父亲耘田,“我”割草的场景……梦里的归乡是诗人思乡之愿望的实现,梦幻里温馨、宁静的意境是诗人对生命本真的理想的建构。但最后,“海水一阵阵地冲开了窗门,异乡的小孩子失掉了一切;故乡的影片一片片地都飞散在不可知的海上,渐渐地被海水湿了”。[3]109-110梦里暂时的皈依最终躲不过现实的摧毁,梦幻花园的营造仍免不了坍塌的可能性,诗人或许早已知道这一事实,才不免在现实中执着地唱着“自己的挽歌”。[2]2
“齐美尔认为,流浪者是个证人,不是参与者,他置身于路过的地方,但不属于那个地方,是一位观察者,随演出的进行而建构自身”。[6]徐玉诺漂泊的旅程也是自我建构的历程,他向往孩子般单纯、本真的生命,向往梦幻花园的自由自在,因此,诗人在旅途中,除了寻觅儿时的故乡,同时也在寻觅童年的自我。“我的步伐,是小羊在羊场上的挑浪,我们得歌唱,是小鸟在树林中流离;我们的心浪漫而且狂热”[2]86-87(《小孩子》),这是诗人生命状态的自我隐射,疏离社会,远离苦难,追寻生命本真的那份净土是诗人的愿望。诗人深知这份愿望在记忆中的童年和现实的处境中不可得,只好从梦境中寻得。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梦描绘为由向新近材料转移而改变的童年情景的替代物”,[4]510诗人由此替代物中获得心灵的皈依。
(二)由死向生:形而上的寻路
徐玉诺不仅是一位诗人、旅人,同时也是一位哲人,他的作品中时常透露着对生与思的形而上的哲思。由此层面而言,徐玉诺的寻路过程也是自我对生死的认知过程。
徐玉诺深受现实苦难的折磨,厌恶记忆,认为记忆是苦涩的稻草。因此,“他赞美倾倒记忆的幻梦,羡慕泯亡记忆的死灭,以为在这两个境界里尝到的总不是现在所尝到的苦酸的味道了”。[2]117于是,诗人在《小诗》中幻觉两小鬼立于死亡之门径时,他却感受到“死之美”。诗人在《墓地之花》中开启了与墓下死者的对话,幻想死后是“温柔安适”的,甚而以死亡作为寻路的方向:“向墓的深处走去”。[3]119-120作者在现实的战乱中深感生命不能自主,由此而构想死亡的温床,因而他所建构的死亡不是常人所认为的阴森恐怖,他笔下的死后是拥有灵魂和快乐的另一个世界,是另一种新生。
徐玉诺很早就体会过亲人的离世,如妹妹10岁的病逝,二弟徐言倬婚后病逝,1927年,大女儿雪荷的夭折,1931年,叔叔徐教海遭土匪所杀等,亲人的相继离世及战乱中百姓的流离失所加深了徐玉诺对生死的认知。诗人将生死视为辩证统一而存在,认为生命是在生可通向死、死可通往生的轨道中获得永恒。诗人在《人与鬼》中就明确指出“人生是鬼的前程,鬼是人生的前程……由死鬼到人生,由人生到死鬼;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膜——这是死鬼和人生的祖先传给他们儿子的,使鬼和人的孩子们都爱他们的生,怕他们的死”。[3]93在诗人眼里,死亡是另一种生,是一种超脱,即自我记忆的泯灭,自我与世俗生活的断裂,进入宇宙的维度以寻求超脱与安宁,这与梦幻花园中美与自由所编织的生命本真状态不谋而合。诗人在现实与梦幻中寻找着人生的路,现实中寻而不得,转为梦幻中寻觅,因梦幻坍塌的可能性而转为哲学层面的寻路,以寻求漂泊灵魂的皈依。
诗人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以“为人生”作为文学创作的宗旨,其寻路的艰难历程隐射了现实的残酷和生命的力度。诗人在现实的探寻、梦幻的营构及哲学层面的思索三维空间里求索人生,因而现实与梦幻的对立与隐射、现实与哲学层面的对照与指引,及梦幻与哲学层面的交织互涉凸显了生命体验的张力。
注释:
①痃痖:《特立独行徐玉诺》。见于《鲁山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总第2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2005:176.
[1][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北京:北新书局,1930.31-32.
[2]徐玉诺.将来之花园[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3]刘济献.徐玉诺诗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M].张燕云,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周作人.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N].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3-8-1.
[6]王淑贵.孤独徘徊的异乡人——徐玉诺的生存体验与自我建构[D].河南大学.2008:33.
The Tension O f Life Experience——Discription of Dream In Xu Yunuo's Prose Poem
LITi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Jujian,350007,China)
Modem poet Xu Yunuo was inflexible in pursuit of love and beauty of life in realistic suffering. He consciously createdmany prose poem works and was committed to creating dream in theworld of prose poem. The thought and form of his"dream"works implied the poet's real experiences,thus revealing the tension of the poet's life experience.
Xu Yunuo;prose poem;dream;life experience;tension
I206
A
2095-3763(2015)04-0084-04
2015-06-17
李婷(1990-),女,湖南永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