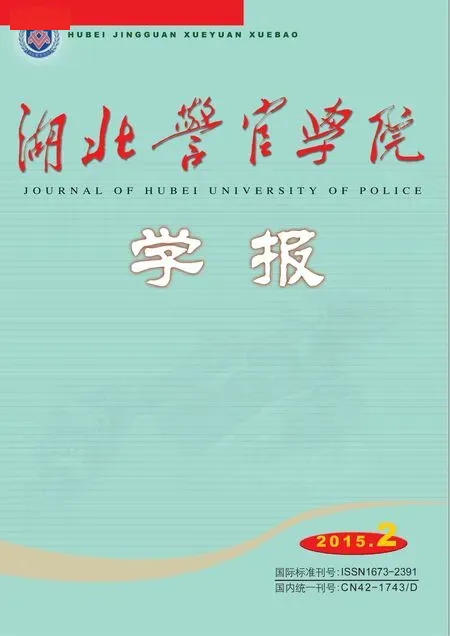美国“弗格森”事件的刑法学思考
王 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2014年8月9日黑人青年迈克·布朗被白人警官达伦·威尔逊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射杀,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但受到全世界关注的“弗格森”事件并没有“消停”的迹象,反而随着大陪审团泄密①圣路易斯县的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大陪审团成员的不当行为,在达伦·威尔逊一案中,在大陪审团做出是否对达伦·威尔逊提出有罪控告之前,有大陪审团成员私下和朋友讨论本案证据,并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对达伦·威尔逊签发逮捕令,这些都违反了大陪审团的保密原则,如果查证属实,检察官办公室必须重新选任大陪审团。The Washington Post,Grand Jury Considering The Ferguson Shooting I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Misconduc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nation/wp/2014/10/01.和9月28日警员被枪击事件②9月28号,密苏里州发生了2起警员被枪击的事件,一起发生在弗格森,另一起发生在伯克利附近。这两起枪击案和迈克·布朗被射杀案是否有联系,目前正在调查中。Ferguson Police Officer Shot,Another Fired On In Nearby Berkeley.http://mashable.com/2014/09/28/police-officer-shot-in-ferguson.的发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民众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抗议,正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质疑和愤怒无时无刻不在笼罩着这座位于密苏里州的小城。
弗格森事件给全世界提供了进行广泛讨论的素材,学者们可以从政治学角度,探讨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管理制度;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如何建立和谐的警民关系;还可以从种族关系上讨论美国是否依然存在种族歧视;等等。作为一个法律人,笔者拟从法学视角,尤其是刑法学视角思考弗格森事件给我国带来哪些启示?
一﹑刑事司法如何应对民意
根据矛盾论,矛盾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无时不在的。可能很多人觉得一提到矛盾就是件不好的事情,就像在生活中即使和某人有很小的矛盾也会给自己带来或多或少的痛苦。殊不知,在这个世界上,矛盾与我们如影随形。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感谢矛盾,是矛盾避免让我们停滞并让我们发展,而这一切听起来也是多么的矛盾。司法和民意也是一对矛盾,二者有一致的时候,也会有冲突的时候。冲突会被无限放大,人们所记住的往往只有冲突,以至于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留给一般民众的印象就是:刑事司法就是民意的天敌,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当事人都会认为是不公正的,不管法律如何规定,都应不停地申诉或者上访。这种情况所表现出的就是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严重不信任,“唐慧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③严格来讲是“唐慧女儿案”,唐慧年仅11岁的女儿乐乐(化名)被强迫卖淫,其间还被强奸,唐慧要求判处七名被告死刑立即执行,一审法院判决两名被告死刑立即执行,唐慧认为量刑过轻,不断上访,因此又被称为“上访妈妈”。2014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将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9月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两被告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989323/9155605.htm?fr=aladdin/2014/10/02.笔者认为,唐慧对此判决结果可能还会申诉或上访,“民意”也认为两被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关于此案的讨论还会持续下去。近年来,“民意”影响司法或“民意”绑架司法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某某人是被“民意”杀死的,或者某某人是被“民意”救的。①我国有着悠久的“人治”历史,“人治”传统给“民意”影响司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途径。当然,“民意”影响司法也具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在司法实践中,有因为“民意”发现错案、纠正错案的积极例子,也有司法屈从于“民意”被“民意”绑架而丧失司法独立性的消极案例。媒体上常见这样的报道:某人虐待自己的孩子,孩子被虐待受伤的照片放在互联网上。此类案子,若情节严重,就是个简单的虐待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即可。法院仅仅这样做的话,“民意”肯定是不同意的,从网民的评论就可以窥见一斑:这样的人直接拉出去枪毙、千刀万剐;不判死刑,民愤难平;如此等等。语言是如此的血腥和暴力,令人心惊肉跳。殊不知,虐待罪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重罪,而且虐待罪更是个自诉罪名,不告不理。当然,如果虐待罪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另当别论。谴责罪恶无可厚非,但用更暴力来应对暴力、用更血腥来对付血腥,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永远都走不出暴力的怪圈,一个崇尚暴力的民族是令人可怕的民族。我们也会看到相关的报道:某不肖儿子,横行乡里、不务正业,而且对年迈父母经常是非打即骂,父母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杀死了恶子(这里排除父母正当防卫的情况)。按照刑法,父母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无疑,但在量刑时,如果对父母判处重刑,“民意”也是不同意的,整个村的父老乡亲都会联名上书,希望法院不判刑或轻判。此种情况下,法院一般都会为了顺应民情、民意轻判或定罪不量刑,“民意”又一次绑架了司法。
(一)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
现代司法,从它创立之初骨子里就流淌着民主的血液,我们应采取措施保证司法的民主性。一般来说,立法机关对法官的任免和监督、媒体对审判的报道和监督、陪审团制度的建立、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和表决等都是司法民主在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表现。当然,听取“民意”也是司法民主特别是刑事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但是,在贯彻司法民主时,我们一定要避免两个极端:(1)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对立论。这种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是完全的独立,提倡司法独立就不能要司法民主,民主是对司法独立的破坏,司法是法律职业人员的事情,和圈外人没有任何关系,绝不允许“外人”来干涉,任何对司法的监督都是不必要的,不论这种监督和制约是通过何种形式进行的。笔者反对这种观点。不可否认,审判独立和职业化是司法独立的重要原则,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完美的,审判独立和职业化也是一样,司法民主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一种补强机制,就是为了弥补司法职业化可能存在的缺陷。(2)民粹主义。②民粹主义是在俄国和欧洲兴起的一种左派政治思潮,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来源。它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烈的改革,并把普通群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民粹主义强调所谓极端民主,提倡群众运动。很显然,民粹主义和司法职业化、审判独立是格格不入的。民粹主义在司法领域的表现就是片面强调“民意”的重要性,衡量司法判决公正与否、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顺应民意,是否有民愤和民怨。如果人们群众不满意、有意见,案子就要重审,就应该改判。
(二)“民意”与司法民主
一般认为,听取“民意”是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但何谓“民意”、如何听取“民意”、“民意”如何影响司法,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何谓“民意”?从字面意思看,“民意”就是人民的意志,但此概念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很难准确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何谓“民”?是指全体人民还是人民的大多数,美国“弗格森”事件中,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能代表“民”吗?在网络上针对某一案件发表评论的网民能代表“民”吗?“唐慧案”中的一些媒体能代表“民”吗?③如果在“唐慧案”中,一些支持唐慧的媒体、律师或者一般民众可以代表民意,笔者想问的是,那些不支持唐慧的民众,特别是7名被告人的亲属,他们正“模仿”唐慧积极地申诉和上访,他们的意见是否也是“民意”,在出现两种或多种“民意”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要听取哪种“民意”呢?这些都是没有定论的问题。笔者认为,“民意”有以下特点:(1)易变性。“民意”就像孩子,总是喜欢变来变去,根本就不存在固定的“民意”。司法是不是也要随着“民意”变来变去呢?(2)易受引导性。口口相传和媒体是我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事实经过以上两种途径的过滤,再加上某些人或某些媒体为了某种目的会有意夸大或隐瞒事实,最后呈现在民众面前的事实可能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民意”并不可靠,根据“民意”做出司法判决是不可靠的。
如何听取“民意”?在美国弗格森事件中,两个月来,“民意”可谓是汹涌澎湃④“民意”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司法部长赴弗格森处理骚乱,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表示“弗格森”事件显示了执法部门和民众之间的不信任,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将召集一个有40位市长和30位警长参加的论坛,专门讨论种族关系和社区警务,更重要的是,“弗格森”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民众的主要诉求就是要逮捕白人警官达伦·威尔逊并对其定罪。但美国司法部门并没有立即按照“民意”行事,把达伦·威尔逊逮捕、定罪,审理此案的大陪审团可能到2015年的1月7号才会决定是否对达伦·威尔逊提出有罪指控。可见,一切都在法制和法治的框架内进行,“民意”的影响止步于独立的司法审判。我们在西方的政治选举中经常听到“民意调查”这个词,如前所述,“民意”具有易变性和易受引导性,因此“民意”并不可靠,但也要承认“民意”的相对可靠性,就像在哲学中,不但要承认绝对的运动,也有承认相对的静止。但问题是影响司法的所谓“民意”经过实证性的“调查”了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可能有人会问,你上文所举的“父母杀逆子”的案例中,全村男女老少联名要求法院轻判难道不是一种“民意调查”吗?对此,笔者想问的是,这种“民意调查”范围够广吗?这种“民意”具有代表性吗?
行文至此,笔者想提出一个问题,在我国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民意”如何发挥作用才是合理的、合法的?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种途径:(1)代议机关。①由于国情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的代议机关是不同的,例如,在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而西方国家主要是议会。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名称的不同,其更有实质内容的区别。代议制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每个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议员都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传达选民的诉求,同时要受选民监督,选民在必要时可以罢免代表。当然,代表也就有义务传达选民有关刑事审判的“民意”。人民法院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是我国宪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但要杜绝“个案监督”,不宜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进行评价,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应体现在工作监督和对法官的任免上,根据政治功能理论的“让渡尊重”原则,②“让渡尊重”原则是指权力在各个主体之间被分配以后就具有了界限,各个主体要尊重其它主体正当的权力行使,避免对其它主体行使权力的不正当干涉,“让渡尊重”原则是一种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原则。现代社会,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分立是一种常态,“让渡尊重”原则要求这三种权力相互尊重,不可越权。“让渡尊重”原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的蒋惠岭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杨奕在“司法民主的界限和禁忌”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人大的监督应止步于具体的诉讼程序,同样,“民意”也要止步于具体的诉讼程序。立法机关在听取“民意”的基础上立新法、修改或废除旧法,司法机关根据新的法律审判案件,“民意”通过这种合理、合法的途径影响司法。比如,“民意”对“盗窃罪”保留死刑不认同,③我国以前在刑法中对“盗窃罪”还保留有死刑,主要针对以下两种情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后来《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盗窃罪”的死刑。选民就可向自己的代表反映意见,人大代表就可通过正常的程序提出关于此罪名的修改提案,立法机关通过新的刑法修正案废除“盗窃罪”的死刑,以后的审判机关对“盗窃罪”的量刑就不会再出现死刑。当然,我们也要贯彻“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保持刑事判决的稳定性。可见,“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是通过立法实现的。(2)陪审制度。④陪审制度为民众参与司法、保障司法民主的重要途径,受到很多国家的推崇。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较完善,陪审团参与案件的审理已经常态化,陪审团只对定罪与否作出决定,量刑则交给法官。我国的陪审制度虽然已经法制化,但起步较晚,很多案件没有陪审员的参与,即使有陪审员的参与也是过于形式化,很多陪审员只是陪而不审,一味地依附于法官,丧失了陪审员的独立性,和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陪审员对定罪和量刑都要参与。陪审员很多都是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民众,他们在案件受理中以一种“普通人的、世俗的角度”看待问题,和法官相比,陪审员不具有高度的职业化特征,但陪审员是可以“接地气”的,陪审员来自于民众,他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民意”,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的意见也是“民意”的一部分,因此,在陪审员做出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意”的影响,⑤当年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就是“民意”影响陪审团决定的极好例子。因为辛普森是深受黑人和少数族裔喜欢的橄榄球明星,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希望挑选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的白人女性作陪审员,而辩护方律师则希望挑选文化程度低、喜欢橄榄球的黑人或少数族裔男性作陪审员。双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诉求呢?因为不同的群体代表不同的“民意”,而不同的“民意”针对此案会有不同的观点,前者倾向于辛普森有罪,后者则倾向于辛普森是无辜的。结果是刑事诉讼的陪审团主要由黑人组成,辛普森被判无罪,而后来的民事诉讼的陪审员主要是白人,辛普森被判对死者的死亡负责并支付巨额赔偿。正如《陪审团制度》一书的作者Jeffrey Abramson教授所说:“此案刑、民事诉讼中所有的区别均因两个诉讼中陪审团的黑白分明的人种组成而逊色。两个陪审团,两个社会,两部正义的法典。”“民意”通过这种方式又一次影响刑事司法。
“民意”影响司法只应通过以上两种途径进行,通过“民意”沟通渠道对法院施加压力,造成法官为迎合“民意”而不惜曲解法律,这是不允许的,“民意”或司法民主必须要有界限和禁忌。
二、刑法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发生在弗格森的骚乱也是一场群体性事件,在骚乱过程中发生了打、砸、抢、烧等暴力性活动,警察逮捕了一些骚乱者。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我国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发生。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说,弗格森事件反映了警民之间存在信任的鸿沟。笔者认为,警民之间不信任感的消除、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并不是靠刑法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那么,刑法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如何发挥作用呢?笔者把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分为常规性应对和非常规性应对。
(一)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常规性应对
刑法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面对群体性事件,刑法主要应发挥保护社会的作用,因为群体性事件是没有合法性依据的规模性聚集,而且在群体性事件中经常会伴有打、砸、抢、烧、故意伤害等暴力性犯罪活动,针对这些情况,刑法要果断地处置,按照相应的条款进行定罪和量刑,决不能手软,这些可以看作是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常规性应对。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常规性应对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方式,在群体性事件规模不断扩大、暴力性不断增强、破坏性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常规性应对日益显得力不从心。①笔者不准备从“治标”和“治本”的角度来论述刑法的常规性应对的局限性,因为刑法作为一种手段无法承担起“治本”的重任,群体性事件首先是一个社会性问题,然后才是个法学问题,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所以要彻底解决群体性事件问题,还是要依靠良好的社会政策。刑法的常规性应对针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活动定罪量刑,具有单一性和分散性,仅仅是一种事后处置,无法从总体上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把握和处置,更无法适应群体性事件的最新发展。
(二)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非常规性应对
由于群体性事件的暴力性在不断增强,对无辜群众的人身和财产的威胁也在不断扩大,而刑法常规性应对有其局限性,不足以解决群体性事件。基于此,笔者建议,对严重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亚恐怖主义化。②亚恐怖主义是笔者借鉴亚文化、亚健康等概念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某种犯罪、事件或运动从表面上或传统上看并不完全符合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但从危害性上或从对恐怖主义犯罪概念发展的角度看,把其归入恐怖主义犯罪范畴是合适的,而且对其采取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措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美国一直以来对国内的暴力性群体性事件都采取强硬对策,而且拒绝其它国家的干涉,③针对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指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表示:“美国的情况与其它国家没有可比性,人们有权说出他们想说的,也有权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进行讨论,但我也有权不同意他们进行的此类比较。”参见http://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40821/18727008.html.从中可以看出亚恐怖主义化的端倪。
一般认为,恐怖主义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为了一定的政治或社会目的;第二,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手段;第三,袭击目标具有随意性。严重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与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特点相吻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重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有一定的政治或社会诉求,在弗格森事件中,参与者的直接诉求就是将白人警官达伦·威尔逊逮捕并定罪,其深层次的诉求是加强对黑人的保护、提升黑人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应该得到支持,因为,目的是中立的,我们不能根据目的来判断对错,即使像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ISIS,其目的是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其目的是邪恶的,这还要看手段和受害者。其次,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我国,严重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都会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打、砸、抢、烧、伤害充斥其中,对人身和财产造成极大伤害。最后,严重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都会从和平的诉求演变成对无辜民众和财产的暴力,烧毁警车、抢劫店铺、袭击警察和无辜群众等。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减、变化,恐怖主义犯罪也是一样,我们决不能坚守一成不变的恐怖主义犯罪类型,严重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具有恐怖主义的特质,它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并不亚于传统类型的恐怖主义犯罪,因此,把严重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亚恐怖主义化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它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