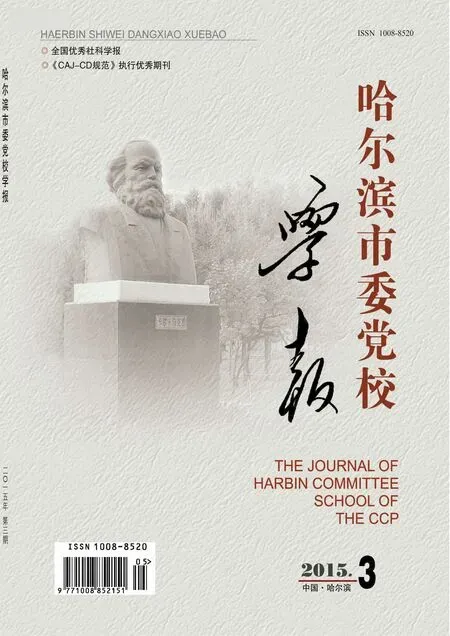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宫丽艳,宫力平
(1.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22;2.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150040)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类开启了大规模作用于自然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主客体的二元存在论,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人类认为自己比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具有更高的价值,产生了主宰自然、支配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的实践活动将自身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变得疏离和对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显。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物质生存,也威胁到精神生存,人类的发展陷入了双重困境。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全世界人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类社会必将由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走向更高阶段。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五位一体”的战略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提出通过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蕴含着极高的德性要求,不但需要物质形态的支撑,也需要精神形态的推动。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实然状况和应然理念的理论探讨。从古代圣贤哲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中汲取营养,构建当代生态伦理体系,民众更容易在文化心理上产生认同感,更容易将生态伦理观念转变为生态道德意识,进而付诸于生态实践。
一、继承“天人合一”思想,建立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观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观念的基本出发点。“天人合一”思想起源甚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周易》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说卦传》)《周易》通过人道看天道,参照天道看人道,阐述了天地人“三才”理论,体现的正是“天人合一”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周易·乾卦》),阐述圣人君子之德,与天地相契合,与自然相适应,表达的也是“天人合一”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自然界客观存在,人与自然相统一,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1]。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尽心而知性,人性以天为本,所以天人是合一的。“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人与万物一体,人性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荀子也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人是万物的一部分,天地人“三才”相统一,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共生。汉代董仲舒依据阴阳五行理论提出“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人类同,可以相感相动。他指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他看来,天、地、人三者是合而为一的,“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北宋哲学家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的本性是一致的,天之实理与性之良能共处共存,故天人合一[2]。宋代程颐认为:“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在儒家圣贤哲人看来,“天”既具有精神属性,也具有物质属性,“天”既是主宰之天、义理之天,也是自然之天,人与“天”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浑然一体,人是“天”的一部分,是统一的共存关系。
道家也主张“天人合一”,以道为基础强调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其中的“道”指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指万物运行的规律,而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天地万物共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同生于道,万物同源。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庄子·秋水》)他指出人不是自然的主人,和其他事物一样,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佛教认为“万物一体”,即一切现象都是相互依存的,都有因果关系,世间万事万物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因缘和合的角度,阐述了生命主体与自然之间相互联系的因缘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二者相互依存。佛家还提出了“依正不二”原理,即正报(生命主体)与依报(所处环境)同为一个整体。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界是万物的本源,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继承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利于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建立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观。工业文明下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使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我们应吸取过去的教训,转变过去以人类为中心、将人的主体性理解为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观念,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二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悖、对抗的关系。要坚持“人——自然”有机整体的观点,明确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性方面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对待自然,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3]。我们还应积极发展生态经济,将人类的经济系统纳入生态系统,使科学技术成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修复生态系统的有利助手,而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把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耗能、低污染、高产出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二者的和谐共生。
二、学习“仁者爱物”的思想,建立关爱自然的生态观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爱的对象不仅是人,还有天地万物。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孔子指出君子热爱自然,对自然山水充满崇敬之意。孟子则将仁爱的主张应用于自然界,不但对人,对天下万物也持仁爱的态度。他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仁爱之心由亲人扩大到他人,由他人扩大到万物。“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在这里,“不忍见其死”、“不忍食其肉”所体现的正是儒家对其他生物的仁爱之心、关怀之情。汉代董仲舒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矣谓仁?”(《春秋繁露·仁义》)不仅以仁爱之心对人,也要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对自然进行伦理关怀,爱护天地万物。宋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强调人应该具有仁爱之心,博爱济众,维护天地万物。他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即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天地是我父母,百姓是我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必须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明代王阳明则进一步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可以看出,儒家仁爱的对象是天地万物,要实现“仁”,就要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主张自然界的万物无贵贱之分,人类不能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平等,人不是自然的主宰,应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人不仅应该珍惜爱护自己的生命,也要爱护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命。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从道作为万物产生的本原来看,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具有平等的价值,不但人类具有价值,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同样具有价值。列子指出“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列子·说符》),强调物无贵贱,人与万物同源。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小到尘埃,大到宇宙,所有生命都是有佛性的,皆不可伤害。因此,佛教提出“不杀生”、“素食”等一系列道德信条,强调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善待万物、关爱众生[4]。佛教教导人们对所有生物都要有“爱”或“慈悲”之心,甚至要牺牲人类自己的利益,庇护自然万物。
中国传统文化将人类的道德情感引入了自然界,认为自然万物都有其生存的权利,不可违背自然生物的本性,剥夺他们的生长自由,对自然万物充满仁爱之情。学习传统的“仁者爱物”思想,有利于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建立关爱自然的生态观。我们应加强对民众仁爱万物和生命情怀的教育,使民众形成生态道德意识,认识到自然界的生物都有其存在的权利,而人类没有权利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进而将这种生态意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尊重一切生命的内在价值,对自然界的万物保持仁爱之心,施以伦理关怀,爱护自然,保护万物,善待生命,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肆意地伐生、杀生,不过分干涉非人类世界。要通过生态道德教育,使民众承担起关爱自然的道德责任,自觉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不再做大自然的掠夺者,而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如保护野生动物,维持物种的存在;保护森林植被,大量植树造林,禁止乱砍滥伐;保护土地资源,防治土地沙化、盐碱化,分类回收垃圾,对可利用垃圾进行再利用,对不可利用垃圾进行妥善处理;保护水资源,严格管控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保护空气资源,严格管控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排放;等等。
三、提倡“道法自然”的思想,建立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观
道家思想以“道”为核心,崇尚自然。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意思是说,事物运行要以自然为纲,效仿自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只有遵循自然的法则,不任意“妄为”、“乱为”,人类才不会同万物产生抵触,也才有可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老子认为“道”之所以受尊崇,“德”之所以被重视,就在于“道”对万物不加干涉,“德”对万物不加以主宰,使万事万物自然发展或成长。老子主张遵循自然法则,“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老子还指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十六章)。也就是说,自然万物有各自的生长发育规律。只有“知常”,即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才能维护大自然的良性循环。庄子进一步指出,“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庄子·渔父》),“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即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不遵循它就会死亡或失败。因此,万事万物都要遵循贯通宇宙的道,遵循贯通天地的德。庄子讲:“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庄子·至乐》)要按鸟的习性来养鸟,遵循自然法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提出遵循自然的准则,一切任其自然,不随意按照人的意志进行改变,不任意妄为,人为地破坏自然。
儒家也重视自然规律,主张按自然法则行事。《周易》载:“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自然界有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规律。“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天下万物各有其运行规律,能够和谐共生,不相冲突。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自然界有其运行变化的客观规律,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守自然界的根本法则。荀子又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即人们可以按照客观规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有其治”,与天地相配合。佛教从因果关系角度来讲自然规律,“如来出现若不出现,法性常住”(《稻秆经》),不管释迦牟尼佛是否出现,自然规律是一直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自然规律,且不能违背。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应效法自然,敬畏自然,将天地之道作为活动的最高准则。弘扬中国传统的“道法自然”思想,有利于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建立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观。自然规律有其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违背自然规律必将自食其果,人类征服自然的每一次的尝试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我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必须遵守自然规律,顺应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选择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遵守自然规律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我们要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少干预自然界的客观进程,不能以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老路。我们应建立和谐的经济运行模式,在利用知识和技术开采、加工自然资源,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要以自然规律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要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对自然进行的改造要在其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人在自然面前,可以发挥能动性和主动性,但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否则就会动摇人类的生存基础。
四、借鉴“取物有节”的思想,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儒家提出了“用之有节”、“取之有时”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主张节约简朴,适度消费,爱惜自然资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即不用渔网捕鱼,不射杀已归巢的鸟,不使用灭绝性的工具,取物而不尽物。孔子指出“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反对过度采伐、滥捕动物。孔子的弟子曾子也提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孟子讲:“牛山之木尝美矣,以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粟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灌灌也。人见其灌灌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如果毫无节制地使用资源,不加以保护,就会造成生态的破坏,难以恢复。孟子又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把编织得致密的渔网放入洿池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完。持刀斧的樵夫如果按照时序进入山林采伐,木材也会用不完。遵循万物的生长规律,取物以顺时,取物而不尽物,就可以实现动植物的永续利用。荀子也认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荀子指出利用森林资源、动物资源、农业资源等自然资源时,不应违背动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取物而不尽物,“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荀子·富国》)。荀子提出既要节约用度,不过分消耗资源,又要充分利用资源,这样就能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
道家崇尚简朴的生活,认为贪念不但有可能使人丧失生命,还会败坏社会的风气,主张节俭、少私寡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四十六章)老子认为人们如果贪得无厌,不知节制,就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老子的人生原则是“知足常乐”,即“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他指出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这样人们就可以保持长久的平安。庄子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庄子·刻意》)庄子也认为不存贪念,保持平易恬淡之心,则忧患不能进入内心,邪气不能侵袭。佛教认为猪马牛羊、花草树木、山川河流等自然万物都有其内在价值,主张珍惜节俭,不能挥霍浪费。在日常饮食中,也强调“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即思量粒米维艰,来处不易。佛教要求信徒不起贪念,不憎粗砺,珍惜并合理利用万物。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之本,要求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取予有度,珍惜节约。借鉴中国传统的“取物有节”思想,有利于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来对待,要充分认识到其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任何形式的生产和消费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因追求奢华生活而大肆破坏自然,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我们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不仅关注短期利益,更要重视长远利益,避免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使自然资源既得到合理利用,又得到有效保护。只有坚持适度原则,合理利用并珍惜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才能维持人和自然的平衡。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反对乱垦、乱用土地;合理利用水资源,加强对水利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反对乱砍滥伐;合理利用矿产资源,采用先进技术开采;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保护珍稀物种;等等。只有实现取物有节,不浪费使用自然资源,才有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也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中国古代圣贤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审视和考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未知的客观世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天人合一、善待自然、道法自然、简朴节约等丰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虽然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难以用其直接解决工业文明时代所造成的资源匮乏、环境破坏、生态退化等诸多问题,但其倾向于以人文主义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道德情怀、德性之知,注重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他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知灼见,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愈发彰显穿越时代的生命力和活力。从时代的价值维度,创造性地诠释和汲取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能够为当代生态伦理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1]袁梅.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育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3).
[2]李宗桂.生态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J].哲学动态,2012,(6).
[3]严耕,等.生态文明理论构建与文化资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4.
[4]周光迅,等.中国古代哲学的生态思想及其对构建现代生态哲学的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