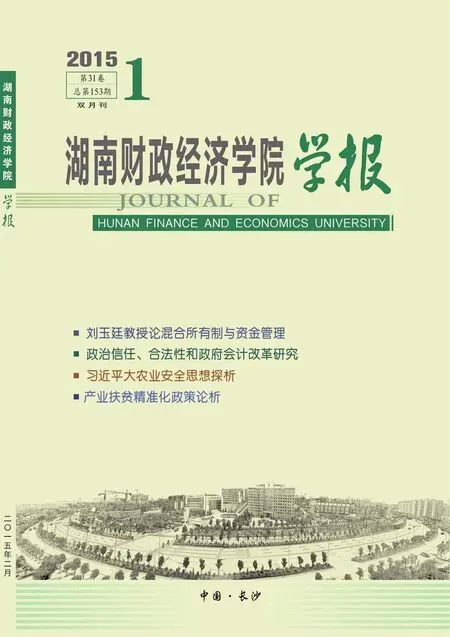《乌宝传》揭露元楮币“外若方正,内实垢污”的思想
沈端民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公元1329-1412年)在《南村辍耕录》所记载的高明(字则诚,浙江瑞安人,[元]至正五年即公元1345年进士)创作的《乌宝传》,是一篇用拟人手法撰写的传记文学作品。乌宝者,元代流通的主币──楮币(又谓元钞、宝钞等)也。作者假托为“乌宝”立传而“以文为戏”,猛烈抨击元代的钞法。该文对元代以货币滥行为标志的堕落世风的严厉针砭,或称类似[西晋]鲁褒的《钱神论》,颇为流行[1]。谢应芳(公元1296-1392年)《邀高则诚郊居小集》说:“逢人为说乌宝传,此客合贮黄金台。”[2]“逢人为说”,足见《乌宝传》流传之广泛之深远了。《乌宝传》为何如此广泛而深远地流传于世间呢?因为它对元钞丑恶本质的揭露非常深刻,极大地引起了憎恶元钞的广大民众的强烈共鸣。最犀利的一笔莫过于骂乌宝“外若方正,内实垢污”一句。“内实”,指其内在的本质;“垢污”,指藏纳于内质的肮脏丑恶的东西。乌宝的“内实”藏纳了哪些“垢污”?笔者将其概括为“五性”并做具体剖析。
一、生平经世的投机性
生物体是有生命的,其出生却不由自己,而决定于其前辈。但无生命的非生物体的出现,虽然也有其规律性,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是由人们根据其需要而制造的。“然则宝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乌宝传》所描写的乌宝是人们根据社会商品交换的需要而择“时”推出的一种可以交换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商品。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轨迹,是事物新兴与灭亡、昌盛与衰败的历史的具体记录。任何事物的新兴和昌盛都有一定的“时”机性。“时”机不可失,失去不再来。“时机”是具有顺序性、持续性的“时”中的一个“机”会,是“时”中的一个“分子”或“细胞”。某个事物要在无限延长的“时”间概念中获得一个生成、发展的良“机”,几率很小,很难准确把握,必须精心选择。大凡选择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对或错,常是对的少错的多,要冒风险。选“择”时机正确与否,结果完全相反,顺“时机”者昌,逆“时机”者亡。择“时”者,人们为了生成和发展某个事物以达到某种目的而断然选“择”的最好“时”节(机)。对“时机”的这种抉“择”本身就带有很大的投机性。乌宝很会投“机”,也很幸运,准确抓住了“顺”之而生的最好“时机”,非常“昌”盛起来了。
作者在约546 字的短文《乌宝传》中不惜浓墨反复描述了乌宝的历史渊源:乌宝的祖源有三条支流。一是乌氏,曰“乌氏见于《春秋》、《世本》”,“皆为显仕”。二是钱氏,曰“宝之先有钱氏者”,“迨宝出,而钱氏遂废”。三是楮氏,曰“其先出于会稽楮氏”。
由此可见,乌宝出现前后的历史状况及其变化是非常复杂的。
乌氏家族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曾经“显”赫数世,举为名“仕”。但世间没有永不凋谢的花朵。乌氏“显”赫数世之后败落了,消退了。“至唐,承恩重,胤(按,后代)始盛”。这就是“飞钱”乘机问世的历史背景。“飞钱”是用纸写的汇兑凭证。唐代中期(唐宪宗年间),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持此凭证者可在异地提款购货。
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记载,宋代出现了“川界用铁钱”太重而使人“难以携持”[3]的弊病。“飞钱”借其机摇身一变而为“交子”和“会子”,并广泛行之于世。史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4]
到了元代,元朝统治者为了满足扩张领域战争之需要,要求军伍携带的货币轻巧易藏,于是元钞楮币应运而生了。元钞又借朝廷禁止铜钱流通(即使“钱氏遂废”)的敕令而一跃到了主币的崇高位置,并充斥市场,左右着市场的交换活动。
乌宝随着历史和现实市场的变化之“机”而应变之。曰“至宝,厌祖、父业,变姓名,从墨氏游,尽得其通神之术”,“宝裔本楮氏,而自谓乌氏”。
这里讲述了乌宝从祖“先”及其后“裔”在历史变化中蜕变的几个具有个性特征的变化情节:宝本于三氏,即乌氏、钱氏、楮氏,后“从墨氏游”而改姓,“自谓乌氏”。人们“知与不知,咸谓之乌宝云”。
这些个性情节的变化充分表现了乌宝背叛祖先,“素趋势利”、投靠市侩等恶劣的投“机”行为。
乌宝为了获利,什么“下贱”之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封建社会以“孝“治天下,而乌宝公然“厌(弃)祖、父业”并改“变姓名”等,其行为是当时人们深恶痛绝的大不孝。至于趋炎附势,背叛“世尚儒”的信仰和老传统而跟“从”有所谓“通神之术”的“墨氏游”等行径,更是“尤甚”的“害道伤化”的罪恶,更不为人所齿。
作者经过匠心独运的编织,不仅无情地揭露了乌宝数典忘祖、忘恩负义而“遂废”钱氏的可耻行为,而且巧妙地将具有悠久家族历史的乌氏和经世不久的楮氏合二为一了,并使其心甘情愿地“自谓乌氏”之“宝”,简谓“乌宝”。作者的这种艺术穿凿使乌宝的生平经世充满了投机性,或者说,作者以其犀利之刀笔的刻画使乌宝投机的嘴脸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个性品格的曲随性
乌宝以投机而问世,又以投机而处世,浑身充满了投机性。这种投机性锻造了他“曲随”的个性与品格。“曲随”的具体表现,《乌宝传》从三个层面做了揭示:
1、“轻薄柔默”
其体态“轻”巧、单“薄”、“柔”软,常缄默不语,城府很深。一个“柔”字,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其顺从人意、投人所好的谄媚形象。
2、“善随时舒卷”
有“舒”有“卷”,随人随时而“舒卷”自如,极力称人之心如人之意。一个“善”字,说明他遂心于人的“舒卷”技巧非常娴熟。
3、“曲随人所求”
曰“凡有谋于宝,小大轻重,多寡精粗,无不曲随人所求”。宝之待人可谓尽心尽意,热情周到。无论“大小轻重”之事,也无论“多寡精粗”之活,有求必应,应必满意。在其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的字典里找不到“原则”二字。在“无不曲随人所求”中的“曲随”一词,极大的丰富和具体化了“柔”、“善”二字的意蕴,并把其行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地。
乌宝的曲随个性与品格有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基础,颇受人众的欢迎。《乌宝传》曰“凡达官势人,无不愿交。”又曰“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作者选用“无不”、“莫不”二词,足见人们与之相交,对其敬爱的程度之深之广。
《乌宝传》还用两个具体事例形象地描写了人们“无不愿交”和“莫不敬爱”的情景。一例从名人的角度表现:“是时,昆仑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从革生,皆能济人,与世俯仰,曲随人意,而三人者亦愿与宝交,苟得宝一往,则三人亦无不可致,故时誉咸归于宝焉。”此三人“皆能济人,与世仰俯”,虽在“曲随人意”方面手段高明,表演出众,但都不及乌宝,是乌宝的徒弟下手。“故时誉咸归于宝焉”,当时人们把对三位曲随性的称“誉”都“归(功)于”乌宝之教。换言之,乌宝堪为“曲随性”之最。另一例从普通家庭的角度揭示:“人争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则老稚婢隶,无不忻悦,且重扃邃宇,敬事保爱,惟恐其它适也。”一个“争”字,毕现了“老稚婢隶”“迎取邀致”而“无不忻悦”的热烈场面。
以上两例都突出了人们对乌宝的“敬爱”,从侧面衬托了乌宝“曲随”性的个性品格的强烈社会效果。
三、社会流通的腐蚀性
古人谓钱为“泉”。泉水的本性是流动,货币的本性是流通。流动的泉水既滋润着万物的生长,也侵蚀着万物的机体。任何物质长期浸泡在水中就会变质、腐烂。具有泉水特性的货币也如此,既带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加快人际交往的频率,促进社会发展的速度,也对社会和人类产生着严重的腐蚀性,它可以使沉溺于钱中的人和社会腐化、堕落、衰败。
《乌宝传》曰:“宝好逸恶劳,爱俭素,疾华侈。”“好逸恶劳”的具体表现是“疾俭素,爱华侈”。因此,原文中的“爱”与“疾”的位置是搞错了的。错位的原因可能是陶宗仪“记”忆上的问题。《南村辍耕录·乌宝传·序》曰“余幼时,尝见胡石塘先生《玄宝传》,今不能记其全篇。有人出永嘉高则诚明《乌宝传》相示。”[1]陶宗仪对《玄宝传》不能“记其全篇”,当然也难“记”准《乌宝传》“全篇”。记不准确,再现起来,错误在所难免。“有人”“相示”的《乌宝传》也可能是传抄本,传抄出错,屡见不鲜。现从逻辑上把搞错了位置的两个字更正过来有利于正确理解原文的真意。乌宝“好逸恶劳,疾俭素,爱华侈”的特性像腐蚀性极大的硫酸,泼洒在人身上,就会把人烧伤,甚至烧死。
1、达官势人触之“皆不利败事”
曰“凡达官势人,无不愿交,而率皆不利败事。”“败事”,腐败衰颓之事。“不利败事”,“不利”于改变其腐“败(之)事”;或皆使自己处于“不利”状态而堕落于腐“败”祸“事”之泥潭。凡笃“愿”与乌宝相“交”者,一个个都沾上了腐败的祸水,日渐侵入心骨,不可收拾。
又曰“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其子姓蕃衍,散处郡国者,皆官给庐舍而加守护焉。”“自公卿以下”的大小官吏“莫不敬爱”乌宝,实际上是都受到了乌宝的腐蚀。他们像吸毒品一样,越吸越想吸,希望得到更多的乌宝腐蚀。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争迎取邀致”,千方百计地巴结其迅速繁殖的子孙。他们对“苟得至其家”的乌宝及其子孙倍加呵护,“皆官给庐舍而加守护焉”。即把所得到的乌宝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保管好,希望他能沁入肺腑。于是乎,许多官吏都被钱迷住了心窍,被钱浸泡得骨髓发臭心黑烂,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2、挟诈者售之“后皆败死”
曰“自宝之术行,挟诈者往往伪为宝术以售于时,后皆败死。”诚然,乌宝作为货币的代称,是被人利用的工具。人们常常利用它从事正常的经济交换活动。乌宝也竭诚为这种活动服务。乌宝既有生存发展的本领,又有反抗破坏它生存发展的本能。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某些行“诈”者,常常“伪”称自己用的是乌“宝之术”,从而兜售其奸。行“诈”者严重违背货币的初衷,肆意破坏货币自身的客观规律,因而引起了货币乌宝的强烈反抗。假的就是假的,应当剥去“伪”装。乌宝对玩弄他的“挟诈者”毫不客气,借用毒蛇反咬一口之法以吐射毒液,严重腐蚀其血液,使其“皆败死”。
3、流俗自得而“多惑之”
曰“常自得圣人一贯之道,故无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这是讲乌宝腐蚀一般黎众的情况。货币能无翼而飞,无足而行,能神奇地流通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渗入人的每一个毛孔。货币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者”(马克思语),任何人只要按一定的程序即“圣人一贯之道”,都可以“自得”一定数量的货币。但由于人们对货币的利用各有不同,或成营养,或成致疾的病菌。“流俗”者与“达官势人”一样,也“无不愿交”乌宝,也无不“敬爱”乌宝。因此,凡“宝之所在,人争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则老稚婢隶,无不忻悦”。此句可谓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流俗”者对货币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情景。“流俗多惑之”的“惑”字是形声字,其“心”已经被重重地压到了最底层,说明“流俗”者被深沉地困“惑”、迷“惑”在货币的污泥浊水之中,不仅骨肉被腐蚀得荡然无存,而且“心”也被腐蚀透彻了。句中用一个“多”字概括数量,说明钱对黎众的腐蚀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一个社会,如果“多”数人都成了虔诚的拜金主义者,都淹没在钱(“泉”)水之中,时间一久,不仅“多”数人会被水腐蚀得没有生命,而且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命也会慢慢消逝。货币的腐蚀性多么可怕啊。
四、取人弃人的势利性
势利性,指趋奉有钱有势的人而歧视无钱无势的人的恶劣作风。乌宝在取人(趋奉人)与弃人(歧视人)等方面“素趋势利”。他对“富室势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对“窭(ju,贫穷)人贫氓,(虽)有倾心愿见(者),终不肯一往”。如弘农田氏家业兴旺发达时,他“常客于”他家,“竭诚与交”。而“田氏没,其子好奢靡,日以声色宴游为事”,家势日渐颓败,“宝(则)甚厌之”。又如“邻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为也,(家业火爆),(乌宝)遂挈其族往依焉”。“往依焉”之后如何,作者没有描述乌宝的具体行为,留下了空白供读者思考。其实,作者已经在“往依焉”字句之背后写下了潜词,商氏子也如田氏子那样“日以声色宴游为事”而沦为“贫氓”,于是乌宝“遂挈其族离弃之”。上述二例说明,人若在富,乌宝则“竭诚与交”,“常客”之,或“挈其族往依焉”,为其添薪加火,促其更兴旺发达。人如果贫穷了,乌宝则或“甚厌之”,或“挈其族离弃之”,见死不救,落井下石。乌宝之于人之取弃,何其势利!
乌宝在对待思想潮流方面的态度亦然。儒家兴旺发达,乌宝则“世尚儒”。儒家受挫,他则“尤不喜儒”,“虽有暂相与往来者,亦终不能久留也”。一旦墨家走红,乌宝则改名换姓而跟“从墨氏游”以“尽得其通神之术”。其“势利”之丑态实在令人作呕。
五、市场交换的多诈性
货币产生于市场的交换,又反过来积极促进市场的交换。市场交换既是商品广泛流通的生动形式,又是货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们运用商品和货币赚钱的良好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商品和货币等各个方面都在千方百计地展示自己的内涵、实力、能力、智慧和技巧等,都在努力利用市场的运转秩序谋求自己的利益。但市场是多种运动形态的集中和交汇之地,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事物都在用自己的特殊运动方式顽强地表现自己的特色,都在为自己的存在──或为成为市场的主宰者,或为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进行不懈的奋斗。在“奋斗”中,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制胜的方法,行“诈”是常见的一种方法。如果各种事物都按正常秩序运作,那世界就陷入单调、平静、死板的状态之中,就会丧失发展的动力。正常和不正常是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是对立的统一。二者缺一,就无法对立,也无法统一,因而也就无所谓事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非正常活动的“诈”也是市场交换的一种“合理”的“技巧”,是对市场正常交换活动的一种推动和补充。
“诈”,欺骗,因从“言”,以语言诓骗的成分为主。乌宝混迹、穿梭于市场千奇百怪的复杂交换过程之中,对“诈”听(见)怪不怪,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倾心学之,并在实践中“尽得其通神之术”,完全掌握了“诈”的本领,可以随口而出,信手拈来,娴熟运用。高明写乌宝时,从不同角度三次用到了“诈”字。或曰:“其为人多诈”;或曰:“挟诈者”;或曰:“则变诈亦可知矣”。使用频率如此之高,说明“诈”在乌宝性格中的重要位置。高明把乌宝性格概括为“为人多诈,反复不常”八个字,并对其在市场交换中的“多诈性”做了以下几种深刻揭示:
1、使用变色龙变幻儒墨颜色之法以招摇过市而取利
乌宝时而自称“世尚儒,务词藻”;时而“厌祖、父业,变姓名,从墨氏游”。交换穿着儒、墨两种不同颜色的外衣招摇过市,蛊惑人心,迷乱众眼,以在更多的人中“诈”取利益。如“其子姓蕃衍”,到处可以得到“官给(的)庐舍”。在很多人上无片瓦的封建社会,能获得“官给(的)庐舍”,的是非常耀眼的财富。
2、使用魔术师变幻死活之法以套取社会财富
乌宝时而使自己“子姓蕃衍,散处郡国者皆官给庐舍而加守护焉”,生动活泼,钱财奕奕,富雄一时;时而又装成可怜巴巴的“老死者”,并被官吏强“聚其尸而焚之”,只剩下一团死灰。它这样变来变去,其目的是捞取钱财。它每一变,都可以套取大量的财富。
元朝各皇帝经常以比前代皇帝快十以至数十倍的速度印制钞币。据《元史卷93·食货志》载,“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矣,大抵至元(公元1264——1295年)钞五倍于中统(公元1260——1264年),至大(1308——1312年)钞又五倍于至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发行“至正交钞”,“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又载,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3]。元钞泛滥成灾,严重贬值,出现了“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3]的物价暴涨的情况。
朝廷掌握着纸钞的印造大权,常用印钞票并投放流通市场的方式以促使社会流通的纸钞贬值。其具体手段是:一方面,用一定数量的纸钞收购人们的产品如粮食等。他们把收购进来的粮食等囤积起来,严格控制起来,不准随便流入市场。另一方面,又向市场投放印造的大量钞币,使市场钞币的流通量大大增加。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市场上粮食等商品稀少,而钞币很多。“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是之谓也。人们好不容易获得的一些钞币,几乎成了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废纸,钱贬值得不值钱了。钱虽然变得不值钱,但人们毕竟还有一纸在手,多少还能得到某些心理安慰。朝廷连这一点“安慰”也不给人们,敕令朝“官”们强行搜验人们手中的纸币,把旧的、破损的纸币称之为“老死者”,并野蛮地“聚”之“尸而焚之”。一炬之下,彻底销毁了许多交换商品的凭证,并导致了官民两个相反的结果:朝廷已经通过发行货币“合法”地将粮食等有关商品(物资)牢牢地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普通老百姓把自己的产品倾倒给了朝廷,家里空空如洗,而手中持有的用粮食等交换来的“不值钱”钞币也被“搜验”去投入熊熊火炬之中化为乌有了。人们一无所有,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乌宝玩弄这个“诈”骗魔术,不知不觉地把广大民众的“鲜血”和膏油抽尽了和熬干了,非常有效地帮助统治者套取了大量社会财富。
3、使用金蝉脱壳逃离之技以推卸罪责
在元代,用货币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以及某些人为了钱竟然铤而走险以抢劫等负面作用被充分地暴露和凸现出来了。人们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加深了对“金钱是万恶之源”的认识。许多元曲作家反应最强烈,他们把钱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猛烈攻击钱的负面作用。例如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钱霖《般涉调·哨遍·看钱奴》等等作品都咬牙切齿地咒骂钱“是招灾本”、“是惹祸因”、是熏人的“铜臭”。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钱成了过街的老鼠,急于变幻身份,逃避斥责。乌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乌宝从“以通神之术显”耀的“钱氏”腹中脱胎而出,“其术亦颇(与钱)相类”。钱与万物一样有新陈代谢的生死规律。“迨宝出,钱氏遂废”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钱氏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社会交换中所发生的“灾”与“祸”,“不知者犹以为钱”所为。因此,人们仍然把货币的负面作用归罪于钱。乌宝则经过金蝉脱壳后,改换了姓名,掩盖了钱在其身上烙下的深刻的历史印迹,使许多人根本不知他与“钱氏”浓浓的血缘关系。于是,他可以堂而皇之站立在社会,完全不负“钱氏”负面影响的责任了。又于是,他以新的面孔出现于社会后便可大言不惭地接受人们的欢迎,出现了“人争迎取邀致”,“老稚婢隶,无不忻悦”的热烈场面和或“倾心愿见”,“竭诚与交”的动人情景。乌宝借机割断了与钱血缘关系,从而推脱了他应该担负的一切历史责任。它不背负历史的包袱和责任,便可毫无顾忌地“趋势利”,轻松地“无入而不自得”其利益了。
4、使用推波助澜作恶之法颠倒黑白以浑水摸鱼
元代社会本已世风堕落,“败事”频频发生,乌宝乘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使社会更加乌烟瘴气,浊水横流。具体表现在对待儒墨的态度上。他虽“世尚儒”却一反常态而“尤不喜儒”,打破了人们长期遵循的思想传统。他“变姓名,从墨氏游,尽得其通神之术”,并加以大肆张扬。姑且不论儒墨谁是谁非,但看谁能稳定社会。
当是时也,儒家思想早已成为社会的传统思想。在其制约下,人们多以“和为贵”,以“安”为本。宝也自称“儒”家后裔,其言行一向遵循儒家思想的原则。其时,社会有了新的发展动向,“其先出于会稽楮氏”的“宝者”虽“务词藻”,“然皆不甚显”。宝耐不住寂寞,动摇了信念,毅然“厌祖、父业”,否定儒家传统而“从墨氏游”,并“得行其志”。
稳定一个社会的秩序,关键在有一种能够支配这个社会一切言行的思想。思想确立了,人们的言行就有具体标准以遵循。否则多种思想混杂标榜,人们便会无所适从而乱套。乌宝在信仰上“反复不常”,在儒墨之间荡秋千,不仅混淆了人们对儒墨界限的认识,而且加深了“儒墨之素不相合”的矛盾。
其实,墨家思想在当时“害道伤化尤甚”。乌宝“性本恶”,悍然“从墨”,并用以攻击儒家的传统,混淆了儒墨的严格界限,颠倒了黑白是非,搞乱来了社会秩序。其影响非常严重,十分恶劣。“虽(使)孟轲氏复生,(也)不能辟也”。辟,复辟,即恢复原来“世尚儒”的社会秩序。此语意在说明:乌宝助纣为虐,充当墨家的帮凶,对社会的破坏严重,“害道伤化尤甚”是也,难以收拾。就是叫儒家亚圣孟子再生也无“能”力恢复原来人们“廉介自持”的社会风尚。深刻揭露了乌宝“从墨游”的严重恶果。
乌宝颠倒黑白,四处为乱,浑水摸鱼。摸到了什么“鱼”?《乌宝传》说他摸到了如下三条大鱼:
(1)抓住了出生的大好“时”机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者,“天时”排在第一。一切事物都生长于一定的“时”机。生不逢“时”,一切都枉然。“然使宝生于唐虞三代‘时’,其术未必若是显。然则宝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这里讲了两个“时”字。第一个“时”指远古“唐虞三代(之)‘时’”。那“时”乌宝精血未凝,不可能产“生”。第二个“时”指元“时”。乌宝经过数千年历史的孕育,到了元“时”,“时”机成熟了。有如怀有十月的胎儿可以一朝分娩了。乌宝牢牢抓住了这一最好“时”机应运而出生了。
(2)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乌宝生逢吉“时”,蓬勃发展。一是“子姓蕃衍”“族”而“夥”。二是几乎独占了流通领域的巨大舞台,“其术益尊”、“益著”。三是官运亨通,“皆为显士”。
(3)登上了神圣的主币宝座
“迨宝出,而钱氏遂废”。据《史集(卷3俄译本页135)》载,丞相孛罗谏曰:“钞乃是上面盖着皇帝印章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全中国,而硬币在那里不用,将全归于国库。”国君乞合纳谏,“下令速制造纸币”,“并下令凡拒用纸币者立即处死”[3]。乌宝走上了极好的“时”运,受到了皇上的特别宠幸,因而“得行其志”:能够大“显”身手“使之”“其术”,充分“显”示其主币的“尊”贵,享有不可一世之威严。
乌宝因为抓住了几条大鱼而沾沾自喜不已。其实,这不过是他“变诈”的一种丑恶表演。
元代纸币为长方形状,一般长25-26 厘米,宽16-18 厘米。四周的花边是与楮币整体相对应的相似长方形。这就是《乌宝传》之谓“外若方正”。乌宝用“方正”的外貌给人以“正人君子”的假象。其实,经过高明《乌宝传》“以文为戏”的笔法的彻头彻尾、彻骨彻心的揭露,其宽阔的“方正”“外”形之“内”藏纳着厚“实”杂多的“垢污”,其形态丑不可视,其气味臭不可闻。
[1]赵 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37-339.
[2]百 度 百 科.乌 宝[EB/OL].http://baike. baidu. com/link?url=P13TaAHye3B1aC3X5z6Kx1lzXuHEqXNrqmjJTVJzpb IFiG-li6Xyzt2_ d_ sNIOewAyG6JpShr3HDsh4bTbhBIa,2014-09-18.
[3]邓广铭、韩儒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五册、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99;1981.126.127-128.260.
[4][元]脱脱(等).宋史·志·第一百三十四·食货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