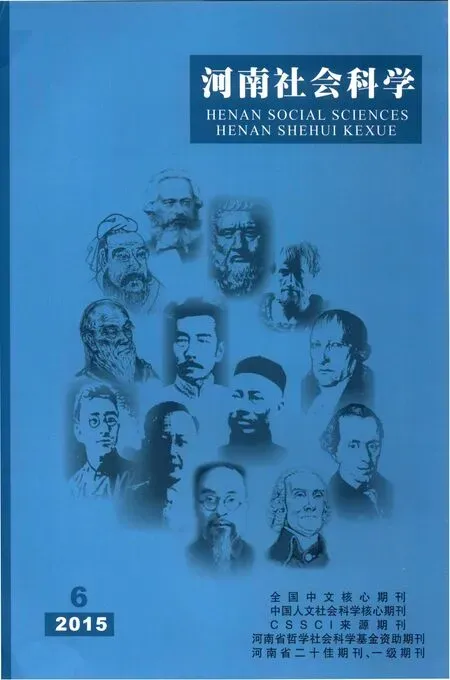从旅游学角度论则天朝的宴游诗歌
赵丽霞
(南阳理工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0)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吸引着历代文人对之进行不懈的追崇和研究。对于唐诗的研究,发展至今已经有着丰富的历史积累,传统的学术形态如诗歌作品、群体流派、文献考证、艺术特征、思想文化等仍不断向纵深挖掘,而新型的唐诗研究理论方法也不断涌现,最突出的体现是研究视野的宏观化和视角的多元化,以及跨学科的横向整合研究。现代的学术触角已延伸至史学、艺术、哲学、宗教、美学乃至建筑园林、地域交通等交叉领域,这种运用跨学科思维对传统诗歌的探索,有助于以全新的视野开拓出唐诗领域尚未被涉及的新领域。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唐代的诗歌中相当一部分是与旅游密切相关的,诸如大臣陪皇帝出巡时的陪侍、宴赏游,官员迁谪时的沿途游,到任后的驻地游以及众多文人游玩山水的漫游等,这些游赏活动都与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文学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对彭定求版《全唐诗》的粗略统计,仅初盛唐时期,与旅游相关的诗歌作品就有3000 余首,因此本文以现代旅游学为依托,以武则天及群臣在河南各地的宴赏游活动及诗歌创作为切入点,尝试将古典诗学与现代旅游学进行良性对接。
一、古代“游”之回溯
旅游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相始终的,远古时期的迁徙与游居,是被追溯为最原始的旅游活动。中国的古人从未固守“安土重迁”的思想,他们不仅亲身游历,并且对“旅”与“游”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追溯“旅”与“游”的本源,两字在甲骨文的象形表述中均带有“”字,“”本即表示旌旗的形状,可见“旅”或“游”都有执旌旗而行的原始意义,徐复观曾解释为:“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系缚,故引申为游戏之游。”[1]这与现代旅游学中“游”具有的闲逸、游乐功能不谋而合。旗帜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解释:“这是古代氏族迁移或游居时常见的现象,旗子代表氏族的徽号。”[2]可见,“旅”“游”最初释义中的旗帜飘扬的流动性、氏族奉神举旗行走的畅游性,都是与无拘无束的自由相关联的。
无论是儒家的孔孟还是道家的庄老也都有对“游”的不同表述,“游”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的一生游历丰富,孔子为了他的人生理想曾周游列国,亲身实践远游,他的游历生涯对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极大。孔子虽主张近游,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3]的论说,但孔子并不反对游,相反还推崇接近自然。孔子的弟子曾点曾述己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深以为然,赞曰:“吾与点也!”[3]足见孔子也是乐于游的。事实上,孔子奔走四方,求学会友,正是在远游中实践和提升着自己的理论道德修养。在道家的思想体系中,道家的游观,主要以“逍遥游”为核心思想,《庄子》一书以《逍遥游》开篇,而书中使用“游”字多达一百多处,“游”在庄子思想体系的地位可见一斑,他所追求的养生之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皆是自“游”衍生而来,以“游”论道,以“游”得道,道游一体,成就了庄子任性适意的独特游观。庄子曾论:“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4]表达出庄子投身自然、情系山野和逍遥无欲的游的本质观,也折射出道家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倾向。
“游”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作为一种跟生命活动密切关联的哲学范畴,它既是俯察仰观的身体活动,也是“游心太玄”的精神活动。从词源学角度看,“游”有遨游、神游之意;就时空而言,“游”不拘泥于一时一地,具有适性漂泊的自由;就心灵而言,“游”既有从容通透的洒脱,也是消解人生困苦的良药,被后世知识分子引入了内心世界,成为士大夫隐逸遁世的精神标杆。鉴于古代“旅游”核心的“游”具有包含现代旅游学又不局限于现代旅游学的丰富内涵,就更迫切地要求当下结合现代旅游学,对古代旅游活动及相关的思想、文学作品加以还原与解读。
既然“游”在古代具有如此复杂的内涵,而与之同步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关游览、记游、行旅类的丽彩华章也是俯仰皆是。虽然古代典籍并未单列“旅游”类别,但不能否认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中,大量游山玩水的作品符合现代旅游文学作品的界定,或存在某种相似性。仅以宋代李昉《文苑英华》在其第二册“诗”部中,专列有“巡幸”卷和“行迈”卷,即体现了古代文人已对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旅游类目有所重视,并专列卷目进行研究。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将唐、宋律诗分49 类,其中登览类、宴集类、闲适类、旅况类、川泉类、庭宇类、迁谪类都与旅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旅况类更是与现代标准的旅游文学相差无几。从这些古典文献的分类归纳足见旅游在古代文学所占之分量。根据对《全唐诗》电子文献的检索,《全唐诗》中以“旅游”为话题的诗就有5 首,而“旅游”一词在诗句中出现的次数为25 次,如白居易的“江海漂漂共旅游,一樽相劝散穷愁”(《寄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张籍的“过岭万余里,旅游经此稀”(《岭表逢故人》)等。虽然仅从“旅游”为话题或入诗的数量看,似乎并未在诗歌类别中凸显优势,但唐人曾经大量的旅游活动及流传下的旅游诗歌创作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全唐诗》中以“游”为题的诗歌也不在少数。这其中,作为唐代唯一女皇的武则天虽未有惊艳绝伦的旅游佳作流传于世,但她及围绕其周围的文学群体对开启唐人的旅游风尚和在唐初即将审美视角由宫廷山水转向自然风光的先行者,对盛唐乃至整个唐朝旅游诗歌的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二、则天朝的旅游文学观
对初唐诗歌的研究,学界多注目在初唐四杰、陈子昂、沈宋对唐诗的贡献,而将数量庞大的宫廷诗歌弃之于文学研究视野之外。事实上,作为受命文学的宫廷诗歌不仅在唐初诗歌中所占数量丰富,并且内容也涵盖广阔。宇文所安认为初唐的诗歌时代即是宫廷诗的时代,他的整部《初唐诗》几乎都是在研究分析宫廷诗及宫廷诗的对立诗派(在他看来不包含在宫廷诗的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余恕诚也对初唐宫廷诗的价值地位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认为在诗人所占比例上,初唐220多位作家,除包括四杰在内的十分之一属中下层文人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宫廷文臣、帝王、贵族、后妃。而即使仅占十分之一的下层文士,如陈子昂、四杰等也或短或长的任过宫廷学士或王府幕僚[5]。以帝王群臣、侍臣文人为创作主体的宫廷诗歌,其诗歌范围不仅局限于宫廷内的诗歌创作,也包括帝王在宫廷外封禅郊祀、狩猎出征、驾幸宴游时君臣所作诗歌,而诗歌内容包揽众多,歌功颂德、宫廷游赏、游幸寺观、出巡宴赏等无所不在其列,这其中旅游赏玩是宫廷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统计仅初唐宫廷应制旅游诗就有611 首,占到初唐宫廷诗的40.1%,约占到初唐1100 余首旅游诗歌的58.0%,因而从旅游的角度考察唐初旅游诗歌绕不开以帝王为核心的宫廷旅游诗歌创作。
高宗至武周朝的宫廷旅游文化整体氛围是由颂美型趋向自然型,这是与太宗朝很不相同的。太宗贞观时期,虽也曾有宴游、巡幸之类活动,但作为大唐基业开创者的君王及随其历经战乱、戎马生涯的朝臣来说,却深知前朝奢侈之祸。故太宗建国之初反对秦皇周穆,汉武魏明的“穷奢极丽”并欲以“麟阁可玩,何必两(一作山)陵之间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的宫廷近游取代前代的游幸四方,这也间接倡导促成了贞观贻始的皇宫内游乐赏玩的盛行。即使偶有出游巡幸,也多是怀游故地,并发以追古抚今的忧患之思,或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情。即使在太宗后期赏游略有增多,诗文略喜文丽时,也没有失掉贞观君臣缔造盛世的豪迈情怀和以儒治世的责任感。
至高宗武后朝宫廷旅游诗歌即由重儒雅转向重文采,高宗在位期间,前期承贞观余荫,后期朝政由武后把持,故高宗武后朝的文治导向实际仍由武则天掌控。武后为巩固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不仅广开科举,在制度上打破士庶界限,而且采取“以赋取士”的政策广招文学高才之士入朝,遂在武后至武周朝形成了“北门学士”和“珠英学士”两大学士群。武后朝的大部分群臣诗人已不再有贞观君臣建国打天下的豪情和亲历创业的艰辛与恭瑾,加之武后出于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轻儒重文,出现“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重文艺”[6]的趋势,因而宫廷旅游诗歌的主流也渐由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和铺陈宏大的颂体取代了贞观朝的骨鲠之气。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武后兴起的宫廷宴游之风,《大唐新语》卷八记载:“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记……”李峤为此专作《奉和天枢成宴夷夏群僚应制》一诗,极力铺陈明堂的恢宏气势和宴游的壮大场面,借以歌颂武后的丰功伟业。
武周统治时期政坛渐脱离武后时期的高压政治局面,政治较为清明,经济繁荣,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出于则天本身对文学的热爱,加之文学的政治功利色彩较武后时期渐弱,整个社会形成了探讨诗艺的热潮和对诗歌艺术创造才能的崇重,凭借文赋步入政坛的侍臣学士群体,迎合了武则天游览宫廷时爱好颂美的心思,诗词仍多繁缛华丽,至则天中晚期时随着国势的日盛和都市的繁华,尤其是武则天更加频繁的出游活动,士人的宫廷旅游诗风相较与武后时期的辞藻雕琢,而转向更注重旅游诗歌的自然之美。
武则天时期的旅游文学观还体现在则天朝对旅游诗作鉴赏的评判方式上。武周朝的宴赏活动较前朝更为频繁,为了给宴赏活动助兴,还加入了对宴赏诗竞赛点评的部分,每逢君臣游赏宴饮时,群臣应帝王之命应制赋诗,由此次旅游活动的最高权力者依其个人喜好评判诸人成诗速度的快慢和诗作质量的高下,并对获胜者赐赏以兹激励,这也相应地增添了宴赏游的娱乐氛围。宫廷游赏时的诗歌竞赛多是点到为止的娱乐形式,评判也以君王的喜好为标准,且夺冠者由君王授以奖励,这也调动了群臣创作的积极性。这种形式虽未言明是比赛,但文士在君主面前都会竭力展现自己的诗意,以求博得赏识,这也间接促进了则天时期旅游诗歌创作的繁荣。
最为典型的君臣游赏时应制竞赛所作,即是宋之问的龙门应制诗作。长安元年春,武则天游龙门,此次游赏,群臣赋诗众多,《唐诗纪事》卷一一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7]东方虬诗已佚,现已难窥其诗歌优劣。举宋之问的夺袍之作《龙门应制》: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凿龙近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云罕才临御水桥,天衣已入香山会。山壁崭岩断复连,清流澄澈俯伊川。雁塔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阳沟塍殊绮错。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骎骎映晚花。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嚣声引飏闻黄道,佳气周回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
宋之问诗为杂言歌行体,虽字面仍显秾丽,但由于注重气势,辞随势转,故并无龙朔诗歌繁芜、斧凿之痕,反而更见皇家华美气派。首四句“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点明此次旅游的时节,是在春雨初霏,万物回春之时,紧接着是对武后出游盛大场面和东都洛阳及龙门寺壮丽景象的渲染,“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描绘了游幸规模的庞大,而对自然之景的描写“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更是高华雄整,气势恢宏,自然天成,毫无应制应景诗的做作之感。“下辇登高望河洛。东城宫阙拟昭回”交代了游览的行进过程。其后“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虽有应和则天喜好的“七宝台”“仙乐”等辞藻,但与游景自然融合,使诗歌更有仙境意味,至日暮时分,游览观赏即将结束,又继续铺写宴游队伍之盛况:“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最后“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息春”回到歌颂帝王、赞美武周统治的颂辞中来,虽为应制惯例,但与整首诗水到渠成,融为一体,也不显过于突兀。这首诗作为典型的宴游诗,即使仍遵循应制诗的惯例格式,但因述景境界开阔,韵度自然,且述景大气,还兼有对游览规模的铺陈渲染,故不失为宴赏旅游诗的佳作。
武则天自高宗至武周时期所倡导并亲自实践的旅游文学观,也体现在她本人的诗歌作品中,武则天所存诗歌除郊庙、祭祀乐歌外即为宴游诗歌居多,《早春夜宴》《游九龙潭》《从驾幸少林寺》《夏日游石淙诗》《腊日宣诏幸上苑》均是此类,所作诗歌往往对宴赏活动及所赏景观加以生动描绘。而在则天时代凭借文才步入政坛的众多人士如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张说等还历经中宗、睿宗甚至玄宗诸朝,不仅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是宫廷旅游诗歌创作的主力,对整个初唐乃至盛唐旅游诗歌的诗风及诗体的完备成熟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则天朝的石淙之游
武则天时代不仅形成了有别于前朝的旅游文学观,并且以武则天为核心的宫廷诗人也亲自实践了由宫廷内苑迈至自然山水的第一步,在武则天的带领下,诗歌创作走出皇家花园,投入到大自然中去,从一味的颂圣转向了欣赏山水。武则天在执政后期,尤其是武周时期,为了宣扬武周奉成天命,常带领众臣出游名山大川,举行封禅祭祀活动和皇家宴游。
武则天时期最为著名的皇家宴赏活动是其石淙之游。石淙又名平乐涧,位居登封县内的嵩山,“石淙之水,源出于嵩,流合于颍。”[8]石淙汇入颍河,颍河现为淮河最大支流之一,石淙因两岸危石从立,形状异常,石群因水击石响,故称“石淙”。
武则天曾多次到石淙所在的嵩山巡幸。《旧唐书》则天皇后纪:“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山。……癸巳,至自嵩岳。”[9]她还把阳城县改名告成县,以示祭祀。圣历二年(699)二月,则天又幸嵩山。直至久视元年(700),则天第三次游幸嵩山,《资治通鉴》载:“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太后)幸汝州之温汤。戊寅,迁神都,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6]原注:“三阳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万岁登封元年改东都阳城县曰告成,以祀神岳告成也。”正是此次幸嵩山,在告成县石淙河修建了三阳宫,并在此年五月十九日率群臣于石淙河畔游览。
石淙山应制组诗是对武则天时期出游石淙的记载,武则天的第三次石淙游,包括武则天亲自赋诗七言一首《石淙》,共留下了17 篇诗作,除武则天诗作,剩余16 篇均为皇子、侍臣奉和所作并诗序一篇,合为《夏日游石淙诗并序》。虽然初唐皇家宴游活动盛行,但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君臣相伴宴游于自然山水间,也并不常见。《全唐诗》中狄仁杰《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涂山》诗下注曰:
石淙山。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里。有天后及群臣侍宴诗并序刻北崖上,其序云:石淙者,即平乐涧,其诗天后自制七言一首,侍游应制皇太子显、右奉裕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相王旦、太子宾客上柱国梁王三思、内史狄仁杰、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中山县开国男张昌宗、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给事中阎朝德、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薛曜、守给事中徐彦伯、右玉铃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杨敬述、司封员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佳期各七言一首。薛曜奉敕正书刻石,时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也。[10]
按:此事新旧唐书俱未之载,世所传诗,亦缺而不全,今从碑刻补入各集中。
此段话对石淙会饮的规模和参与赋诗之人作了整体说明。《全唐文》有武则天的《夏日游石淙诗并序》,诗序描绘了石淙的美景,介绍了游赏诗作均为七言赋诗,还对陪侍群臣的应制诗作提出了创作要求:“无烦崐阆之游,自然形胜之所……庶无滞于幽栖,冀不孤于泉石。”由此创作要求也可窥见武则天的诗歌审美已逐渐由奢侈华丽的颂美渐向细腻生动的自然美转变。当时君臣诗成后,由书法家薛曜书写,勒刻石壁,“楷书39 行,行42 字,分为三截,保存完好”[11]。另有宋之问的《三阳宫石淙侍宴应制》诗,也有论者认为作于此次石淙游,但未刻石,“王昶按语引《说嵩》及《河南通志》,谓亦为本次侍游所作,可从”[9]。同年秋,武则天又在石淙与群臣宴饮,张易之撰写了《秋日宴石淙序》,仍由薛曜书写,刻于石淙南崖石壁,与北崖所刻武则天序遥遥相向。
石淙的胜景奇观,吸引了武则天及其群臣屡次游览此地,而由皇家组织的赋诗唱和并刻诗于崖,也用文字形式永久保留了石淙的美景。石淙游所作君臣唱和组诗,虽仍有迎合武后早期爱好华美文风之嫌,如:“三山十洞光玄箓,压峤金峦镇紫微”(武则天)、“羽仗遥临鸾鹤驾,帷宫直坐凤麟洲”(狄仁杰)、“自然碧洞窥仙境,何必丹丘是福庭”(李峤)、“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帝壶”(沈佺期)。诗词或用珠光宝气之词渲染皇家出游的华贵奢侈、场面的宏大,或将自然景观吹捧为人间仙境。
石淙之游又因是典型的宫廷应制旅游诗,诗歌形式仍拘于固定模式,遵循“三部式”结构,即“首先是开头部分,通常用两句诗介绍事件。接着是可延伸的中间部分,由描写对偶句组成。最后部分是诗篇的‘旨意’,或是个人愿望、感情的插入,或是巧妙的主意,或是某种使前面的描写顿生光彩的结论。有时结尾两句仅描写事件的结束”[12]。首句如“宸晖降望金舆转,仙路峥嵘碧涧幽”(狄仁杰)、“羽盖龙旗下绝冥,兰除薜幄坐云扃”(李峤)、“金台隐隐陵黄道,玉辇亭亭下绛雰”(阎朝隐)等,用“金舆”“羽盖”“玉辇”“万骑”交代此乃帝王游幸,这也是武则天早期宫廷旅游诗歌惯出现的词语。而结尾句如:“微臣献寿迎千寿,愿奉尧年倚万年”(于季子)、“五百里内贤人聚,愿陪阊阖侍天文”(阎朝隐)、“今朝出豫临悬圃,明日陪游向赤城”(崔融),或感恩陪游的尊荣,或对整个游宴的总结,都体现了宫廷宴赏诗的规范。但同时这组旅游诗在对景物的描绘也生动形象,所写景物能从大处着眼,气势磅礴,如:“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武则天)、“霞衣霞锦千般状,云峰云岫百重生”(李显)等,都极力展现了石淙景致的阔大壮美;而于石淙的高峻朗拔中又不乏某处的细腻生动,如“飞泉洒液恒疑雨,密树含凉镇似秋”(狄仁杰)、“鸟和百籁疑调管,花发千岩似画屏”(李峤),可谓于深山大壑之全景中不乏绿藤繁花点缀其间,点面结合,灵动细致。
石淙之游虽只是武则天及其朝臣众多游赏中的一例,但因其规模较大,且旅游意味浓厚,与现代所主张的旅游文学更为贴近,如张易之序所言:“耳目所接,天下之为奇也;游践所经,天下之为绝也。”[9]故可以视为武后则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宴游诗歌创作,葛晓音对此也有所评价:“像这样君臣一起大规模游山玩水题诗的活动,在唐诗史上还是首次。七律在初唐尚未成熟。这次活动不但刺激了宫廷山水诗的发展,对于七律的推广也有明显的影响。”[13]
的确,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一生并未局限于宫廷内苑之中,尤其是将交通便利、旅游资源丰富、人才汇集的洛阳定为东都,武则天寓居洛阳达49年之久,在其称帝15年间,仅有两年居于长安,其余时间都长居洛阳,以洛阳为中心,则天及其群臣辐射游幸周边众多秀丽河山,邙山、嵩山、少林寺都曾留下女皇及其侍臣游赏美景、宴游赋诗的足迹。而则天君臣久视元年的这次石淙之游,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诗歌创作之丰富在唐代也是首开先例的,正是由武则天的带领倡导下,宫廷旅游诗歌才逐步迈出由宫廷台阁至自然山水的第一步,旅游诗歌创作也从一味地颂圣转向了欣赏山水。不仅如此,以石淙之游为典型代表的则天宫廷宴游活动,十几人共同作七律奉和诗歌《夏日游石淙诗》,虽然辞藻仍未脱则天朝前期华丽风格,且七律诗歌并非都全部合律,但因句法平易,语调流畅,要比五言要更显自由。之后中宗更为频繁的宴赏活动,以及七律在中宗宫廷的广泛应用,都是与则天朝宴游活动及七律诗歌首开此风密切相关。可以说,以武则天为首的宫廷宴赏旅游诗歌,不仅为唐代旅游诗歌开拓了诗境,也为随之而来的盛唐旅游诗歌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2]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余恕诚.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J].文学遗产,1996,(1):42—51.
[6]司马光.资治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56.
[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张慧民,王关林.嵩岳文献丛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9]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10]彭定求.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段宝林,江溶.山水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宇文所安.初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3]葛晓音.诗歌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