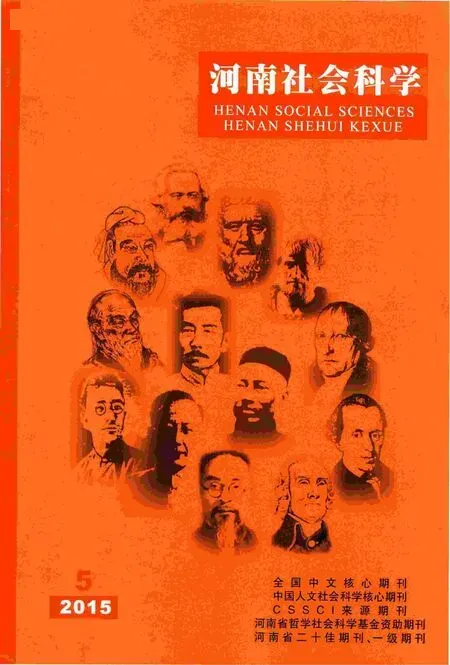华语电影的国族形象建构与传播
惠恭健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仅就资本与市场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世纪以来的华语电影以不断刷新的纪录创造了电影工业史上的扩张奇迹,中国亦成为好莱坞和其他民族国家电影热切向往的大票仓。然而在文化上,华语电影是否在先前的期待视野里找到了新的方法来表达华人族群在这个时代所经历的情感与经验的变化,进而是否与华人社会形成一种有效的对话关系,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肯定的问题。
一、族群认同的跨文化遭遇
完全可以写入文化史的一个小细节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曾是一个流行词语的“全球化”几乎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这个微妙的变化多少都意味着全球化已经作为某种常识被普遍地接受了。然而这种常识并不意味着跨文化的经验已经抹平了族群认同的紧张关系。曾与冯小刚联合执导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郑晓龙在2001年根据王小平的同名小说改编了电影《刮痧》。影片的主人公许大同是个游戏设计师,和妻子在美国生活了8年,一次因为孩子丹尼斯生病,爷爷用中国传统医术中的刮痧疗法为孙子治病,从而引起了一连串事件。在美国,中医刮痧疗法并不能得到医学界的承认,且被作为许大同虐待儿童的证据。因此丹尼斯被送进儿童监护中心,许大同被剥夺对儿子的监护权。在极度痛苦中,本来幸福的家庭在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下出现了破裂,许大同多次向法官和朋友解释刮痧是一种古老的治疗术,也总是令人一头雾水;在西方人或西医看来,这简直就是胡说。沿着这样的主线,电影中处处表现出中西两种文化上的冲突,比如丹尼斯和许大同的朋友昆兰的儿子打架,许大同打了自己的孩子,他对昆兰说“我打孩子是对你的尊重”,这在昆兰看来不过是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而他的老父亲则认为“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不摔的孩子长不大”。许大同和亲人不能理解美国法庭为何要剥夺自己的权利,而美国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刮痧当作治疗手段。这两种文化撞在一起,使得中国文化作为跨国境遇中的他者文化从而失语,用影片中爷爷的话说,即“我在中国还算个知识分子,可在这儿我成了聋子,成了哑巴”。
这表明了中国文化面对另一种文化时的精神困境,即东西方文明的内在隔阂。影片开始,许大同站在领奖台上自豪地喊:“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这是一种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融入,却没有认识到两种文化内在的陌生性,而这种陌生性必然要带来一定的文化冲突。许大同对美国文化的态度一方面暗示了中华文化在全球境遇中的弱势特性,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认同——一直以来美国引导着世界的方向,许多第三世界的人都以能够融入美国而自豪。但是我们发现,从一种文化融入另一种文化并非像一件物品移置到另一个地方那样简单。刮痧作为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有着自己独特的存在语境,一旦被移置,就会失去效用。这个语境就是中国民族文化语境,它目前还不能被西方所接受,也就意味着这种他者的话语无法真正获得认同。《刮痧》正戳中了两种文化冲突的痛点,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因而本身成为一部颇具文化内涵的影片。
文化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并无大碍,文化冲突的主要成因在于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互不了解甚至是误解。刮痧是中国民俗,也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寻求认同的话语信号。因此,新世纪以《刮痧》为代表的民俗影片竭力推崇“东方民俗”面向全球文化的勇气,并试图融入全球文化。这是新世纪民俗文化传统走向国际的第一步。
不同于《刮痧》里的激烈冲突,美籍华裔导演王颖执导的《雪花秘扇》试图通过重新寻访过去而达成某种和解。王颖将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放置在了更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电影中古与今、中与外的时空交错突显了清末和当代两个不同时间段两对女人的人生遭遇,并重新深刻地解读了传统“女书”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意义。两段故事,一古一今的对比,是时间维度上的文明推进,它引出了当代“女书”的新故事,而这个新故事又是发生在来自韩国的索菲亚和中国的妮娜之间的空间组合,传统民俗“女书”从古代穿越于时空之中,成为全球化语境中重新寻求价值意义的文化载体。而在语言上,影片中英语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同时各种语言的交杂也暗示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混杂的现状。影片开始对在华人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邓丽君音乐对妮娜所听流行音乐的否定的描画,即是新旧两代人对待新文化时的冲突态度。然而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很难判定文化价值的高低,妮娜和索菲亚这两个现代社会的文化个体恰恰又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了拯救情感的方式,最终通过“女书”化解了两人之间的隔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于《刮痧》将传统文化放置在西方话语之下的被动,《雪花秘扇》积极发掘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正是东方民俗在西方参照下的一种突进。
二、动作类型与中国人的神奇身体
如果说王颖试图通过性的秘密寻访一个古老的中国,那么,另一位华人导演李安则通过神奇的身体动作来制造出另一个古老的中国。在他执导的《卧虎藏龙》中,其武侠精神高度浓缩了东方文化色彩,它“让世人认识到,为侠并不仅仅取决于功夫的好坏和输赢,最重要的是人物自身的修行和境界,这是中国式的佛道哲学”[1]。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武侠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武术的展演,重要的是“侠”的精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侠”指的是一种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助被侮辱者的人或行为,《史记·游侠传》说“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侠客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卧虎藏龙》将东方文化的神韵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它“将中国人的励志、克制、情感的含蓄以及‘用励志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的观念加以充分表达”[1]。李慕白的言而有信、俞秀莲的行而必果、玉娇龙以生命牺牲换取爱情的永恒,整部电影显得平白朴素,没有所谓的江湖侠义、刀光剑影,也不以宏大的武打场面吸引眼球,而是将事件限定在狭小的家族范围内,融入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充满着人文关怀,尤其是在轻烟缭绕的竹林的决斗场景中,尽显东方神韵,诗意盎然。有学者评论说:“李安这份独特的武侠情怀,改变了以往大部分武侠电影只停留在表层动作的观赏上,将这些武侠电影中表现的古代江湖世界简单的恩怨情仇也提升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神韵。”[2]《卧虎藏龙》之所以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也多半因为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传达得十分深刻,给国外观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参照。正是在这种差异中,中国电影才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不可替代性。
新世纪电影中的武侠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十分能够体现中国文化及其世界观的民俗元素,它作为在全球化视野里西方文化参照系之下的一个文化终端,代表了区别于第一世界文化的理想和梦。“电影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再怎么样避免……还是不能摆脱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文化观。”[3]因此,“只要稍微用心,以多一点的角度去观赏一部电影,就不难发现存在于电影中的文化意象所代表的生活团体及其世界观”[3]。武侠元素或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它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运用,无疑饱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一种东方文化的世界观。恰如麦茨所言:“某种类型的研究的目的就是使隐藏在电影的天然性背后的编码作用显露出来。”[4]在东方武侠精神及其所体现的东方神韵背后,即是东方人特有的文化生活和价值观,也即相对于西方世界的某种他者性。
不同于《卧虎藏龙》的是,叶伟信执导的《叶问》将其故事背景转换到了中西冲突展开的近代,从而为身体动作赋予了更加强烈的民族国家内涵。这是一部弘扬民族精神的影视作品,尽管其中有对叶问出神入化高超武术的展示,核心却在叶问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武术精神,它所涵盖的文化意义,也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宏大政治背景下得以凸显出来的。影片中,叶问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在与廖师傅比武的过程中毫不声张,对廖师傅的失败他的态度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仁厚之道。在这里,叶问所体现的中华武德,和日本利用武力征服他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影片中叶问在上台与三蒲比武时,心中沉思:“武术虽然是一种武装的力量,但是包含了中国儒家的哲理,武德也就是推己及人,这是你们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道理,因为你们滥用武力,将武力变成暴力去欺压别人,你们不配学我们中国武术。”
影片中作为传统文化的武术是民族性的体现,在外族入侵和社会动乱的时代境遇中,它曾不断遭到挑战,甚至受到侮辱和摧毁。叶问的功夫代表了传统武术的精髓,他首先受到的是来自内部的挑战,金山找为了在佛山开武馆,前来向佛山的武师寻衅,并将其一一击败。金山找身为习武之人却缺乏武德,这是民族性格本身的一个缺口。而来自外部的挑战自然是日本民族的侮辱。借用影片中日本人自己的话说,跟中国人比武,输赢就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国家民族的荣辱。武术上的较量被升格到国家层面的较量。而三蒲将军要和中国人比武,也流露出一种高傲的神态。中国功夫传统悠久,其文化博大精深,对中国功夫的侮辱和践踏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践踏。此类影片中对中国民俗,以及东方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呈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方面也掺杂了对民族性的张扬。
在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也越来越隐蔽,中国新世纪民俗电影中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历史事实的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东方民俗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破坏和毁灭的影像呈现,使得这些珍贵的民俗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些影片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5]。这意味着对电影文本的阅读,必须通过对文本的历史化“超越读者与文本的局部冲突,进入到使文本和阅读成为可能的语言和文化符码层面”[6]。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新世纪电影中民俗影像呈现的价值和意义。
三、情欲、窥视和中国式造型
关于《卧虎藏龙》的一个有趣细节是,尽管片中也有玉娇龙和俞秀莲等女性角色,但在造型上,李安却通过宽袍大袖的服装最大可能地压抑消解了性别特征。这似乎暗示着只有男性才能拥有强劲的力量和神奇的身体,女性则只能在情欲主题之下出场。就电影而言,色情和窥视是一套辩证法,而“视觉本质上是色情的,就是说,它的结果是迷人的、缺乏思考的幻想”。“色情影片只是整个影片的强化,它邀请我们凝视世界,仿佛世界是个裸露的躯体。”[7]“电影是一种身体的体验。”[7]因此,通过电影,我们将自身的欲望植入其中,使其成为社会秩序的一种象征。而色情电影则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征用或挪用,“将女性完全作为对象而非主体的代码使用”[8]。在观看色情电影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一方面被男性消费,一方面更加固化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尤其在全球化中西文化对峙的历史境遇中,作为弱国对弱势女性的展示,则构成了一种双重的消费。
这种消费表现在郑晓龙导演的《大鸿米店》里,就是五龙对米店老板两个女儿的践踏、宣泄和报复。农民五龙在一次洪灾中逃难到城里谋生,饥饿迫使他食生米而苟活下来。米店的冯老板收留五龙做了伙计,白天他卖力干活,晚上便躺在米槽中感受米从头到脚撒遍全身而带来的快感。米店使五龙的食欲得到了满足,却又让他落入性欲的陷阱。米店是生动展示人性恶与贪婪欲望的场所,生存作为生命的第一要义在这里超越了一般道德的层面。尽管织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格,这也是因为受传统伦理束缚而发出的抗议,但是这样的抗议最终迎来命运的悲剧。她在米仓里和五龙的交媾,不仅暗示着“米”和“性”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主题,更隐含了女性在生存面前的被动。
“电影机器承接了一种图像理论,这种理论并非孕育于性别的规范之外。”[9]这种性别的规范更多的是将女性还原现实的弱者身份,一种低下的、非文明的原始情调。在《白鹿原》中,一片片金黄色的麦浪,象征着生命的成熟和欲望,那种沉重的色彩、结实的晃动的麦穗,隐隐透露着女性的原始气息。田小娥和黑娃的情欲戏大都是上演于麦地或麦垛上,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实场景、一种野性的体现。麦禾的金黄色饱满而深沉,将两个黝黄的肉体浸泡其中,整个画面的主色调也是黄色,令人充满感官的想象和视觉的刺激。
无一例外,在《色戒》《大鸿米店》等电影中,这些情色镜头的色调均是浓厚、沉重的金黄色。“黄”是古代皇家贵族的颜色,因此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某种色情意味,也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而这种压抑又是一种落后的、尚未启蒙的文化状态,对其的观看和消费则是一种对原始情调的体验。“它可以看作西方自卢梭以来或中国自鲁迅以来的现代艺术家,为着现代人的特殊需要,而对过去生活所作的想象的和象征性的重构。”[10]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对中国传统女性进行的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描画和对性的原始情调的挖掘和调用,无法排除其迎合西方猎奇心态的嫌疑,事实上,电影作者们也确实是客观地将这一原始情调通过活生生的民俗元素呈现、并置在西方高大的文化身影之下。
相对于《卧虎藏龙》中的女性造型,《色戒》展示了另一副不同的模样,女主人公王佳芝几乎从始至终都身着旗袍,充分地暗示了暧昧的情欲特征。按照服装美学的解释,旗袍具有鲜明的东方女性的身体美学特征及民族个性,如采用独块衣料依据东方女性人体特点进行收腰、收廓、紧身,从而表现东方女性的苗条身材以及含蓄、典雅、矜持的性格特点。因而,通过东方女性所特有的形体之美,旗袍一方面呈现中国传统民俗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中国女性及与之有关的情色与欲望。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自古以来女性一直生活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之中。早在《诗经》中我们就能读到各种关于东方女性形象的描绘,诸如《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红楼梦》中描写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以及白居易“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羞涩。东方女性的温婉含蓄、阴柔妩媚,无论是在诗歌文章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将这一形象搬上影视舞台,自然会吸引各种观众的兴趣。而随着电影的出现和发展,“主流电影把色情编入了主导的父权秩序的语言之中”[11]。东方女性形象则开始逐渐偏离审美的轨道,成为一种经过反复包装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讲述了诸多中国女性悲剧中的一个故事,女性被男性当作工具运用于战争、公关等领域,古时候称“美人计”。“美人计”作为一个历史典故,是“三十六计”之一,已屡见不鲜;又语出《六韬·文伐》:“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可见“美人计”有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色戒》中,身着旗袍的王佳芝漫不经心地打着麻将,魔鬼一般的身段在旗袍的包裹下,呈现出诱人的曲线美。旗袍是清代满族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穿着方式,它代表了清代独特的审美观,能够展示女性的体态和线条,因而颇具魅力。这也是东方独特的审美现象,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最富民族风情的女性服装之一”。旗袍的线条简洁、色彩绚烂,女性穿着时能够显得风格优雅、雍容华贵,非常适合表现中国女性的独特韵味。因此王佳芝身上散发着古典、纯净的气息,颇具民国时期的文化风范。在影片中,她象征着传统中国男性的欲望,是男权社会里男性的他者,其最大的不幸就是被男人利用、控制和玩弄。王佳芝作为一个执行刺杀汉奸任务的诱饵,被放置在易先生身边。易先生一方面作为男人,他要占有女人;另一方面他身居国民党要职,是社会权力的象征,有着控制社会的力量。因此,他对王佳芝的控制和虐待具有了双重意义,对作为女性的王佳芝的控制和作为社会财产的王佳芝的权力控制。而王佳芝的美貌和富于魅惑的装扮目的就是为了让易先生上当,让他沉醉于女性身体的消费中(易先生当然不止有一个女人)。同时,她作为一个舞台形象,本身也充满了色情意味;毋宁说,在这个商业时代,无论是影片中的主人公还是场外的观众,都作为窥视狂,消费了汤唯的女性身体。这种消费不仅是对欲望的一种满足,更是男权力量的一种实现。影片“完全按照男性欲望裁剪的幻觉,却编造出美妙世界形态以抵消对其主导意识的怀疑。即使女性形象以获得相当的饱和度,其作用仍在以恋物的幻想空间掩盖创伤所在,以美丽覆盖匮乏”[12]。
四、作为奇观的战争叙事
《色戒》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情欲的故事,它同时以另类的方式讲述了现代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同样的类型叙事还有姜文的《鬼子来了》和管虎的《斗牛》。《鬼子来了》使用地道的河北方言,各种人物状态原始落后;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影片不同,方言的大量使用意味着对官方叙述的拒绝,同时也意味着姜文所采取的立场是民间的,虽然从民族与国家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思和批判了民族的愚昧。影片中方言、土炕、古老的城墙,五舅老爷、八婶子的水烟斗,都展现了中国落后农村与外界隔绝的原始生活状态。这种原始状态还表现在官方的缺场,也即现代性的缺场。挂甲屯的村民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环境中,在遭遇历史动乱之前,他们代表了世界上最纯朴的人性,他们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习俗,都是独立自足的。但是两个俘虏的出现,以及官方力量隐含的凌驾却顿时让他们生活在了恐惧之中,而这种突然的凌驾与在场是通过西方列强,抑或是现代侵略战争引发的。在这里,姜文似乎有意暗示,官方的缺场及其无形的在场,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现代性的入侵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他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土地上,展现着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葆有农民的天真、淳朴。而战争作为一种性格参照,却使他们的善良逐渐模糊乃至混沌不堪。影片还将故事地点设定在偏僻的乡村,表明这个没有开化的人群或民族,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阅和考察,必须接受官方的领导,必须认识到自身民俗相对于现代世界的落后状态,纵然他们是天真的、无辜的,此时,传统的中华美德——人性的善良——也被摆在价值重估的位置上。如果说类似于《血战台儿庄》等主流影片是对顽强杀敌、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的弘扬,那么《鬼子来了》则从反面描绘了另一种民族性格,这一民族性格在全球文化席卷的历史语境中成为与现代性相对而言十分落后的社会寓言。
相比较而言,2009年管虎的《斗牛》更多地侧重于小人物的命运悲剧。《斗牛》与姜文的《鬼子来了》不同,它没有太多批判,而是饱含深情地描述了一个乡村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个人遭遇,没有民族叙事的宏大主旨,也不像《建国大业》等影片具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和《鬼子来了》里的人们一样有着传统农民的善良,破旧的村庄、荒凉的山石,围绕一头奶牛举行的抓阄,以及村长凭着家族领头的身份将九儿嫁给牛二当老婆,江湖郎中,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原始。这种淳朴的人性在日军的侵略下显得脆弱不堪,通过牛二的个人遭遇,影片也揶揄了社会的现实问题,突显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自足性在社会变革下遭遇的悲剧。和《鬼子来了》一样,这里官方的缺场(或只是偶然出现)成为人民生活自足的前提,官方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鬼子来了》中突如其来的两个麻袋,以及《斗牛》中硬是塞给牛二的荷兰奶牛,都表明传统文化不断接受外界现实的干预,乃至西方文化的侵略。
但是,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一味沉浸在小农的封闭世界中,只能遭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操控。《斗牛》中,牛二自己的小黄牛在为了保卫荷兰奶牛的过程中被日军屠杀,正是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写照。于是影片对民俗以及在列强入侵下民俗的摧毁和解体的描写,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五、结语
即便是对华语电影在过去十几年里讲述的故事一无所知,各种媒体的报道也早已将中国电影票房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神话广为散布。这一位置显然表明中国在世界电影格局中获得了新的位置,但是这种位置却主要是由“大”而非“强”促成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现状只是一个迅速膨胀的票仓吸引了韩国、美国乃至欧洲的创作人员和生产资本。这意味着中国仅仅是以市场的身份加入了电影工业全球化的进程,它所拥有的只是可供资本增值的空间,而不是文化表达的主体;或者更干脆地说,这种体现在统计学层面上的繁荣徒具逐利的吸引力而无文化的影响力。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势下,华语电影若要从单纯的规模之大走向真正的力量之强,必须在生产和传播两个方面实现革新。
生产方面的首要问题是以重建电影与族群和社会的关联来再度确认文化身份。在内容上,一方面要加强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整理,选择新的视角来重新讲述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敏锐地捕捉时代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带来的巨大冲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也有一些严肃地回应了时代现实的影片。比如陈凯歌执导的《搜索》,就以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因为身体不适未给老人让座而意外地卷入道德审判的故事,审视了眼下这个“媒体时代”的问题。“《搜索》则将镜头对准转型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现实困境,以充满温情的目光关注个体命运、揭示人性挣扎、表达人文关怀,呈现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陈凯歌看来,这是电影人的责任,也是电影人回馈社会的方式”[13]。影片在个人和群体、私利和公义之间编织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并且冷静地剖析了隐藏其中的暴力,从而密切地关联起了产生这一问题的社会与时代,重新获得了对话现实生活的能力。惟其如此,我们的电影才是真正做到了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不是停留于中国讲述的故事。重建电影与族群和社会的关联也需要在表现对象上完成重要的调整,不能像《非诚勿扰》系列那样仅仅将兴趣集中在中产阶层的感情困扰上,也应该去讲述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情感。难得的案例是张猛执导的《钢的琴》。该片讲述的是下岗工人陈桂林的妻子离开了他,嫁给了有钱人,并且以她能提供更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为由带走了女儿。为了赢得女儿的抚养权,陈桂林发动昔日的工友们一起制造了一台“钢的琴”。影片不仅呈现了工人阶层在变动的社会结构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以充满喜剧色彩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智慧、友谊和乐观主义精神。
生产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进一步丰富电影的类型格局。在最近的这些年里,喜剧片成为华语电影最为重要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由于喜剧片的制作成本小,生产周期短,利润期待高,因而刺激了大量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导致喜剧片迅速沦为一种庸俗、低俗和恶俗的代名词。更加糟糕的问题还在于大量的喜剧片都传达了一种不那么端正的价值观念,甚至包括广受赞扬的《人在囧途》和《人再囧途之泰囧》,其所提供的“笑料”也只是王宝强扮演的底层民众不恰当的生活经验和不得体的行为方式。突破这种类型单一化和劣质化局面的图景有两种,其一是借助尖端的制作技术促成功夫片和动作片等传统的优势类型实现新的飞跃,其二是结合本土的实际积极地开发新的类型。近年问世的一些影片表明了这种积极的尝试正在出现。高群书执导的《西风烈》试图以现代背景重新激活当年由《双旗镇刀客》开创的中国式西部片,程耳执导的《边境风云》和刁亦男执导的《白日焰火》则在修订了类型惯例的基础上成功地创作出了中国式的黑色电影。
然而,无论是故事内容和表现对象的转向,还是新类型与新风格的尝试,这些影片的票房业绩都不怎么醒目。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可以追究到影片本身,但是更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来自电影的发行与放映环节。当前的电影发行与放映几乎完全是以营销规模和票房回收预期为原则来排片的。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些试图实现某种突破的影片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市场风险,因而在发行和放映环节就很难获得支持。正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华语电影故步自封的僵局。现在看来,只有当管理部门通过政策杠杆的作用影响发行和放映系统的排片规则,或是在商业院线之外开辟和建立另一种替代性和补充性的发行与放映渠道,这样的僵局才有可能被打破,华语电影才能获得新的成长空间。
这样的成长空间绝非可有可无,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主体位置。如果只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么,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位置就只是吸引资本流向的一块洼地。只有进一步开拓创造的空间,同时也是以丰富的、新颖的、具有中国品格的方式来塑造和表达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空间时,我们的电影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将吸引力转换成影响力和辐射力。
[1]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厉震林.中国国际获奖电影的国家形象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3]王文正.电影文化意象[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51.
[4]克里斯蒂安·麦茨.论电影语言的概念[A].克里斯安·麦茨,等.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93.
[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William C.Dowling.Jameson,Althusser,Marx: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可见的签名[M].王逢振,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8]南野.结构精神分析学的电影哲学话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玛丽·安·多恩.电影与装扮:一种关于女性观众的理论[A].李恒基,杨远婴,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659.
[10]王一川.第二重文本:中国电影文化修辞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A].李恒基,杨远婴,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640.
[12]南野.结构精神分析学的电影哲学话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3.
[13]饶曙光.陈凯歌:从《黄土地》走来[EB/OL].人民网—人民日报,2014-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