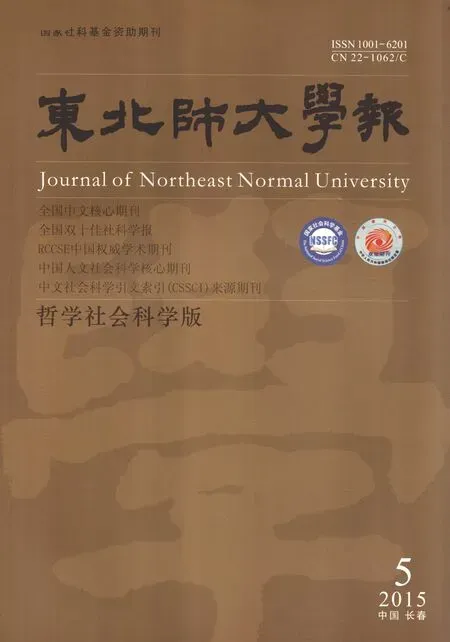对话与融合: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考察
王卫平,万 水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我们现在言及现实主义早已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狭小局限,也不会再把现代主义看作是“颓废”、“落后”的代名词。我们对兼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点的文学作品也早已习以为常,特别是当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们对那种融合了多种风格和手段的“魔幻现实主义”更是推崇备至。我们的这种文学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本文认为它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新老文学流派和各种关于文学的不同观点几乎在同一时间集中上演,场面可谓壮观。其间各种流派基本可以划归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派别。这两大流派的争论与相互靠拢构成了80年代中国文坛的基本样态。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二者的矛盾与斗争的方面,本文试图从二者相互融汇、借鉴的角度来考察,探究它们融合的实践和原因。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一)在艰难中前行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概念都属于西方的舶来品,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之行”是一次故地重游,其第一次“中国之行”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伴而来,它们共同的对手是以文言文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古典文学,所以当时作为同一阵营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歧和矛盾没有凸显出来。但是,很快“陈腐”的古典文学就被这股“新鲜”的异域艺术思潮冲垮,随之而来的是,伴随着对手的消失,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开始分道扬镳。由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革命”终于压倒了“启蒙”,而现实主义因为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一跃成为30年代以后的主潮。现代主义则由于过于注重个人话语、个性解放甚至是个人主义,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左右,对于文学说来,现代主义仅仅是一个含义不明的古怪概念。”[1]
1949年至1970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命运颇为奇特。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排斥现代主义,一般读者甚至不少当代作家都不大清楚有这样的思潮和作品存在。这一时期,为数极少的能够公开讨论现代主义的例外是茅盾的《夜读偶记》。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现代主义”真的绝迹了,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作品在一种叫作“内部读物”的内参性质的读本上生存着。这些内参书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60年代初刊印的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统所批判的“叛徒”或“修正主义分子”,如密洛凡·德热拉斯、特加·古纳瓦达纳等的作品;(2)60年代刊印的有关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如亚尔培·加缪、奥斯本、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等的作品;(3)70年代初刊印的有关西方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如费正清等的著作[2]125-126。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据孙绳武回忆:“1960年,作家协会的领导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苏联、东欧的了解较多,而同西方接触较少。这几次会议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的青年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3]这说明当时译介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基本也是当时正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也就是说,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共时性地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大陆,这也为日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创新或称叛逆的现代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
20世纪80年代初,和第二次在中国大陆重新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形成竞争的是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我国,五四时期伴随着强烈的西学东渐之风,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的各种艺术上的“主义”一起涌入我国,其时的学者根本没有时间来清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一时间“客观”、“写实”成为其时现实主义的特征;1933年2月出版的《艺术新闻》第2期刊登了林琪从日本《普洛文学》翻译的《苏俄文学的新口号》,在中国首次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同时30年代出现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40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提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说法;1953年9月,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我们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58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概念被提出;新时期初期,在第四次文代会前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三种提法经常同时登场,其中以茅盾和周扬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茅盾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一致性,而周扬更多的是维护“两结合”的最高指导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我国的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基本上集中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三个概念上,这三个概念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其共同的指向都是企图确立一种“最好”的文艺创作方法来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都强调文学艺术对人的启迪教育作用,都在一定程度忽视了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反映了文学的总体性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具体要求、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使命。”[4]
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我国的文学理论界虽然有着各种不同名号的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现实主义的框架,现实主义以外的流派是没有资格参与论争的。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在相较以往开放的文化政策下,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潮流与现实主义展开了真正地交流。
二、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一)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靠拢
贺桂梅根据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年)和何望贤选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争论集》(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概括总结出“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层含义:“现代主义”与“现代派”、“先锋派”在当时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它既可以指西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一个历史阶段或文学史阶段(历史阶段为从“一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史阶段为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衰落到经由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演变而来的现代主义文学阶段),又可以表示一个除现实主义之外的西方20世纪(加上19世纪中期的唯美主义)各种艺术流派的总体概念,这里涵盖了“二战”前产生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以及“二战”后产生的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各种艺术流派,如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2]139。
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实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量有关研究杂志的创办和专门出版机构的成立。其中杂志包括:《外国文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译海》、《外国小说》、《苏联文学》、《俄苏文学》、《日本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动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等;出版机构包括: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离出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第二,文化界多次围绕“现代派”的争论。这其中包括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进行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专栏讨论、包括徐敬亚事件在内的有关“三个崛起”的讨论,以及关于“萨特热”和存在主义的讨论。
这一时期围绕着现代主义的讨论,形成的主流立场认为:由于50—7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严密封锁,而这一时期又要有限度的接纳它,所以最好能够使其平滑过渡,从而将其纳入新时期的话语体系之中。用内容与形式的“两分法”,剥离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取其新奇、先进的表现手法,是其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在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主张在坚持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现代主义作为“补充”的观点,也属于这样一种立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实践最终结果不是越来越否定现实主义,而是渐渐地融汇了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的宣扬者为了能够尽快把现代主义“合法化”,大都采用了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化”的策略。规避掉现代主义的“唯心主义”色彩,使之尽量向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靠拢是现代主义的宣扬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所以就出现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构不成一对矛盾”的说法,因为“真正有价值的‘现代主义’作品也是‘反映’现实的,其中往往也有广义的现实主义,也有广义的浪漫主义。”[5]袁可嘉认为:“大多数现代派作家虽说以象征手法为主,目的还是在反映现实生活,只是侧重从内心世界来写。”[6]47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诸如心理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生命现实主义等,它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把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等一系列特有的手法纳入到了现实主义的范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陀在1986年的一次名为“现实主义及其发展”的讨论会上对当时现代主义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表述,他认为“现实主义在国外已分裂出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多种形态,中国也正在面临着这个问题。”叶立文在《“无边的现实主义”——论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策略》一文中,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在80年代现代主义为了能够顺利传播而采取的有意的“误读”策略[7]。
现代主义的宣扬者其次要做的工作是:给予现代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荒诞、悲观、虚无等思想内容以合理地解释。西方典型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如上思想内容一般都是某种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反映,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之于其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在8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多习惯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来解释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的合理性。如袁可嘉称:“现代派(又称先锋派或现代主义)文学总的倾向是反映分崩离析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和物质、自然和个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绝望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这样,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荒诞、悲观、虚无等思想内容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荒诞、悲观、虚无的表现,以及对其的批判[6]46-48。
现代主义的宣扬者第三要做的工作是:把一系列的经典现代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化,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李士勋、舒昌善的《表现主义》一文为证明卡夫卡的现实主义性,还引用卢卡契对卡夫卡现实主义的定性来为自己找论据。把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比肩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并将其称为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腐朽没落的反映,也是当时的论者的习惯性表述。
以上的所谓“现代主义的宣扬者”基本上都属于比较温和的一派,他们在解读现代主义的时候大都采用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视角,而且把现代主义看作是现实主义的新发展。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显然的“误读”并没有阻碍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相反,更加促进和加速了对现代主义的接受。其实,在把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化的过程中,论者们明显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现实主义和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的区别。“作为文学精神的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作家直面现实的精神,并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独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方法均需有这种精神。”[8]
也许这正应了法国人阿兰·罗伯格里耶的那句话:“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9]
(二)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敞开
从五四时期现实主义的概念传入我国开始,现实主义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被冠以一系列的非文学性限定语,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等,以致现实主义被弄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新时期开始以后,现实主义亟待恢复名誉,一系列关涉现实主义的讨论随之展开。其中有两个问题的讨论显示了向现代主义开放的趋势。
第一个问题:关于“写真实”的讨论。“写真实”一向是现实主义者对文学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是“什么是真实”这个问题却不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关于“写真实”讨论的实质内容便是讨论什么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以及追求艺术真实是否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其间产生了一些十分有见地的观点,比如王蒙发表在198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一文认为:“对于主观世界,真诚的东西就是真实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印象派、象征派、超现实主义……各有各的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各有各的反映生活的路子。从广义上说,我们是坚持文学要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望文生义地、轻率地否定其他流派和风格。”[10]虽说该文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的认识还基本囿于反映论,但是其对主观世界以及各种非现实主义流派的肯定,显示了其对文学艺术本质的宽容理解。
第二个问题:关于“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命题的讨论。
鲁枢元的《文学,美的领域——兼论文学艺术家的“感情积累”》一文是较早地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提出质疑的文章。该文认为应该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物质世界和文学家艺术心灵(如资禀、气质、人格、性情、思想、才学等)的有机结合体,而且,在这一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还应该是文学家的创作实践活动。”[11]周来祥也批评了把艺术归结为一种认识活动的观点,并认为艺术应该是介于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形态[12]。程麻则认为文艺活动不仅仅是认识活动,更表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所以仅凭反映论难说清文艺问题[13]。上述文章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从反映论和认识论角度解释文艺现象,更多地强调文艺的体验性、价值性、生存性等特点。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大大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范畴,使得心理现实、情感真实等主观要素合理、合法地进入到现实主义的范畴,同时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反映论和认识论的范畴,这都为在不否定现实主义的前提下肯定和融合现代主义做出了必要的准备。
到了80年代末期,学界出现了一种鼓吹“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该观点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彻底地批判和否定,提出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认为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当前我国文坛应该倡导的是一种“新现实主义”,它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继续,而是19世纪现实主义和五四现实主义的继承。而且“新现实主义”吸收和融合了现代主义因素,最重要的是它“吸收了现代主义的精神——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14]
三、结 语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思潮在其发源地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从时间上看,现实主义始于对浪漫主义的反拨,终于现代主义的兴起;从哲学基础上看,现实主义以唯物主义为基础,而现代主义以各种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为基础。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强调“模仿”与“再现”,强调真实性和整体感,强调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而现代主义强调运用变形、象征、意识流等手法表现作者内心的真实。那么它们为什么能够在80年代的中国文坛呈现出相互融合之势呢?原因有二:第一,中国的现实主义在被引进之时就没有足够重视在它的发源地所强调的“模仿”、“再现”两大核心[15],而过多强调的是对生活的介入精神和态度,这就为日后在现实主义范围内接受现代主义奠定了基础。第二,中国的现代主义本身就包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王富仁认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与“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相对的概念,它理应包括“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文学作品。”[16]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上兴起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现实主义重构”问题,即现实主义在新的时代需要下,根据新的现实发展的问题。讨论中,现实主义需要向现代主义开放成为一部分学者的共识。但是经过我们的考察,此种观点并不是90年代才开始形成的,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两种文学观念相互靠拢的趋势。关于文学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学观念的多元化是文学的本质性需要,一元化的文学观只能扼杀文学本身的多样性,历史已经证明其不足取,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在分类学意义上对诸种文学观念进行区分,否则一旦概念失去了边际,就等于取消了概念的自足性,加罗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和马尔科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就是前车之鉴。
[1] 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J].南方文坛,2009(4):6.
[2]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孙绳武.关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A].张立宪.读库0703[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82.
[4]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3.
[5] 卞之琳.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构不成一对矛盾[J].读书,1983(5):45.
[6]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J].百科知识,1980(1).
[7] 叶立文.“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9.
[8] 崔志远.重整现实主义的理论武库[J].文艺争鸣,2010(2):115.
[9] 阿兰·罗伯—格里耶.从现实主义到现实[A].柳鸣九.20世纪现实主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20.
[10] 王蒙.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A].郭友亮,孙波.王蒙文集:第6卷[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58-59.
[11] 鲁枢元.文学,美的领域——兼论文学艺术家的“感情积累”[J].上海文学,1981(6):43-44.
[12] 周来祥.审美情感与艺术本质[J].文史哲,1981(3):29.
[13] 程麻.仅凭反映论难说透文艺问题[J].当代文艺思潮,1986(5):76.
[14] 杨春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J].文艺评论,1989(2):16.
[15] 张传敏.中国左翼现实主义观念之发生[J].文学评论,2008(1):30.
[16]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上[J].天津社会科学,199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