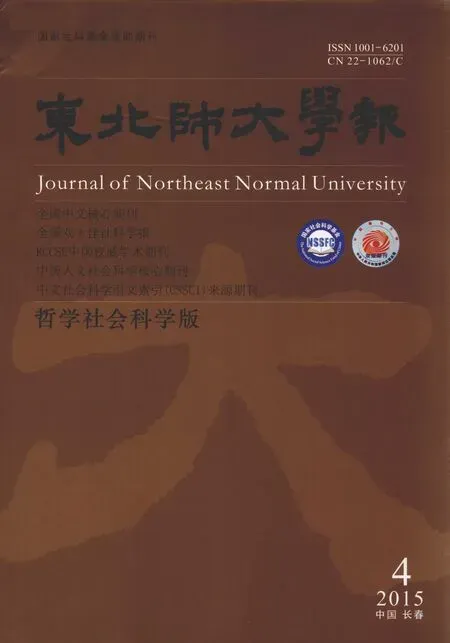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批判和启示
李 鸿,王冰玉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批判和启示
李鸿,王冰玉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和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界遇到了“理论过时”和“理论局限”的挑战。其中,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中所提及的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在西方社会劳动过程背景中失效,就是其中的标志性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是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精髓为基石的,尤其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中国经验的工厂政治和劳工处境在特定时代相遇,都迫切需要我们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精髓进行再阐释,并对其当代意义进行理论探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精髓是立足于劳动实践,以劳动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劳动的解放为取向的辩证劳动过程理论。布洛维误解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精髓,其劳动过程理论是二元的、僵化的和保守的劳动过程理论,而且,他提出的“制造同意”机制论没有超越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视域。中国经验的工厂政治和劳工处境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当代现实印证。
马克思;劳动过程;工人;布洛维;资本
一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在当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思想中遇到了“理论过时”和“理论局限”的挑战。布洛维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就是其中的标志性挑战。布洛维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产业工人的社团化和产业斗争的体制化使得资本主义的劳资冲突不再凸显,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并不能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只有从工业社会学的视角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布洛维尝试了在一个公司长时间内对劳动过程进行的细致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布洛维在对“联合公司”调查的经验主义语境中,提出了“超额游戏”的生活基础和资本主义制造工人同意的机制,并认为自己正确地回答了为什么工人会卖力地工作的问题。“大体上,工人们并不将他们生产的产品与他们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差别归结到自己的劳动中。关于剥削与无偿劳动的观念,在今天的车间日常生活中比起马克思的时代更加感受不到了。”[1]49布洛维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并认为劳动过程应当从强制和同意的特定结合方面来进行理解,这种结合能够诱发资本家与工人在追求利润当中合作。
作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是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石和精髓的,尤其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中国经验的工厂政治和劳工处境在特定时代的相遇,都迫切需要我们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精髓进行再阐释,并对其当代意义进行理论探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精髓是:立足于劳动实践的辩证唯物史观,通过劳动实践的认识与反思过程,追求劳动异化的解放过程。
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批判布洛维,我需要在下文中阐释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的精髓并标明布洛维理论误区和对马克思的误解,提出应当恰当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清晰地看到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的缺点和不足。布洛维是一位“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有所改进。他通过组织理论、前后资本主义的比较以及“超额游戏”分析对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探索与思考。布洛维力图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组织理论结合起来考察车间组织特征,用工厂社会学视角提出劳动过程中“制造同意”机制,但它没有超越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视域。中国经验的工厂政治和劳工处境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当代现实印证。
二
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一书中首先借用马克思的思想论述到:一切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因而也是一切历史的前提,是人必须处于某个位置生存从而才能够创造历史。然而,生存首先需要饮食、居所、衣物、和许多别的东西。因此,第一件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求手段的生产,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将自然转变为有用之物。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进入了彼此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就形成了。如此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特定关系界定了经济生活的性质,即生产样式和生活模式。历史是由不同的生产模式构成的,生产关系并不只是界定了如何分配与占有劳动时间及其产品的特定方式的一种关系。它还是一种占用自然或者生产有用之物的特定样式。从而,生产关系总是与一组相对应的关系相结合,人在对抗自然,将原材料改造成他们想象之物时进入的关系,就是劳动过程。劳动过程有两个不可分但有别的方面:关系方面和实践方面[1]37。布洛维又阐述到:资本主义下工人们不能独立于资本家而自行开动生产工具,不能靠自己改造自然以及自主地提供自己生计所需。他们是被剥夺了对自己的生产手段——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使用权的。为了生存他们别无他法只有出卖自己劳动的能力——劳动力给资本家以换回工资,然后他们再将工资变为生存手段。在为资本家的工作中,他们将自己的劳动力转变为劳动;他们的工资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在工作的整段时间的补偿。事实上他们只是被给付工作的一部分价值款项。剩余劳动价值则作为市场上的利润而被实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空上是分开的。劳动的整个产品是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们不能依靠他们在车间里生产的东西生活,唯一途径是通过市场、通过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换回工资,再换回消费品。工人们既不拥有生产工具,他们也不能自主使用。他们是通过对资本的代理人——指挥劳动过程的经理——的臣服从而从属于劳动过程。管理的目的是企图从工人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关于生产活动的斗争发生在车间里[1]195(注释4)。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他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劳动与资本的结合才能实现双方的需求。商品生产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布洛维有明显肯定马克思的部分,这也是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的合理成分。但是布洛维又认为:劳动过程的关系是生产中的关系或生产关系。生产的政治与生产中的关系相连,全局政治与生产关系相连。如果剥削剩余劳动的生产模式即特有的生产社会关系要被再生产就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这个机制就是必须有保证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一套机制——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关系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或变革。布洛维还强调,车间里的活动不能脱离生产组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工人们的理性是一种特定生产组织的产物,是工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38。自此,布洛维已经彰显了其劳动过程理论的二元论性质。
布洛维批评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大体都是基于劳力的付出是由强迫来决定的假设,认为马克思在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中没有为同意的组织留出空间,而同意的组织对诱发劳动者在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中具有合作意愿是必需的。在劳动过程中,同意的基础在于仿佛为工人们呈现了真实的选择,但又明确地限定了这些选择应是什么的这些行动的组织。正是这些对选择的参与产生了同意。剩余价值的保证也必须作为强制和同意的各种组合的结果来理解。布洛维通过考察联合公司在劳动过程的变化,阐明了上述机制:在车间内组织同意、使工人成为个体而非阶级成员、调整劳动和资本之间以及工人和经理之间的利益。至此,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的二元论性质已跃然纸上。
布洛维从二元论出发,夸大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车间政治对工人劳动过程的影响力,把加大剩余价值追求力度的资本家贪婪行为与工人自愿同意工作行为看作是同一性的东西。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利益分化的至极之处加上了工人同意的法码,无视劳资矛盾正由于工人暂时同意的表象背后劳资逐渐紧张和崩解的危险。此处,有一个富有嘲讽意味的事件对我们的观点是一个事实的印证:布维30年后又回到了他立足于民族志考察的联合公司,发现整个芝加哥南部在工厂一家接一家的关闭之后成为一个工业的死寂之地,联合钢管厂是维持到最后的企业之一,它最终没有摆脱倒闭的命运。所以,布洛维的劳动过程理论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
三
在生产生活表象世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布洛维认为,马克思作品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自主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关系是被历史地决定的,而他却强调生活经验及其加诸于意识形态之上的限制。统治阶级被意识形态所塑造多过他们塑造意识形态。生活经验产生了意识形态,而不是反过来。意识形态植根于使之出现的行为并表达了该行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具体幻想的创建,它作用于被分离和打散的人们,使之觉醒并组织其集体的意志。”意识形态担当了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它使个体彼此结合;它使当下的经验彼此相连,也使之与过去的、未来的经验相连。由于意识形态表达了人们体验关系的方式,所以通过意识形态“人们意识到……矛盾,并通过斗争来解决它”。当斗争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时,斗争的后果必须通过细查意识形态背后的真实关系来理解。但是,布洛维紧接着问到:如果这些斗争不是关于利益实现的斗争,那它们又是什么呢?并且利益显然是从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并认为此时遭遇了从实际与假设行为之间的差异中滋生出的下述问题,即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的、利益的实与虚、短期与长期、直接的和根本的等问题。
布洛维认为,利益不能在对社会关系的特定自发意识之外来理解。利益并非完全系于一个既定社会,并不是该社会与生俱来的,利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个体在其中变成超乎他们控制的动机的奴隶。利益的表达传达出对需求已经堕落为贪欲。“阶级利益”不可能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动机:真正的动机,要从拜物中解脱出来,被工人阶级的“根本需求”所代表。布洛维问到:“但是资本主义容许这种根本需求吗?它是否像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资本主义产生它们来作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呢?如果这样,那又是如何这样做、在哪里这样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呢?并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根本需求可以在新社会中实现?什么样的环境可以成为将潜在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基础?”
布洛维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中同样强调工作现场和劳动过程在引发工人斗争方面的中心地位。但是,他作为一名“生产中关系”的民族志研究者指出,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那就必须考察劳动生产过程怎样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塑造了工人阶级。在书中他强调了与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是怎样在工人“同意”的基础上确保和掩盖了剩余价值。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布洛维有关利益在意识形态中的根植性和意识形态对现实劳动生产的形塑之思想,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立场,否定了劳动过程的辩证法。按照马克思劳动过程辩证法,劳动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劳动之所以能改造世界,在于人在劳动中形成的意识通过反思现实生活世界,使劳动按照人的意愿改造现实生活世界。社会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现实,是通过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超越,是否定现实的结果。布络维心目中的意识形态是与劳动过程关系的现实直接同一的,他忽视了意识形态基于对劳动过程反思性而作用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动力量,最终否定了劳工运动辩证法。
布洛维不仅把马克思的部分思想融进组织理论,并定格在组织框架中,实质上是抛弃了马克思劳动过程辩证发展的理论精髓。尽管布洛维一再强调他的劳动过程理论把劳动看成是“活劳动”,并自许克服了组织理论结构性分析的行动与结构的混淆,批评了社会学以诸如“角色期望”的观念摧毁了关系与行为之间的区别。但实质上,布洛维的理论仍然是僵化的关系与行动的同一性分析。布洛维批评马克思仅仅主张没有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就将崩溃的事实,而没有解释资本主义的存在,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商品论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存在的解释。剩余价值的追求和劳动价值市场化、商品化的事实是劳资结合的根据和理由,也是劳资关系运动的内在机制。剩余价值的追求程度和劳动产品资本化程度则决定了劳资关系紧张的程度。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工人们尚处在没有形成阶级觉悟的“自在阶级”阶段,而不是劳资关系崩解时的“自为阶级”。
四
布洛维认为,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与强制导致严重的劳资冲突,从而引发的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在西方社会没有发生,而他立足民族志考察的“超额游戏”则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超额游戏”中可以看到,资本家们狡猾地将劳资矛盾转移成为工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或管理者们强调和谐,内心却关注工人之间的冲突的出现。游戏中的玩家即资本家思考的重心是采用何种手段来提高效率。“游戏隐喻暗示了一个带有自身‘法则’的‘历史’,它超出了我们的控制,然而却是我们行动的产物。”[1]99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体现了工人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不仅使工人产生“同意”,还是给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超额游戏”的最终目标是对资本家利益的产生与形成,是不可能以工人的利益为转移的。在规则和关系的固定性情况下,“超额游戏”将满足人的需求的可能性作为工人参与劳动过程的诱因。
布洛维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工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工人对整个劳动过程的认同感,忽视了组织文化背景的稳固性和管理者的强大操作性。而他看到的“超额游戏”则对增强工人满意感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当超额已经成为一种“乐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计件工资制在经济之外的价值:“超额游戏”可以“使工人不至于无聊”。“超额游戏”因为满足了工人们的“相对需求”,因而再生产了“自发的奴役”。“超额游戏”体现的是矛盾的隐藏或者说是矛盾的转移。一方面,一旦工人被锁定在一个固定的职位时,他们就容易为了求取更好的报酬比率而与底层管理者、时效调查员、辅助员工之间产生冲突。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这种流通,在减轻了阶层之间的纵向冲突时,往往制造出更多的横向的冲突。技术和组织在“超额游戏”中起作用,机床、刀具等生产工具的改进使生产更少地受制于任意的停顿,但工资率也可能更加严格了。车间流行将工作分为“有油水”和“脏活”两种类型,前者有着格外宽松的工资率而后者则有格外严格的工资率。布洛维观察了工人作为个体参与劳动过程的自主性,认为同意是从事这些行为的个体承载的一种主观的思想状态,是通过行动组织来表现且也是行动组织的结果。同意应当在劳动过程中,同意的基础在于仿佛为工人们呈现了真实的选择,但又明确地限定了这些选择应是涉密的这些行动的组织。正是这种对选择的参与产生了同意[1]47-48。
我们认为,布洛维对马克思的批评是表面的,不能令人满意,他没有理解马克思劳动过程深层次的意涵,布洛维误解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实践意涵,不懂得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所蕴含的劳动解放追求。尤其他没有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工在劳动中被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所异化的内在机制。马克思眼中的劳动实践不仅仅是将原材料转变为制品,也不仅仅是通过劳动实践活动展示人类创造潜能,而是要凸显劳动实践促使劳动者的自我觉醒与劳动解放。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使工人的劳动转化为商品和资本,从而使劳动成为自己的对立物,而且,“工人被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工作机器上劳动,工人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了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因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人的异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的存在未必是合理的,虽然它的存在还有它存在的理由。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为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一切事物是暂时的,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的觉醒促成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而布洛维则强调了生产关系方面表达了自由合作的生产者组成族群共同体的潜质,生产关系塑造了劳动过程的形式和发展,而劳动过程反过来为生产模式的转型设定了限度。布洛维将超额游戏植入联合公司车间内部的考察,脱离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全社会性,弱化了工人与资本家依靠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为纽带的劳资结合关系的张力和冲突,仅就超额游戏发生的意识形态的塑造,仅以超额游戏的“乐子”为根据,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意”机制的促成和意识形态的塑造,认为车间政治对劳动制约的力量超过对剩余价值追求带来劳资冲突力量,并把这种游戏中的“乐子”作为工人实践生活的根据和理由,以此阐明游戏是如何有助于掩饰并确保剩余劳动的。这是放弃了根本性的深刻社会关系力量,抓住了临时性的表面的社会关系力量,放弃了强大的全局性和社会性的矛盾,仅顾局部的车间内部的劳资同一性,贬低了工人阶级反思、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的能力。从根本上不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因而布洛维没有理解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不可超越性。其所谓的“同意”不是建立在对劳资关系的充分认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车间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干扰基础上,因而,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是暂时的、不确定的、脆弱的。因为布洛维不理解社会发展与劳工运动的联系,最终偏离了劳动运动解放的立场和社会永恒发展的立场。
五
布洛维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将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重要的一环进行主题化,从而解释工业社会学的合理内核。正如梁萌所评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过程的理论是布洛维整个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布洛维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将生产与政治相联系的理论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详细分析了生产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将生产体制的变迁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变迁联系起来,并关注各自的内部变化与影响。最终,布洛维希望通过这些寻找到社会主义实现的理想道路以及工人阶级在实现这一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布洛维的研究为后继的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2]这种理论和理论探索虽然难能可贵,但是他是否真正完成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与组织理论优势有效结合的研究任务呢?这对于研究劳动过程问题的研究者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我们可以通过对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缺点和错误的批判,联带性地研究西方各种形形色色的所谓超越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潮流,也可以以此纠正中国学术研究中对西方劳动过程理论的盲目崇拜,比如,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发达国家工业社会的原有的生产形式逐步被新的生产形式所替代,在后工业生产条件下,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创造日益改变社会关系,并生产人际关系的生态政治[3];哈利·布雷弗曼则在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中认为,马克思的利润公式过于抽象,无法给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存在着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劳动逐渐退化的历史,资本通过深化劳动分工特别是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从工人手中夺取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工人退化为一个生产工具,并认为战后劳资关系的不断发展恰恰是资本家对于工人控制不断增强的过程[4];1977年,弗莱德曼出版的《工业与劳动》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工人抗争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没有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回应其内部矛盾(如工人抗争)而调试自己、使得其生产方式得以维持的。重要的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适应工人抗争的,而不是简单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因为工人抗争而可能被推翻的。波兰尼非常注重市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主义。他还认为,资本主义最破坏基本人性,把多样性的个人转化为利益的算计者,世界必须在两个极端中选择:要么是法西斯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葛兰西由于俄国的十月革命而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他将关注点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一个包括国家和社会的相对自主领域,将上层建筑来划分资本主义的标准。但是他的理论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一种具体化和空想[5]。有学者对继马克思之后研究劳动过程理论的社会学家们的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认为他们都保留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即认为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只是购买到一种劳动的潜力,也即认为劳动力是一种可变资本。这种可变性意味着把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利润的有效劳动需要资本对劳动过程进行系统的控制[6]。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西方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阶段过渡,但是许多国家经济体系仍然停留在工业领域,而且经济体系是在全球范围内运行。“如果说工业在西欧和北美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那主要是因为在一种新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中,他已经被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3]
我们还可以通过批判布洛维等人的劳动过程理论,推进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精髓的再阐示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形式的变化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理论过时了呢?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精髓对当代社会劳动生产变化中的适应性研究显得非常重要[7]。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精髓与组织理论优势结合起来研究,走出一条普遍适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工厂社会学的学术研究道路,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走向世界学术前沿和学术论坛。
我们还可以通过批判布洛维劳动过程理论,推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中国劳工的状况、工厂处境的本土研究。尤其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仍然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加快经济建设,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是我党面临现实国情进行的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策略。在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下,非公企业迅速崛起和车间政治的需要的矛盾,解决中国企业发展和劳动权益维权的张力问题,推到日程上来。世界工厂向中国领域的扩张,也急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理论支撑和理论解释,有效排除我们对新形式下人们对中国劳动问题和企业发展问题的错误认识和思想的迷忙,推进中国特色的劳工运动理论都有重要意义。
无论上述哪种需要,都迫使我们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进行再认识,通过批判布洛维等人的劳动过程理论思想,彰显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生命力,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
[1] [美]麦克·布洛维.制造同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梁萌. 在生产体制中发现工人阶级的未来——读布洛维劳动过程三部曲之一《辉煌的过去》[J].社会学研究,2007(1):229.
[3] [英]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1):33-34.
[4] 闻翔,周潇.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7(3):30.
[5] [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01-225.
[6] 游正林.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有关文献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6(4):182-183.
[7] 涂良川,李爱龙.劳动与需要: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双重视野[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85-90.
Burawoy’s Labor Process Theory Cri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LI Hong,WANG Bing-yu
(Faculty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Marx’s labor process theory encountered challenges of “theory old-fashioned” and “theory limitation” during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among the West and Western social science intellectual. One of the iconic challenges is the Burawoy’s labor process theory which mentioned the failure of Marx’s labor process theory in the Western context. The Marx’s labor process theory with China’s political ideology is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labor process,especially the meeting of Marx’s labor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actories experienced political and labor situation in a particular era encounter,we have an urgent need to reinterpretate the essence of the Marx’s labor process,and to explore the theory of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he essence of Marx’s labor process theory is based on the labor practices,with the fou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which is a dialectical process theory orientating to the liberation of labor. Burawoy misunderstood the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of labor process,whose labor process theory is binary,rigid and conservative labor process theory. What’s more,his “manufacturing consent” mechanism does not go beyond the horizon on Marxist theory of labor process. Chinese factories experienced political and labor situation confirms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Marxist labor process theory.
Marx;Labor Process;Workers;Burawoy;Capital
2015-03-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A009)。
李鸿(1965-),女,吉林通化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王冰玉(1992-),吉林白城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研究生。
A811.1
A
1001-6201(2015)04-0088-06
[责任编辑:秦卫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