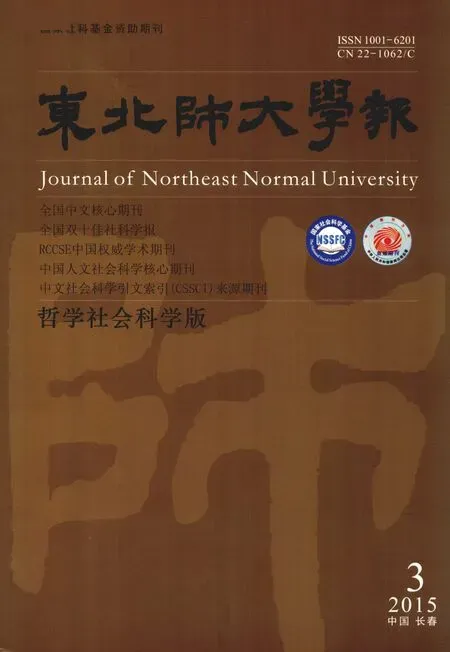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变异性接受
高 红 梅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变异性接受
高 红 梅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托尔金、刘易斯和罗琳等为代表的英国现代奇幻文学借由立体化的现代传媒席卷全球并进入中国,从而催生了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中国玄幻小说在接受英国现代奇幻文学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过滤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制约,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接受发生了变异,主要体现在创作机制与传播方式、文本写作以及文化动因三个方面。在多元文化并存与社会转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玄幻小说面临缺失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特色与人文传统失落的尴尬境地。
奇幻文学;玄幻小说;变异性;文学接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奇幻文学随着《魔戒》、《哈利·波特》等系列电影和小说进入华语世界,并逐渐渗透到文化产业的各个层面,从而引发了大陆读者对奇幻文学的兴趣与旺盛的阅读欲望,网络上的玄幻小说大潮也随之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玄幻小说是在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从英国奇幻文学到中国玄幻小说,经历了一次次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交流与实践,文化过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因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1]。在英国奇幻文学与中国玄幻小说的交流过程中,中国玄幻小说创作者总是不自觉地以中国文化语境来理解英国现代奇幻文学,从而使得英国现代奇幻文学被误读、异化甚至遗漏;同时,伴随当代文化转型语境的浸润,中国奇幻小说的创作产生了迥异于英国奇幻文学的样貌。
一、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生产
英国现代奇幻文学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牛津大学教授托尔金创作的《霍比特人》和《魔戒》的出版为标志,托尔金也由此被誉为“现代奇幻文学之父”,这一派作家还包括C·S·刘易斯和J·K·罗琳等。托尔金开启的奇幻创作传统,不仅深受图书市场欢迎,而且屡次荣获雨果奖等严肃文学奖项。中国玄幻小说的产生可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电玩杂志《软体世界》的“奇幻图书馆”,甚至于更早期香港作家黄易所指认的“建立在玄想基础上的幻想小说”,而真正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是以2002年专门登载玄幻小说的“起点中文网”成立为标志。由于产生的时代语境不同,这一切都使得英国现代奇幻文学与中国玄幻小说从生产机制到传播手段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回首英国奇幻文学初创时期——20世纪30年代,托尔金和C·S·刘易斯在牛津大学附近的小酒馆相约各自写一部奇幻史诗,它们就是后来誉满全球的《霍比特人》与《纳尼亚传奇》。关于托尔金的《霍比特人》的灵感来源,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一次,托尔金在给学生批考卷时,遇到了一张空白卷,随手在上面写下了“In a hole in the ground there lived a hobbit”(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这引发了他一系列的联想,霍比特人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从此,中土世界诞生了。可见,奇幻文学是作家主观创造的精神产物,具有原创性与不可替代性,不是亦步亦趋的“山寨”,更不是对某种既定程式的偷梁换柱。“独创性可以说具有植物的属性:它从天才的命根子自然地生长出来,它是长成的,不是做成的”[2]。到20世纪末,欧洲奇幻文学被J·K·罗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她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畅销全球,被翻译成65种语言,销量超过4亿本,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英国奇幻文学非同凡响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促使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与现代电影技术相遇,《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魔戒三部曲》等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神话。
从文本到文本的图像化,英国奇幻文学完成了从创作到传播的漫漫长路,延续了文学创作引导文学接受的传统话语秩序和审美范式。与此相反,中国玄幻小说对英国奇幻文学的接受过程,却走了一条文学消费决定文学生产的路径,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固有格局。
大陆本土与英国奇幻文学接轨恰逢《魔戒》系列影片上映之际,译林出版社借由电影版海报的宣传效应,在《魔戒》出版之时创下了2 000多万码洋的销量。随着电影《魔戒现身》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中国的热映,读者阅读奇幻文学的需求不断高涨,2002—2003年期间中国网络写手兴起了模仿英国奇幻文学的风尚,网络文学也从此走上了一条玄幻之路。我们发现,在接受英国奇幻文学的影响时,中国本土正处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转型大潮之中,新媒体文化市场与网络文学的消费热潮,导致了中国玄幻小说大潮的出现。“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的、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动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3]。中国玄幻小说的文学生产是以网络的点击率为基准的,不是以作家的主体创造性为起点,而是将文学活动框定在生产、流传、阅读、接受、再生产的商业运作之中,文学写作从自由的创作变成了依据读者审美倾向、阅读习惯等诸多社会因素的生产。
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民众身受生活与精神负重的双重挤压,追求阅读娱乐化、平民化倾向明显,网络玄幻小说迎合了大众这样的审美需求。逐梦的虚幻空间与魔法世界让读者可以暂时逃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剑侠、魔法师的神通广大补偿了读者受世俗制约的失衡心理。而网络的对话性与平等性,则赋予读者以参与创作的广阔空间。奇幻文学最大的受众群乃是青年一代,他们在文化趣味上追求“高度的丰富性和高度的游戏性”。“这些青少年成了中国现代以来最敢于消费的一代……他们的趣味和爱好现在主导了文化消费的走向……于是,这种和电子游戏相关联的玄幻文学就有了异常广阔的发展前景”[4]。“起点”中文网、“天鹰”、“龙的天空”等专门玄幻网站的点击率激增,甚至可以达到千万。到2012年6月,“幻剑书盟”网站的《诛仙》网络点击率已经达到52 016 573次[5]。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截止到2013年,玄幻小说(包括玄幻、仙侠)与都市类小说继续居于网络文学主流[6]。
二、从原型的本土化到本土化的皮相
奇幻文学的英文名称是“Fantastic Literature”,从属于幻想(fantasy)文学。托尔金认为,奇幻文学旨在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无关但与现实平行的“架空世界”,那是一个充满英雄、神怪、超越时空的魔法世界。中国玄幻小说也接受了奇幻文学的影响,追求作品的“架空性”,但英国奇幻文学与中国玄幻小说对“架空性”的理解与表达却是有差异的。
“架空世界”是奇光异彩并充满魔力的,但其背后所包含的厚重文化底蕴才是英国现代奇幻文学魅力的真正源泉。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架空世界”充满着深厚的凯尔特文化原型,既包括来自北欧古代神话传说、史诗与骑士文学的原型,又涵盖了基督教文化原型。从叙事模式来看,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移用了《圣经》、中世纪英雄史诗及骑士文学中善恶对立的模式来结构作品。这种模式“通常涉及神祇或魔鬼,并呈现为两相对立的完全用隐喻表现同一性的世界,人们向往其中之一,厌恶另一个。与这种文学同属一个时代的宗教中存在着天堂和地狱,所以人们往往把文学中的两个世界分别与天堂或地狱等同起来。”[7]刘易斯以纳尼亚王国与恰恩世界的对立象征天神与魔鬼的对抗;罗琳通过魔法世界与麻瓜世界的并存隐喻天堂与地狱的对立。从英国现代奇幻文学惯用的意象来看,宝剑、巫师与英雄在作品中不断复现。剑的原型最早可追溯到冰岛史诗《埃达》中的“格拉墨”,《贝奥武夫》和亚瑟王文学都沿袭了北欧神话中把剑作为意象塑造英雄形象的传统。巫师意象代表着魔法世界的神秘、灵性,英国早期的巫师名称来自凯尔特语Druid,凯尔特文化有久远而又深厚的巫术传统。从奇幻作品的母题来看,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追寻母题。例如,哈利·波特寻找魔法石,《魔戒》中各个人物对魔戒的追寻以及《纳尼亚传奇》中凯斯宾为找到勋爵旳历险。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凯尔特文化原型潜在的意义模式使这个“架空世界”显现为一个完整的神话系统,它源于英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却又是一个全新的神话世界。托尔金、刘易斯是研究中世纪语言、文学的资深专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重新建构神话已成为他们自觉的追求。在追忆《魔戒》的创作过程时,托尔金说:“在1937年《霍比特人》一书写出,但尚未付梓之前,我就开始写续篇,但中途一度搁笔,因为我想先将上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收集整理完毕,并理出头绪来。”[8]对创造奇幻世界的目的,托尔金的说法也最具有典型意义,“恢复英格兰的史诗传统并以自己的神话的方式表现出来”[9]。
中国玄幻小说也试图以“架空性”来印证自己的奇幻身份,达成与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顺利接轨。但中国玄幻小说以电子游戏的方式虚拟中国传统文化的皮相的同时,抽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养分,在“架空世界”中张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又毫无节制。
众所周知,所谓“架空性”是指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平行,是一种对世界的重构与创造。在英国奇幻文学进入大陆本土两年后,中国玄幻小说似乎很快就完成了从魔法、巫师到武功、武侠的本土化,具有中国古典文化意味的名字也频频粉墨登场,将神话传说和各个朝代的人物、古籍中的动物、植物和器物直接复制并粘贴到文本之中,拼成一个个“架空世界”,如同毫无连贯性与内在联系的镶嵌画。玄幻小说这种表象上历史文化的热闹、繁盛反倒突显了玄幻写作的机械性、随意性,结果不仅没有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玄幻小说想象力的支撑与源泉,甚至还成为玄幻小说生搬硬套典故、牵强附会历史的策源地。中国玄幻小说本土化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借鉴并融合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写法,尤其是萧鼎的《诛仙》被人们誉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但如同《诛仙》一样,很多玄幻小说都没有发掘并继承武侠小说的精髓,即武侠小说不仅展现了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层意义上的契合度。学者陶东风指出,“以《诛仙》为代表的拟武侠类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它专擅装神弄鬼,其所谓‘幻想世界’是建立在各种胡乱杜撰的魔法、妖术和歪门邪道之上的,比如魔杖、魔戒、魔法、魔力、魔咒,还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怪兽、幻兽。这些玩意儿可谓变幻无穷,魔力无边。”[10]
中国玄幻小说以戏仿、拼凑的方式粉饰自我,以中国传统文化之名给自己冠以文化的标签之时,读者收获了瞬间的快感,但传统文化的博大与深厚也随之弥散,失去了精神的内涵。再者,当中国玄幻小说将历史文化碎片化、零散化处理,历史失去了线性的逻辑,成为一种共时的空间。在这样的文本面前,人们区隔历史、现实与未来已经毫无意义了,历史意识消失的同时,中国玄幻小说也出现了“深度消失”的问题,平面化、浅表化成为其显著特征。最后,中国的传统文化难以成为玄幻小说的底色时,传统文化被消费、消耗的同时,会有更多浅表化的历史文化充斥于玄幻文本之间,很难在其间发现作者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在玄幻小说中传统文学所追求的主体性、创造力与终极关怀纷纷败走麦城。在这个意义上,玄幻小说本土化只停留于“皮相”,难以真正消化与借鉴英国奇幻文学的本土化。
三、从寻找失落的人文传统到人文传统的失落
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热潮席卷全球,但是,透过英国奇幻文学的轰动效应造成的喧哗与骚动,我们可以发现更为深层次的西方文化思潮——对失落的人文传统的寻找。
英国现代奇幻作家托尔金与刘易斯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毁坏力让他们重新反思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他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如同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人类提供了开拓世界、改造世界的崭新手段并创造了强大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灵魂陷入日渐枯萎的境遇。“这是一个不但丧失了众神,而且丧失了灵魂的世界,随着我们的兴趣从内心世界转移向外部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与早期的时代相比增加了一千倍,但我们对于内心世界的知识和经历却相应减少了。”[11]托尔金和刘易斯作为深谙古典神话体系的牛津学者,他们希望通过“架空世界”重构一个属于英语世界神话体系的目的在于,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寻找失落的人文传统。“托尔金怀疑甚至是蔑视20世纪,他有那么一点点勒德主义思想*勒德主义:强烈反对在任何领域推行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主张,反对机械化、自动化。,认为科学与科技对人类的命运毫无建树。……可以说他并不希望生活在现代世界,而他对现代社会的不认同心理从某些方面来说,刺激了他的创造力,他更喜欢中土’。”[12]刘易斯也通过《纳尼亚传奇》,“为普通读者恢复了已经失落了几个世纪的能力,即理解隐喻和回应隐喻思维方式的能力。”[13]
托尔金与刘易斯对失落人文传统的寻找,暗合了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时代运动”,而正是“新时代运动”的文化思潮成就了英国现代奇幻文学近20年来的畅销神话。所谓“新时代运动”就是要破除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体系,复兴长期被挤压到边缘或遭到迫害的异教思想及相关知识体系,涵盖了巫术文化、原始信仰、占星术、炼金术等,恢复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对灵性的重视。新时代运动掀起了西方社会文化寻根的热潮。托尔金、刘易斯和罗琳所构建的“架空世界”(魔法世界)的内核,就是凯尔特的巫术文化。奇幻作家们将失落的凯尔特文化作为他们反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反思现代性的一种文化资源,并希望建立“二希”之外的一种新的欧洲文化范式及其社会信仰与价值体系。“无疑地,新时代运动正在冲击和形塑着西方文化,甚至有人认为,新时代文化已经与基督教和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并驾齐驱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文化。”[14]
当英国现代奇幻文学携着西方的文化寻根热潮与中国文学产生交集时,从学界到公众的关注都聚焦在“魔幻”本身。对于文化寻根热,除了叶舒宪等学者中国学界很少有人问津;而中国文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寻根”热也早已冷却。在消费主义盛行、人心浮躁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玄幻小说创作的核心目的就是娱乐至上。
中国玄幻小说是与中国时下的流行文化同呼吸、共命运的,流于创作的扁平化,从而丧失了小说的文学性与人文精神。玄幻小说的“架空世界”来自文学与电子游戏、网络的结合。首先,玄幻小说写作手法追求游戏化,而忽略其文学性。作者更倾向于追求画面切换的快速与炫酷,以带给读者感官上的冲击为能事;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扁平化趋势;单一强调故事情节的历险模式,并设置闯关、修炼等环节以增强读者的参与性。游戏化的写法体现了玄幻小说的娱乐性,却抹杀了价值意义的理性维度,将创作变成了纯粹自我的展示。其次,“架空世界”是文学与网络的结合。中国玄幻小说是网络文学的一种类型,兴起、繁荣于网络,写手多半都出自理工科专业,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作家或难以成为专业作家,他们只能被称为“网络写手”。进入玄幻小说的网络写手,只要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熟谙玄幻小说的情节模式、对文字和故事有驾驭能力,就能进入这个比传统文学门槛低的写作领域。作为网络文学,玄幻小说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网络小说发表的形式是网络连载,网络写手的写作要义在于不断提高点击率,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写作的主观能动性。网络写手只能靠新、奇、炫、酷甚至于“卖萌”来取胜,至于作品的文学品质、理性思考与人文内涵都已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能给读者提供的不是丰富的精神养分,而是寡淡的速食面。在2005年中国玄幻年的繁荣之后,中国玄幻小说的创作仍然存在良莠不齐,数量与质量难以成正比的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玄幻小说“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停滞转型时期”。
中国玄幻小说在追求娱乐至上的途中,既丢弃了本土文化的衣钵,又丧失了现当代文学传统的人文精神,将文本变成了纯粹自我表达与商业利益的工具,玄幻小说也就沦为了市场的奴隶,这是中国多元文化并存而又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必然结果。
在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语境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与融合是比较频繁与剧烈的,这会引发三种情形。一种情况是,在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照中,对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逐步增强,而坚守本土文化立场;另一种情况是,被全球化的魔力吸进外来文化的风潮之中,在消费风尚来袭中模糊了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理性上认同传统文化,但很难在商业逻辑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在传统文化的定位中放纵娱乐至上的欲望与诉求,体现了面对文化多元的迷惘与困顿,如当下的中国玄幻小说。
中国玄幻小说不仅要面对多元文化的语境,还要遭遇中国文化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开放的程度也日益扩大,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文学遭遇到了更深度的焦虑。一方面,在社会改革的震荡之中,原有的思想价值体系、伦理观念、生活态度遭到破坏,而新的还在重建过程中;另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当下中国出现了社会进化的“压缩”与“重层”现象。“宇野木洋教授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完成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完成这个过程,欧洲用了几百年,日本用了一百几十年,而中国只用了几十年。这是对中国进化过程的一种‘压缩’。正像中关村的高科技、工厂的大机械生产、走进郊区就能看到的前近代的农业耕种同时并存所象征的那样,和这一‘压缩’直接相关的是社会存在的‘重层’现象。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学都存在着同样的‘压缩’和‘重层’。”[15]中国玄幻小说的“重层”在于,在中国玄幻小说借鉴英国现代奇幻文学的过程中,英国现代奇幻文学所竭力批判的技术理性与物质主义,恰好是它进入并促使中国玄幻小说产生的外部条件与动力,而试图实现本土化的中国玄幻小说却在本土化的路途中失落了人文传统,走向了英国现代奇幻文学寻找失落人文传统的反面。
四、结 语
中国文学一直都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作家也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精英意识,虽然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争议不断,但一直具有独立的存在意义与美学意识。上个世纪末以来,面对多元文化并存与社会转型的阵痛,在社会“压缩”与“重层”的挤压下,文学已经沦为大众媒体的脚本,这标志着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人文传统旁落、世俗价值兴起的中间断裂带。文学娱乐化固然不能绝对否定和批判,但文学娱乐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光荣。
[1] 曹顺庆,王富.中西文论杂语共生态与中国文论的更新过程[J].思想战线,2004(4):76.
[2] 菲利普·锡德尼,爱德华·扬格.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M].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82.
[3] 汉斯·罗伯特·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A].世界艺术与美学:第9辑[C].章国锋,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2.
[4] 张颐武.玄幻:想象不可承受之轻[N].中华读书报,2006-06-21.
[5] 吴华,段慧如.文学网站的现状和走势——基于五家著名文学网站的实证考察[J].湘潭大学学报,2012 (6).
[6] 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N].人民日报,2014-04-22(15).
[7] [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97.
[8] J.R.R.Tolkien.TheLordoftheRings.Fellowship of the Rings( Book One)[M].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9:15.
[9] Tolkien.The letters of J.R.R.Tolkien. edited by Humphrey Carpenter,with the assistance of Christopher Tolkie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2000:231.
[10] 陶东风.中国文学已进入装神弄鬼时代?[J].当代文坛,2006(5):8.
[11]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218.
[12] 迈克尔·怀特.魔戒的锻造者—托尔金传[M].吴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2-163.
[13] Helen Gardner.TheProceedingoftheBritishAcademy,vol.2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423.
[14] 朱锦良.约翰·萨里巴.基督教对新时代运动的回应:批评性的评估[J].哲学门,2006(2):27.
[15] 刘晓峰.日本的面孔[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278-279.
From British Fantasy Literature to Chinese Fantasy Novel:Reception with Variation
GAO Hong-mei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British Fantasy Literature,represented by J.R.R.Tolkien,C.S.Lewis and J.K.Rowling,via multi-dimensional modern media has swept the globe and entered China,thus stimulating the creative writing and burgeoning of Chinese Fantasy Novel.Cultural filt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Fantasy Novel receiving the influence of British Fantasy Literature.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there are variations from British Fantasy Literature to Chinese Fantasy Novel,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creation mechanism and mode of transmission,writers’ subjective intention and cultural causes.Under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nese Fantasy Novel falls into the plight of being devoid of localization and loss of humanistic tradition.
Fantasy Literature;Fantasy Novel;Variation;Cultural Reception
2015-01-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36)。
高红梅(1974- ),女,辽宁岫岩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I0-03
A
1001-6201(2015)03-0137-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