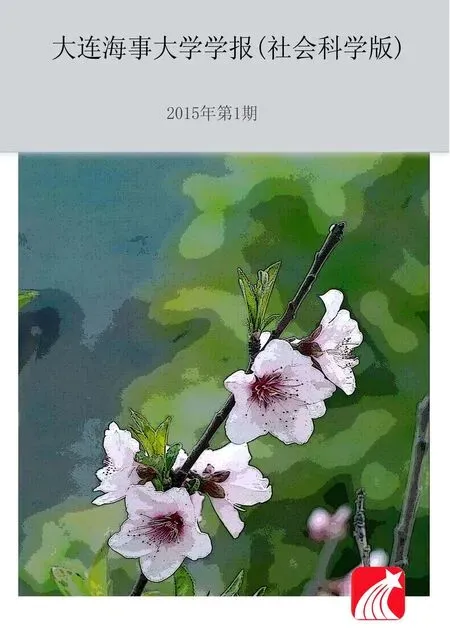论中国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
张 虎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论中国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
张 虎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从中国现行界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入手,分析中国仲裁裁决国籍确定标准引发的问题,包括缺乏统一标准和缺乏对非内国裁决统一认识引发的问题。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界定“外国”的标准,即地域标准、非内国裁决的标准和《纽约公约》标准,提出完善中国仲裁裁决国籍界定标准的建议,分别为明确“地域”为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和不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
仲裁裁决;国籍;非内国裁决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国际经贸、航运市场风波不断,争议频发。基于仲裁在解决争端方面所特有的保密性、高效性、中立性、专业性及在裁决执行方面的便利性,许多企业均倾向于将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实践中,我国企业或个人在国外面临仲裁的情况亦时有发生,一旦仲裁失败,就可能会涉及债权人在我国申请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而法院审查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案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仲裁裁决的国籍归属,囿于我国法律之规定,理论和实务中对如何确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均存争议。本文将阐释我国有关国籍标准的规定,详析其引发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中国现行界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
针对界定仲裁裁决国籍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是我国对其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的通知》(以下简称1987年《通知》)也对界定“外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实际上存在地域标准和仲裁机构标准两个不一致的界定标准。
1.仲裁机构标准
《民诉法》是规定我国解决民事争议、申请承认与执行所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律,该法第283条①《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是有关在我国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规定,从该条可以看出,我国《民诉法》以“国外仲裁机构”为准即仲裁机构的国籍为准来界定仲裁裁决的国籍。
2.地域标准
加入《纽约公约》后,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贯彻执行公约,同时也为了细化公约的条款,让法院更加熟悉其相关规定,于1987年4月10日颁布了《通知》,1987年《通知》的第一条便对何谓外国仲裁裁决作出了规定:“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该公约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有不同规定的,按该公约的规定办理。”不难看出,1987年《通知》是以地域为准来界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尽管1987年《通知》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给地方法院及专门法院为贯彻实施《纽约公约》的指导意见,并非法律,但其亦是法官审查案件时的一个重要补充依据,且其所规定的“领域”标准也系《纽约公约》判断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之一,符合1987年《通知》的“外国裁决”也必定符合《纽约公约》的规定。所以,1987年《通知》规定的标准与《纽约公约》规定的标准并不冲突,而与《民诉法》却不一致。
二、中国仲裁裁决国籍确定标准引发的问题
由于存在两个国籍确定标准,尤其是依据两个标准所得出的仲裁裁决国籍相异时,法院该如何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便会引发系列问题,也将影响到仲裁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1.缺乏统一标准引发的问题
目前,根据我国现行立法之规定,仲裁裁决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仲裁法》第63条和《民诉法》第237条作为执行依据的国内仲裁裁决,该类仲裁裁决是由国内设立的仲裁机构作出的完全没有涉外因素,是纯粹的国内仲裁裁决。第二种是以《仲裁法》第71条和《民诉法》第274条为执行依据的涉外仲裁裁决,根据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之规定,各地成立的国内仲裁机构也有权受理具有涉外因素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所以,国内设立的仲裁机构受理的具有涉外因素案件作出的裁决,均属此类。第三种是《民诉法》第283条所规定的“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该类仲裁裁决的执行依据是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或互惠原则。三种仲裁裁决均以仲裁机构为划分标准,这一标准严重不符合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因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和实践中,地域标准已经成为各国判断仲裁“国籍”普遍认可的标准;[1]且目前的仲裁实践中,仲裁机构的国籍与仲裁地发生分离的实例越来越多,这也对我国所确立的以“仲裁机构”所在国为依据的标准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也导致了法院在具体判断过程中的混乱。此外,界定仲裁裁决国籍标准的不同,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果,这无疑将给实务带来困境。
《民诉法》规定的以仲裁机构的国籍为标准,势必会出现如下几种需判断的情况:第一,某一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的国籍;第二,国际组织所属的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在国外作出的仲裁裁决;第三,某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第四,国际组织所属的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庭在我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
依据《民诉法》规定的判断标准,第一、三种因是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论是在我国国内还是国外作出,均应认定为外国仲裁裁决;对第二、四种则无法确定其裁决的国籍,而《纽约公约》所确立的标准,除第一种情形的判断与依《民诉法》得出的结果相同外,其他三种情形均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第三、四种情形,依《纽约公约》规定的“非内国裁决”的判断标准,还可能被认为是“非内国裁决”从而适用《纽约公约》在我国予以承认和执行。
由此可见,《民诉法》以仲裁机构所在国决定裁决国籍的标准严重与《纽约公约》及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地域标准不符,而《民诉法》又是我国审查外国海事仲裁裁决最基本的法律,所以应当尽快明确我国界定外国仲裁裁决国籍的判断标准。
2.缺乏对非内国裁决统一认识引发的问题
《纽约公约》第1条第一款对公约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在一个国家请求承认和执行这个国家不认为是本国裁决的仲裁裁决。”这是对公约适用于非内国裁决的规定,但是公约并没有规定什么是非内国裁决,而是将其存在与否的判断权授予各缔约国国内立法予以确定。从《纽约公约》的规定来看,应当分两步来判断仲裁裁决是否适用于《纽约公约》:第一步,以裁决作出地为标准,在某一缔约国作出的裁决就属于该国仲裁裁决;第二步,根据某一缔约国的法律,在该国作出的仲裁裁决不属于该国仲裁裁决的,就是非内国裁决。[2]所以非内国裁决成立的条件是:在某一缔约国作出,但该国法律不承认其为本国裁决。由此可见,非内国裁决既区别于一个国家内国的裁决,也不同于外国裁决。
理论上讲,判断非内国裁决的法律为执行地国法,如果依据执行地国确定裁决国籍的标准,对在其国内作出的裁决认定为非其本国裁决的裁决,就是非内国裁决。在我国,由于判断国籍的标准本来就不统一,以至于对非内国裁决的判断也存在争议。对于外国仲裁裁决,我国《民诉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相应的确定标准,但并没有有关非内国裁决的规定,也没有确定非内国裁决的统一认识。
其一,《民诉法》及1987年《通知》均未将“非内国裁决”作为我国国内法认定外国仲裁裁决的标准,这就引发了“非内国裁决”如何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问题。我国已经加入了《纽约公约》,国外仲裁机构在国外作出的裁决在中国执行已经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国外的仲裁机构到中国内地裁决的案件是属于国外裁决还是国内裁决,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
其二,《纽约公约》仅限于公约裁决的适用,且要受到《纽约公约》第1条第三款所规定的“互惠”保留的限制,《纽约公约》第1条第三款的互惠保留并不影响“非内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了“互惠保留”的声明,根据1987年《通知》有关互惠保留的规定,我国仅对在另一国领土内作出的裁决承认和执行适用《纽约公约》,且“非内国裁决”并非在其他缔约国内作出,据此,我国并没有义务承认和执行《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3]。事实上,这种理解并未抓住《纽约公约》所规定“互惠保留”的本质,《纽约公约》第1条所规定的“互惠保留”强调的是“互惠”而非“缔约国”,即缔约国之间彼此互相予以承认与执行的关系,在这点上并不强调裁决的国籍问题。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ICCA)对《纽约公约》的解释指南,“原则上,《纽约公约》适用所有外国和非内国裁决,对提出互惠保留国家的法院则仅就在其他缔约国领域内做出的裁决,或如果裁决是非内国裁决的,但与其他缔约国有联系的情况下适用《纽约公约》”。由此不难看出,ICCA主张即使作出互惠保留的国家,依然应承认与执行“非内国裁决”,如美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也作出了“互惠保留”,但其法院曾多次承认与执行在美国国内作出的法院认为是《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Bergesen V. Joseph Muller Corp.,710 F2d 928 (2d Cir.1983),Gueyffier v. Ann Summers,Ltd.,144 Cal. App. 4th 166.而《民诉法》则适用于所有公约裁决及非公约裁决,尤其对非公约裁决的国籍判断,只能依照《民诉法》予以确定。那么针对外国仲裁裁决就会出现公约裁决适用一类标准,非公约裁决适用另一类标准的现象。
实务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至今尚未出现以非内国裁决请求适用《纽约公约》的案例,但地方法院已经出现了是否援引《纽约公约》关于“非内国裁决”规定的争议,以旭普林公司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4)锡民三仲字第1号]。为例,该案由ICC仲裁庭适用ICC的规则在我国上海作出的裁决,我国法院对此裁决国籍的认定就存在争议,一方面认为是“国外裁决”即外国裁决,一方面又认为是“非内国裁决”。这一判断实际上体现出我国法院在判断裁决国籍时,存在着将外国仲裁裁决与外国仲裁机构裁决混为一谈的情况,以至于得出国外裁决和非内国裁决不分的结果。
三、国际上其他国家界定“外国”的标准
目前,国际上各国界定“外国”的标准主要有三种。
1.地域标准
地域标准是指:“以被请求执行国的领域为界,在被请求执行国领域以外国家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即为外国仲裁裁决,在被请求执行国境内做出的仲裁裁决为内国仲裁裁决。”[4]采纳该标准的如瑞典*瑞典1999年3月4日制定的《仲裁法》第25条。、法国*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六编第1501条有关“对在外国做出的仲裁裁决或者国际仲裁裁决的承认、强制执行与提起上诉”。。
2.非内国裁决的标准
“将在本国领域内做出的又在本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在承认与执行该裁决时适用有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律规定,这种认定方式通常被称为非内国裁决标准。”[5]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非内国裁决”的标准,非内国裁决是在执行地法院所在国内作出的,如依上文提及的“地域标准”来判断,此类裁决应认定为执行法院地内国裁决。但“非内国裁决”的标准的作用就是将此类裁决排除在执行地国内裁决之外,比照外国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采纳这一标准的如德国。在起草《纽约公约》的过程中,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典和瑞士等8国曾提交修正案,主张采用该标准来界定仲裁裁决的国籍。
3.《纽约公约》标准
《纽约公约》标准是以《纽约公约》第1条的规定为准来界定何谓“外国”仲裁裁决,亦即采用地域或非内国双重标准来判定仲裁裁决的国籍,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认定为外国仲裁裁决。但是,非内国标准与地域标准并非平行关系,而是主从关系。非内国标准仅适用于执行国执行在其本国领域内作出并认为不是其本国的裁决时,即当承认和执行国与裁决作出国为同一国时,如果执行国认为在其领域内作出的裁决不是其内国裁决时适用此标准。[6]
除了以上三个标准外,有些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重叠适用地域标准与当事人国籍标准来界定什么是“外国”仲裁,如泰国*1987年泰国《仲裁法》第28条。;也有采取重叠适用地域标准及适用的法律为标准,如印度*1961年印度《外国仲裁法》第9条。。
四、完善中国仲裁裁决国籍界定标准的建议
由于仲裁裁决国籍的界定直接影响到有关的国际公约能否适用,也关系到各国的法律制度的设置和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因此,各国大抵根据本国国情在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及有关法律中界定了外国仲裁裁决的范围。相较国内法倾向于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及侧重考虑本国国情而言,国际公约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兼容及妥协的产物。所以在修改相关规定时,既应照顾到国际公约的规定,也要考虑到国内法的实践。比较国际上其他国家以及《纽约公约》的规定之后,我国应从以下两方面完善我国仲裁裁决国籍的界定标准。
1.明确“地域”为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
国籍原本是国际法上的概念,是指“一个人作为特定国家的成员而隶属这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7]。后期为了区别对待的需要,“不仅法人、船舶、飞机被赋予了国籍,仲裁裁决也被贴上了国籍的标签”[8]。仲裁裁决的国籍是其法律效力的来源,也是其国籍国司法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的依据,一个国家的法院也仅有权对具有该国国籍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行使撤销权;对该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仲裁裁决,只享有承认和执行或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权利。所以,仲裁裁决的国籍是仲裁理论体系中的根本问题,应当由一个国家的仲裁法予以明确规定,如1996年《英国仲裁法》第85条之规定。
而《民诉法》主要是规范法院和当事人民事诉讼行为的程序法,不宜规定有关仲裁裁决国籍的基本理论问题,但有关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程序问题,则应由《民诉法》进行规定。
因此,为统一标准,便利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国籍认定,也为了更好地与《纽约公约》相衔接,建议我国《仲裁法》在修订时,加入确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条款:应明确仲裁裁决具有裁决作出地的国籍;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约定的仲裁地与实际仲裁作出地不一致的,以约定的仲裁地国籍为准;当事人对仲裁地没有约定的,以实际仲裁作出地国籍为准;实际仲裁作出地无法确定的,以仲裁机构所在地或仲裁进行地国籍为准。
同时,将《民诉法》第283条中的“国外仲裁机构裁决”改为“外国仲裁裁决”。这样就避免了与修改后的《仲裁法》在判断仲裁裁决国籍上的冲突问题。
2.不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考虑到上文对界定仲裁裁决“国籍”界定的完善建议,要解决非内国裁决在我国运用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我国不应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具体理由如下:
(1)与我国传统立法相适应。从《纽约公约》中“非内国裁决”制度产生的背景看,由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国内特殊的法律设置——根据仲裁程序的准据法可以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例如德国仲裁法将在该国境内依外国程序法作出的仲裁裁决认为是外国裁决。针对这一类裁决,在裁决作出国是外国裁决,而按照单一的地域标准又是其国内裁决,从而无法根据公约申请承认与执行。为了使《纽约公约》也能适用于这类裁决,《纽约公约》才加入了“非内国裁决”的规定。可见“非内国裁决”的规定,主要是为那些国内法中包含以仲裁程序作为评价国际标准的国家所设定的制度,且这种立法例并不多见。而我国并无此类制度的设置,1987年《通知》第5条规定,申请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公约裁决的前提,是该裁决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因此,在我国,法院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案件时,《纽约公约》仅适用于另一缔约国内作出的裁决。由此可见,公约裁决的范围不包括在我国境内作出的裁决,也就无承认“非内国裁决”之必要。
(2)开放仲裁服务的选择。与诉讼作为国家行使司法权的行为不同,仲裁作为一种争端的解决方式,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项协助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服务,只是其因涉及不同国家的法律的运用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即便如此,这也无法掩盖仲裁已成为一种服务的本质,且这种服务并非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议定书所禁止。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逐步开放国内仲裁服务市场也将是未来仲裁发展的大势所趋,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外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在我国进行并作出裁决,而依据我国现行确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这类仲裁裁决如何在我国执行将遇到法律的空白,可见上文提及的仲裁国籍的判断标准的完善已迫在眉睫。而如果我国相关立法作出了修改,并确定了将仲裁作出地作为判断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那么只要在我国作出裁决的仲裁就是具有我国国籍的仲裁裁决。倘若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而我国又无配套的法律制度予以确认,这样就又可能引发国外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在我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国籍争议。
因而,随着我国仲裁服务的逐步开放,在以裁决作出地为准的新的仲裁国籍标准确立后,为避免国外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在我国所作出仲裁裁决的国籍冲突问题,就不应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
(3)司法主权及司法监督的需要。由于仲裁服务涉及法律的运用和当事人间争端的解决,而根据司法主权的原则,这又属于各国司法机关强制监督的范畴,所以,从立法价值取向考虑,我国除通过立法加强对外国仲裁服务准入的管理外,还应掌握对国内进行仲裁行为的监督权。“非内国裁决”制度的存在,将本在一国国内进行的仲裁认定为外国仲裁,实质上剥夺了这一国家对该仲裁的司法监督权。未来我国也将逐步开放国内仲裁服务市场,外国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也会越来越多地在我国国内从事仲裁业务。如果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那么我国法院就无权监督这一类的仲裁行为,这显然是与维护我国司法主权的立场不符的。
在我国以裁决作出地为准的新的仲裁国籍标准确立后,这一类裁决可直接认定为我国国内裁决,我国法院就有权根据本国实行撤销、执行等方面的司法监督,这样既不会对我国的司法主权造成影响,还可以满足我国仲裁服务开放的需要。
(4)完善国内法与国际公约衔接的需要。虽然《纽约公约》将地域标准和“非内国裁决”标准均作为其判断外国的标准,但依然存在偏向,即只有在根据地域标准作出系内国裁决的判断后才考虑非内国裁决的标准。而从我国传统的立法来看,我国一直没有“非内国裁决”制度方面的规定,且就我国目前的立法而言,不论是《仲裁法》对仲裁种类的划分,还是《民事法》对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均与《纽约公约》的规定存有差异。如何完成国内法与《纽约公约》在这一方面的衔接,这也是我国仲裁立法的一个重大课题。
显然,相比将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标准由仲裁机构标准改为仲裁作出地标准而言,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带来的法律制度变化要复杂得多。所以,为完成国内法与《纽约公约》在这一方面衔接的目标,捷径即不承认“非内国裁决”制度。
五、结 语
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了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要求必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仲裁立法一直是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关于外国仲裁裁决审查时的法律规范更是付之阙如,而完善外国仲裁裁决审查的立法,首先就应该明确仲裁裁决国籍的判断标准。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及仲裁的实践,认为判断仲裁裁决的国籍,我国在借鉴国外法律和《纽约公约》规定标准的同时,也不能完全予以采纳,而应在摒弃“非内国裁决”的基础上,直接规定以“地域”为标准。
[1]赵秀文.论纽约公约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简论我国涉外仲裁立法的修改与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2010(2):160.
[2]RUBINO-SAMMARTANO M.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M].Peking:Citic Publishing House,2003:34.
[3]吕炳斌.论外国仲裁机构到我国境内仲裁的问题——兼析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的保留[J].法制研究,2010(10):71-74.
[4]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纽约公约》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8.
[5]韩德培,肖永平.国际私法[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36.
[6]周佳.1958年《纽约公约》第一条评述——兼论我国仲裁法律体系下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J].北京仲裁,2005(4):46.
[7]李浩培.国籍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0:5.
[8]王天红.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J].人民司法,2006(9):34.
2014-12-01
张 虎(1984-),男,博士,讲师;E-mail:stevenzhanghu@163.com
1671-7031(2015)01-0053-05
DF97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