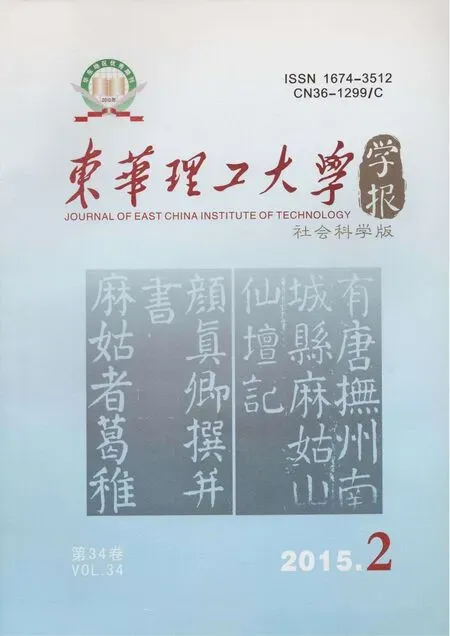文化符号视阈下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利用——以闽西客家为例
李 崧, 徐维群
(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龙岩 364000)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的繁荣发展一方面让人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引发怀着乡愁精神的人们关注和忧虑,其中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对客家地区的人们一样产生深刻影响,也经历着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挑战。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由于聚集而居,地处偏远受冲击不大,反而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客家人也开始迁居城里,或外出打工者增多,使得客家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基础受到前所末有的动摇。是慢慢放弃消失还是传承、保护、利用?这是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现实[1]。本文试图从文化符号视阈的角度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功能分析,探寻如何利用文化符号规律更好地传承与利用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符号的界定
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明确定义,即“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主要形式有表演艺术、民俗文化、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客家民系在长期生活和生产中形成的以非物质文化形态存在的、生动体现在客家群体生活中的各类传统文化,包含客家语言文化、客家民俗文化、客家技能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存在于群体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中,有着更鲜活的形象、可明确解读的内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丰富情感。客家民系素来聚集而居,语言的相通、习俗的传承、社区的完整、互动的频繁,是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较为完好的汉民系之一。
所谓符号,是约定俗成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可感知的形象,一是对象意义内涵部分。任何文化都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与之相关联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某种文化的承载体或表现形式,是特定文化的内容、特征和关系的具体标志。文化以符号形态表现,使文化内容得以丰富、形象、生动,从而有效反映和广泛传播。文化符号最初总是起源于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代表了某一民族民系传统的生活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遗产。不同民族民系有不同意蕴的文化符号,客家民系也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符号,从文献典籍、艺术珍品到规章建设、器物营造等形式,代表客家文化精神实质的文化符号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内容上既有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历史文物遗迹,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又有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
2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符号的功能
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3]。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起到鲜明展示和体现文化精神内核与实质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文化符号功能更加鲜明。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格尔茨指出:“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4]文化符号具有重要功能,包括认知功能、沟通功能、审美功能。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备这三项基本的符号文化功能,起着客家群体沟通、文化认同的功能,而且极具审美观赏价值,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文化资源。
2.1 客家非物质文化符号的认同功能
人们对某种文化的认知是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来实现的,符号起到对特定文化的一种“认知”和“记忆”作用。民系的文化认同常常表现为集体文化认同,是文化归宿感和对自身文化符号的接受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的接受,包括认同语言、服饰、生活习惯、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等。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群体文化的符号标志,是客家群体归宿认同的精神家园。例如,客家话作为客家群体的共同方言,是客家人认同的祖宗语,因为共同的方言使客家人之间的交流感觉亲切自然,乡情亲情油然而生;再如客家服饰里的蓝布衫、红花布、花头帕成为客家妇女的显著标识;还有客家民俗文化反映了客家民系共同的自然认知、生命理念、与精神面貌;而客家技能文化、美食文化又反映了客家人历代先民的创造性和智慧的结晶,是客家民系的文化记忆。客家非物质文化相对于静态的不能再生的物质文化而言,它是动态的、不断生成的,存在于民众的真实生活中,是客家文化的“活化石”,发挥着民系文化认同的指示标志作用,也对客家后代起着潜移默化、教育熏陶的作用。
2.2 客家非物质文化符号的沟通功能
沟通功能是非物质文化符号的核心功能之一。符号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重要中介,包括语词符号如语言,和非语词符号如表情、装饰、色彩、姿势、人际距离等。例如,作为语词符号的客家话既是客家群体的交流沟通工具,也是客家群体的标志性符号,语言相同,群体间便有了共同的沟通的习惯和表达方式,更容易交流和形成共识,节约交际成本,更易达成一致的目的。再如,作为非语词符号的客家情感表达方式,诸如好客热情、邻里相帮等民系性格表现,反映了客家人相对于其它民系的人际距离更紧密,容易形成和谐的小社会。还如,客家的节庆习俗、饮食文化符号,作为客家非语词的群体沟通方式,显现出来的热闹节庆、亲朋相帮、热情好客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客家群体意识及民系特点。综上可见,客家人对外热情和对内团结,容易沟通且易于合作,说明客家社会是个开放型、宽容型的群体社会。
2.3 客家非物质文化符号的审美功能
文化符号形象、具体、直观、丰富,具有表层的审美价值,通常能够满足人们的视觉要求,从而形成一定的观赏审美功能。这种审美功能,从客家非物质文化符号中也可看出。例如,客家语言文化里的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或讴歌生活,或劝诫后人,或传递美好情怀,其旋律悦耳动听,歌词文采优美而对仗工整,语言生动丰富而内容朴实无华,透出客家山歌的秩序美感。同时,客家山歌是表达情感的民间艺术形式,劳作里人们寻找寄托,聚会联络情感的手段,给人美好的感受和精神的升华。再如,客家的民俗活动很丰富,常与节庆相联、信仰相依,有各种色彩符号和形象生动的表现,寄予了客家群体的愿望。这些民俗活动不管是什么形式,都突出一个宗旨:和谐热闹欢快,有利于家族的发展和幸福,展现了客家和谐小社会的精神风貌,也体现了客家社会的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民系性格。又如,客家工艺技能体现了客家人的智慧与创造性,其中美食的丰富多彩,服饰的独特漂亮,均有很高的观赏审美价值。总体上看,客家非物质文化符号生动体现在客家小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给人以乡土、本色、简单、快乐的情感愉悦和审美体验。
3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利用中的挑战和冲击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上升到文化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地位,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但我们要看到,在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等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变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基础受到强烈冲击,其传承、利用中呈现出明显弱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大致说来,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受到的冲击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3.1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基础发生了变化
现代化与全球化取代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文化事象与文化习惯渐渐隐入现代生活的视角。全球化、产品模式化、消费模式化使不同群体的互动日益纳入一个共同体中,体现个性化、慢时光、费时费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失去了需要基础和日益走入过时的淘汰格局。客家语言、客家技能、客家民俗都有这种潜在的危险,甚至于客家话都在下一代培养中成为可有可无的沟通方式。
3.2 客家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城镇化、市场消费社会改变了乡村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现代化导致人们生活情趣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城市化使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持续地向农村渗透。在客家地区我们也可看到这种变化:如年轻人外出谋生打工,老年人儿童留守村庄,许多长期坚持的民情风俗活动因为缺少人手和居住的分散而淡化甚至放弃,年轻人参与的动力不足,不理解不支持,客家工艺技能更是后继乏人。
3.3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足
客家民众保护意识淡薄,传承人断代,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严重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些年轻人心中没有位置,乡村文化的变迁也使人们不再重视它存在的意义,导致损坏、破坏现象比比皆是。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一般是年纪大的群体,它的传授方式是口传心授,微利、成就时间漫长,这种文化的继承与扩散方式的持续性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继承人不认同、功利因素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年轻人的眼中利益不大、需要不强,学习和继承的动力不足,造成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严重不足。
4 发挥文化符号在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中的作用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示的文化符号功能在传承利用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客家文化、维护客家和谐小社会、增进客家群体的凝聚力、加强两岸客家民众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桥梁。文化符号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发挥文化符号在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4.1 按文化符号分类,收集整理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闽西是客家祖地之一,是海外客家乡亲的故里,纯客县六个,是客家大本营之一。闽西客家区域非物质客家文化资源丰富,大量的客家非物质文化资源有待整理和收集。客家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产业的前提和基础,客家文化符号的鲜明性体现客家文化产业的特色性和本土性,并决定客家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整理客家非物质文化资源还有利于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有利于客家文化的交流、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开展。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客家先民代代相传中,它们不仅存在于客家人的动态日常生活中,还散落于客家社会,大到不同区域小到不同村庄都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它们有相似之处却又有各类个性化的内容。由于呈现动态发展,它们既有传承的形态,又有发展创新的形态;有保存完好的,也有缺失不完整的;既有存留于文本中的,也有保留在传承人身上的。因此,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和整理是一项大的文化工程,具有较大的难度,必须费大力气。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鲜明,可按文化符号规律进行分类收集整理。一方面,建议编纂《客家非物质文化资源大全》,编纂中注意体现符号特色,图文音像并茂,同时记录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所在地、继承人、活动方式等内容,从而有利于为政府保护决策提供参考,也为客家文化创意提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建议按区域建设客家非物质文化资源符号库或文化符号网,如闽西地区大致可分客家民俗文化、客家文学艺术、客家戏曲艺术、客家工艺、客家食品工艺、客家竞技(客家体育)、客家文献典籍等类别。
4.2 按文化符号规律,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和利用
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包含着“能指”与“所指”两方面的内容,即显现的和隐藏的文化信息,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从表现形式看也可分为内隐性和外显性两个部分。比如说,艺能文化等资源属于外显性部分,而民俗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则是内隐性的,一般通过载体或文化氛围表现出来。民俗文化旅游达到高层次时很注重文化环境及文化氛围的营造过程,即能满足旅游者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享受的需求,只有借助文化符号作为中介才能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转化。按文化符号规律,一方面要充分保护外显部分的内容,在文化旅游中充分展示客家文化符号标识,展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另一方面,客家人的精神面貌、民系性格特色内含于客家群体的动态生活中,因此不要简单把这些作为表演形式,而必须保护原生态的客家民众生活方式,使之更具文化本味的吸引力和趣味性,以便引导游客参与、体验、感受客家文化的真味。同样,在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可以充分利用客家非物质文化资源中显现的部分,如客家艺术表演、民情风俗观赏、客家美食品尝、客家体育竞技表演、客家工艺展示等,它们属于具有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化产业种类。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内隐的精神文化部分又需通过符号渗透于相关的客家文化创意产业中,必须加强客家文化产业的符号经济意识,把客家文化符号渗透于各产业链中,提高相关产业的文化含量,从而提高产业的文化竞争力。
4.3 认识文化符号的意义,加强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教育
加强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宣传和教育,必须认识文化符号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客家民众的保护意识,培养文化继承人和文化创意人才。当前,由于客家地区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外出务工的客家子弟增多,山村往城内搬迁成为主流,盖新楼而放弃土楼聚族而居的现象比较明显,客家民众对存在于自己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客家方言、客家艺能、客家风俗等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淡漠的趋势。虽然各级政府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的力度在增强,但作为其传承者和使用者的参与性、主动性不足,必将影响到文化的传承和利用。因此,要加强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地方文化窗口、媒体等渠道,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提高客家民众对客家文化符号的认同,自觉保护和传承文化。当然,在发展客家文化产业中,政府是主导,市场是平台,民众是主体。政府要注意在保护中执行民生原则,充分调动客家民众积极参与文化产业的体验经济、符号经济,要让他们能在从中得到利益的同时明白自身文化的长远价值,引导他们不能急功近利、杀鸡取卵,以保证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而且,城镇化更不能以破坏当地文化为代价,仍要把客家乡土文化的回归和认同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题。
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可按不同种类传承人的特点和现状分类保护,一要给予传承人政策资金的支持与保护,二要加强下一代传承人的培养,以免失传。同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抓好下一代客家文化的乡土教育。让客家语言教育、客家文艺教育、客家工艺教育、客家体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鼓励创建客家文化特色学校,减少下一代对客家文化符号认识上的缺失;在高校开设客家文化创意设计专业等,培养客家文化高级人才。
4.4 突出文化符号的功能,建构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的合作平台
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不同客家区域各具特点,但也有许多共通之处、相似之处会以文化符号为标志,比如客家方言、客家民系的文化性格、客家服饰、客家信仰等;不同区域具备不同的文化符号,比如不同地方的民俗活动特色、不同地方的美食文化、客家艺能技能等。如果能立足于客家文化符号特色上建构合作平台,就更容易达成共识和交流的目的,在资源保护经验上可以取长补短,在产业发展上合作共赢。
台湾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上,特别是在对客家乡土文化教育、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客家乡土教育方面,台湾比较早意识到市场社会、城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客家社团主动加强下一代的客家方言的教育,注意宣传和保护客家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中重视产业扶持、科研支撑、人才准备,客家文化产业突出客家文化符号的功效,文化符号渗透产业,并创意形成了新的一些客家文化符号。比如台湾客家乡村借助桐花祭,开发了桐花系列产品,使桐花成了客家社群的新标识、创意洪流的鲜明符号,且日益显示出其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5 结论
客家区域在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成功处皆因突显文化符号的作用。以符号带动保护和利用,坚持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不改变乡土,不放弃原味,不丢失传统。只有在这前提上去探寻文化产业的创新,才更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进而处理好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使客家传统文化为客家乡民造福并源远流长。
[1]徐维群.论客家文化符号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产业合作中的功能与运用[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2),149-152.
[2]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8.
[3]杜克芮,托多洛夫.语言科学百科辞典[M].莫斯科:霍普斯金大学出版社,1979:99.
[4]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3.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