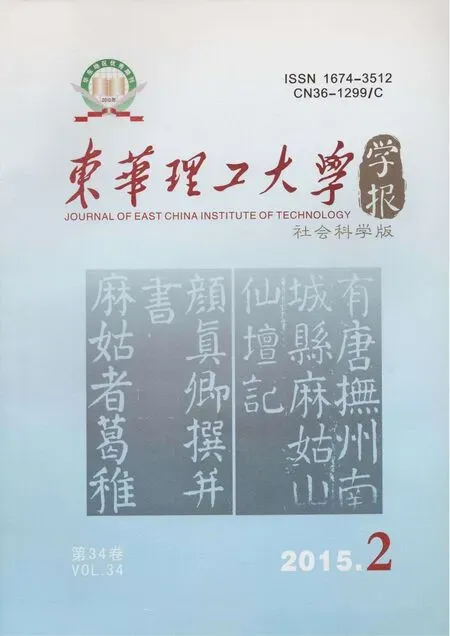南柯梦中的两个世界——试论《南柯记》的叙事结构与演述干预
陈红艳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作为戏剧作家,汤显祖无疑是我国古代戏曲界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他的《牡丹亭》和《南柯记》的影响直至当代依然深远。但就今日的剧评者来说,大多都喜欢评述其剧的意旨、探究作家的创作动机,或者赏析其中爱情的韵味[1],这当然很必要。不过戏剧是极具叙事力和表现力的作品,我们对《南柯记》形式方面的构成缺少深入分析和极少将《南柯记》置于活剧场上审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并不做全面的梳理工作,只是就此剧的叙事结构和戏中人物的演述干预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1 《南柯记》的叙事结构
结构在戏剧中,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既可说是空间意义上的基本架构,也可以说是时间意义上的叙述脉络。就前者而言,它使戏剧的意义变得有立体感,有可触摸的味道,容易消除戏剧与观众的隔阂;就后者而言,戏剧的叙述语言让戏剧更富有张力和生命力。
《南柯记》在叙事结构上展示了两个不同时空双线发展过程中的平行与交叉。两个时空即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它们的平行与交叉在于淳于棼的时空转换,换言之,淳于棼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关节点与桥梁。这两个世界的切换之处,就是叙事聚焦的位移之处,而剧作家的意绪就是这种切换与位移的关键和内驱力。
剧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刻画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戏剧的开头与结尾,也就是淳于棼清醒的时候。第二出《侠概》开篇便言:“四海无家,苍生没眼,挂破了英雄笑口。”[2]510为现实世界定下了失意的基调。现实世界是失意的世界,这个失意的世界主要是为淳于棼而设的。他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整个叙述围绕着他有条不紊地进行,节奏与秩序都十分稳妥。先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接着介绍他自己的个人现状,而这些叙述都是围绕着内在基调:失意。其失意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情感上的失意。“传至先君,曾为边将。投荒久远,未知存亡”[2]510,与父亲失散多年,毫无音讯;其次,现实世界中的淳于棼,生活落魄潦倒,虽然怀才,却仕途坎坷,“精通武艺。不拘一节。累散千金。养江湖豪浪之徒。为吴楚游侠之士。曾补淮南军裨将。要取河北路功名。偶然使酒。失主帅之心。因而弃官。成落魄之像”[2]510,这是事业上的失意;再者,知交别离。周弁、田华子两位好友即将离去。“恨不和你落拓江湖载酒游,休道个酒中交难到头。你二人去了呵,我待要每日间睡昏昏长则是酒”[2]513,想必此刻淳于棼心情是“酒入愁肠愁更愁”。
由此可见,作家的叙述是层层递进的,不断为淳于棼渲染着失意的世界。从亲人到朋友,从家庭到事业,现实世界给予淳于棼的都是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肠断江南,梦落扬州”是对其极为精准的概括。
虽然现实世界的笔墨不多,然而,现实世界却是梦中世界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剧作家非常巧妙地将现实世界的背景设置于扬州。扬州本身就是造梦的地方,多少文人墨客在扬州这个温柔乡中拥有属于自己的梦。其中最早以诗歌形式展现的当属唐代杜牧。他的《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3]此诗是收录在杜牧的《樊川文集》的外编,这诗最早见于唐孟棨《本事诗》,为“三年一觉扬州梦”。同为“三年”版本的,还有宋初《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篇,元末明初的学者陶宗仪所编纂的《说郛》。从杜牧在扬州入幕的时间来看,“三年”比“十年”更符合客观现实。然而,从情理上看,“十年”也未尝不可。“十年”并非指杜牧实际入幕扬州的时间,而是杜牧的心理时间,强调他对扬州生活的眷恋与追忆。“扬州梦”承载着诗人的扬州小美好,让诗人暂时摆脱现实的纷扰。其他关于“扬州梦”的例子还有:
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宋秦观《梦扬州》)
琼壶歌月,白发簪花,十年一梦扬州。(宋周密《声声慢》)
十载扬州,梦回前世楚云远。(宋刘天迪《齐天乐》)
如此看来,无论剧作家是有意还是无意将故事的地点设置在扬州,但这的确为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之间的交流创造了可能性。
作家在叙述现实世界的同时,另一个世界即神话世界也在平行发展。它与现实世界构成一种均衡。就叙述结构而言,神话世界基本是按照时间的发展脉络进行构思的。虽说是神话世界,但它无不迎合着现实世界,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延展与拓宽。也正因为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共性,才推动下文淳于棼空间转移的可能性。而这共性主要是体现在对女性的看法和教育上,如瑶芳年芳十八已到适婚年龄,国母对瑶芳“三从四德”的教育,“夫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而从子。四德者:妇言,妇德,妇容,妇功。有此三从四德者,可以为贤女子矣。”[2]523-525而这贤女子的标准与现实世界对女子的要求是一样的。
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的共性是两个世界之间存在交集的可能,而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性是它们产生交集后继续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推动故事的线性发展重要因素。这两个世界除了人蚁之别外,还存在其他差异,如在选婿的要求上,“若于本族内选婚,恐一时难得志勇之士,不堪扶持国家,要于人间招选驸马。……但有英俊之士,便可留神”[2]525,这是与现实世界不一样的,现实中选婿当选有才之士,且选与自己门当户对者,而在神话世界中,选婿既不选才智者,也不选门当户对者,只要在异族中选个英俊之士便可,从现实观之,这是荒诞与不解,但这事放在神话世界中,便存在着合理性,这也为故事的叙述预设了可能性。
此外,剧作家为了安抚淳于棼空间转换的恐惧,增加神话世界的真实性,还为此寻找其存在的理由,“汉朝有个窦广国,他国土广大,也只在窦儿里;又有个孔安国,他国土安顿,也只在孔儿里。怎生槐穴中没有国土?古槐穴,国所居”[2]548。如此一来,作家便顺利实现了淳于棼的空间转换,也顺着空间的转换,笔墨便也转入了对神话世界专注的刻画和描写。
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刻画,汤显祖对于神话世界的描述更为深入和全面,基本占了整个叙述的三分之二。夸张言之,淳于棼的一梦便是一生。
时空的转换也为淳于棼人生带来彻底的改变,无论爱情还是事业都两得意了。但准确地来说,是因为爱情的得意,带来了事业的风生水起。而这叙述结构与层次,与一般的才子佳人剧是有别的。一般才子佳人剧基本上按照如此套路:才子佳人相遇,一见钟情便相爱,却迫于现实的无耐——佳人地位显赫,才子只是一介书生没财没势,因此便受到女方家长的反对与阻扰,此时常有的解决办法是科举,才子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而且才子总能中举状元,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换言之,才子是先有事业才有佳人的,而在汤显祖的神话世界中这种状况恰恰相反。先说一见钟情,的确淳于棼与瑶芳公主也是一见钟情,但他们的一见钟情开始是因物生情,早在他们真实见面前便已情根深种。因为在《选婿》时,淳于棼已对瑶芳公主的“巧金钗对凤飞斜,赛暖金一枚犀盒”一见钟情了,“看他春生笑语,媚翦层波。把灵犀旧恨,小凤新愁,向无色天边惹”[2]540,此时淳于棼已种下情根,管鹦哥怎么叫“蚁子转身”,他只听成“女子转身”。再说婚姻,淳于棼与瑶芳公主的婚姻是来得如此容易,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扰,便顺利结婚。一般才子佳人剧中,成婚便是故事最美好的结局,而在这,成婚只是故事的开始。上文说到在现实世界中淳于棼的失意时,主要有两大失意,分别是情感和事业的失意。这些失意也随着结婚而迎刃而解,“公主入宫,一来替驸马寄书令尊,二来替驸马求官外郡”,因为婚姻的得意,消解了事业和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
由此可见,剧作家的叙述策略是两个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先将对象置于潦倒的境地,然后再对此作极端化的转换,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不断为故事的顺利展开设置一些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因素。
2 《南柯记》中契玄禅师的演述干预
戏剧是存在于活剧场中,剧中每个人物都是活脱脱地展现在舞台上,紧扣着现场演出而演出,如同一部《南柯记》,丑角山鹧儿出场说帮相公买酒,在台湾国家大剧院上演时,他说买台湾的金门高粱,而在广州大剧院上演时,他则说买顶好的一线天,以此来迎合台下观众,与观众套近乎。同样地,《南柯记》中的其他人物也是贴近舞台,贴近观众的。
对于《南柯记》中的众多人物,学界大多都是将焦点聚焦在淳于棼身上,的确,淳于棼是一剧之主。如果说整个剧是一串佛珠,那么淳于棼是串起这串佛珠的绳子,他穿梭于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引出了剧中每一位成员。然而,剧中还有一位人物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是一位超脱于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的得道高僧,也是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交融点——“契玄禅师”。
契玄禅师一出场就为我们道出了此剧的因缘:
梁天监年中,身曾为比丘,跟随达摩祖师渡江。比扬州有七佛以来毗婆宝塔,老僧一夕捧执莲花灯,上于七层塔上,忽然倾斜莲灯,热油注于蚁穴之内。彼时不知,当有守塔小沙弥,颜色不快,问他敢是费他扫塔之劳?那小沙弥说道:“不为别的,以前圣僧天眼算过此穴中流传有八万四千户蝼蚁。但是燃灯念佛之时,他便出来行走瞻听。小沙弥到彼时分,施散盏饭与他为戏。今日热油下注,坏了多生。”老僧闻言,甚是忏悔,启参达摩老师父。老师父说道:“不妨,不妨。他虫业将尽,五百年后,定有灵变,待汝生天。”[2]519
禅师的出场在第四出,第二三出分别是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的展现,此时,契玄禅师犹如剧作家的化身,既为观众消释了心中的疑惑与不解,解释了神话世界存在的原因,暗示了其最终命运,同时也把控着整个剧的开始和发展。在这活剧场当中契玄禅师有三重身份:
(1)在《南柯记》中以“净”扮相出场
(2)剧中人契玄禅师
(3)具有全知视角的剧作家本人
这三重身份并不是机械交替的。陈建森先生于《宋元戏曲本体论》书中说到:“宋元戏曲是‘活’在剧场的艺术。剧作家写完剧本,虽退居幕后,但其创作视界却隐藏于演述者‘话语’之中,造成对戏曲剧场演述的强势‘干预’。此时,场上演述者则暂时成为沟通书会才人与剧场观众视界的‘中介’,控制剧场演述的进程,引导剧场观众的审美取向。”[4]而以“演述干预”的角度来审视《南柯记》中契玄禅师的形象,也是同样如此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剧作家的价值观、价值判断以及情感取向都以潜在的形式注入剧中人契玄禅师的话语中,引导淳于棼“立地成佛”,控制着整个演述的进程。
从淳于棼与契玄禅师的第一次见面,淳于棼向禅师问烦恼因果:
(生)如何是根本烦恼?
(净)秋槐落尽空宫里,凝碧池边奏管弦。
(生)如何是随缘烦恼?
(净)双翅一开千万里,止因栖隐恋乔柯。
(生)如何破除这烦恼?
(净)惟有梦魂南去日,故乡山水路依稀[2]537。
字里行间禅师已经向淳于棼暗示了他在神话世界的遭遇,还洞察到淳于棼最后“立地成佛”的结果。与其说契玄禅师很“神”,不如说是作者在背后把控着淳于棼的命运,通过禅师的身份向观众预示着剧情的发展。尤其在最后一出《情尽》:
【北收江南】呀!你则道拔地生天是你的妻,猛抬头在那里?你说识破他是蝼蚁,那讨情来?怎生又是这般缠恋?(叹介)你挣着眼大槐宫里睡多时,纸捻儿还不曾打喷嚏。你痴也么痴,么痴,你则看犀盒内金钗怎的提?
(生醒起看介)呀!金钗是槐枝,小盒是槐荚子。啐!要他何用?(掷弃钗盒介)我淳于棼,这才是醒了。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小生一向痴迷也。
【南园林好】咱为人被虫蚁儿面欺,一点情千场影戏,做的来无明无记。都则是起处起,敎何处立因依?
(净)你待怎的?(生)我待怎的?求众生身不可得,求天身不可得,便是求佛身也不可得,一切皆空了。(净喝住介)空个甚么?(生拍手笑介,合掌立定不语介)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净)众生佛无自体,一切相不真实,(指生介)马蚁儿倒是你善知识。你梦醒迟,断送人生三不归。可为甚斩眼儿还则痴?有甚的金钗槐叶儿?谁敎你孔儿中做下得家资?横枝儿上立些形势?早则白鹦哥泄漏天机,从今把梦蝴蝶掐了羽翅。我呵,也是三生遇奇,还了他当元时塔锥,有这些生天蚁儿。呀,要你众生们看见了普世间因缘如是。
(众香幡乐器上,同净大叫介)淳于生立地成佛也(行介)[2]696—697。
契玄禅师引导着淳于棼淡然面对世间的患得患失,领悟人生如梦的真谛,也借助于淳于棼的得道,宣扬了自己的佛思。因此,可以说,契玄禅师既引导着淳于棼立地成佛,同时也在引导着观众接受视界的审美取向。“要你众生们看见了普世间因缘如是”,既是剧中人契玄禅师的言语,也是剧作家企图借契玄禅师之口向观众们传达着自己的佛学禅宗思想。
3 小结
《南柯记》既是读者们经典的案头读本,同时也是观众们精彩动人的现场剧。汤显祖有条不紊地叙述着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层层递进地推进着戏剧的发展,极为吸引人眼球[5],同时剧作家隐身于“契玄禅师”这一角色,宣传着自己的思想和引导着观众的审美。
[1]张鹏飞.论汤显祖戏曲“梦幻叙事”范式的文化情韵[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19-123.
[2]汤显祖.汤显祖戏曲集[M].钱南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杜牧.樊川文集[M].何锡光,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7:1375-1376.
[4]陈建森.宋元戏曲本体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4.
[5]陈建森.千年四入杨妃梦 邀月举杯戏春秋——曾永义新编昆剧《杨妃梦》观后[J].四川戏剧,2012(04):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