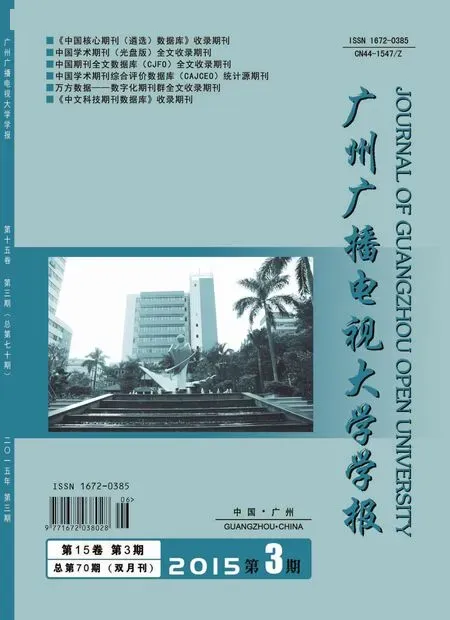元代翰林国史院与题画诗的创作
摘 要:翰林国史院作为元代二元政治格局的产物位尊而权微,使得翰林文士生活闲适,任职稳定,加之其普遍深厚的书画艺术修养,保证了他们交往持久、唱和频繁、诗画理念趋同的可能性,从而引领元代题画诗创作风气。文人画的大兴,使得山水题画诗和以梅兰竹菊为主要题材的咏物题画诗成为最能代表元人精神和时代风貌的题画诗创作取向。在元人尚意与复古的共同艺术审美追求下,翰林文士的题画诗创作普遍气韵生动、意态丰满,以诗体的形式言说着书画艺术思想,实现了诗歌与绘画美感的互递,成为元人宗唐复古过程中无意识却最有力的工具,坚守并强化了诗歌作为正统文学的雅正清逸之风。
收稿日期:2015-03-24
作者简介:张婉霜,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学文献整理及研究。
题画诗是一门悠久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渐趋成熟,到了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兴盛,题画诗也蔚为大观,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局面。根据清初陈邦彦编纂的《御定历代题画诗类》的统计,在短短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元代就一共产生了3798首题画诗,可谓历朝历代题画诗最多的一个时期。题画作诗风气之盛,使得当时的文坛、画坛名流无不涉足这一领域。清代顾嗣立《元诗选》收录题画诗2000多首,该书340位诗人中有题画诗者达三分之二, [1]从诗人的别集来看,王恽、虞集、柯九思、贡性之等翰林文士的题画诗皆在百首以上。作为馆阁文臣,他们创作题画诗的背景是怎样的呢?其题画诗创作取向有何表现?对于元代诗坛又有怎样的影响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一、传承与发展:翰林国史院引领元代题画诗风气
元朝自始至终未有如宋代那样明确集中的专业画院,其宫廷绘画机构多样而复杂,许多中央机构兼有掌管书画活动的功能,继承和发扬了唐宋以来的绘画事业。其中翰林国史院、集贤院以及后来的奎章阁学士院,与题画诗兴盛关系尤为密切。这些机构的任职人员多通经博史,能诗词善书画,是文人画家的典型代表。尤其是翰林国史院,集中了全元几乎所有的诗文大家:王恽、程钜夫、赵孟頫、高克恭、商琦、虞集、袁桷、马祖常、邓文原、揭傒斯、柯九思、康里巙巙、朱德润、黄溍、柳贯、贡师泰、欧阳玄、陈旅、余阙、张翥、危素等等。
元代翰林国史院渊源于前代翰林院,这一机构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世祖中统二年(1261)秋七月,元代初置翰林院,准确来讲,叫翰林学士院。第一任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认为“翰苑载言之职,莫国史为重” [2],上疏备陈修史的重要性,于是翰林院才正式兼修史之任,更名翰林国史院。 [3]翰林国史院设立之初,主管几乎所有的国家文化事业,其后不久,蒙古翰林院、集贤院等一批机构相继设立,翰林国史院的主要职掌便只剩下“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 [4]三项, 终元之世不改。对于翰林国史院在政权中的地位,元人李冶之言堪谓一针见血:“翰林视草,惟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专,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犹以翰林、史馆为高逸,是工谀誉而善缘饰者为高选也。吾恐识者羞之。” [5]可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翰林国史院都仅仅是一个实权甚微的清要机构。加之“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私物。” [6]凡是机要关键部门,汉人、南人皆不得用,因而他们大多聚集在翰林院、集贤院等处任职,升迁变动较少,即使有所调动,也往往不出翰林国史院、奎章阁、集贤院等相关文化机构。职位的相对稳定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保证了交往的持久性和艺术思想的渗透力;清贫而又闲适的生活保证了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来切磋诗艺,唱和吟咏,作画题诗。雅集酬唱与同题集咏成为他们创作题画诗的最佳交流方式。另外,元文宗时成立奎章阁,专门用来陈列珍玩,储藏书籍,其中的很多文士都曾经在翰林国史院任职。而且经过元初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积淀,特别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平定南宋之后,南宋宫廷所珍藏的历代书画文物等均被遣送至大都。因而元代宫廷也无异于前朝各代,同样汇聚了众多的文物珍品。得益于这如此丰富的收藏,翰林国史院文士们的艺术审美力与品题鉴赏力更是大大提高,题画作诗的风气也愈加盛行。综上这些,都为他们创作题画诗和趋同的诗画理念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对汉人、南人施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分化。元有文学名家近400人,然“高蹈不仕”或先仕后隐者有一半以上。整个时代精神由外在的建功立业转为追求内在的心性修养,元初刘因云:“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矣。艺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而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学也。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 [7]刘因认为元人应顺应世变,游于当今“诗、文、书、画”之艺,以儒家心理诉求之下的艺术全修,实现“华国、治物、饰身”之目的。这无疑成为元人特殊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也促进了有着怡情冶性功能的题画诗的兴盛。翰林国史院文士群,作为身居闲职的上层文人,空负有为之志,却不得尽见于事,心中的抑郁和不平,便通过题画诗这种便于寄寓难言之隐的形式来表达。由于题画诗不仅表现手法含蓄,而且具有理解上的伸缩性。所以既可以充分表达诗人的感情,却又不至于锋芒毕露,引来不必要的杀身之祸。
综上可见,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都推动着翰林国史院文士的文人画和题画诗创作。他们身居高位,便于阐发文艺理念,启迪后学,引领了整个元代的题画诗风气。上承唐宋,下启明清,在题画诗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衔接作用。
二、山水与咏物:翰林国史院文士题画诗创作取向
元代文人画大兴,强调创作中的主体意识。山水画和以梅兰竹菊为主要题材的花鸟画成为最能代表元人精神和时代风貌的画科。相应地,山水题画诗和咏物题画诗也成为元人题画诗中的两朵奇葩。“比德”与“畅神”是中国的两大自然美学观,“比德”主要反映儒家思想,“畅神”则折射着道家观念。山水题画诗往往传达“畅神”的审美观,展现出人对自然的情感需要。以花鸟虫兽、梅兰竹菊为题材的咏物题画诗则主要反映“比德”的审美观,投射出人对自然的伦理追求和人格追求。
(一)山水题画诗
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皆源于道,天地之道,自然之道,皆在于对生命的超越,对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的追求。作为自然山水的艺术投影,山水画既是眼中之山水,亦是心中之山水。山水题画诗,往往传达出诗人心有所感,情有所动,神思飞扬,物我两忘的道家“畅神”审美观。美学意义上的“畅神”之说,最早见于南朝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峰岫高嶷,云林森眇,圣贤英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 [8]“畅神”的核心是精神愉悦超然,与自然大化融融相乐,它侧重审美主体的审美心境,是人的自然化。欲想达到此种境界,审美主体须澄怀味象,有一颗林泉之心,恬淡自然、透明澄澈、自由虚静,摒弃世俗功利,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去品味万物,观照万物,发现自我,发现宇宙无限的生命,发现潇洒自由的人格理想。
翰林国史院文士政治地位上的尴尬,使其对元政权始终保持着游离心态,加之元代社会隐逸之风盛行,翰林文士大都以儒学为主要思想基础,并出入于释道,隐入诗、书、画,身在尘世而向往山林自然之乐。他们向往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以道家的境界之道圆融儒家的伦理之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种精神的平衡点,以求达到从容自若、进退自如的人生境界,实现对宇宙人生的考察和对现世社会的深刻批判。最为典型的代表如赵孟頫,他不仅是延祐诗坛上首领风骚的人物,而且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在书画史上堪称一流的巨匠。由于他兼善诗、书、画,所以也是有元一代最重要的题画诗人之一。他空有远志而充任闲职,即使官高一品、荣际五朝,内心的苦闷矛盾依然无法排解,故其题画诗表现最多的依然是归隐之情、林泉之思,并且几乎成为他一切情感的震源,因为“当外在的反抗和经邦济世前途渺茫或力不从心时,人们就会转而追求内在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的完美以及性情的抒发。” [9]在大量的山水题画诗中,赵孟頫描绘出一种闲适恬淡、酣乐不暇的隐逸生活,如《题四画•桃源》:“桃源一去绝埃尘,无复渔郎再问津。想得耕田并凿井,依然淳朴太平民。” [10]表达了其向往田园生活的林泉之思和对自然的情感归宿。李泽厚认为,宋元时代的隐逸不同于六朝时代政治性的退避,而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身为翰林学士的赵孟頫表现出的这种归隐之心、林泉之志,乃是元人普遍的心灵归宿和生命情致。
(二)咏物题画诗
在中国古人那里,“人”与“物”异质同构。天地自然,不仅与人的情感相感应,而且与人的道德品质、精神修养相勾连。天之道有阴阳,地之道分柔刚,人之道辨仁义,此即“比德”之说的理论根基。“比德”审美观念形成于周代,但在儒家思想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和集中,浸染着浓重的伦理意义和人格象征色彩。荀子《法行》篇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将玉的温润细腻、坚刚不屈和君子的仁、知、义、勇等品德相类比。事实上,孔子早在《论语》中就以山水比德于君子之仁智。可见,儒家“比德”审美观念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寻找自然审美对象和人的品格之间的相通之处,是自然的人化。清人盛大士曾言:“作诗须有寄托,作画亦然。旅雁孤飞,喻独客之飘零无定也。闲鸥戏水,喻隐者之徜徉肆志也。松树不见根,喻君子之在里也。杂树峥嵘,喻人小之暱比也。江岸积雨而征帆不归,刺时人之驰逐名利也。春雨甫霁而林花乍开,美贤人之乘时奋兴也。” [11]这些凝练积淀下来的观念“符号”或“原型”,以比德之义投射出人对自然的伦理追求和人格追求,成为一定人格象征和民族意识的载体。而“题画之作,别是一种笔墨。或超然高寄,霞想云思;或托物兴怀,山心水思”, [12]可见,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咏性情,画中的比德之义或是人生感受的寄托,通过题画诗正可得到升发。
宋代绘画尚有不少宫廷院体式的比德意识,或道德劝诫,或歌功颂德。到了元人这里,文人比德成为主流,绘画主要是寄寓个人独特的理想与道德情怀以及不吐不快的情感郁结。异族的占领和统治,使隐逸之风在元代文士中重新大作。而且与此前从魏晋至宋的隐逸相比,展现出一种新的意义。理学思想适应了蒙古统治者的需要,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义正与理学所提倡的气节相连。翰林国史院文士们往往托物自励,借助笔下的梅、兰、竹、菊、松柏、水仙等来表明个人审美意趣的清高雅致和精神品质的超越流俗。据不完全统计,元代题咏梅兰竹菊的题画诗在八百首以上,约占元代题画诗的四分之一。 [13]这固然和元代的花木绘画有关联,但诗人主要的意图仍是托物言志,梅之孤高清雅、兰之不求名达、竹之阳刚坚韧、菊之睥睨霜露,恰好契合元人标举节操的思想现实。这些画中多贯穿着有我之境,诗画合一,共同表现出文人学士的抗俗气节和激愤不平之气。赵孟頫创作了许多关于松、竹、梅的题画诗,如《题洞阳徐真人万壑松风图》:“谡谡松下风,悠悠尘外心。以我清净耳,听此太古音。逍遥万物表,不受世故侵。何年从此老,辟谷隐云林?” [14]表达了高尚气节和退隐自藏、返朴归真的思想。又如《题仲宾竹》:“幽人夜不眠,月吐窗炯炯。起寻管城公,奋髯写清影。此君有高节,不与草木同。萧萧三两竿,自足来清风。” [15]诉说自己“不与草木同”的坚贞节操。文学创作的本质在于“形象”的塑造。诗人在对画意理解的基础上融入自我形象,通过文学的阐释达到了“自寓”的效果。从赵孟頫的题画诗中,可以感受到他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以及对生命的体悟和对自由人生的渴望。
不过,翰林国史院中蒙古色目作家在咏物意象的选择上,饱有较强的民族特色。作为西北雍古部族后裔,马祖常虽未曾经历草原游牧生活,但其天生具有的草原民族特性,使其不自觉地在题画诗中涉及到除了传统文士偏爱的墨、竹等对象外的鹰、牛、马等意象,如《画鹰》、《画牛》、《瘦马图》、《春风御马图》、《龙眠画马》、《骏马图》等。由于蒙古色目人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本民族的豪爽敦厚个性,同样是题画马图,他们少有汉族文士的家国之寓和幽怨沉郁,而是极力歌颂马的天生神骏和忠直报国。以一种主人翁的精神渴望家国和平、政权稳定、人才得到重用,完成了对于“马”这一传统绘画题材的重新解读。此外,对民间疾苦的揭露也较为大胆深刻,如萨都剌《织女图》、雅琥《御沟流叶图》等。
三、尚意与复古:诗文书画理念的激荡与弥合
元代文人多身兼数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宋以前诗人书画,人各自名,即有兼长,不过一二。胜国则文士鲜不能诗,诗流靡不工书,且时旁及绘事,亦前代所无也。” [16]胡氏这段话虽难免有片面之处,但他所指出的元代文人多擅书画却是可信的事实。翰林国史院中的文士,很多都是著名的画家,除了被称为诗、书、画“三绝”的赵孟頫外,还有高克恭、周之翰、商琦等人。这些能诗善画的文人,一方面在作画之后,往往自己在上面题诗;另一方面,他们所作之画富有意境,很便于其他诗人为之题诗。于是,“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 [17]诗与画的结合,从来也没有像元代这样紧密过。同时,元人于书法也颇为擅长,“鲜于、赵、邓,诗为书掩;虞、杨、范、揭,书掩于诗。他如姚公茂父子、胡长孺、周景远、程文海、元复初、卢处道、袁伯长、欧阳原功、张仲举、傅与砺、陈众仲、王继学、薛宗海、黄晋卿、柳道传、柯敬仲、危大朴、贯云石、萨天锡、贡泰父、杜原功、倪元镇、余廷心、泰兼善,皆以书知名。” [18]故明代沈颢在《画塵》中总结说:“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后来书绘并工,附丽成观。” [19]元代真正实现了诗文书画的合一。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的书画大家之多,质量之高,具有独特的地位,因而他们的诗文观念、书画鉴赏观点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在诗歌上,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们批判宋季诗风,宗唐复古,自觉维护唐宋以来的雅正审美传统。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传统的审美愈来愈朝着静态美、和谐美的方向发展 [20],中和雅正的诗歌风貌当然受到理学修养深厚的翰林国史院文士的推崇。元初赵孟頫即认为,南宋“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辑新巧为得” [21],为了改变诗文时弊,必须以古为师,诗歌要“本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 [22],为文“皆当以六经为师” [23]。所以他的诗歌直承魏晋六朝之清丽高古,同时融入盛唐之圆润流畅。除了赵孟頫外,同时期的程钜夫、吴澄、邓文原及中期的“虞、杨、范、揭”四大家均为倡导雅正复古之风的馆阁领袖。欧阳玄于京师诸名公诗风曾有比较准确的概括:“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变而近于古。” [24]当然,元代末期,由于政治生态的剧变,雅正之音难以为继,这里不用赘述。
不过由于题画诗的诗画一律,雅正理念在题画诗的美学呈现上出现了直观的相合与深层的相悖。直观上来看,由于元人作诗力洗宋调,宗唐得古,以雅正工致为美,所以题画诗自然注重诗歌的风貌造境、天趣和音节的婉转流利、轻扬。如袁桷:“诗中传画意,画里见诗馀。山色无还有,云光卷复舒。” [25]闲适恬淡之境与雅正中和之则甚为相合。深层上来看,元人题画诗大量流露出的林泉之思和仕隐之间的心迹矛盾确实不符合“雅正”的诗学表述,一定程度上暴露出雅正诗风的虚幻性。但正是这种深层的寄托与畅神,反而更加强调题画诗的含蓄婉转而不失意度。与雅正美学的相合与相悖最终共同造就了元人在题画诗创作中的尚意复古,寻求气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诗歌创作由温柔敦厚到性情自适的走向。可以说,翰林国史院作为文坛正宗,在题画诗这种诗画结合的特殊的诗歌类别的发达过程中,确是起到了倡导风气的作用。
其次,在绘画上,“唐人尚巧、北宋尚法、南宋尚体、元人尚意” [26],虽前有南宋院体画的曲折,但元代文人画家继承北宋传统。其中翰林国史院文士的主导地位,使元代的文人画更为成熟,他们深厚的学术修养以及高雅的审美情趣,使元人更为注重画的意趣,崇尚内美。赵孟頫强调“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 [27]其“复古”论调显然是针对南宋院体画风而发,强调对“神”和“意趣”的追求,以复古为创新,追攀魏晋风度气韵,力扫南宋院体画弊端。色目文士代表高克恭推崇平淡天真的审美趣味,强调艺术的抒情性,邓文原《题高房山墨竹图》一诗谈到了关于创作论和欣赏论的问题:“人才有我难忘物,画到无心恰见工。欲识高侯三昧手,都缘意与此君同。” [28]“画到无心恰见工”,可见其对于静穆境界和尚意风气的追求。此外,黄公望的“逸墨撇脱”,吴镇的“墨戏”,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等,都体现对了“重神而不重形”的追求。与之相对的另一面,是绘画中追求气韵生动、率简高古之风,王恽言:“看画当观其气,次观神,而画笔又次之。” [29]可见,王恽品评绘画的方式与赵孟頫的主张也有内在的一致性。以上重神似和重气韵的主张正是古意的内涵。今人杜哲森也认为“元代绘画更注重诗的意蕴和情境的发掘与表现,更善于在物象实景中发出性情之美和格调之淳,使绘画与文学在审美理想上得以汇合……以诗情入画” [30],这种审美观念使得题画诗的创作更加注重阐释画外意境、表达作者思想以及补充整体的画面结构,进而实现诗与画的完美结合。
四、结语
题画诗作为典型的空间化了的时间艺术,为诗歌在口头流传、结集流传之外新开辟出随画流传的新方式。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题画诗作为传播媒介,不仅传达出画中及画外之意,成为扩展、完善和升华画境的重要载体,而且深刻地阐发了诗艺观点。在民间俗文学盛行的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作为文坛正宗在题画诗创作上的示范作用,客观上刺激了元代题画诗的发达。其题画诗创作以诗体的形式言说着绘画、书法等艺术思想,诗画合一,虚实相生,实现了诗歌与绘画美感的互递。而以诗言画,为了传达画面之“气韵”,造就了诗歌普遍形象生动、意态丰满的特点,即便是理学之士也不例外。可见,题画诗本身即为元人宗唐复古中无意识却最有力的工具,坚守并强化了诗歌作为正统文学的雅正清逸之风。
李泽厚云:“唐人题款常藏于石隙树根处(与外国同),宋人开始了写字题诗,但一般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影响对画面——自然风景的欣赏。元人则大不同,画面上的题诗写字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很大画面,有意识地使它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31]如张中《桃花幽鸟图》上有近20位文人墨迹,画面上水泄不通,以至于见缝插针。那么,这样是否会造成“诗夺画意”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同时,作为馆阁之臣,翰林国史院文士的题画诗中也充斥着大量无聊的酬赠、应诏之作,内容贫乏,缺少寓意,且诗味不多,也需要我们客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