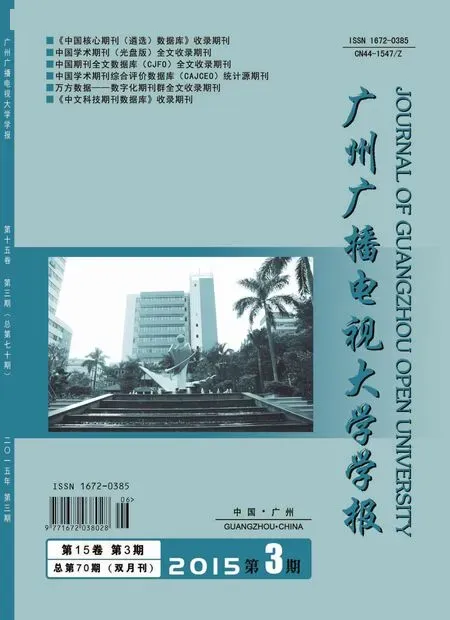从刘禹锡诗文看其在连州、夔州、和州的政治努力
苗 苗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刘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1],贞元十一年,“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2],至此“三忝科第”[3],踏上仕途。从作于贞元年间的作品看,刘禹锡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对当朝弊政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其《因论七篇》中的《讯氓》,是贞元十二年(796)汴州三乱后董晋初至镇时所作,通过与流亡农民的对话,深刻阐明了政治上“声”与“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应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声实之先后。这种政治上的求实精神在官吏为政的要求上就表现为一种实干的精神,刘禹锡在《与刑部韩侍郎书》中提出“既得位,当行之无忽”[4],这实际是对当政者提出了在其位谋其政的要求。然而永贞革新持续时间太短,刘禹锡虽进入了革新集团核心,但却未能尽情施展政治抱负。宪宗元和元年(805),刘禹锡“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5],在朗州十年,元和十年(815),自武陵召还,然复出为播州刺史,又改受连州刺史。虽然在朗州时有过消极怨愤,但作于朗州后期的《何卜赋》中透露出自己坚定的政治理想,赋末云:“于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6],更见其实现理想的决心和意志之坚定。在随后的连州五年,夔州四年,和州两年多的刺史任上,刘禹锡用实际的政治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做出了不俗的政绩。
一、支持削藩
唐朝藩镇割据自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陈寅恪曾说“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7]到德宗时期,藩镇势力更加锐不可当,《新唐书》卷七赞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 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 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 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8]刘禹锡在贞元年间就认识到德宗朝的弊政不可不除,并做《鉴药》一篇以刺时政。永贞革新有裁抑藩镇的措施,但因革新持续时间太短,还未取得显着成效。反对藩镇割据是革新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刘禹锡一贯的主张。
元和十二年(817),由裴度督师,李愬率军攻占蔡州,活捉吴元济,平息了淮西叛乱。远在连州的刘禹锡闻知此讯,万分激动,向朝廷上了《贺收蔡州表》,向裴度上了《贺门下裴相公启》、《上门下裴相公启》,并挥毫写下《平蔡州三首》:
蔡州城中众心死,袄星夜落照河水。汉家飞将下天来,马棰一挥门洞开。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狂童面缚登槛车,太白夭矫垂捷书。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四人归业闾里间,小儿跳踉健儿舞。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四夷闻风失匕筋,天子受贺登高楼。妖童擢发不足数,血污城西一抔土。南风无火楚泽间,夜行不锁穆陵关。策勋祀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常山。[9]
如果说《贺门下裴相公启》、《上门下裴相公启》还有刘禹锡希冀裴度秉上重用之嫌,那《平蔡州三首》则是真情的表露,远在贬所,闻削藩取得胜利的动情之作。诗中一云狂童,再云妖童谓吴元济也,据瞿蜕园笺证,“其实元济年非童幼,禹锡概恶宪宗之淫刑,诛及稚孺耳。”[10]按此说则这三首诗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首先,刘禹锡确实为削藩取得胜利感到高兴,“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也对裴度和李愬表示赞扬,对朝廷中央政权的稳固加强了信心。但同时,禹锡于宪宗之穷兵黩武,深所不取,“猛士按剑看常山”可见其曲折之义。
元和十三年三月,王承宗上表请求悔过自新,并交出德、棣二州。刘禹锡又上了《贺雪镇州表》,表云“大河以北,化为礼乐之乡。率土之滨,重见升平之日”[11],由衷的喜悦足见刘禹锡支持削藩的态度。元和十四年二月,割据淄、青十二州的李师道又被部下刘悟所杀,师道所管十二州平。刘禹锡再上《贺平淄青表》,并作《平齐行》二首。表云“五纪巢穴,一朝荡夷。遂使齐、鲁之乡,复归仁寿之城。”[12]这都因“感我仁化,激其深衷”[13]。《平齐行》中也热情赞扬了削藩的胜利:“驿骑函首过黄河,城中无贼天气和。朝廷侍郎来慰抚,耕夫满野行人歌。”[14]用削藩来维护国家统一,是刘禹锡始终的主张,远在岭南,不能为削藩出谋划策,但依然心系朝廷,由衷地为削藩胜利感到欣慰。
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与实际努力
元和十年刘禹锡自朗州奉召回朝,本以为迎来了事业第二春的他,却再次被贬到播州,虽是刺史,实为“官虽进而地益远”[15]。后因裴度上奏得以改授连州刺史。两唐书关于连州有如下记载:《旧唐书·地理志三》记“隋熙平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连州。天宝元年,改为连山郡。乾元元年,复为连州。”[16]《新唐书·地理志》七上载连州隶属于岭南道,管辖县有三:桂阳、阳山、连山。贞元二十年,韩愈被贬至连州阳山令时,其《送区册序》谓“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邱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17]由此看来,连州是一个偏远遐荒之穷地,生存环境险恶,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韩愈被贬阳山时,内心感情极度激愤,带有愤懑抑郁怨仇之情,或许评价并不客观。刘禹锡初至连州,就写了《连州刺史厅壁记》,在文中详尽描述了连州的天文地理、建制沿革、山川气候和人情物产,展现了一个民风淳朴,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连州。“山秀而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林富桂桧,土宜陶旊,故侯居以壮闻。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丽闻。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驱温……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墟也”[18]。可见刘禹锡对连州的印象颇佳。记中还提到“或久于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翘颙载于歌谣”[19],表明了他治理地方的宗旨,将“功利存乎人民”,作为一以贯之的目标。
(一)深入了解民情,大量写作民歌
囿限于地方官职的身份,刘禹锡难以以正式的文书向朝廷呈奏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自古就有采诗的传统,刘禹锡转而在自己的诗文中将政治理念曲折地表达出来,以俟采风者。早在朗州时期,刘禹锡就在《答饶州袁使君书》中深刻论述了自己治国安民的想法。提出统治者在施政时当因时、因地,灵活变换政策,还建议统治者设缿筒,接受百姓的监督检举,杜绝地方权贵滥用职权。到连州之后,深入了解民风民俗,体察百姓生活,创作了《插田歌》、《莫徭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蛮子歌》等作品。这些诗歌的创作,拉近了他与当地百姓的距离,对维系地方统治大有益处,是刘禹锡在贬所维系世道民心的有力手段。中唐时期,岭南少数民族不堪唐朝官吏的压迫和剥削,曾多次起来反抗。连州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 ,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对与之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莫徭歌》对莫徭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婚姻制度、买卖生产等方面进行描述,诗云: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20]
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则选取观猎这一角度,歌颂莫徭狩猎人狩猎的壮观场景:
海天杀气薄,蛮军部伍器。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如烧。围合繁铮息,禽兴大斾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麏时踞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馀鹄血,鞍傍见雉翘。日莫还城邑,金笳发丽谯。[21]
莫徭之名,最早见于《梁书·赵缵传》,莫徭得名,是由于“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22]然而至中唐,一系列的削藩运动造成财政紧缺,宪宗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整顿江淮财赋入手,加强赋税征收,尤其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的赋税分配。元稹《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中说:“请令天下州县,有山野、溪洞无布帛、丝绵之处,得以九谷、百货,一物已上,但堪本处交易用度者,并许折纳,便充留州、留使钱数。”[23]既然“山野、溪洞”等少数民族亦应征税,此时莫徭是否依然享有免征徭役之待遇也未可知。且韩愈被贬阳山所作《送区册序》中云:“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24]这足以说明此时莫徭需要征税。新旧唐书中也有关于莫徭与朝廷发生激烈冲突的记载。以上皆可说明,中唐时期,尤其宪宗朝,莫徭与朝廷关系颇为紧张,禹锡正任职连州,并作有以上作品。
不论是《莫徭歌》中对徭族同胞在千仞溪涧这般恶劣环境下勇敢的生活状态的赞扬,还是《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里饱蘸热情的语言展现出的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狩猎景观,都饱含着刘禹锡对莫徭同胞的友好感情。作为被二度贬谪的地方官员,能做到知百姓疾苦,试图增进彼此的了解与感情,是一种政治职责所在,更是一种胸怀。
(二)抨击现实,不遗余力
《插田歌》亦作于连州时期,与上面两首不同的是,不但有当地农民在田间劳作的描写,还具有批判精神。全诗如下: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傍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田夫诘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罢,眼大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25]
诗歌前面部分记述了连州田妇、农夫在田间劳作的欢歌笑语以及田间村落景色的优美宜人,将色彩、动态和音响的词汇交织在一起,意境清澹闲远,诗人语气平和,饱含赞美。从“自言上计吏”开始,诗人笔锋一转,将计吏用头等细布换取禁军空缺的丑恶嘴脸娓娓道来,计吏的狡黠无耻同农夫的淳厚正直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地的风土人情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缩影表现出来。沈德潜《唐诗别裁》中云:“前状插田唱歌,如闻其声;后状计吏问答,如绘其行。”[26]刘禹锡这首诗或许并非无心之作,永贞革新时,王叔文曾亲任计相(度支副使),刘禹锡、韩晔等人在计司任职,一度使“奸吏衰止”[27]。但革新失败后,奸吏复起。刘禹锡将奸吏的嘴脸揭露出来,正是其想要匡正恶习,整顿吏治,进而净化社会风气,使百姓免于奸吏的欺压和迫害。与创作民歌,深入百姓生活一样,这种批判的背后依旧是刘禹锡以民为本的思想。他曾在《贾客词》中揭露官商勾结、商贾垄断市场,导致贾雄农伤的局面,一句“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28]深刻道出了农民生活之艰辛。如今远在岭南,无法像从前一样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却有机会与百姓接触,更直接地发现国家弊政之所在。一路贬谪的刘禹锡做了五年亲民爱民的连州刺史,不忘初心,一如既往的坚定。
(三)全力救灾,心系百姓
如果说民歌创作和抨击社会现实还都只是以诗文为武器,那么在和州的赈灾之事则毫无疑问是刘禹锡心系百姓,以民为本的最有力的证明。由于常年贬谪远州,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下层百姓的真实生活。夔州所作《机汲记》就是对当地人民生活进行细致观察与了解后所作。长庆四年正月,敬宗即位,夏,调刘禹锡为和州刺史。刘禹锡抵达和州后,正值当地旱灾之后。在《和州谢上表》中,刘禹锡云“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恩,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方。”[29]关心百姓之情充斥其中。在去夔赴和所作的《历阳书事七十韵》中云“退思常后己,下令必先庚。”[30]同样是先百姓后自己的博爱胸怀的表现。据卞孝萱《刘禹锡评传》,段文昌大和元年六月四年三月为淮南节度使,耳闻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的政绩,加之与禹锡素有交往,故表荐入朝。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禹锡和州时期政绩斐然。
三、对人才任用和州县治理的深入思考
唐穆宗长庆元年,刘禹锡被任命为夔州刺史,夔州即今重庆奉节,地处巴东,是湖南和四川的交界处。与连州相比,夔州距离京城要近很多。刘禹锡于长庆二年抵达夔州,即上《夔州谢上表》,“竟坐连累,贬在遐藩”,“又遭馋疾,出牧远州”,此次至夔州,“伏感天慈”,但又“空怀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可见其渴望回京,再干一番大事的心情。事实是,刘禹锡没有等来回京的诏令,但还是表达了自己认真治理夔州的决心并且向朝廷提出了自己恳切的意见。
长庆三年和长庆四年分别向朝廷呈上《夔州论利害表》和《夔州论利害表二》,前表中有言“臣伏见贞观中诏许群臣各上书言利便。马周时一布衣,遂因中郎将常何,献策二十余事,太宗深奇之,尽行其言,擢周为御史。至龙朔中,壁州刺史邓弘庆进平索看精四字堪为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迁弘庆为朗州刺史”[31]。以太宗和高宗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之例,进而谈及“则知苟有所见,虽布衣之贱,远守之微,亦可施用。”[32]发表了对于任用贤才的看法,其中虽不免有渴望被任用之意,但对于任贤用能的观点是有助于中央加强统治的。永贞革新时王叔文任用贤能,刘禹锡长庆三年依然提倡,可见其革新精神并未消磨殆尽。
第二表以开元十八年裴耀卿上便宜事,论转输甚详却不被采纳之事开始,“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再以前事奏论,方见允纳。”[33]结果成效显着:“比及三年,漕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馀万贯。”[34]瞿蜕园笺证曰:“今录十八年(七三〇)耀卿之奏于下,以见牧守之于当地利害知之较切,且以禹锡所陈必非泛泛者,惜其陈奏之文不传矣。”[35]深刻道出禹锡上此表的远见卓识,地方官员关于当地治理的意见,朝廷如若采纳,无论对中央还是地方都大有裨益。
据《唐会要》卷六八载:“十二年四月勒:‘自今以后,刺史如有利病可言,皆不限时节,任自上表陈奏,不须申报节度观察使。’”[36]刘禹锡以上两表即据此勒。夔州时期,还上奏一篇《奏记丞相府论学事》,概禹锡所陈利病之具体内容。禹锡反对大肆花费于州县释奠,而应将钱款用于学校经费事。具体呈奏如下:
十一月七日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夔州刺史刘某谨奏记相公阁下:凡今能言者,皆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而不扬,非天不生材也;亦犹不耕者而叹廪庾之无馀,非地不产百谷也。伏以贞观中增筑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馀人。时外夷上疏,请遣子弟入附于三雍者五国。虽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胶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圮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能振学也,病无赀财以给其用。鲰生今有一见使太学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
礼云:凡学官春释奠于其先师。斯礼止于辟廱判官,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于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汉初定,群臣皆起屠贩为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孝元时,韦玄成以硕儒为丞相,遂建议罢之。夫以子孙尚不敢违礼以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之道而首违之乎?祭义曰:祭不欲数。语云: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旧飨,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愤悱也。[37]
文章前两段先以比喻引出话题,进而提出“非学官不能振学也,病无赀财以给其用”[38]的观点,第二段则由《礼》至汉代关于释奠的做法层层展开,自然引出“与其烦于旧飨,孰若行其教道”[39],为下文提出自己关于罢释奠而移作学校经费事做了铺垫。刘禹锡详细陈述了夔州当时的情况“谨按本州四县,一岁释奠物之直缗钱十六万有奇。”[40]进而推导出“举天下之郡县,当七千百不啻,羁縻者不在数中。”[41]基于此种情形,提出自己的建议“罢天下县邑牲牢衣幣。……然后籍其资,半附益所隶州,使增学校,其半率归国庠,犹不下万计。筑学事,具器用,丰籑食,增掌固以备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率令折入。学徒既备,明经日课缮书若干纸,进士命讎校亦如之。”[42]这样不但能强化教育体制,而且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可谓一举两得。增学校,使得国家多了培养人才的土壤,与之前《夔州论利害表》中谈到的任用人才也有密切关系,都对国家建设有重要意义。后大和年间,刘禹锡任集贤殿学士近四年的时间里,供进新书二千馀卷。也是其对于文化教育极其重视的佐证。
四、结语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自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在外二十多年,经历了朗州十年的思索总结,其后的连州、夔州、和州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俟时而志坚,功利存乎人民的刘禹锡。无论是为削藩胜利的欢欣鼓舞,还是以民为本的政治思考与实际努力,亦或是不懈上表呈奏利害,都是刘禹锡渴望对国家建设出一份力,为黎民百姓做一点实事的直接体现。被“贬谪”二字跟随了大半生的刘禹锡有着难能可贵的乐观精神与积极态度,《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3]曲折的道路并未使他蹉跎一生而是更加激发了他坚强的意志与进取精神。正如《浪淘沙词九首》中言:“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44]诗人有坚定的信念,狂沙终究盖不住真金,迁客刘禹锡以诗文为见志之具,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这份努力本身就值得肯定,更遑论还卓有成效。
[1][5][16]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0,1619.
[2][3][4][6][9][10][11][12][13][14][18][19][20][21][25][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4]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501,358,274,22,764,765,354,356,768,218,813,751,838,566,369,1477,373,375-376,544-545,864.
[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13.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9.
[1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709.
[17][24]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98.
[22]魏征等主编.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98.
[23]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414.
[26]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
[27]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64.
[3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203.
[43]陈鼓应,赵建伟注释.周易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