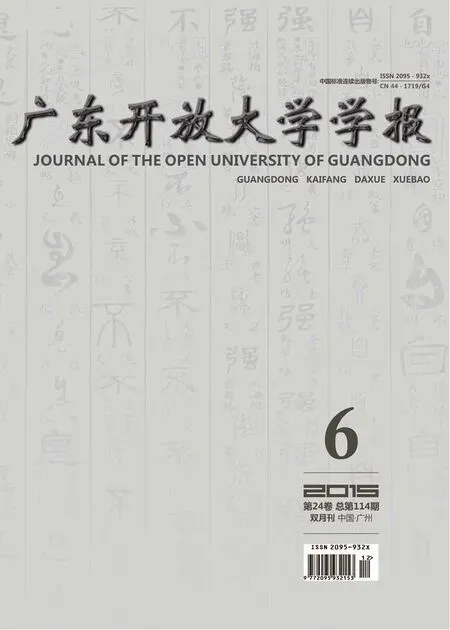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兼谈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吴华眉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66590)
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兼谈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吴华眉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66590)
西方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强调平等的“女权”运动到强调差异的“女性主义”到以“身体”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三次大的浪潮,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经历了从相互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到逐步融合到一体的发展过程。厘清这一关系对丰富发展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至关重要。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平等;差异;后现代
女性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阵营,派别林立,其自身包含了许多矛盾的观点与理论困境,但女性主义却有一面共同的旗帜,即努力消除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使女性获得充分自由和全面发展。以此为基点来梳理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女性主义经历了早期强调平等的“女权”主义,而后强调“差异”的女性主义,到当下以“身体”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三次大的浪潮和思想阶段。仔细考察西方女性主义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逐步融合的历史关系。
一、两条理论线索: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认为,女性是未完成的男子,在发展的阶梯上尚处于较低阶段。男性天生优越,女性天生卑劣,一方统治,另一方被统治[2]。可以看出,男女不平等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直到近代,男女不平等问题才真正获得人们的关注。
从理论线索上来看,女性问题研究在西方社会的缘起大致有两条线索[3]。第一条线索是占主流地位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早在17世纪就有了女性主义者的系统理论①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英国女性艾斯泰尔就进行了稍具规模的女性主义抗争(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理论趋于成熟。女性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年发表著作《为女权辩护》,其核心思想是倡导两性平等教育,抨击传统教育模式不鼓励女性发展理性能力。半个世纪后,1851年,哈丽特•泰勒发表《妇女的选举权》,1869年女性主义男性学者约翰•穆勒出版《女性的屈从地位》,他(她)们在坚持颂扬理性和平等教育的理念的基础上,将平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看成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关键。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强调女性受压迫的性别根源,从人权角度要求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新制度。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女性运动掀起第一次浪潮②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运动的目标主要是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如女性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此外,这次运动浪潮还提出女性流产、避孕和生育方法等女性身体的自治权利,不过,从总体上看,此时的女性主义者在对自我的认知上仍是把传统的男性特征设想为女性改造的样板,通过强调男女的同一性来实现男女平权,并进行相关实践。
女性问题研究的第二条线索起源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其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和发挥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压迫的社会现实。傅立叶第一次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并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4]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傅立叶关于女性地位和女性解放的思想,认同傅立叶关于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革命的标准这一结论,始终支持和维护妇女的社会平等权利。马克思在其早期和成熟时期的许多著作中,“不仅对西方传统性论述及其社会文化基础进行了批判,而且集中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性论述的政治经济基础,集中批判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国家官僚机构的决定性作用”[5],表明了“有性别的身体”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历史概念③近来,一些学者对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性别观进行了重要区别,他们认为恩格斯对性别的理解更具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马克思的性别观更为辩证(相关研究参见Heather Brown.Marx on Gender and the Family :A Summary, Monthly Review, Jun2014, Vol. 66 Issue 2, p48-5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阐释了两性分工、私有制和家庭中妇女受压迫地位的根源,指出私有制导致了性别分工的奴役形式和父权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是参加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妇女运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妇女运动是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这两条理论线索影响下的女性运动,分属于西方社会的女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两大系统。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整个女性运动处于低潮。
二、逐步融合:西方女性主义在第二次浪潮中对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探索
20世纪初以来,女性的选举权和受教育权等基本政治诉求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得到解决,此后,西方女性主义便开始寻求和建构新的女性解放理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理论探索过程,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兴起。这次浪潮中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不断增长,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它们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消除两性差别,在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一切领域中争取男女平等。追随西蒙•波伏娃《第二性》的中关于“女人不是天生的”著名论断的指引。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特点,关注身体在社会关系与文化情境中的被动构成。她们对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构成性的“社会性别”(gender)进行了区分,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制度是“一套安排”,社会通过这套安排把生理性别转变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父权制社会正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建构出一套所谓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身份与行为,力图使所有人相信它的文化建构不言自明是“自然”的。同时,她们以“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为口号,强调性别政治中身体的重要性,强调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以及女性身体自治的愉悦。不过,综观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者对身体的认识,会发现她们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仍然是在一种自然/文化的二元论之下展开的,仍是一种理性主义关照之下的静态物质身体论。
这次浪潮影响巨大,除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之外,女性主义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者尝试把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以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詹姆斯(Selma James)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直接师承马克思、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阶级、生产等概念范畴,围绕家务劳动对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和女性解放的途径从物质和经济层面展开探讨。她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将女性受压迫的终极原因归结为阶级歧视而非性别歧视,认为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结束对女性的压迫。由此,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④国内学界对此没有统一界定。陈学明把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学术界日趋活跃的一股社会思潮(参见陈学明《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批判》,《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张一兵认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后马克思思潮(参见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秦美珠将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统称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参见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本文采用第三种说法。的社会思潮也开始形成。
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女性的解放,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上的性别盲点,也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局限。因此,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以哈特曼(Heidi Hartmann)、萨金特(Lydia Sargent)、沃格尔(Lise Vogel)、贾格尔(Alison Jaggar)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不是简单的阶级歧视或性别歧视,而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她们致力于理解由资本主义父权制派生的权力体系,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的有效途径。
三、一体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转向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文化危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最集中充分的体现,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人早在西方社会文化危机初露端倪时就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三位怀疑大师的叛逆精神交互渗透构成强大的批判力量,对20世纪的厌倦传统抽象哲学的思想家发挥了重大影响。从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拉康到罗兰•巴特、布尔迪厄、福柯、德勒兹、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Chantal mouffe)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将马克思的实践和批判精神作为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于人的自由解放的诉求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诠释。尤其是当经历苏共垄断的官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以及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之后,许多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宣称马克思的自我批判的反思精神,将对马克思的研究推进到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起到重要作用。在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身体、主体、主体性、语言等概念成为哲学家反思的基本点。他们批判甚至解构了理性主义的主体概念,提倡身心合一的思维方式,反对身心分离。
面对马克思思想的“再出发”和后学研究的冲击,西方女性主义开始新的转向。当代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当代思潮相融合,进入新的“后现代主义”发展阶段。女性主义开始逐步扬弃西方启蒙主义建立在宏大叙述基础上的认识论,转向对语言、文化和话语实践的研究。此时,强调差异和多元化的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兴起,对不同社会文化中女性之间的差异研究加强,将对“身体”的哲学研究上升到其理论的核心位置。朱迪斯•巴特勒的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体的颠覆》(1990)、《身体至关重要》(1993)、露丝•伊利格瑞的著作《此性非一》、《性别差异伦理学》、埃莱娜•西克苏的文本《美杜莎的笑声》以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恐惧的权力》等都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关于身体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女性主义者有关身体的理论虽不尽相同,但她们被统称为“身体女性主义者”(corporeal feminist),她们的共同特点表现为:详尽审视二元思维的弊病;解构固定化的主体性概念;拆解二元论中将男性与精神、女性与身体进行嫁接的父权话语。从而,探究重新思考身体的新方法;建构独特的身体话语;将女性从生命中无法承受的肉体重负中解救出来,回归充满活力的身心合一的身体。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型(特别是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独领风骚)和女性主义的新转向,尤其是面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政治实践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危机,一些曾经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者(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开始认识到仅仅从物质生产、经济层面探讨女性所受的压迫以及女性解放问题,不能说明女性的作用和女性受压迫的复杂性。她们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关于意义和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等几种话语结合,转变为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既坚持社会的总体分析,强调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包含了后现代的语言与主体性,同时涉及对“身体”的唯物主义解释。在这里,关于身体研究的重要文本有艾莉斯•杨的论文集《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1990)、堂娜•哈拉维的论文《赛博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文集《类人猿、赛博格和妇女》(1991)、陶丽•莫伊《性与文本的政治》等。其中,无论艾莉斯•杨对现象学意义上身体体验的强调,还是堂娜•哈拉维对作为人机统一体的赛博格形象的想象等,都与身体女性主义的理论相互论证和融合,突出了对身心统一的强调,对身心分离的批判。不难看出,此时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中,大大扩展了其分析和批判的领域,进入一体发展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发展之初并不归属于一条理论线索,然而,在其各自的理论开端上,它们都有着对女性平等地位和自由解放的共同追求。因此,随着理论的发展,它们逐步走向不断地融合和共同发展。这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使然,同时也将使得它们对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这一伟大目标更好地得以实现。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7.
[2]【美】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M].金发燊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120.
[3]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与现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4]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A].全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74.
[5]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70.
(责任编辑: 弱水)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Western Feminism——Concurrentl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Marxism
WU Hua-me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China,266590)
The feminism development has three stages: from “equality of the sexes” to “differences of the sexes” and ‘body’of post-modern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feminism and Marxism has also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clues to partially combined one,then to integration. The paper stated that it is crucial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sm and Marxism.
feminism; Marxism; equal; differences; post-modernization
D440
A
2095-932x(2015)06-0053-04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女性身体观研究”(13DZXZ01);第56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2015-09-07
吴华眉(1980-),女,山东济宁人,博士,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哲学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性身体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