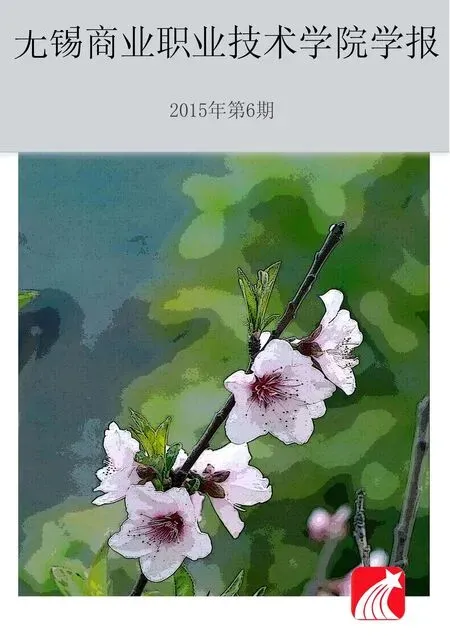党建对于社会组织失灵的矫治作用研究
王傅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州 511442)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党建对于社会组织失灵的矫治作用研究
王傅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州 511442)
社会组织失灵是一个普遍但不为人们重视的现象。纠治失灵的方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有所不同。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在社会组织中建立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基层党组织,有利于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能力,更有效地实现公益目标。
党建;社会组织;失灵;矫治
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非营利组织的称呼繁多,如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免税组织、第三部门、独立部门等。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全权控制社会,自然而然地将社会上的组织分为官办组织和民间组织。自2007年11月起,社会组织一词的启用,正式取代了民间组织,从名分上消除了人们在字面上对“民间组织是与政府相对应甚至是相对立”的误解,成了中国式非政府组织的代名词。
在配置资源进行社会治理的手段中,市场被认为是效率最高的,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但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均和区域经济不协调等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发现了“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于是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即“看得见的手”。但政府并非万能,政
府工作人员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干预带来了政府规模膨胀过度、巨额财政赤字、寻租、交易成本增大、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等问题,即政府失灵。在两大失灵并存的情况下,人们把视角投向了社会,希望社会组织(第三部门)能够终极地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然而事与愿违,社会组织同样也出现了失灵问题。
一、社会组织失灵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社会组织失灵的表现
最早对社会组织失灵进行探讨的是萨拉蒙(Salamon),他站在慈善角度称之为“志愿失灵”(Voluntary Failure)[1],指非营利组织行为偏离公益机制,出现资源配置低效或非公共性现象。萨拉蒙认为社会组织失灵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1)慈善不足(Philanthropic insufficiency),即所募资源不够开支。
(2)慈善活动狭隘性(Philanthropic particularism),即只面对了特定社会群体,忽视了另一些急需帮助的群体,导致资源浪费。
(3)家长作风(Philanthropic paternalism),即内部管理的不民主和不透明。
(4)慈善组织的业余性(Philanthropic amateurism),即慈善工作由志愿人士去做,他们爱心有余,但专业性不足,影响服务质量。
在我国,由于组织结构因素、法律制度因素、文化背景因素,以及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失灵更为严重[2]。除萨拉蒙所述一般性失灵表现外,还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失灵表现,如违规行为、腐败现象、公信力缺失、自身合法性不足、生存状态艰难等。
(二)社会组织失灵的原因分析
1.内部因素
(1)历史因素导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低。数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使得中国的社会组织发育很不充分。往往是到了王朝末年,皇朝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各种社会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社会组织与其说是非政府组织,不如说是反政府组织,他们往往利用迷信或邪教蛊惑人心,煽动人民作乱,目的是改朝换代。自晚清以降,近百年来,我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动”(梁启超语),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逐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社会组织管理也从“严格限制”向“逐步放松”转变。在改革开放前的严格限制时期,除了党和政府自己设立的工青妇组织和几个人民团体外,其他社会组织几乎不存在,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社会领域也不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职能转换和权力让渡,社会组织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但由于长时间对社会的自我治理重视不够,社会组织发育严重滞后,发展程度依然较低。
(2)现实中营利性诱惑导致社会组织丧失使命感。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第三部门)三大社会治理主体中,政府是唯一可用国家强制力来控制第三部门的,但企业凭借丰厚的财力资源对第三部门的影响力更大,第三部门很难抵挡企业的大笔资金诱惑[3]。尽管社会组织应该为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所驱使,追求社会效益,满足社会需求,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任何组织都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组织成员也多是理性经济人,难免受到利益的诱惑。
据邓国胜的《中国NGO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发现,中国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中政府补贴占到53%,服务收费占31%,民间捐赠占10%,外国援助仅占2%,还有其他收入占4%。经费不足造成了令所有非营利组织都头痛的危机。为弥补经费不足,非营利组织只能走向商业化,这是非营利组织功能扩张和资源获取难度加大的必然趋势。然而商业化运作也为非营利组织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许多社会组织直接从事营利性商业活动。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补偿,有些社会管理者甚至将许多时间花在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上,利用国家优惠政策逃税漏税,如此酿成一个又一个公益腐败事件。比如,1995年,美国最大的NGO之一“联合劝募”的前任秘书长威廉·阿拉莫尼由于挪用巨额善款而入狱7年;2001年,中国最早的民间自发NGO领导人之一,号称“中国母亲”的胡曼莉也因为一场跨国官司而走下了神坛,被发现利用慈善聚敛钱财,等等,都是现实中营利性诱惑导致社会组织丧失使命感的表现。
2.外部因素
(1)准入门槛过高,影响了社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合法性是一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有很多社会组织的身份面临着合法性问题。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例,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当前我国未经登记的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占到了90%以上。登记条件苛刻是原因之一。在
这种情况下,许多草根公益组织,初创时只是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在有限的空间、以有限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在缺乏法规规范和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在工商注册甚至是“黑户”的背景下,依靠志愿精神培育中国的公民意识,或者自生自灭[4]。这些非法组织并非不愿意取得应有的合法身份,而是因为不能达到现有法律要求,从而无法取得正式社会组织的身份。据《法治周末》记者对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访谈[5],为了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慧灵”专门成立了公关小组,但小组负责人李萌坦言,近百次的公关活动都以失败告终。
(2)制度缺失或不完备,使得社会组织缺法可依。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等法规,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规章,但这些行政法规或规章立法层次低,且着眼点都在登记上面,而且登记条件苛刻,将很多正当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与严格的登记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规对社会组织的保护、规范及监管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形成了把门严与监管松并存的奇怪局面。
(3)缺少社会治理文化根基,使得社会组织起不到大作用。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体系是一个差序格局,是“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从已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6]。人们在遇到困难或者灾祸时,往往是沿此格局逐步求助的。先找亲戚,再找朋友,再找熟人,当个体的社会资源用尽仍然无助时,人们便乞求于清官或者圣君为民做主。解放后,政府公权力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便习惯于“有困难,找组织”“有困难,找政府”或者“找警察”。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成了人民群众的爹妈。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企求人们将希望寄托于他们并不熟悉的社会组织有些勉为其难。在现实中,很多人对社会组织完全不了解,以社会工作行业为例,2014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调查”对全国3012人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高达73.4%的受访者不了解社工行业,其中,50.2%的人误以为社工就是义工或志愿者,23.2%的人将社工当成了居委会人员[7]。可见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二、党建工作对于社会组织失灵的矫治作用
(一)党建可以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
社会组织登记条件之所以严苛,与政府对社会组织不够信任有很大关系。社会组织信任一方面源自于内部成员,另一方面则在于组织外的信任,包括其他个体与组织,其中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信任至关重要,直接决定和影响着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取与活动空间等。缺乏执政党与政府的信任,社会组织连生存都成问题,发展更是举步维艰。一项对中国草根慈善组织做过的调查显示[8],能够生存两年以上的组织不到30%,能够生存3-4年的只有15%,草根慈善组织队伍不稳定,与其活动资金来源有很大关系。缺乏政府信任的草根社会组织,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获取社会资源。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信任不足,我们可以借鉴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加以分析[9]。科尔曼认为,信任是两个理性行动者(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在这个理性行动中,双方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面对着对方不守信用的风险。当委托方信任受托方时,受托方如果违背诺言,会暂时得利,但将使受托方处于劣势,利益受到损失。因此信任行为意味着风险,特别是对于委托方而言。同时,由于任何行动都需要一定时间,委托方只能在受托方提供服务或者交付产品之后,才能做出反应,这一时间差使得委托方风险更大。
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互动和博弈中,就存在这种信任危机,比如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当政府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为了承接此服务,往往会美化自己,以提高承接中标率。中标后,政府购买的费用将交付给社会组织,此时如果承接的社会组织想谋求利润,就会降低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政府只有到了社会组织提交服务成果的时候才知道此次政府购买是否物有所值或者遭受到了蒙骗或者道德风险。如果社会组织善于伪装或欺骗,可能会蒙蔽更长一段时间。
政府不信任社会组织,还与当前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如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间组织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民族分裂分子建立社会组织开展分裂祖国的活动,伪气功与邪教组织以养生保健和拯救苍生的名义招摇撞骗并泛滥发展,外国在华人士和港澳台人士在内地擅自设立民间组织制造舆情等。尽管很多草根公益组织的确是一心
一意为改善民生,但很多敌对势力或者邪教组织在成立之初,同样也是打着改善民生的旗号,这使得两者在早期阶段无法鉴别。换言之,政府对社会组织给予信任是有一定风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就需要一个媒介或桥梁,作为两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有学者尝试用社会组织孵化器做中介,但很多孵化器本身也是草根公益组织,政府对他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戒备心理。因此,在社会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将会是最好的联系方式。
在社会组织中加强党组织建设,将具有党员身份的人组织起来,如此将形成三赢的结局。一赢,对于党员个体而言,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基层党组织之中;二赢,对于执政党和政府而言,能够有效管理社会组织;三赢,对于社会组织而言,获取了一个赢得执政党信任的重要渠道。三方面和谐共赢,将有利于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安定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党建可以提高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
社会组织的价值在于服务社会。从理论上讲,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社会组织正好有优势。但现实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相当数量的社会组织守法意识薄弱,诚信不足,服务意识和水平不高,规制不力,效率低下,掌握资源较少,公信力不强,未能较好得到社会和服务对象的认可,在公共服务事业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除历史发展时间较短之外,社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是重要的原因。社会组织的天然缺陷源自两个方面。
首先,自愿性和志愿性造成社会组织结构松散,缺乏凝聚力和执行力。关于社会组织的定义,最受认同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的定义——“凡符合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五个特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非营利组织”[10]。自愿性是志愿服务的特性。社会组织的自愿性和志愿性,使志愿者能够为公益信念所驱使,不计较个人得失。志愿者个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也会因为想法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倡导自愿和志愿的社会组织对于这种情况却无能为力。这对于志愿者个人来说是来去自由,无牵无挂,但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却会造成损失,甚至会造成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的结局。这样的组织,自然没有什么执行力。
其次,缺乏必要的强制力,使得社会组织常常难以有效调动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组织与政府相比,缺乏国家公权力,与企业相比,由于其非营利的性质,又缺乏充足的资金。对于其内部成员,也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往往只能靠使命和信念来驱使,其热度是有限的。社会组织整合资源的能力往往不如政府和企业,比如社会组织在参与灾害救援中,很多志愿者空怀一腔热情参与救援,既没有专业技术也没有管理才能,所在的组织也不能有效整合这些资源,管理制度也不健全,在救灾应急工作当中,难以全面协调志愿者的救援工作,反而导致帮倒忙的现象出现,极大地伤害了志愿者的公益心[11]。
为了维系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很多社会创业者会采取一些灵活的管理方式。上海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认为,对于公益组织,应该“高层讲使命,中层讲专业,底层讲待遇。中低层人员的待遇我认为应该尽量靠近市场价格,要给予其体面的收入。”[12]这是进行社会组织管理的务实之举,也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很多社会组织成员并非为了崇高的目标而奋斗,更多的只是将在社会组织工作当成谋生的饭碗,获得应有的报酬。
与社会组织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其稳定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从毛泽东的“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邓小平的“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江泽民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胡锦涛的“要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直到习近平的“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等论断,都表明了我国历代领导人对于纪律的重视。正是因为有严格的纪律,我党才能够始终顺应时代潮流,团结高效,在战争年代是意志坚决的革命党,在和平年代也逐渐演进为善于科学治国的执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在社会组织中建立起一个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纪律的基层党组织,可以有效地改善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其决策能力和执行力,增强组织成员和志愿者的凝聚力,在提供社会服务时,能够迅速有效地整合和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为实现公益目标实施有效的行动,起到应有的作用。
[1]Salamon L M.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the Scop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A].Powel W W.The Nonprofit Sector.A Research Handbook[C].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110-113.
[2]潘左华.第三部门失灵及其矫治[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4):53-55.
[3]康晓光,冯利.2011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
[4]徐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56.
[5]“草根”民间公益组织的尴尬[EB/OL].[2012-07-12].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118.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
[7]调查显示七成人不把社工当职业[N/OL].[2014-05-22]. http://zqb.cyol.com/html/2014-05/22/nbs.D110000zgqnb_ 07.htm.
[8]戴先任.民间慈善组织该如何突围[EB/OL].[2013-07-29].http://guancha.gmw.cn/2013-07/29/content_8438863. htm.
[9]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99-125.
[10]王名.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芦山地震志愿者被村民骂走部分志愿者帮倒忙[EB/ OL].[2013-04-29].http://finance.stockstar.com/FB201304 2900000669_3.shtml.
[12]公益创业的6个阶段、9个难点和20个忠告——映绿同仁来自“第十一届晶报名人演讲周——阳光照亮公益”演讲活动的分享[EB/OL].[2012-07-19].http://www. npodevelopment.org/item.php?itemId=10205.
(编辑:林钢)
The Corrective Effects of Party Building on Social Organizations’Malfunction
WANG Fu
(Gua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Trade,Guangzhou,511442,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s'malfunction is not uncommon today but paid less attention to.Corrective methods of the malfunction would b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s.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China,Party building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stressed,and strict-discipline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established.All the doings above are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establishing trust betwee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government,but good for improvin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serve the society,thus,achieving its objectives of serving the public welfare effectively.
Party building;social organization;malfunction;correction
D 262
A
1671-4806(2015)06-0058-05
2015-07-16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课题(2012QN08);广东省高职教育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课题(YGL2013099)
王傅(1977—),男,湖北大悟人,讲师,社会工作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