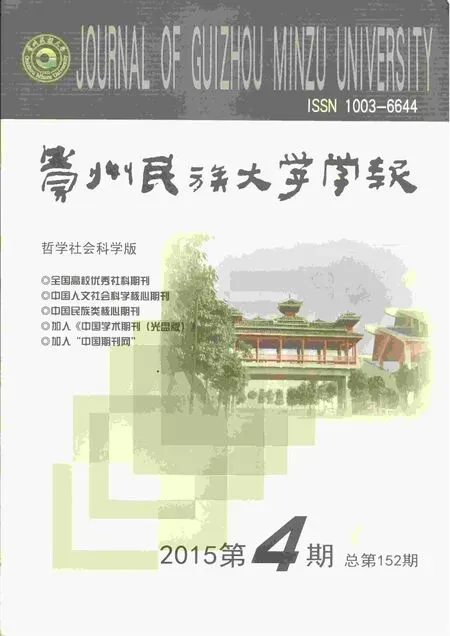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①
石经海,刘兆阳
(1、2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醉驾”因《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而成为《刑法》第133 条之一(危险驾驶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实施了“醉驾”行为是否一律构成犯罪,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没有达成共识,①并引发了审判实践中“醉驾”案判决理由的诸多差异,②以及因对“醉驾”案法律适用不完整进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践困忧。究此,这主要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弱视了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进而违背教义学方法的基本原理。本文试就法教义学视角对“醉驾”定性困境问题及其出路进行探究,以就教于刑法理论与实务同仁。
一、“醉驾”定性的理论纷争及实践尴尬
(一)“醉驾”定性之理论纷争
我国《刑法》第133 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据此条款可以看出,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应否有情节限制,《刑法》并没有做具体的限定,而是仅仅规定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一行为要件。由此,便自然引发了理论界关于“醉驾”行为“是否应一律定罪(入刑)”的定性争议。对此争议,有“一律定罪”和“区别对待”两种代表性观点。持“一律定罪”说的学者认为,“就《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而言,醉酒驾驶并不是以‘情节恶劣’为要件,‘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醉酒驾驶”,也就是说,“只要达到了醉酒标准的就构成犯罪,无需其他因素的考量”。[1]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层面上,“‘醉驾’一律入刑的主张,不违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刑事政策的刑法化要求刑事司法必须坚守法治这一立场”。[2]而与此观点相对应,“区别对待”说则认为,《刑法修正案(八)》的“醉驾”入刑条件虽然没有设置“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等程度要件,但“在理解和把握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时,必须受《刑法》总则条款规定的制约和指导”;[3]就罪刑关系而言,“醉驾”一律入刑“是说明了罪与刑之间的不对称,立法上入罪,但司法上不是所有的‘醉驾’都被认为是犯罪”,也就是说,“即便‘醉驾’是罪,也不一定都入刑;即便入刑,刑罚也有轻重”,基于此,“‘醉驾’入罪是立法理想,而‘醉驾’不一定入刑则是司法常态”。[4]
以上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在司法实务部门中也存在不同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原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则透露,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门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分别针对“‘醉驾’入刑”问题表态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厅负责人表示,对于检方来说,“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将一律起诉。
(二)“醉驾”定性之实践尴尬
基于“醉驾”定性之以上理论争议,在审判实践中,对“醉驾”行为入罪的定罪标准问题,是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在实践中,由“醉驾”行为入罪标准不明确引起的“醉驾”案定性尴尬,在众多刑事判决书的判决说理部分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部分地区法院根据《刑法》第133 条之一规定对实际遇到的性质相同的“醉驾”案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③综观“醉驾”入罪标准的相关规范,关于“醉驾”行为入罪的醉酒标准,只有《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④和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规定。然而,对于行为人具备此规定中酒精度的要求,是否就构成《刑法》第133 条之一的“危险驾驶罪”,在《刑法》所有条文规范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如此便造成一种困境,在“醉驾”行为人的醉酒程度满足《意见》中(醉酒驾驶机动车)酒精度的标准时,是否只要实施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便可以直接根据《刑法》第133 条之一(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定罪?
针对如此疑问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如此立法施行后不久的5月10日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所谓的“醉驾行为不一定都入刑”说明。⑤然而,如此说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并招致了部分“专业人士”的批评:“一个新法刚开始实施,其效应正在显现的时候,你就出来喊‘担心’”;“就算你说的是真理,多少也有些不合时宜”;“将本来确定无疑的‘醉驾’入刑规定‘讲晕了’”。[5]P172据此,同年5月18日,公安部向媒体通报了其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的态度和做法;5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通过其新闻发言人表明了他们关于“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的观点和做法。一项法律条文在施行伊始就引发“公检法”相继发出不同声音,不仅在中国立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也足以表明“醉驾”定性的实践尴尬。
二、法教义学是破解“醉驾”定性尴尬的必要工具
以上“醉驾”案判决说理部分的差异及关于“醉驾”案定性的理论纷争表明,无论是当前司法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醉驾”行为是否应一律入罪,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究其根源,在于对“醉驾”案的法律适用欠缺一种法典化的整体性立场并忽视了《刑法》总分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刑法思想史来看,没有方法论的转变就没有刑法学的发展。”[6]P5鉴于此,坚守整体性立场和体系化分析处理问题的法教义学方法原理,是解决“醉驾”行为定性尴尬的必要工具。
(一)法教义学方法及其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功能
对于何为法教义学,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然而将法教义学分为法教义学方法[7]与法教义学知识,⑥并将法教义学方法理解为一种“体系化的解释方法”,应是没有多大争议的。法教义学方法作为“建立在对法律有效性做出承认的基础上”[8]P92的一种无国界的普适性方法论,其具有方法论上的预设功能、体系化解释功能和批判修正功能,以使法律得到正确法律适用。
首先,法教义学方法具有预设性功能。“法教义学是以实证法,即实在法规范为研究客体,以通过法律语句阐述法律意蕴为使命的一种法律技术方法。”[9]将其表述为一种“教义”⑦,只是说法教义学方法与宗教信仰有着相似之处和一定联系,并不意味着二者等同。众所周知,宗教教义作为一种经典,有其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而这种不可置疑的“权威性”与法教义学方法论不可动摇的“预设性”有着相似之处。这种理解“其实是以给定的内容和权威为前提,而不是对该前提进行批判性检验。”[10]也即,法教义学方法论的预设性,是以既存的法律规范为前提条件,而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国界性要求其必须以本国现有的法律知识作为不加怀疑并予以接受的权威。可以说,对我国现行《刑法》的所有规定进行解释而形成的观点、学说和理论体系,就是刑法教义学知识;而对现有《刑法》通过一定的途径而形成法教义学知识的方法,便是法教义学方法;将现有的本国法律知识作为不加怀疑并予以接受的权威,便是法教义学方法中预设性功能的体现。任何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进行,都必须以本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前提,而预设性功能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是一种体系化的体系解释方法。法教义学方法首先是一种体系化的方法论,法律是由不完整的法条构成,只有与其他条文结合才能独立的成为进行法律适用的一个完整依据,这些不完整的法条“与其他条文结合成一个规整,只有视其为规整的部分,才能获悉个别法条的意义”。[11]P204这个规整部分即为法典化的法律体系。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化功能在法律中的作用即为,将繁杂的法律条文通过一定的顺序和逻辑方法予以归类、筛选和整合,使这些条文成为一个较为清晰、简洁的规范整体。不仅如此,“刑法教义学者可以根据实践理性的要求,对刑法规范做出与既存学说或者判例不同的解释结论,但是,这种新的解释结论不能与《刑法》条文规定相冲突”。[12]作为一种体系化的体系解释方法,法教义学方法在将现有的法律条文作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予以遵循的基础上,“根据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从而阐明其规范意旨”。[13]P144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断章取义,在保持《刑法》规范这一整体内部要素协调的同时,避免不完整的法律适用。例如,《刑法》第50 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此条文中,前两种情况均规定了“2年期满以后”,那么,对于第三种情况,是否只要实施了故意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便需立即执行死刑?或者说是否也需要具备“2年期满以后”才可以执行死刑?细察《刑法》第50 条的规定便可发现,该条规定的三种情况均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这一条件作为前提。因此,运用体系解释方法论可以得出,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一统摄性的前提条件下,三种情况所满足的条件应当具有同一性。因而,对于“故意犯罪”的情况,也应满足前两种情况即“2年期满以后”的条件后,方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以上论述仅是就《刑法》第50 条“死缓的法律后果”规定本身而言。其实,该条文中“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之所以没有明文规定“2年期满以后”的条件,还与《刑法》第48 条关于“死刑的条件、执行方式与核准程序”规定有联系。《刑法》第48 条第1 款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该款关于“死刑缓期执行”中“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的规定实际上对《刑法》第50 条已经做了总括性的限制。因而,“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作为《刑法》第50 条“死缓的法律后果”规定的一部分,需受《刑法》第48 条(2年期满后方可执行死刑)的制约,如此方法,也是体系解释论的一种具体体现。
第三,法教义学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还具有批判和修正功能。“法治是一种理念:法律应当遵守的一种标准,但是,法律可能(并且有时)的确彻底而系统地违背这一标准”,[14]P194由此而言,批判和修正功能在刑法学中的地位便愈加必要。法教义学的批判性任务也是法学研究与理论自由的依据,“它必须认识、公开和排除表面依据,并迫使隐藏的法律政策的价值标准公之于众。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和修正是法学(信条学)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15]P141
以上仅是对法教义学方法的各项功能进行的罗列和阐释。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是法教义学方法本身具有体系化的特征,以上所列举的三种基本功能本身便存在着彼此呼应的关系,并构成一个体系化的整体(系统)。具体就三者的关系而言,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化及其解释功能必须要以预设功能的实现作为其前提条件,即体系化的体系解释方法得以运行的基础和依据必须是已经得到认可和接受的本国法律条文规范。不仅如此,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化及其解释方法的运用也为批判修正功能的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也即只有以体系化的系统作为前提,要素之间的批判和修正才能实现。离开了体系化的系统整体,要素也就成为无稽之谈。由此看来,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化功能及其体系解释方法,不仅仅是维系法教义学方法的预设功能和批判修正功能的纽带,而且是法教义学方法的核心功能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精髓所在。
具体到法律适用过程而论,一方面,就法教义学方法的三种功能而言,法教义学方法的预设性功能要求其必须以我国现有《刑法》的所有规定作为不加怀疑并予以接受的前提,以此为基础启动刑事司法活动;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化的体系解释功能要求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必须以现有的刑法体系作为法律适用的法规依据,并在《刑法》规范整体中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解决疑难问题的法律适用;法教义学方法的批判与修正功能还要求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对适用法律发生错误情况时的修正和对适用法律不完整时的补充乃至修正。而另一方面,就三种功能的基本关系及体系论的地位而言,在进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将体系化的系统论作为根本方法论,并基于系统这一前提下,重视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具体到刑法典中来看,便要求《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予以限制、补充和修正。
(二)法教义学方法下的《刑法》分则的规范实质及总分则关系梳理
在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论下,《刑法》分则实质上是一个并不完整的法律规范。因而,在运用法教义学方法论进行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时,必须要以刑法典的所有规定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法教义学方法论的批判与修正功能正确处理《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内在关系,即重视总则对分则的补充、限制和修正功能。
法教义学方法论下的《刑法》分则,相对于刑法典而言,实质上是一个并不完整的刑事法律规范,它是相对于《刑法》总则而存在的。我国《刑法》总则(刑法典第1-101 条)对于犯罪、刑罚和刑罚的具体运用做了一般性的规定,如《刑法(总则)》第25 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两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但对于共同犯何种罪行及该种罪行的具体构成要件的内容,则没有明确规定。而相对于《刑法》总则而言,《刑法》分则将犯罪的一般类型分为十大类,并分列于我国《刑法》分则(刑法典第102-451 条)的十个章节中。因此,分则实际上是对具体罪名及其具体构成要件的法律规定。相对于总则的规定的一般性、统摄性的特征而言,《刑法》分则对具体个罪的规定本身便体现出了一种特别性的特征。再就《刑法》分则罪名条文的结构来说,《刑法》分则的罪名条文包括罪状和法定刑两个方面。其中,罪状是对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的描述,法定刑则是对具体罪名处罚内容的体现。将分则的罪状、法定刑与总则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特征相联系,不难看出,《刑法》分则的罪状实质上是一种特别的定罪要件,而《刑法》分则的法定刑实质上则是一种特别的刑罚配置。具体到个案而言,许霆案中,许霆先后取款171 笔,合计17.5 万元,潜逃一年后被抓获。一审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处以无期徒刑;二审在认定许霆犯盗窃罪的基础上,改处以5年有期徒刑。如果按照《刑法》分则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那么上述一审判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便不足质疑。然而,二审改判的结果与一审判决的结果的差异虽有天壤之别,却广为包括刑法理论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究其原因,在于二审法院充分运用了《刑法(总则)》第5 条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总则)》第13 条的“犯罪的概念”、《刑法(总则)》第37 条以及《刑法(总则)》第63 条的“减刑”等的相关规定,以此作为基础指导分则的具体适用过程,从而实现了“相对合理而又合法”的定性和处罚。
法教义学方法论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和修正功能,还表现为体系内此要素对彼要素的批判和修正方面。具体到刑事法律体系中而言,主要体现在总则对分则的功能具体表现在补充、限制和修正三个方面。
首先,《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具有补充功能。以我国《刑法》中的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例,我国《刑法》第133 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仅对“醉驾”行为予以明确,但并没有对“醉驾”行为的主体、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情节恶劣”的具体表现作出规定。这便需要《刑法》第13 条、《刑法》第17 条、《刑法》第17 条之一、《刑法》第18条、《刑法》第19 条以及《刑法》第5 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相关规定予以补充。此外,《刑法》分则中仅对个罪的构成要件予以表述,只是一种基本的犯罪构成,但在一人犯数罪的情况下却难以解决罪数问题,而《刑法》第69 ~71 条“数罪并罚”、第65 ~66 条“累犯”的规定,则较好地解决了行为人犯数罪和重复犯罪在分则中产生的定性和处罚等难题。
其次,《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具有限制作用。刑法中的“数额犯”是较为典型的代表。例如,在伪造货币犯罪中,《刑法》第182 条规定:“伪造货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仅仅按照此规定,那么,只要实施了伪造货币行为,无论数额的大小,都应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但司法实践中,对于伪造1 元货币的行为并没有立案和公诉。究其原因,在于2000年9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伪造货币总面额在2 000 元以上不满3 万元或者币量在200 张(枚)以上不足3 000 张(枚)的,依照刑法第170 条的规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结合此规定可以看出,《刑法》分则中的“伪造货币罪”除具备伪造行为外,还应当具备司法解释中伪造货币币量(数额)的要求方可构成。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司法解释,其应受立法上的相关规定的指导。司法解释的“司法性”是基于刑法典的“立法性”的指导而存在的。这里,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如此解释性文件的不是其它,正是《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一切……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法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由此而言,与其说是司法解释在限制着《刑法(分则)》第182 条的法律适用,不如说,是《刑法(总则)》第13 条等的相关规定限制着《刑法》分则关于伪造货币罪的罪名条文的适用。
最后,《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具有修正的功能。分则中个罪的犯罪构成是一种具体的、基本的犯罪构成,而《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则是一种修正的犯罪构成的体现。就共同犯罪而言,在两人共同蓄谋实施杀人行为的情况下,一人实施了杀人行为,而另一人仅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并最终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的发生。如果仅按照《刑法》分则关于个罪具体罪名的规定,则仅能对两人分别以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如此判决结果显然难以实现《刑法》第5 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为此,《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便对其判决结果进行了很好的修正。不仅是《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刑法》总则中关于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⑧、罪数形态以及修正的刑罚处罚制度(如减轻处罚、免于刑罚处罚)等等,都是《刑法》总则修正《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文体现。
综上可知,《刑法》分则罪名条文的规定只是对犯罪行为的基本描述,是否依照刑法定罪,还必须要结合《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综合判断。在对行为的定性过程中,既要看到《刑法》分则之“罪状”这一特别的定罪要件的规定,也要考虑到《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的补充、限制和修正功能。如此,才可谓正确理解并较为恰当地运用了法教义学方法论。
三、法教义学方法下之“醉驾”行为定性分析
基于法教义学方法论的上述功能和刑法总分则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否需要认定“醉驾”行为成立危险驾驶罪,需要在考虑我国刑法典的所有规定的基础上,运用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论和批判修正功能进行综合分析。
就“醉驾”行为定性而言,明确“醉驾”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是司法实践的首要任务。而这些法律规范不是其它,正是我国现有的刑法典,也即“醉驾”行为符合刑法规定,并不意味着只符合《刑法》分则的规定,而应是综合地符合了总则与分则的所有相关规定。反过来讲,离开了整体化刑法典的适用,剥离了《刑法》总分则之间的内在关系,无异于“盲人摸象”,必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结论,理论界不考虑醉驾个案的具体事实和忽视《刑法》总则的规定而得出的“‘醉驾’一律入罪”观点即为适例。如此论断的产生,及由此而引导司法审判实践所造成的“一律入罪”定性偏向,不仅于司法裁判过程的公正性无益,对于公正刑罚的做出乃至刑法目的的实现,必然会徒劳无功,甚至会适得其反。因而,对“醉驾”的定性只有在将我国的刑法典的所有相关规定作为不加怀疑并予以认可、接受的前提下,才可以做到较为全面的适用法律。这正是法教义学方法中“预设功能”的体现。
在充分考虑我国刑事法律所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并准确运用《刑法》总分则的内在关系,对于“醉驾”定性而言愈加必要。这不仅是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论的体现,也是犯罪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等特征紧密联系的内在要求。
“醉驾”定性需将法教义学的体系论方法作为基本方法予以运用。在运用刑事法律处理具体的“醉驾”案件时,仅罗列了所有相关法律规定还不够,还要树立一种系统性的整体立场,即考虑刑法典的重要性。任何刑事法律规范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存在的,如《刑法》总则是按照“‘犯罪’—‘刑罚’—‘刑罚的具体运用’”等主线展开的,《刑法》分则是按照“‘类型化罪名’—‘具体个罪’”予以展开。可以说,无论是总则的主线,还是分则的结构组成,都是体系化刑法学的体现。因而,对“醉驾”行为进行定性的过程中,需要运用体系化的思维,考虑刑法典相关法条之间的协调关系。⑨在对“醉驾”定罪与否进行判断时,重点考虑《刑法》第13 条“但书”与具体行为事实的契合度。
具体就法教义学的体系论方法之运用而言,实施了“醉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结合醉酒标准和《刑法》第13 条的规定进行综合评判。
一方面,实施了“醉驾”行为,并不一定构成犯罪。首先,对于行为人实施了酒后驾驶行为,但并没有达到“醉驾”所要求的醉酒程度(80 毫克/100 毫升),并且行为可以被评价为《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时,通常应以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行政处罚。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刑法意义上的犯罪,都必须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等特征的统一。行为人虽实施了酒后驾车行为,但并不具有“醉驾”所要求的刑事违法性程度,并且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时,将行为排除于犯罪圈的评价范围之外,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特征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并不背离社会危害性等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对于司法上的具体个罪来说,具备刑事违法性、严重社会危害性只是意味着具备了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但《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各种犯罪,都不能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16],还应结合《刑法》第13 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只有行为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才可以被评价为犯罪。其次,对于行为人实施了“醉驾”行为,并符合《刑法》第13 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定时,仍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人实施了“醉驾”行为,只是满足了《刑法》分则关于个罪的基本规定,但在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论下,《刑法》分则实质上是一个并不完整的法律规范。分则作为一种特别的定罪要件,需要《刑法》总则一般性、统摄性规定的指导和修正,离开了《刑法》总则相关条文规范的适用,“醉驾”的定性只能是一种盲人摸象的过程,只能呈现类似凤毛麟角的结果,并不能揭示出案件所反映的本质特征。“醉驾”行为应否认定为犯罪,仅仅满足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所体现出的刑事违法性特征还不够,必须要在《刑法》第13条等相关规定所反映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如此过程才能算是考虑了罪刑法定之“法”,而非只是“法”的局部,在此过程基础之上做出的判决结果才有可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基本原则的实质要求。
另一方面,行为人不具备《刑法》第133 条之一规定中的“醉酒”等酒精度标准,也可能构成犯罪。前文中对“醉驾”的酒精度标准在2013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已有规定,即“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由此规定便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实践中,行为人血液酒精含量未达到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驾驶机动车符合《刑法》分则的个罪成立要件并且非《刑法》总则“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时,是否需按照《刑法》第133 条之一的规定定罪?易言之,“血液酒精含量在20毫克/100 毫升以上不满80 毫克/100 毫升”时,是否可以按照《刑法》第133 条之一的规定定罪?其实,《意见》只是通常情况下界定“醉酒”的标准,但具体到特别情况下的个案而言,对于行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度含量虽未达到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但血液中酒精含量超出一般(20 毫克/100毫升以上)标准,且(饮酒后驾车)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分则)》第133 条之一行为的规定和非《刑法(总则)》第13 条“但书”的情形时,是完全可以按照《刑法(分则)》第133 条之一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的。因为,无论是《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中的醉酒标准,只是一种形式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饮酒量对行为人的实际影响情况,具有相对性。从具体个案的适用角度来看,该标准需考虑到不同的人因生理因素的特殊性而对行为人的实际影响情况。因而,就行为本身而言,酒后驾驶虽无形式违反该规定之疑,但若造成了严重的实质性危害后果,考虑到行为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并且不符合《刑法》第13 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定时,则应为犯罪圈所评价。如此定罪并对行为人处以与之相应的刑罚,不仅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实质要求,更是“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的应有意蕴。与之相对应,对于行为人血液中酒精含量虽符合《意见》中的“醉酒”,也符合《刑法(分则)》第133 条之一行为的规定,但符合《刑法(总则)》第13 条“但书”的情形时,则需在犯罪圈之外考虑其他应对举措。
“醉驾”定性还需要运用法教义学的体系解释论。在运用体系论将刑法“典”视为一个由《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和《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条文规范等要素组成的刑法系统的同时,需运用体系解释论协调条文之间的衔接缝隙。对此,需要在结合上下条文之间的关系和其体现的立法者意图的基础上,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刑法发展的时代要求,做出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合理解释。具体就“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而言,“《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刑法》第133 条之一规定是为了弥补在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肇事罪之间所存在的处罚漏洞,⑩应当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解释为过失的抽象危险犯。”[17]一方面,从体系化的上下文关系来看,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置于《刑法》第133 条(交通肇事罪)和《刑法》第134 条(重大责任事故罪)规定之间,从形式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该罪的罪过为过失;另一方面,就条文的规范目的而言,不能仅仅因为行为人是故意醉酒,并知道自己是在醉酒状态中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就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刑法》第133 条之一第2 款的规定,评价对象并不是行为人是否“在醉酒状态中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而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这是《刑法》第133 条之一规定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罪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易言之,如果行为人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了机动车,却完全不可能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那么其必然符合《刑法》第13 条规定之“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定”,因而不可能属于《刑法》第133 条之一规定所调整的范围。
总之,“醉驾”定性应当在刑法典这一整体性系统之下,通过洞察法律条文的内在关系并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并由此运用法教义学方法的体系解释论和批判修正功能做出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性结论。如此之定性过程,必然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过程。然而,值得欣喜的是,在理论呼声中,已出现了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对“醉驾”定性进行思考的点滴。⑪相信随着法教义学方法论的普及和相关研究的深入,“醉驾”定性难等问题会迎刃而解。
注 释:
①理论界对“醉驾”行为的定性问题,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律定罪”和“区别对待”;而司法实务界对于“醉驾”的定性问题,同样存在着类似情况。
②如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在一起“醉驾”案的判决理由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重庆市某县人民法院则在一起“醉驾”案的判决理由认为:“被告人李某某违反道路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了交通事故,侵害了道路运输的正常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从两个判决理由中可以看出,是否发生危害结果和侵害法益的危险,是二者的差异之处。资料参见: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2015)×法刑初字第00084 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某县人民法院(2015)×法刑初字第00050 号刑事判决书。
③《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已经2010年修订并于2011年7月1日实施。
④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军5月10日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也就是说,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 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
⑤河南省安阳市某县人民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认为:“被告人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河南省某市人民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则认为:“被告人某某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从不同判决理由可以看出,实施行为后是否造成潜在的危险是二者判决理由的差异所在。有关资料请参见:河南省安阳市某县人民法院(2012)×少刑初字第44 号刑事判决书;河南省某市人民法院(2012)×刑初字第315 号刑事判决书。
⑥“法教义学”一词由“Rechtsdogmatik”译出,从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引进。其中,法教义学知识以本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内容本身作为不加怀疑而予以信奉的前提,强调现存知识体系的权威性,有国界之分;法教义学方法作为一种体系化的体系解释方法论,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无国界之别。本文仅对法教义学方法予以论述。
⑦该词存在不同表述,台湾学界通行的译法是“释义”,如陈妙芬等学者;大陆学者则更多将其译为“教义”或“信条”,如“法律信条学在解释现行法时,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参见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M].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37)、“部门法学就是法教义学”(参见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J].河北法学,2007,(10):20)。
⑧《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犯罪完成形态的修正,表现在《刑法》第24 条,该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行为,并且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会使得《刑法》分则给予刑罚处罚的规定丧失实际意义。
⑨这里主要指的是《刑法》第3 条“罪刑法定”、《刑法》第5 条“罪责刑相适应”、《刑法》第13 条“犯罪的含义”和《刑法》第133 条之一“危险驾驶罪”之间的关系。
⑩类似表述如“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补充关系”。(参见叶良芳.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证成和规范构造[J].法学,2011,(2):20.)
①理论界如赵秉志教授认为,“‘醉驾’入刑不设置情节限制,并不意味着不考虑任何情节都予以入罪,而是原则上应该入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依据《刑法》第13 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之规定,不作犯罪处理”。(参见赵秉志.“醉驾”入刑专家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21.)
[1]吴飞飞. 不宜将但书规定作为醉驾免罪依据[N].检察日报,2011-06-06.
[2]陈伟.醉驾:一律入刑还是区别对待[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1).
[3]刘宪权.醉驾入刑应杜绝模糊地带[N]. 法制日报,2011-05-17.
[4]卢建平. 一个刑罚学者关于醉驾入刑的理性审视[N].法制日报,2011-05-27.
[5]赵秉志. 醉驾入刑专家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6]周光权. 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7]丁胜明.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J].法学研究,2015,(2).
[8]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哲学[M]. 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9]陈兴良. 刑法教义学方法论[J]. 法学研究,2005,(2).
[10]沃尔福冈·弗里希.法教义学对刑法发展的意义[J].赵书鸿译.比较法研究,2012,(1).
[11]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方法[J].中外法学,2014,(1).
[13]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M]. 朱峰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5]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M]. 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6]刘明祥.论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相关规定的协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
[17]冯军.论《刑法》第133 条之1 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J].中国法学,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