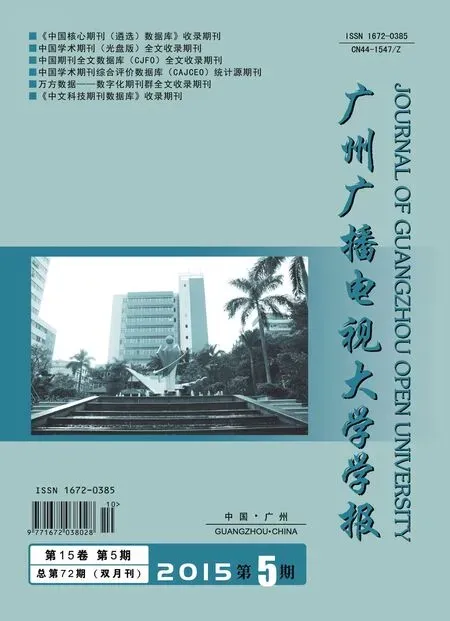由死往生的朝气与向死而生的静默——对比莫言的《蛙》与阎连科的《丁庄梦》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5)05-0085-06
收稿日期:2015-07-11
作者简介:张月,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正如阎连科所言,“我们和这个时代太和平共处了,太和睦相亲了,太相安无事了,太缺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萧红那种文学与时代对峙、对立的紧张关系了。好在近几年,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和描写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蛙》等,都是最直接关注当下大陆现实的力作。” [1]和莫言的《蛙》所关注的敏感话题——计划生育一样,本着超越政治而不回避现实的写作立意,阎连科写出了第一部以艾滋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再一次调动了创作和现实的紧张关系。
在当代文学史对两位作者的定义当中,莫言和阎连科都是乡土作家,而《蛙》和《丁庄梦》这两部作品都立足于民间,关注个人与现实、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把历史变迁和现实动荡作为展示人性迁徙的背景。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作家审视现实的态度以及对社会批判的力度有所不同,因此这两部作品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感走向。笔者将从三方面入手,从情节内容到情感内涵逐步剖析两部作品对现实的言说方式的异同,从而探讨作者是以何种批判姿态存在于作品背后。
一、无尽的压迫:权力与民间
评论家洪治纲曾在《中国六十年代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一书中指出,经历过那一段疯狂的历史的作家们都会对权力意志持有一定的、深刻的理解,权力意志对民间意志的压迫通常会以主要的书写对象出现在作品当中。莫言和阎连科都生于60年代,一起在部队就职,从民间走向权力,使他们形成一套对权力意志的系统的、自下而上的理解。
为了说明“权力——民间”的特殊关系,《丁庄梦》和《蛙》都采用了一个三层的权力运行机制。第一层是是权力意志的象征,政府;第二层,是沟通政府和民间的媒介,丁辉和姑姑;第三层,是权力意志作用的对象,村民。两部作品的前半部分中,这三层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利用:在《丁庄梦》当中,政府利用丁辉,让村民们大量卖血致富以制造政绩;丁辉则利用政策与职权之便,肆意敛财,草菅人命;村民们通过卖血,解决生存问题。在《蛙》里面,政府利用姑姑以实施各项生育政策,姑姑利用政府赋予自己的使命以获得存在感和生存价值,村民在姑姑的帮助下,获得了健康生育的机会和环境。但是,故事发展后面,这个权力机制的运行出现了转变。当丁庄的村民集体患上热病之后,大家开始憎恨给村子带来疾病和死亡的丁辉,而丁辉利用职权之便倒卖物资,配冥婚的行为又持续地激起民愤。此时,村民开始反抗丁辉。当姑姑从送子娘娘变成杀人恶魔时,生存本能受到阻碍的村民由此展示出一种奋力抵抗的强悍的民间力量。
如果说莫言在处理权力意志与民间意志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在权力意志的强悍干预下,民间意志被迫屈服的悲壮,那么阎连科则把目光投放到民间意志无意识地认同归顺于权力意志的荒诞与无奈。
(一)被迫屈服的生命
《蛙》这部作品当中,通过村民对生存权利拼死捍卫到最后被迫妥协的过程,展示村民在与政治话语对抗的尖锐和紧张关系,莫言把批判的矛头更深入地指向权力意志的不合理性以及其对人性本能的扭曲压迫和残酷摧毁。
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有其必然的社会合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但是这种合理与合法并不能代表民间意志和生存本能,而当社会政策有悖于生存本能的时候,民间的反抗就会呈现出生命意识的浓烈色彩。同时,这种生命色彩也将会因为反抗的激烈和惨败的结局而变得悲壮。特别是小说中姑姑驾船追赶怀孕五个月的孕妇,孕妇为了保住胎儿跳河逃命,最终因为体力不支一尸两命;还有姑姑为了逼自己的侄媳妇堕胎,不惜“大义灭亲”,扒房揭瓦,“连环保甲”,而王长腿以及其家人仍旧与姑姑僵持,最后因为害怕被殃及的邻居们陆续地妥协,最终迫使王长腿“投降”,并“献出”两条人命。
(二)主动认同的奴性
《丁庄梦》在对权力与民间的表达中,选择了一种悖谬的言说方式。村民一方面痛恨着给自己带来死亡的丁辉,但是另一方面又默许丁辉滥用私权,倒卖物资,配对冥婚等行为。作者通过丁跃进和贾根柱两个人谋权徇私的情节,将这种滥用私权的行为合理化地移植到村子当中,将其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定位在深度挖掘贪念荒诞和奴性顽劣的角度,从而彰显出民间意志以生命的损耗作为认同的代价,对权力意志盲目崇拜,体现出一种固有的奴性文明。
故事的一开始就从大量村民患有热病开始叙述,把“过去”的患热病的原因插叙在属于“现在”的情节时间里面。作者有意淡化权力意志本身对丁庄灾难的推动作用,而着墨于丁庄人如何在政策契机下,以其贪念酿造了灾难。丁辉不仅仅是一个推行权力意志下传的媒介,更是丁庄人对权力崇拜的缩影,是伴随着村民卖血、患病、争权、砍树、盗墓的一系列道德失范行为的另一个欲望符号。表面上看,村民们的无限贪婪和不断堕落似乎是由丁辉刺激而生,村民所有违背常理的行为都缘起与丁辉:村民疯狂卖血,是因为丁辉在金钱的驱使下做了丁庄的血头;村民患病,是因为丁辉为了节约成本不顾卖血卫生;村民争权,是因为丁辉当上县里的小官之后滥用私权倒卖物资;村民砍树,是因为丁辉倒卖本应该属于丁庄人的棺材;村民盗墓,是因为丁辉把死去的患者拿去配阴亲以达到敛财目的。但实际上,是丁辉不义的敛财手段一方面给予了村民冠冕堂皇作恶的理由,帮助了村民推翻道德伦理的高墙;另一方面,丁辉的行为也充当了村民内心欲望外化的标准和载体。
而在这一问题上,《蛙》和《丁庄梦》有着相似之处,也有着本质的差别。相似的是政策实施的过程使通过损毁人们的生命作为基础,而不同的是,在《蛙》里面,村民们最终对权力意志让步是来自于对仅存的生命的捍卫,是出于一种对生死做出权衡与取舍之后做出来的让步,“生”被置放于一个值得以死亡来捍卫的崇高地位。相反,《丁庄梦》的村民的妥协与让步则是出自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奴性和对贪念的追求。丁庄人为了权力可以践踏生命,为了欲望可以透支生命,生的意义即是毫无意义。
二、无望的迁徙:欲望和死亡
权力意志不仅要求归顺和服从,还要求牺牲个体诉求以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反抗和奴性作为民间意志的两个相悖的力量,在这两部作品当中,既来源于同一个原因:欲望,又走向同一个结局:死亡。两部作品都关注欲望和死亡,但是《丁庄梦》注重的是村民本身的欲望及其自身死亡的关系描摹,《蛙》则关注生存欲望与政治欲望对抗时所引发的死亡。
(一)生存欲望的奴役
阎连科在一本访谈录中说,“生存就是一切,因为生存,导致我对权力的崇拜,对城市的崇拜,对健康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可以说,生存,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2]换言之,生存是阎连科作品的母题。在《丁庄梦》这部作品当中,一切灾难仿佛缘起于对生存的渴求。然而,由于丁庄的村民本着对生存与死亡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理解,把生存的意义简化为通过满足欲望从而消解由崇拜带来的失落感。回顾丁庄惨剧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关于欲望和贪婪的暗线在悄然生长,并与死亡人数呈正比例。高局长积极动员卖血是出于强烈的权欲,丁庄掀起卖血风潮,是由于他们无法控制对金钱的热望。丁庄人把身体里自然流淌的生命原力当作财富的置换品,在盲目的追索中走上了不归路。当鲜血换来百元大钞时,金钱在此彰显出不可抗拒的魔力,轻易就把有形物质转变为无形的精神动力,贪婪的欲望在他们思想中播种发芽并迅速开花结果。从此,“丁庄轰的一声卖疯了”, [3]他们把生命当赌注,一点点耗尽了生命元气。金钱欲凝聚的狂热势头支配着行动,欲望也因此壮大。而热病的爆发不但没有让他们在欲望的泥潭中清醒,反倒是把对欲望的追求意愿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卖血是他们的金钱欲望膨胀的行动表现,那么热病之后,他们对私欲杂念也开始躁动,并渐渐压倒理性和伦常。学校作为病人最后的滞留地,它不是供其静待死亡的温馨家园,而是一个阴谋滋生、私欲纵横的大舞台,垂死之人在此展现善恶较量、权力争斗,自导自演出一幕幕人性堕落的丑剧。
正如《日光流年》里面的一句话所言:“生存就是那样,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 [4],丁庄人在迎向死亡的同时,瓦解了生存应有的道德范式。赵德全和赵秀芹为了小利当上内贼,偷梁换柱;丁亮和小玲抓住生命最后的气息乱伦通奸,丁跃进和贾根柱为合谋掌权,使出卑劣手段害得丁水阳一家分崩离析;垂死挣扎的病人害怕死后没有棺材下葬,不仅疯狂地砍掉了村里的每一棵树还盗窃了丁亮和小玲的豪华墓。
在村民们消费生命满足私欲,践踏人性扭曲伦理的时候,作为生存的对立面——死亡也一并而行。每当有一件关于贪念和私欲的事情发生,就总会引出一个关于死亡的消息。作者有意把死亡和欲望放在一起,是为了阐明死亡就像双面镜,一面放大了死前的痛苦无奈,一面又照亮了人内心的全部隐秘。持久的折磨滤掉了他们对生命的留恋和对伦理的尊重,在丁庄人眼里,死亡似乎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权:就算偷窃、乱伦、争权、夺利,也无须面对法律的制裁与心灵的拷问,道德感、伦理观已然失去的应有的话语权,人性的扭曲成了本真状态,他们甘愿成为欲望的奴隶。
(二)政治欲望的绑架
而在《蛙》这部作品中,同样书写了欲望与死亡,而这里的欲望在人性的范畴里面是合理的,但将其放置在政治的话语场中却成为了不合法,因而,在政治作用下,对合理欲望的捍卫最后导致了死亡的必然结果。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村民们的个体欲望形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村民们渴望繁衍生命的欲望受到了对政治狂热的姑姑的压制。这一对立关系体现了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政治”的理论。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一九七六年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区分了统治者对死亡的权力和对生命的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和君主制国家的君王重要区别是:后者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力,即将人处死的权力,但不具备对“生命”的控制力;而前者则不仅拥有对死亡的权力,还拥有对“生命”的权力,即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 [5]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生命”的掌控。这种统治者对生命的权力,就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小说的第一部分结束于“文革”时期对姑姑进行批斗时,会场冰面的断裂, “许多人,落到了冰水中”。第二部分则以蝌蚪的第一任妻子王仁美被姑姑强行流产,最终母子死在手术台上为结尾。而小说第三部分则以由于姑姑不断追逐“超生游击队”王胆,最终造成后者因早产而死亡收束。从前三部分以“死亡”为结尾的安排来看,小说讲述的似乎就是中国社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生命”开始逐渐被“政治”所掌控,妇女们生育的要求不断受到以姑姑为代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制,“政治”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掌控整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并由此造成“生命”不断被抑制以致死亡的过程。
统治者行使对生命的控制权力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而这个工具,则是小说着力刻画的姑姑在实施计划生育过程扮演的“活阎王”形象。同时,姑姑在履行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义务时,又从中获得了原始的征服感、履行正义的快感以及行使权力的满足感。在小说中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我”的媳妇,也就是姑姑的侄媳妇,请求姑姑给她配一种生双胞胎的药,好让她多生一个。这样的要求虽然荒诞,但也好理解,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姑姑完全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加以拒绝和解释,但是姑姑却另有一套说法,她严肃地说:“你们年轻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要想歪门邪道。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头等大事。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典型引路,加强科研。提高技术,措施落实。群众运动,持之以恒。一对夫妻一个孩,是铁打的政策,五十年不动摇。人口不控制,中国就完了。小跑,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姑姑是共产党员,政协常委,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怎么能带头犯法?我告诉你,姑姑尽管受过一些委屈,但一颗红心,永不变色。姑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现在有人给姑姑起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姑姑感到很荣光!对那些计划生育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姑姑对着虚空猛劈一掌———决不让一个漏网。” [6]在这些完全政治化的说辞中,不仅看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动员和实施模式,也看到了这种政治化的动员模式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姑姑略带夸张而又极具真实意味的手势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一个乡村医生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怜悯,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体自主性,没有反思意识,“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 [7]的政治傀儡,一个完全政治化、符号化的政策执行工具。也因为有了人物对政治意识的绝对服从,作品中各种带有荒诞剧色彩的野蛮执法也就有了合法性的借口。
三、无边的惩治:审判与救赎
同样是描写死亡、生存、欲望和权力,但是,两部作品最终的情感导向却大相径庭。而两者的情节最终转折,都交给了一个审判和救赎的仪式。
(一)错位审判的荒诞
阎连科的作品可以说是“灾难”的代名词,受到侵蚀的土地、患上痼疾的村民、扭曲变异的伦理、演绎荒诞的日子,几乎成了阎连科阐发其生命体验的审美材质。连他本人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的时候也不禁自嘲起来:“都会说我常常浓墨重彩地写人和土地的苦难,还有就是把‘苦难的大师’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说我是‘土地的儿子,苦难的大师’。” [8]阎连科在描写苦难的时候,摒弃了对暴力的极致描摹,规避了对血腥的过渡渲染,而是借由真实的灵魂素描来剖示现实生活的苦难本质。
在《丁庄梦》里面,最能够体现心灵苦难的人物,是爷爷丁水阳。从人物内心苦难的角度去看,《丁庄梦》讲述的是一个受到村里所有人尊重和信任的爷爷,从德高望重跌入到卑微赎罪再到背负骂名,到最后,不得不在传统道德观和现实荒诞性的拉扯中,选择了大义灭亲作为最终赎罪的方式,同时也以此壮烈的举措开始了新的内心苦难之行,最终以死亡结束了所有的精神苦难。简单来说,故事总共分为四部分:劝子认错——代子认错——收养病患——杀子赎罪。从故事的一开始,父子两人之间的硝烟味就欲盖弥彰,斗争在二人彼此的赎罪和犯罪之间越演越烈,同时,丁水阳的心理斗争也愈为激烈。一方面,是难以割舍血缘至亲;另一方面,气恼、怨恨又纠结在心头无处排遣,良心的不安令他越发憎恨儿子。这一场较量又因为双方的特殊关系变得更加触目惊心。最后,爷爷丁水阳亲手杀儿赎罪,代表正义的丁水阳战胜了代表邪恶的丁辉,以一棒猛击结束了丁辉罪孽的一生,同时也狠狠地击中了丁水阳自己的内心。前文对丁辉的罪孽铺叙得越多,越凸显丁水阳内心对他的怨恨以及对村民的负罪感的深重,而这也更能够衬托出丁水阳内心在亲手弑儿之后的巨大悲痛。此外,事后丁水阳逢人便道:“我把丁辉打死了” [9],语气的轻松反衬出内心的疼痛,道义上负罪感的减轻与心灵上悲痛感的加重构成悖论,渲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更荒唐的是,丁水阳审判了满身罪孽的丁辉,虽使自己倍受责难的良知得到救赎,却又导致自己陷入了丧子的心灵折磨当中。丁水阳的救赎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审判当中,而真正的犯罪者并没有觉悟:丁辉只是被救赎,这只是一种构建于外界力量对他的暴力审判之上惩罚,而这一个审判机制最后导向的结局是死亡以及丁水阳重新接受伦理的责难。这种“审判——救赎——再审判”的环形结构,形成了一种生活的荒谬和生存的无奈。
(二)置换救赎的怜悯
在《蛙》里面,审判的仪式由姑姑出现幻觉开始。姑姑在池塘听到一片蛙鸣,于是出现了大批青蛙冲向自己,跳到自己身上叫着咬着,最后姑姑脱掉所有衣服企图摆脱幻象中的青蛙的纠缠,并在一群青蛙的追赶中落荒而逃,赤裸着身体与郝大手相遇。一个女人在几乎赤身裸体的情况下与一个男人相逢,尤其是对姑姑这样独立、坚强的女性而言,不能不说是极狼狈的。“落荒而逃”的诱因是姑姑听到青蛙声想起自己多年来在执行计划生育国策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扼杀的生命,心里的恐怖被无限放大之后,演变成了姑姑的狼狈的逃跑。姑姑说:“她原本是最爱听初生儿哭声的,对于一个妇产科医生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10]文本中的作家蝌蚪不吝笔墨地用了三整页的篇幅去描写这个场景,足以证明这次经历对于姑姑人生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这个场景是姑姑前半生与后半生观念转变的开端,也是姑姑无意识地用生命良知的标尺去审判自己的开端。于是出现了第五部分,也就是戏剧部分的赎罪行为,姑姑与一位泥塑艺人结婚后,与丈夫一起捏出无数泥娃娃,把泥娃娃整齐地陈列的柜子里,每天对着他们说话,忏悔,以此来拯救自己不安的灵魂。
(三)心灵苦难的昭示
评论家洪治纲在《心灵的体验》中指出,“人物要克服的并不是外在生活的重压,更艰难的还是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嬗变。这是一种巨大的心里挣扎和对抗,只有写出这种挣扎、撕裂与剧痛,小说展示苦难的层面上才具备一种精神上的说服力”, [11]而这两部作品都很好地呈现了丁水阳和姑姑两个人在审判之下承受着灵魂剧痛的过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丁庄梦》里面的丁水阳并非受审判对象,而是作为正义的判官去惩罚罪孽之人丁辉,丁辉自己并没有觉悟,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让审判走向救赎,反而使审判罪恶的正义陷入了伦常的审判当中,审判者沦为被审判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丁庄梦》总是透着一种荒寒、绝望以及尖锐之感。
阎连科总是让丁水阳陷入无限的选择当中,在选择的时候,总是在集体利益与家庭利益的尖锐对立中,使丁水阳以承受晚辈罪孽的长者形象向集体利益妥协,比如丁亮和玲玲的丑史败露,丁水阳为了救出被锁着的他们而交出了对学校的管理权;为了给丁辉赎罪,丁水阳又眼睁睁地看着大家把学校里面的一桌一凳全部搬空等等,这些情节的设置都是为了体现个体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相反,在《蛙》这里,审判者是姑姑的良知人性,被审判的是姑姑用政策杀人的罪行,审判者与被审判者身份的同构性使传统意义上的审判起到了积极的意义并消解了对现实尖锐的袭击。而且,正义与邪恶统一身并使正义道德占据主导话语权,映证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代表社会道德和人性普世价值的超我最终压制了对施行权力狂热着迷的本我,自我的调节产生了良性作用,因此,姑姑完成了自我救赎的转变。但是,莫言对其忏悔的描写,大多着墨于姑姑对死去的胎儿和孕妇们的悔恨,这样的精神责难只能称之为悔恨。因为姑姑对自己所一直忠诚的信念,没有一点的警醒,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也就使最终的审判和救赎所体现的出来的情感内质更多的是对罪人的宽恕和对生命的怜悯,而对残害人性的政治的批判力度也就相对削弱了一些。
无论如何,两部作品都写出了“人物内心的抗争过程,使苦难具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力量感” [12],而“善良的人们因为身心撕裂而导致的灵魂上的剧痛,正是苦难叙事的核心之所
在。” [13]
四、结语
现实世界尤其是故乡生活,对于莫言和阎连科来说,既赋予他们无法逃离的乡土经验和乡土言说方式,也给予了他们无法割舍的创作资源和审美题材。他们无法回去童年记忆中的那个故乡,无法融入此时正在转型变迁中的故乡,他们只能以一个过来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记录着故乡土地上的生活。精神返乡与肉体离乡所产生的感觉,就是一种灵魂的煎熬,“在煎熬中活着,就是生活” [14],而他们心中迫不及待地对话故乡直面现实所产生的情感,是一种焦虑和紧张,而“焦虑,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种子” [15]。
凭着这种表达的冲动,二者都履行了再造现实的创作任务,两部作品既实现了想象力的飞腾,在文本结构、语言文字实行了创新;又通过机巧的想象,把合乎常态的生活图景整合并融化在不忍直视的叙事伦理间。然而,二者对故乡的情感成分的不同,对生存、权力、死亡以及欲望的批判态度的切入点的不同,又促使两部作品的情感走向背道而驰。
莫言认为,“故乡都在变,故乡的地形、地貌、人文都在变,我自己也在变,所以这两个变加起来,就使我这个记忆当中的故乡变得像一个童话一样。” [16]尽管在《蛙》这部作品当中,作者以其敏锐的触觉书写了一段敏感的历史,题材和现实的紧张关系消解了作品的诗意,使《蛙》这部作品的行文风格完全不同于《檀香刑》和《红高粱》那样豪放、辽阔与粗鲁,但是,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动摇莫言对人性的礼赞,《蛙》依旧是通过对抒写生命对政治的抗争,对人性中所隐藏的原始力量寄寓了希望,并且由此抨击现实中疲软的人格和蛮横的政治。而现实至于阎连科,是这样的:“生活中美的东西少到几乎不在,而荒诞的东西多到无处不在,它不是走进你眼睛里来,而是一下子、一下子打进你的眼睛里来,打进你的心灵里去。” [17]同时,阎连科本身所推崇的创作态度,是“面对现实时,不仅是睁开两只眼,而且得睁得大,看得细,对现实是正面强攻的,完全采取不回避的姿态” [18],因此,《丁庄梦》直接刻写了被奴性绑架的灵魂以及向现实妥协的人性,同时,展现了失势的个体如何在强悍的权力话语的碾压下集体失声的荒诞而无奈的场面。
王德威指出莫言的小说里呈现的是朝气蓬勃的、那种欢腾的东西,而阎连科的小说呈现的恰恰是一种死寂,是一片死亡后的静默。这无疑是对两位作家创作的代表性总结,也是《蛙》和《丁庄梦》两部作品情感内涵的深刻阐释。
无论是朝气还是死寂,两部作品立意的深度与诚意,都折射出两位作家诚实的写作态度,面对现实与真实所具有的良知和承担精神,以及他们的艺术才华和能力。他们自己坚守着文学审视当代社会和对话当代人命运的阵地,恪守着独立的审美原则和艺术理想,书写着独一而超越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