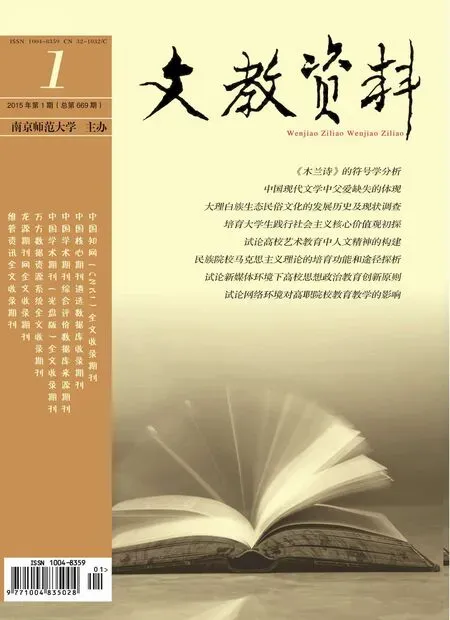底层书写的可能与尴尬—— 浅论《妇女闲聊录》的文体创新
赵婷婷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度成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乡村”作为落后的“前现代”,逐渐淡出主流文坛的视野,欲望叙事、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伴随90年代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对“纯文学”观念的反思,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重新得到呼吁。2001年,国家正式将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且于2003年正式将其写入工作报告。2004年,随着杂志《天涯》发起的一系列“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讨论,“底层文学”作为对纯文学反思与对农村重新关注的结果而渐渐形成一股潮流。
一、表述的焦虑:从“能否表述”到“如何表述”
自底层文学诞生之初,“底层能否被表述”的问题就得到了评论界的热烈讨论。一方面,“从清末改制到改革开放后的百年间,农民阶级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几乎流失殆尽;农民阶级赖以发言的革命话语、阶级话语和道德话语在现代性话语面前统统失效”[1]。另一方面,很多圈禁在都市书斋里的作家,他们所了解的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都是从二手资料中获取的,并不真实,即使是农民出身的作家,也由于远离农村生活而不能捕捉到当下鲜活的农村现场。由此,农民陷入了集体失语的状态。早在2004年“底层文学”刚刚兴起之时,刘旭就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一文中论述了底层几乎不能够被表述和自我表述的命运。如此而言,作家就会陷入“底层无法被表述”的焦虑之中:站在底层的立场说话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就不需要底层文学了吗?但事实上,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只有立足于广阔的现实社会,为人民发出最及时的呼声,其创作才是有意义的。对底层的表述关乎着文学正义与知识分子责任感的问题,关乎文学发展方向的问题,甚至关乎社会变革的问题。因此,底层文学的发展是必需且迫切的。事实上,完全真实的表述是不可能做到的,任何人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都带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一部作品完全真实,只能要求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由此,“底层能否被表述”的问题转化成“我们如何表述底层”的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上,文学界又出现了新的争论。许多作家将底层叙事仅仅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同时将苦难叙事等同于底层叙事,一味渲染苦难而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究其原因,是“作家并没有从本体愿望出发与底层写作对象形成一种真诚的同构关系,无法从写作对象那里获取感同身受的真实体验”[2]。
二、表述的可能:真实或不真实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05年,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一经诞生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部被林白称为“记录体长篇小说”的文本,其实就是将口述实录的形式引入小说创作:《妇女闲聊录》基本上是由一个叫木珍的农村妇女片段式的口述构成,一共有6卷,包括218个小段。在每一卷的开头,林白都明确标注讲述的时间、地点和讲述人,营造出非常真实的艺术氛围。事实上,林白自己也在书的后记中说明:“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实的声音。”[3]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整部文本基本上保留了木珍的湖北方言,甚至“在多处地方放弃了语义的准确性,用发音相近的字代替”[4]223。 可以说,除却林白对文本进行整理加工的幅度大于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口述外,这部文本就是一部标准的“口述实录”。
这种“口述实录”体的采用,使《妇女闲聊录》在实现底层自我表述与表述的真实性方面,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林白作为一个远离乡村生活的作家,她没有凭借媒体提供的经验与自己的想象去描绘乡村,而是选择从作品中隐退,把话语权完全交给木珍,从而让那些最普通的农民成为话语权利的最大拥有者。许多评论家诟病于林白对文本筛选的隐形控制,但这正如前文所说:“纯粹的不介入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 ”[5]事实上,《妇女闲聊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农村世界……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这样一部作品,从外出的打工,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到偏方的使用都如此事无巨细地陈列出来,每一个小片段凑在一起,就像一个多棱镜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的生活。因此,林白的这部作品令人震撼之处不仅在于其创新的文体,更在于其为我们打开“观看世界的一个新的视角,展开了一片我们非常陌生的生活真实”[6]。这也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传统文学和媒体通过新闻与纪录片一直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引导、制造着一种真相,不管这种真相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但的确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看待底层,而对其中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习焉不察。从这个角度来看,语录体的方式在展现一个相对真实的底层世界时的作用更为突出。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真实性的局限性。一方面,林白所记录下来的这个王榨,必须加上“木珍口中的”“林白有选择的记录下来的”“中国湖北省的一个农村”等诸多限定词,因此,其对整个中国农村的代表权是可疑的。另一方面,林白与木珍的对话是极具私人性与隐秘性的,但当这样极具隐私性的对话被记录下来公布于众后,“闲聊”本身的意味便发生了变化。“以谈话的方式进行的绝对隐私话题,被现代媒体利用,一个貌似‘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型的民主化过程,实质上却是生活世界逐渐被体系殖民化的过程,因为私人的隐私,已经被当作一种商品和卖点,在引导一种消费,在重新制造一种‘生活’假相”[7]。 《妇女闲聊录》一旦公布于众,它就成为一种卖点和另一种制造生活的手段。媒体的追捧很可能是因为它已经在无意中被市场和特殊的意识形态给“利用”了。因此,这种“记录体”是否像看上去的那么真实,它的可行性还有待商榷。
三、表述的尴尬:文学或非文学
这种口述实录式方法的使用,致使作品的文学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关于“闲聊”这种叙述方式的“文学性”,有的论者追溯到叙事文学最初的起源,认为“‘闲聊’其实正是中国小说的某种来源”[8]。但事实上,正如贺绍俊所言:“任何一种经过文人加工,后来固定下来的文体形态,它最初的形态肯定都是从民间过来的。”[9]艺术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自有其规律性。文学的精致化和神圣化的确会将文学之路越走越窄,但将几千年来文学发展的一切成就推翻而回到最初的形态以最正宗自居,也不免偏激。尽管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但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思潮,并不是真理。如果只要把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谈话记录下来,那么皆可成为小说。这样的话,文学的价值何在?作者虽然将木珍的闲聊按内容大致分成了几个版块,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很明显地发现叙述者思维的混乱和叙述的重复导致的结构的松散与拖沓。评论家雷达认为“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写《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过于碎片化、零散化”而忽略了艺术概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模糊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10]。 因此,《妇女闲聊录》只能看成是林白个人的实验性文本而不具备普及性。
除了结构的松散与拖沓外,导致作品文学性不强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文本的语言。为了保护“闲聊”的真实性和和原生态性,林白让木珍的乡野俚语肆无忌惮地在小说中登场,只是在个别容易造成阅读障碍的地方进行了稍微修改与标注。如笔直(一直)、作俏(闹别扭)、伯(爸爸)、梗是(全是)等。一方面,口语方言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极强的真实性,且对于底层写作的发展也意义重大,因为它代表了区别于官方普通话的“底层人民”的声音,“文字是庙堂的,声音是民间的”[11]。另一方面,“方言是口语,是一种声音语言、听觉语言,而作品中的方言则是书面语,是一种视觉语言,这两种方言不是一回事”[12]。口语形态的方言只需要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就可以了,而书面形态的方言必须具备审美的特征。因此,真正的方言写作并不是越“方言”越好,而是要求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能够对生活中的原生状态的方言进行提炼、增删、改造,达到审美的目的。这一切,不仅要求作家深谙某一方言,同时也要对一地之地方文化、地域特质、历史传承等谙熟于胸,这样用起方言来才能游刃有余。林白在这两方面的不足必然导致她在“翻译”木珍语言时的吃力与词不达意。口语毫无修改与不加选择地使用,不仅致使语言重复,拖沓,甚至多处有语病,而且造成了语言的粗鄙化倾向。例如:“她拿了一大块啃,没啃完,渴了就喝水,带了苹果,鸡蛋,香肠,糖、饼干、蛋黄派,都有人带。 ”[4]P2“狗婆子逼,细逼,叫你回你都不回!”[4]P116这些都势必给读者造成审美上的障碍。
总而言之,林白的这部《妇女闲聊录》在文体创新的背后存在种种疑虑。但文学史事实告诉我们,“拨乱反正”往往不惜“矫枉过正”。可以说,正是“恰逢”底层文学兴起的文学史背景,才成就了《妇女闲聊录》,但这种成就并不具备普及性与永久性。林白深知这一点:“至于以后的打算,《妇女闲聊录》是我创作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尝试,我想我未必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13]但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文学发展史上,我们都必须承认《妇女闲聊录》为底层书写做出的可贵尝试。
[1]孙国亮.从主体生成论的视角诠释乡土文学发声的困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7-80.
[2]李保平.不要为底层写作“编故事”[N].文艺报,2007-11-20,(2).
[3]林白.低于大地:关于《妇女闲聊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5,(1):48-49.
[4]林白.妇女闲聊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5][英]W·C·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4.
[6][9][10]新浪读书:关注中国农村妇女:暨《妇女闲聊录》座谈会实录[EB/OL].(2005-07-21)[2014-8-20].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5-07-21/2033187133.shtml.
[7]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8][11]张新颖,刘志荣.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J].当代作家评论,2005(1):35-43.
[12]张延国,王艳.文学方言与母语写作[J].小说评论,2011(5):155-159.
[13]林白.彻底向生活敞开[N].南方都市报,2007-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