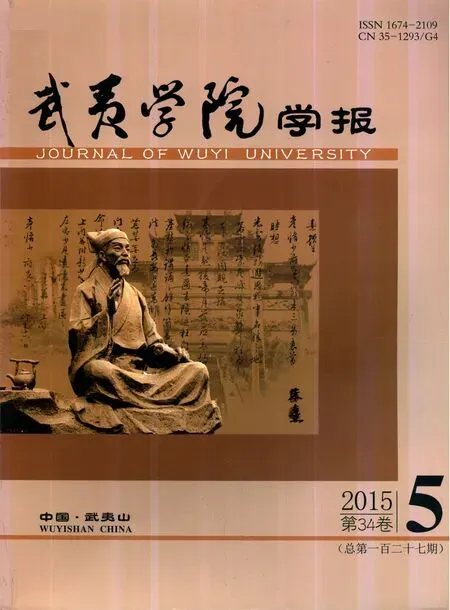试论华嵒题画诗所表现的“离垢”思想及其渊源
景献钰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福州350000)
试论华嵒题画诗所表现的“离垢”思想及其渊源
景献钰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福州350000)
华喦是清朝中期扬州画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代绘画史乃至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作为一个一生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华喦一直挣扎在贫困的边缘,花甲之年还要往返于杭、扬两地维持生计。因此他的画作以及题画诗,不免多为迎合市场需求之作。然而又正如其诗集名称《离垢集》所示,华喦的很多题画诗中却又表现出明确的“离垢”思想及安于贫困、不慕荣华、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
离垢;华喦;题画诗
华喦(1682-1756年),原字德嵩,后改自秋岳,号新罗山人,又号东园生、布衣生、离垢居士等,生于福建上杭县白沙村华家亭。华嵒诗集名为《离垢集》。其中所录诗作最早为1713年华嵒32岁时所作,最晚为1756年华嵒75岁时所作,包括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44年的诗作,共585首,其中题画诗有近300首,约占一半多。
一
《离垢集》中很大一部分是写他不慕荣华、安贫乐道的生活。华嵒一生往返于杭州和扬州之间卖画为生,虽然一直努力经营,多方思索,但一直不能摆脱饥寒的困扰。因为售画不利,他还曾面临断炊的危机:
头上天公欲作雪,黑云四面渐铺设。西北角上翔风来,掀茆卷瓦树枝折。呼儿饱饭入桑林,收拾败枝缚黄篾。担回堆积厨灶边,供给三顿莫少缺。记得前年春雨深,屋溜连朝响不歇。那能著屐出门游,枯坐空斋歌薇蕨。欲向邻翁乞薪米,声语自怕劳唇舌。也碎松桐继晨炊,烹泉不够三口啜。由来忽忽几秋春,此事每将心内说。人生苟得无饥寒,便可闭门自养拙。且携妻子宴清贫,何碍敝衣有百结。况蒙天地客吾间,起息得由情志悦。虽在寒园拟薜萝,亦将矮屋当岩穴。幽画正好青眼,直看竹竿撑高节。(《寒支诗》)[1]
诗中描写了前年因连日春雨无法出门卖画,以至于面临断米断炊之窘境。虽然这件事一直让他对家人心存愧疚,担心此类事情再次出现,但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架秋霜老,满筐豆荚肥。园夫自温饱,闲坐纳山衣。”[1]虽然仅仅温饱的生活要求也时常面临着威胁,但华嵒还是很能自得其乐:
常共妻孥饮粥糜,登盘瓜豉茹芹葵。贫家自有真风味,富贵之人那得知?(《幽居遣兴》)[1]
且把佳肴一一问,世间几种最甘甜?算来滋味无如菜,顿顿登盘总不嫌。(《画菜戏题》)[2]
体味贫困之真味,兼以戏笔出之,可见其面对贫穷的坦然与怡然。“幽居”“闲适”是他中年到晚年一直追求的生活理想。他写山居生活:
白云岭上伐松杉,架起三间傍石岩。妨帽矮檐茅不翦,钩衣苦竹笋常芟。厨穿活水供茶灶,壁画鲜风送客船。自有小天容我乐,且携杯酒对花衔。(《幽居》)[1]
三间傍岩小屋是自己伐木所建,茅茨不翦,苦竹萦前,厨穿活水,壁画鲜风,俨然世外桃源。其《山人》云:
自爱深山卧,常听涧底泉。何如鼓湘瑟,妙响在无弦。落日数峰外,归云一鸟边。未须慕庄列,此意已悠然。[1]
描写山间生活的自在与自得,在这样一种悠然的生活当中,连庄子和列子都不必羡慕了。作者对简单闲适生活的向往一览无遗。即使辛劳一生,仍旧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衣食无忧的生活,华嵒依然保持着洒脱的情怀:
一身贫骨似饥鸿,短褐萧萧冰雪中。吟遍桃花人不识,夕阳山下笑东风。(《题恽南田画册》)[1]
“一身贫骨”“短褐萧萧”,自画的是一幅仙风道骨的形象,而以饥鸿自拟,冰雪自况,全是虽贫犹高的自许。“吟遍桃花人不识,夕阳山下笑东风”,贫困无名而无怨无悔,反倒充满了豪放洒脱之情。
二
与安贫乐道,不慕荣华相关联的,就是他所追求的远离尘垢、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华嵒诗中此类作品亦多。他写诗称赞李白:“李生不受诏,杜老呵以仙。荣利苟弗注,明达何所牵。”[1]他不止一次在诗中赞美隐居生活:
壮鸟呼林开宿雾,鲜云捧日上崇岗。崖峰筑室同人远,竹粉松华和蜜香。(《隐居》)[1]
守陋甘为木石邻,素心吝与茗泉亲。浮名挂齿他时事,老疾钻筋此日身。秋雨欲愁搜乱简,黄花新瘦忆幽人。数声清响江边过,似断还连听未真。(《秋宵有作兼寄魏云山》)[1]
其温故可扪,其冷独堪操,寂寂容吾懒,喧喧任客劳。利名归淡息,风月就闲陶。岂敢言明达,微知惩欲挠。(《和一轩子言心》)[1]
爱此澄潭僻。鱼多水不腥。客来尘外坐。舟入镜中停。(舟从石中入,形环如镜)竹径藏秋响。云岩滴古青。了无车马迹。苔色上茅亭。(《曹山》)[1]
此类作品俯拾即是,反映了他真正甘于淡泊的归隐之心。华嵒七十一岁时,归舟度扬子,还写诗赞扬身居乱世甘充藜藿高隐不出的焦光。诗曰:“独鼓归山兴,长怀采蕨歌。焦山高隐处,千古一青螺。”[1]在这一点上,他的山水类题画诗表现得尤为明显。
华嵒的山水画,在他的创作中不甚引人注目,但此类题画诗却是他诗中最为清新脱俗、最能表现其理想胸襟的上好之作。华嵒出生于崇山峻岭的山村,自小受大自然的熏陶。中年以后又四处游历,远至塞北,饱览了各地的山川名胜。不论是贫困的时候,还是多病的晚年,他对山水的兴致始终不减。他在《自写小像》题诗中说:
嗤余好事徒,性耽山野僻。每入深谷中,贪玩泉与石。或遇奇丘壑,双飞折齿屐。翩翩排烟云,如翅生两腋。此兴四十年,追思殊可惜。[3]
由于对自然山水有着特殊的爱好,华嵒对山水画也情有独衷,这种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是在扬州卖画谋生期间,由于山水画的幽远意境与城市声色犬马的生活时尚相距太远而不大畅销之时,华嵒也在不时地创作山水画。
华嵒的许多山水题画诗,都是寄情山水,借景抒情之作,如雍正七年所做《山水》册页《小东园图》之题画:
幽人家住小东园,老树荫中敞北轩。一部陶诗一壶酒,或吟或饮玩晨昏。竹床瓦枕最堪眠,被褥温香梦也仙。听得微风花上过,却疑疏雨逗窗前。[4]
华嵒的居所建在杭州城东,当时有不少不愿与清廷合作或仕途失意之人聚居于此。或许是出于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认可以及高洁人品的倾慕,很多人都喜欢以“东园”为自己的庭院命名,华嵒的“小东园”概亦取此意。“听得微风花上过,却疑疏雨逗窗前”,这充满诗意的轻灵之句,洋溢着简单安宁生活中的惬意与满足,若无惬意与满足,生活中如此细小的欢乐又如何能入得心来。东园虽陋小,但老树荫中,吟诗饮酒,自晨及昏;竹床瓦枕,温香眠梦,人生如此,又夫复何求?生活固然清贫,但清贫之中可以坚守自己的高洁人品和人生追求,又是多么的令人欢欣:
径静贫游孰,相邀不定归。霜林曲数里,风叶乱孤晖。晚气寒山冽,秋成田户微。所忻茅屋里,予可抱清徽。[4]
画面上山高林密,三个行人正走向筑有茅屋的山谷。秋天的山谷不免萧瑟,而在这一片萧瑟之中,作者的欣喜却又清晰可见。“所忻茅屋里,予可抱清徽”,对华嵒来说,相较于精神上自我期许的实现,外在的艰苦的确是微不足道。如果没有谋生的压力,那就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了:
白云复白云,飘飘起空谷。凉风吹之来,入我香茅屋。举手戏弄之,爱彼冰雪姿。动我搴幽兴,一纵无所定。与之汗漫游,悠悠遍九州。九州不足留,复将访丹丘。丹丘在目如何往,中有人兮白云上。[4]
自己的思绪随着冰清玉洁的白云任情漫游,一向拙于生计的作者,此时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这种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的快乐,也许只有神仙世界中才有,“丹丘在目如何往,中有人兮白云上”,那飘然白云之上的仙人,显然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像。在这里,景物不过是个载体,抒发自己的情志,寄寓自己的理想,才是华嵒最终的创作目的。华嵒出身寒素,虽然青少年时期曾经有入世之心,但在北上京城,企图跻身宦门的理想破灭之后,安贫守素、不慕荣华成为他的人生准则,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离垢”,馆名称作“解弢”,自号“枝隐”,寓意皆在此。他一生酷爱放游山水,执着于山水画的创作,除了自身的兴趣之外,以山水来抒情言志,当是最主要的原因和目的。
三
华嵒毕生追求远离尘垢、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与其思想人格密切相关。华嵒的思想渊源,有儒、有道、也有释,他自称“诗酒撑肠一老儒”,[1]又说“庄墨固华词,构旨厥有托。孔颜垂宣化,百世咸知学。”[1]这是反映其儒家思想的一面。而“山人惟好道”[1]“愿借维摩榻,谈经坐小楼”,[1]又明显带有道释的印迹。作为一个文人画家,儒家思想占有的重要地位自是不言而喻,华嵒诗中颇有一些关心现实、抒发有志难施感慨的作品。但从整体来看,他的题画诗对重大题材兴趣不大,对于统治者所提倡的圣贤名哲,烈女佛像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等,基本都不曾触及。他很少关心重大社会问题,即使是一些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与其说是出于忧世愤世的理念,不如说是对艰苦生活的感同身受:
且说秋收罕有成,菱僵橘癞芋头秔。稀逢苦菜来登市,哪见新棉卖入城?米价渐腾盐价起,晚潮不退早潮生。闲来检点家乡事,钞上藤笺寄阿兄。(《寄金江声》)[1]
诗中具体描绘了收成不好所导致的百姓生活的艰苦,但其中并没有忧国忧民的情怀,“闲来检点家乡事,钞上藤笺寄阿兄”,是在艰苦过去之后,“闲来”想起,才把当时的情况写信告诉对方。不能说华嵒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一面,但这种思想只是对与自己生活境遇大体相同或更为贫困的人的一种同情,没有强烈的儒家忧世忧民的思想。华嵒也有一些不满黑暗现实的作品,尤其是一些钟馗题画诗,更是与其一贯风格相异,如:
山精木魅动成把,更愿扫尽人间蓝面者。(《雨中画钟馗,成即题其上》)[1]
老髯袒巨腹,啖兴何其豪。欲尽世间鬼,行路无腥臊。(《题钟馗啖鬼图》)[1]
一怒独要啮鬼雄,虬髯倒卷生辣风。长声呵咤翻霹雳,魃蜮毕方遁无踪。(《题钟馗》)[1]
我们从中看到了华嵒愤世嫉俗的一面,但这种不平与愤怒,是每一个失意之人都不可避免的,虽然有些诗也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但抒发个人愤懑与不平的成分更多,并不一定都是儒家忧世思想的反映。
从华嵒的主要思想倾向来看,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许是天性使然,华嵒初到杭州(康熙四十二年,1703),就开始了访玄寻友的生活。在凤山门内吴山山麓的紫阳山中,华嵒认识了类似隐者的“和炼师”,《短歌赠和炼师》曰:
紫阳山中有真人,出山入山骑猛虎。披尘逐苍烟,蹑云升紫府。仗剑摇寒星,吹气飘灵雨。
宇宙茫茫视劫灭?真人捏指驱神雷。神雷轰轰九关开,长歌弄月归去来。归卧仙山人不识。朝朝朝礼北斗北。我过丹房扣上真。玄关窍妙通精神。授我以大药。服之度千春。悠悠终不老。许我同登三山岛。我感真人制短歌。短歌不长当奈何。[1]
在与道士们的交往中,华嵒还寻访到了西泠十子的传人。这些人当时都是中老年,大都清贫自守、好道谈玄,喜诵《黄庭》、《南华》。在其后的数十年间,华嵒始终保持着愿与道士交往、探究全真修行方法的热情。这在华嵒诗中多有记载:
夜分人不寐,罢读掩《南华》。栏湿云移树,窗明月浣纱。疏星摇入汉,一鹤叫归家。倚枕支寒坐,青瓷细品茶。(《夜坐》)[1]自别层城不记年,桃花落尽夕阳天。曾无灵鸟传金字,可有痴龙种石田。弱水流来千磵月,孤云飞去万峰烟。遥知鹤发慵梳洗,一卷黄庭枕石眠。(《寄紫金山黄道士》)[1]
碧云堆里墨痕斜,笙鹤横空羽士家。镜展明湖千顷玉,香生小院一林花。石坛夜扫抟春雪,仙灶晨开煮嫩茶。我有闲情抛未得,黄冠何日问丹砂?(《笙鹤楼》)[1]
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道士喝茶、炼丹、休闲、隐居生活的向往。道家清静无为的传统,正是华嵒离垢思想的依托。
当然,华嵒也有对现实无可奈何,自我叹息的一面。他的诗中屡次表达了这样的感慨:
贫居执素志,顾影玩吾真。……露华登夜气,霜鬓老儒巾。欲寐无成寐,凭谁话苦辛。(《梅边披月有感》)[1]
老矣扬州路,春归客未还。遥怜弱子女,耐玩隔江山。衣食从人急,琴书对我闲。耽贫无止酒,聊可解愁颜。(《客春小饮有感》)[1]
欲醉胡为醉,方思无可思。以贫长抱疾,垂老不违痴。寒结拌花雨,香弥浴鸦池。一篇披昼咏,甜苦自知之。(《坐雨》)[1]
老去文章谁复怜,白头空守旧青毡。梨花满院萧萧雨,杜牧伤春又一年。(《题员双屋红板词后》)[1]
一生为衣食奔波的辛苦,的确是无人诉说,苦乐自知,尤其是在花甲之年,还要拖着疲惫之躯奔波于杭、扬之间,这其中的辛酸与感伤,外人又能了解多少。迫于衣食的压力,华嵒常常要画一些应时应景的题材,但只要生活稍稍宽松,他就又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诗画生涯,表达自己远离尘垢、超世脱俗的人生理想和高尚人格了。
结语
华嵒是一个一生在贫困中挣扎的职业文人画家。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对其题画诗影响甚大。作为一个职业画家,迎合市场需求是其生存的首要前提,他的很多题画诗明显反映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但华嵒一生都不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职业画家,只要生活允许,他总是尽可能地投入到自我的创作当中,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又表现出明显的文人趣味。他的题画诗,清淡洒脱,雅俗共赏,将自己的人生情感与世俗趣味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对社会重大题材关注不大,从其题画诗所表现的主题来看,除了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再现,主要是表达自我的情感和寄托。这一情感和寄托的主要指向,就是他一生所汲汲追求的安于贫困、不慕荣华、远离尘垢、超尘脱俗的人生理想。沈端称其“平生志不慕荣利”,[1]林士班谓其“山人志趣超群伦,不慕荣华不祈积”,[1]这已成了对华嵒思想品格的公论。徐逢吉在《离垢集》题辞中评其诗曰:“(华诗)如晴空紫氛,层崖积雪。玉瑟弹秋,太阿出水,足称神品。”主要也是着眼于此。
[1]王冰.秋空一鹤:华喦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离垢集·补钞[M].光绪十五年刻本.
[3]华喦研究:朵云第57期[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4]华喦山水册[M].日本:兴文社,1935.
A Study on the Huayan’s Poems Inscribed on the Ligou Thoughts
JING Xianyu
(School of Art,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0)
Huayan is a very famous artist with good reputation in the Chinese painting history.During the two hundreds years after he died,his influence and status extended increasingly.As a professional painter,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arket was the first precondition for Huayan’s life,so many of his poems inscribed on paintings obviously showed the masses’taste.But Huayan was not content with being a professional painter purely all the time,once he could support his life,he always tried his best to commit himself to the creation.In fact,this feelings and hopes was just the expression of his ideal life in which he could live with poverty,he could no need to admire wealth and he could be apart from the secular life.
Ligou;Huayan;poems inscribed on the flower-and-bird paintings.
J212.05
A
1674-2109(2015)05-0053-04
2014-12-20
景献钰(1973-),女,汉族,馆员,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