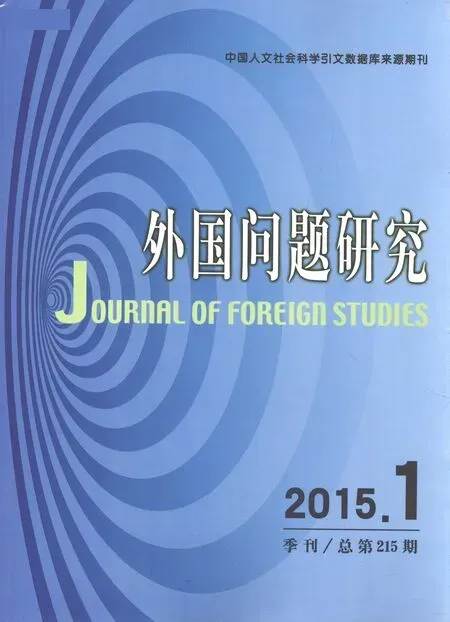古丁研究的几个难点摭议
刘 旸 尚一鸥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古丁研究的几个难点摭议
刘旸1尚一鸥2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东北师范大学 日本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摘要]古丁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又艰涩的课题,与这一研究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并不是靠简单的结论能够解决的。本文选取了日本战败后古丁的创作经历、关于古丁的文学归属问题、“面从腹背”与古丁的生存立场以及古丁的“转向”等四个难点,谈及了对这位伪满洲国大作家的现代认知。
[关键词]光复;殖民地文学;面从腹背;转向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经历了14年殖民统治的东北民众而言,不但是一段漫长的屈辱历史的结束,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生活的开端。所以,东北人习惯把这它称之为“光复”。这一年古丁31岁。长春通往溥仪当时居住的伪皇宫的一条马路“光复路”,便因此而得名。日本的入侵,给中国人、东北人留下了太多的文化思考与烦恼,这种历史的惯性并不是日本战败走人就能了事的,包括古丁和他的文学的清理与收场。让东北人轻易忘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苦楚,显然也不是几代人可以办得到的。这是为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并非人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事情。
按理说,古丁的文学研究至此已可以告一段落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1914年生于长春的古丁,1964年过世时年仅50岁。这意味着“光复”以后作家的人生还延续了近20年,如果忽略掉这段时光,由于社会原因刻意回避掉作家的生活方式与文学改变,显然都为今天的时代所不容许。古丁文学在伪满洲国期间的历程固然是一种重要存在,任何人想跟着他所生存的时代前进,实际上都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古丁与伪满文坛之间出现的断线风筝式的关系,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变了,他的文学环境和生存条件变了,或者说作为文学艺术家他的演出舞台轰然坍塌了。
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因突然事件和不可抗力而改变作家命运的先例比比皆是,一生颇多磨难的古丁当然也不能例外。问题在于,这位生前颇多非议的伪满大作家,死后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95年,由李春燕先生主编的《古丁作品选》出版时,编者曾如实地记录了这种情形:“出版古丁作品集也是时候了。近几年,不少当时的作家,没甚争议的,或有争议可以为自己辩白的,其作品,或单本,或结集,或入系,都已先后再次问世。这是好事,标示着政治的清明。但唯独古丁及其作品,仍无人敢于问津。”[1]661古丁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就中可见一斑。笔者接着问道:“试问,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舍弃古丁行吗?回避是不行的,简单的骂倒也是不行的,只有直面的正视。我们的研究也该进入到古丁这个层次了。我想,像古丁这样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是不应被泯灭,不该被遗忘的。”[1]661往事与辉煌已不复存在,古丁研究进入了一个很不正常的时期。这已不是日本人的所为,但毫无疑问同样属于日本侵华的后遗症的一种显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古丁研究出现这样的情况。问题出在哪里,究竟有多严重。这种情况还会维持多久,理由又是什么。这诸多的疑问,无不形成了古丁研究的魅力和特点,也因此牢牢地牵住了后学者的目光。
古丁属于那种生存能力很强的文人,这在“光复”以后的岁月里他的经历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日本战败以后的次年,他便成为中苏友好协会的秘书,那时候苏联刚刚帮助中国赶走了日本人,所以这样的选择很有一点跟着时代前进的模样。1947年担任《东北文艺》杂志编辑工作,还是没有离开他的文学。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任沈阳唐山评剧院院长,这期间把李季的诗作《王贵与李香香》改编成了评剧剧本;此外还改编过在北方流行的传统剧目《小姑贤》、《快嘴李翠莲》、《牛郎织女》、《新马寡妇开店》等。这样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模式,古丁显然还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涉足评剧之于古丁是一个全新的行当,但毕竟与古丁的老本行相去不远,然而与伪满洲国文学的舞台已经毫无关系了。
当时,东北的新政权显然并没有真正宽容古丁在伪满洲国的历史表现,躲开了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编编刊物、改改剧本,之于古丁已经是不错的工作了,因为他毕竟还是被当做文人对待的。然而,50年代末开始的反右斗争这一劫他却未能躲过,成了罪人。1958年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6年以后因肺病死于辽宁铁岭的监狱中。1979年才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同年12月,译作《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他是握着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叶山嘉树的手告别人世的,这本书也成为他留下的最后的遗产。这同时表明一生手不释卷、钟爱文学的古丁,开始渐渐回到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伪满文坛大作家的轮廓也如海市蜃楼般再一次若隐若现;至于他还有怎样的计划和所想,则由于生命的了结而灰飞烟灭了。
古丁的妻子曹丽娟,也用过曹显明的名字。古丁从北京回到故乡长春以后两人成婚,长期安于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几个孩子长大以后不但都获得了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而且全部成了共产党员。根据梅定娥的考证:“古丁妻子曹显明经过和长子徐彻的商议,为了保全家庭的利益,决定与古丁离婚,终止夫妻、父子关系(这在当时是社会流行的做法)。”[2]曹氏在和古丁家庭生活的后期,曾在辽宁青年剧场工作,1993年离世。根据古丁长子徐彻近年在《沈阳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可知,曹显明是1946年参加革命的,当过唐山评剧院的总务科长和经理,后来一直工作在评剧界,1970年离休。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古丁的工作调动频繁,所以徐彻仅小学阶段就换过五所学校。1958年古丁入狱时,当时家里赶紧把他所有的照片和手札都焚毁了,成为古丁子女永久的遗憾。这其中当然包括古丁在伪满洲国时代的许多印迹,一把火不可能烧掉全部历史,实际上却成为日本侵华对现代文明影响的延续和佐证。1995年,由李春燕先生编辑的《古丁作品选》在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据说古丁的长子曾提供过资助。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徐彻,长期从事晚清和中国代近史、日本史的研究,他的《慈禧大传》、《一代枭雄张作霖》在读者中一直有不错的口碑。作为大抵是子承父业的一代人,徐彻这许多年来对古丁和他的文学却始终缄口、未置一词。
总体上讲,伪满洲国文学和古丁的创作毕竟是日本侵华的产物,作为一种扭曲的文学现实,虽然并无轰轰烈烈可言,但是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与诸多细节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今天的人们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除了强烈地感受到它的久远、更多的是沉浸于它的复杂。古丁曾经和这一时代朝夕相伴,直至把它送进坟墓。日本战败以后,古丁的人生和他的文学,双双平静了下来。即便是偶有色彩和声响出现,也与伪满洲国断无任何关系可言。这表明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无论如何古丁都应该是属于伪满洲国那一时代的。他挣扎过、奋斗过,也感伤过、失落过;无论是他的辉煌,还是他的悲哀,都与日本有着太过密切的关系。把这笔账记到日本人头上,是公平的和无可厚非的。这也应该成为今人评价古丁的基本的、或者说重要的原则和看点。
问津伪满倒台后的古丁文学,也许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前车之鉴便是18世纪中叶问世的、居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首的《红楼梦》。曹雪芹写红楼,以八十卷本名垂青史;程伟元和高鹗完成的百二十回文本,至今仍是红学领域莫衷一是的话题。在笔者看来,为古丁文学20年的空白做一点事情,即便是“狗尾续貂”,仍然是长春人的后代心甘情愿的工作。
二
解学诗在《伪满洲国史》的开篇,便这样清醒地写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东北地区是日军占领时间最长、日伪统治机构最完备、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最为残酷的地方。在这里,日本侵略者既未满足于建立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主权的亲日政权,也没有设置总督府实行直接的军政统治,而是利用废帝溥仪,打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占领区所采取的此种统治模式,有别于中国其他沦陷区,同时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以‘国家’面貌出现,实行实质的军事殖民统治、掠夺的典型。”[3]如何看取伪满洲国的文学,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是不允许孤立地对待的。至少会牵扯到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新文学史的评价问题。应该说,廓清这一问题也是古丁文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条件。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学革命的方法步骤,抑或是文学社会的建立与发展,都同‘五四’的新文学有很大的相似、相同或相近之处。唯独没有因日伪高压的文艺统治而变成奴颜媚骨的‘殖民文学’。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是在继承‘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自然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这种观点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春燕先生提出的,李先生讲这话的时候是1995年,已然是战后半个世纪的事情了。这说明无论是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还是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来说,历史认识的走向正轨,人们都付出了太多的等待。
那以后,又出现了发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晓丽的声音,对伪满洲国文学性质的认识再前进了一步。“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长达 14年,政治黑暗,经济掠夺,文化入侵,民不聊生。尽管如此,这个区域同样生活着以写作为志业的人群,有其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这些作品庄严与无耻共存,闲情与媚颜同在。有反抗的文字,有记录粗粝生存时空的文字,有寄托社会理想的文字,也有安慰、麻醉自己的文字,还有依附于非法当权者甚或向其谄媚的文字。这些作品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内心状态和审美追求带入文学,致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区别于其他时段、地域的独特的文学图景。”[5]
在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的20年间,古丁研究并没有因此得到长足的进展。此间值得提及的便是梅定娥的《古丁研究》。目前尚未见到这本书的中文版,已见的日文版是由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发行的。梅氏的文本较少涉及伪满洲国文学的性质问题,也缺乏与“殖民地文学”相关的理论阐释。也许与个人的经历有关,这位访日学者并没有把国内古丁研究的发展变化提到思考和认识的重要位置上,著书立说的思维方式也明显秉承了日本式的套路。
古丁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又艰涩的课题,与这一研究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并不是靠简单的结论能够解决的。之于那些博士课程的执笔者而言,如果选择一个古代日本或近现代日本的作家作为自己的论文选题,是完全可以规避掉古丁研究的诸多麻烦的。
2.3 高等数学的内容主要是微积分学,对学生来说,数学概念很抽象,比如数列极限的“ε-N”定义,函数极限的“ε-δ”定义等,数学定理的证明逻辑推理很严密,翻转课堂的课前学习环节如果没有教师的及时有效地引导,仅凭观看视频,不易准确把握视频中的重难点,甚至不能听懂授课内容,使学习效果不佳。
毫无疑问古丁研究是需要深入进行下去的,而且至少可以列出下述两点理由:
第一,关于古丁文学的归属,学术界目前已有“东北沦陷区文学”、“殖民地文学”和“伪满洲国文学”等几种意见。应该说这些意见各有各的道理,而且都是面对古丁文学的具体情况产生的。学术研究本来是一个各抒己见的领域,这种情形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日本鲁迅研究的大家竹内好在谈及伪满洲国研究的意义时,曾经讲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历史的善后处理工作必须有人来做。老实说,当由日本来做!‘一心同体’也好,‘同甘共死’也罢,如果那只是口头上的搪塞之辞,国家的道义性主体就会丧失。1945年,‘满洲国’自行发表了解体宣言,而制造了‘满洲国’的日本却并未举行‘满洲国’的葬礼。若无其事,佯作不知,这是对历史和理性的背信弃义。”[6]2侵华战争是在日本强盛、中国卑弱的国情条件下,日本强加给中国的灾难。迄今为止,竹内好所批评的日本在战争反省、包括侵略东北问题上的若无其事、佯作不知,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中国人的文化血液里,对这段历史的屈辱却一直刻骨铭心,这也是当下中日国家关系降到冰点的重要成因。今天的中国人在面对古丁研究时,对这段历史是不可能“佯作不知”的。在这个意义上,古丁研究完全可以看作是颇具现实性的与日本研究相关联的重要课题。
第二,作家作品研究历来都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这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说伪满洲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古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那么这一选题便存在究竟是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日本文学研究、古丁究竟是一个日本海外殖民地的臣民还是一个中国东北作家的问题。关于第一点,把伪满洲国文学看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是文学史家的一种思考方式的产物。其道理无疑在于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历史逻辑,这也是史学界的共识和传统。一般说来,文学史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如果硬性地把文史分开,那么文学史的许多内容便无法得到有效的梳理。所以,把伪满洲国文学看成是中国现代文学一部分的观点,笔者是完全赞同的。
关于第二点,古丁是一个中国人,把他和他的文学视为日本文学的一部分是讲不通的。但同样不能否定的是,古丁和他的文学也是一个被殖民者的精神世界的再现,或者说是一个亡国奴作家的现实印迹。古丁在这样的条件下有过怎样的屈服、挣扎和反抗,无论如何都与凌驾于东北文学之上的日本文学息息相关。日本人认为,“满洲国是一个优秀的独立国家”,然而正如“日满议定书”所说的那样,同时也“是一个在日满不可分关系基础上的国家”[7]。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人,就曾留下过这样的认识:“所谓满洲文学,是对住在满洲的五个民族各自发表的所有文学性产品的总称,如果只培育其中的一种意识,就会使好容易刚刚萌芽的文学发生萎缩。”[8]在这个意义上,这篇论文于是成为笔者关注日本文学的另一方式,实际上也是日本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开拓性实践。那种以为日本文学研究就必须以日本的作家作品为对象的观念,忽略了伪满洲国文学历史的特殊性,或者说没有想过甚至是面对古丁这样的作家的问题,因此主张这是日本语言文学研究的唯一方法的理由,也便是瞎子摸象、似是而非、站不住脚了。
三
“面从腹背”并不是中文里的一个成语,而是借助中文表记的日文、准确地说是日文中的汉字成语。说到他的中文含义,不外乎“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同床异梦”等等。
古丁研究中的“面从腹背”的观点,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最早提出来的。尾崎曾任第十二届日本笔会会长。1971年他在劲草书房出版的《殖民地文学研究》一书中,明确地提到“面从腹背”是伪满洲国的殖民地作家的一种标志性的文化心理。应该说,这是战后日本知识界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一种颇有见地的认识。1981年台湾《中华日报》发表了署名纪刚的文章,不但认同了尾崎的观点,而且把当时活跃在伪满洲国文坛上的作家分为三类。一是少数文化汉奸;二是以纯文艺相标榜的作家们;三是秘密参加地下抗日工作者。古丁是被列入第二类作家的队伍中的。纪刚的立论根据是“未直接参加作战的文艺工作者,姑不论其在伪职上的言行如何,但在敌伪统治下,透过种种环境的限制,仍能写出被人争诵的作品来,有意无意地,在敌人摧残消灭中国文化政策下,做了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守卫者,做了中国新文学的播种耕耘者,使东北青年在殖民地的教育中,仍能接受纯正国语文的熏陶,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最低的贡献。”[9]644纪刚借用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表达了他对古丁的肯定态度,“面从腹背”也成为中国古丁研究的新说。
李春燕的《就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几个问题评古丁》一文,根据“艺文志派”的发展轨迹,探讨了古丁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倾向,并充分肯定了“艺文志派”的文学成就及影响,着重强调的还是如何评价古丁的问题。她认为古丁代表的“艺文志派”的文学活动不只是振兴了当时的文坛,而且培育出大量的文学新人并影响了以后伪满洲国文学的发展。
上述专家们的观点,其实都是针对古丁到底是不是“汉奸文人”这一话题去的。古丁当时已经驾鹤西归,不会知道人们何以还会继续关注他和他的文学。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相交之际,当贫弱的中国豁不出老本与入侵国土的日本相拼的时候,当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为东北军所奉行、近20万大军撤到关内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让一介文人古丁去抗枪打仗显然是不现实的,一定要让他逃往关内同样是牵强的。专家们的这些真正了解伪满洲国文坛的语境,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解决了人们所关注的这一问题。然而,伪满洲国文坛和古丁文学的复杂,传统的思考方式的局限性,仍然为这一话题留下了许多狐疑的空间。其中特别是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及其在方方面面留下的残余意识,还依然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生发着作用。
古丁生前、特别是伪满洲国初期,年轻气盛、桀骜不驯,具备了足够的文人气质,并不是那么招人待见。尤其是他所接受的日本文化中的装腔作势、对形式的看重甚于对本质的追求那一套,甚至是令人生厌的。然而,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他有两个特点是其他作家和文人所不具备的。一是他的出众的文学才华;二是他超人的日语能力。尽管和他具备同样条件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像古丁这样游刃有余的作家却寥寥可数。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伪满文坛的佼佼者。无论如何,是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古丁。而古丁与时代关系的前提,是他首先默认并接受了自己的生存现实。在“人在曹营”的生活理解上,实事求是地说,古丁是比别人更到位的。这不只表现在满洲文艺家协会“大东亚联络部部长”的头衔上,《艺文志》杂志及同人的领头羊上,和三次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唯一的“满人”代表等方面。凡此种种,让他在那一时代的文坛上出尽了风头。然而,在“面从腹背”的过程中,古丁是否丧失了他作为一个中国文人的立场,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文化汉奸,人们的思考却一直在一个极限状态下徘徊,认识的误区也往往出现在政治对文学的干扰强烈之时,从而失去了对古丁“心在汉”的肯定。
冈田英树在自己的《伪满洲国文学》中,曾披露过池岛信平的古丁认识:“满洲托日本的福,开始了重工业,铺设了铁路和公路,还不断盖起了大楼。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这是很高兴的。因为日本就是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把这些设施全部带回去。说完,古丁莞尔一笑。我倏然惊愕,想到汉民族是何等现实的具有可怕先见之明能力的国民啊。”[6]66这份资料还披露了大泷垂直的古丁印象:“古丁先生还说,他要是不做官就好了。因为做官期间虽然还好,可一旦政府更迭就要遭殃。古丁先生自嘲似的说:现在要想在中国过最安稳的日子,只能到边境地区去当农民。‘这个国家以后还能存在几年呢?’‘嘘!’古丁用食指按住嘴唇,然后又把手指变作一个圆圈放在心房处,示意那只能互相在心里考虑。后面的问题,用语言表达出来,我认为现在还不合适。”[6]67应该说,这两份资料都不仅是日本人对古丁的“面从腹背”结论的最好注脚,而且也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的理解方式。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日本的战败已变成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古丁对时局的思考透视出一个殖民地作家的局限,完全看不出应有的理性色彩,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学耻辱推向了极限。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没有理由忽视为这种倾向所掩饰的古丁的文化根性,因为这不仅是古丁其人、而且也是他的文学本质的所在。
归根结底,古丁曾经跟日本人合作过,但是却没有达到死心塌地的程度。因为他是深信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是不会久长的。1941年,他辞官经商的4年以后便“光复”了,这应该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所以,这个在伪满洲国文坛上不甘寂寞的大作家,最终毕竟没有做出什么太过格的事情来。在找不到古丁曾经越界飞行的可资凭信的资料之前,任何源自感觉的推测都毕竟是靠不住的。
还需说及的是,在古丁被指责为投靠日伪政权、并进行激烈的文坛论战时,古丁同时也是被日本统治当局视为左翼作家代表,处在失去信任、甚至是监督控制之中。伪首都警察厅特秘发1414号密件中,曾这样认定古丁等人的动向:“发现古丁、山丁虽然保持沉默,但偶尔也发表文章。”[10]来自台湾的资料同时透露出了这方面的相关情况:“当时伪‘首都警察厅’曾设专案小组,指挥敌特调查他们的言行交往,按月汇报;另有专责的‘文检’人员,对他们的作品,逐件分析。”[9]645这些信息均表明古丁当时面对的是一种应该打上引号的“创作自由”。尽管殖民统治下的东北作家如履薄冰、甚至做出积极参与文坛活动的种种假象,但日本人在“五族协和”的面纱下始终保持着一副狰狞的嘴脸,对古丁这样的人从未放心过。
所以,在古丁与日本人关系问题上,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表面上怎样地虚于周旋,古丁从未认为伪满洲国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他的文学在骨子里也从未屈服过日本统治的淫威,留下过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劣迹。而日本人对古丁看得也很清楚,表面上的客套与安抚,不可能与本质上的防备与抵触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既符合殖民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从来就不是一副面孔,而是带有两面性的鲜明特征。
近代以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力的强盛,步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行列。这个民族在文化上最难让人接受的地方,便是得志便猖狂、最先向给予过它无数文化恩典的中国老师下手。当歧视中国贫弱落后的风气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候,日本人在文化上也不再可能把中国人视为真正的朋友。鄙视中国和中国的一切,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化的一种风格,所以才会也把“满蒙”视为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并因此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和尊严。无论古丁这样的日本通怎样地迎合和靠近日本,最终也会因一厢情愿而告败。
四
古丁的“转向”问题,笔者已著文专门讨论过。基本论点是没有资料表明,古丁当时曾有过“转向声明”之类;在其他正式场合也没有发现可资凭信的相关文字。因此,古丁的“转向”说证据不足,是一种子虚乌有的存在。他当时作为青年学生只是有过牢骚和反省之意,而且这样的材料也是间接的。这样看来,已找不到在这里可以重复提及的理由。问题在于,如果把“转向”的考证,看作是古丁和他的文学中的一种单一的存在,便会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客体,发生概念化和简单化的错误。实际上,这是关系到古丁整个人生和他的全部文学努力的一个关键所在。越是踌躇不前的时候,越是有理由注意到这个原点所联结的那条长长的直线,从而在点线关系的辨析中,发现全新的学术思想。
众所周知,伪满文坛上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古丁与山丁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古丁就中提出了“无方向的方向”和“写印主义”的主张。既有的研究中已然就这场争论有过讨论,容不赘述。笔者所要论及的是,虽然山丁的观点对古丁的发言做出了相对的规定性,但除了争论所设定的制限以外,古丁的理论主张中,同时也包含了在“转向”事件发生以来,自己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理解和对殖民地生存环境下的抉择与取向。“无方向的方向”和“写印主义”的提法,是多少有些怪异的。这种怪异的背后,显然是古丁的文学为了达到“脱政治”的目的而生发的“避世”声明。古丁此后的人生,一直恪守着这样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偶有超越也都是点到为止。这样的建树虽然不是理论式的,对古丁的文学之路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成为这位作家的特殊环境中的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完全没有理由在今天被继续忽略下去的。
说起来,这在文化上也是日本的东西、或者说是日本文化的影响所致。近代的日本文坛上,许多作家关注过这一问题,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表过这样或那样的见解,所以批评界一直有日本的现代文学是“脱政治”的传统认识。“日本文学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确立了独自的民族美学体系,并形成了以写实的‘真实’、浪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和‘闲寂’等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态。这种‘物哀’、‘空寂’、‘闲寂’的特征,使得日本文学处于与政治格格不入的状态。”[11]这样的理解,十分符合生存在伪满文坛上的古丁的心态,不仅为古丁提供了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外来路径。接受的时候,古丁无非是把这样的理解中国化了而已,而且提法上多少有点蹩脚。
回到“转向”的结点上,可以发现古丁的“没有方向的方向”和“写印主义”的文学主张,显然与他自身的文学经历是有关联的,内中带着明显的与左翼文学交割和了结的味道。那以后他表面上不再保持与左翼文学有联系,也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自己在伪满文坛上生存的安全系数。日本战后派文学旗手大冈升平,曾谈到自己与基督教的微妙关系。他曾少年信教,旋即退出。但是后来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耶稣仍然会不时出现并影响了他的文学思考与艺术表现,他曾列举了《俘虏记》的创作来说明这种关系的特点。古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翻译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是否也体现出与左翼文学的那种藕断丝连的关系,现在已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旦植入作家的体内,完全放弃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说目前尚未发现“转向”的文字依凭,即便是有朝一日找到了那个东西,人们注定也会惊异地发现一种灵魂附体般的印迹。
从30年代初期到中期,古丁的文学思想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这不仅体现在他这一时期和其后的创作中,而且成为太平洋战争以后,他被迫向“国策”文学靠拢的一种铺垫和远因。同时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时期他的文学思考也更进了一步。他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描写中的明暗区别,又是文学表现生活所必需的,具备了文学高手直面生活的创造性意识和严谨态度。在这样的理念下,不仅古丁等人编辑的《明明》完成了从综合类期刊向纯文艺月刊的转型,而且也把一批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表现出某种文坛领袖应有的风范和格调。
在伪满文坛上,古丁并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存在。和他风雨同舟的作家中,至少应该包括小松、爵青和疑迟等几位骁将。这些作家的作品题材丰富、技法多变、风格各异,同样标示了伪满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古丁的“变身”,并且对古丁的文学主张的实现,提供了可贵的助力。
小松,原名赵孟原。1938年来到长春,与古丁等人结识并参与《明明》创刊。小松早期创作的诗歌深受19世纪英国抒情诗的影响,专注个人情感的表达,追求“一颗平静的心”,对超越现实的“纯美”的诠释,是小松独特的美学追求,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起点。在《苦瓜集·自序》中,追忆自己早年创作的心境,小松曾坦言:“那时候,我觉得除了纯美之外,并没有什么可写;除了纯美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爱。”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小松浪漫的艺术气质显然是生不逢时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他清楚地意识到未来或许是“险途”,于是,开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依靠自己的笃学和努力,最终成为伪满文艺界“十项的健将”。
古丁称小松是一个“精力家”。面对创作的潜伏期,他的对策就是大胆的“冲破”,“普通的作家的沉潜,往往是化为无文的缄默,而小松作为作家的沉潜却并不然。”[12]《艺文志》时期,小松的创作逐渐减少对“纯美”的追求,注意文学视野的宽广性,关注社会现实。从发表在《艺文志》第三辑上的《铁槛》开始,小松从唯美的浪漫主义转向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在创作上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爵青本名刘佩,在《艺文志》作家群体中地位仅次于古丁,被当时的文坛冠以“鬼才”的称号,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其艺术表现能力几乎无人比肩。1917年生于吉林长春,比古丁小三岁,又是古丁的发小和校友。1933年,爵青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与成弦、姜灵非等人组建“冷雾社”,创办刊物《冷雾》,作品呈现出“超现实”的特征并受到文坛的冷落。他一方面积极地转向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则尝试寻找自己的文学追求与社会现实的交汇点。
他的小说以都市生活为主,主人公大多具有传奇的经历,在似真似幻的气氛中,表达着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擅长用小说讲述自己的思考和观念。“我在《恋狱》里,写了幸福的无计划性,在《艺人杨崑》里,写了生命和艺术的绝对性,在《遗书》里,写了生命的赞歌,在《幻影》里,写了生命和虚妄无力的对决格斗,在《魏某的净罪》里,写了生命的通融自如。”[13]在“另类”的外壳之下,爵青并非逃离了现实,他所展现的正是年轻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生活里的精神危机。
古丁曾这样说过:“是少年的时代,我和爵青的住居仅仅有一街之隔。还能记得:他是那一带的孩子们的最娇的一个。……后来,我们的相隔,实已十数年,在我和《明明》结缘,才留心到当时的文豪。在一本‘淑女之友’看到一副像片,才知道爵青即刘佩,也不知他在几时知道古丁即我,才由哈接到了他的一封信,这才又有了交道。”[14]
在《艺文志》的作家群体中,疑迟的小说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而显得与众不同。疑迟在“北满”一带生活工作多年,精通俄语,喜欢苏俄文学并受其强烈影响走上文学道路。“北满”时期的疑迟,不仅从高尔基、屠格涅夫、果戈理等名家的作品中汲取文学营养,更从东北密林和蒙古旷野中寻找到永恒的写作资源和表现对象。疑迟以翻译苏俄小说登上文坛,直到《山丁花》发表以后,才引起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山丁在《乡土文艺与〈山丁花〉》一文中,称赞疑迟是“一位勇敢尝试的乡土作家”。在此后爆发的关于“乡土文学”与“写与印”的文坛论争中,疑迟也因此成为《艺文志》核心人物中唯一未受到对方批判的作家。
除了小松、爵青、疑迟几位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山丁、王秋萤等伪满文人。他们不但当时作为古丁的对手成全了这位作家的文学;事后又从浩瀚的历史中在发现和照见自己的同时,肯定了古丁。往事如烟,随着伪满文坛成为历史的一页,这些人已不再为今天的人们所提及,完全陌生甚至是忘却。然而,古丁和他的文坛战友的创作却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永远地留在了那段遥远的岁月中。不但成为今天的研究者们仍然关注的对象,而且他们的文学灵魂也注定会在未来的现实里一起飘游。
[参 考 文 献]
[1] 李春燕.古丁作品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2] 梅定娥.古丁研究——『満洲国』に生きた文化人[M].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12:63.
[3]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
[4] 李春燕.就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几个问题评古丁[C]//李春燕.古丁作品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592-622.
[5] 刘晓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J].探索与争鸣,2007(6):58-61.
[6] 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M].靳丛林,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7] 上野凌嵱.国策文学论——答本世纪的课题[N].满洲日日新闻,1938-03-10.
[8] 青木实.满洲文学的诸问题[J].满洲评论,1937,12(20):29-30.
[9] 纪刚.面从腹背——古丁[C]//李春燕.古丁作品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10] 冯为群.评古丁的文学成就[J].社会科学辑刊,1992(4):140-147.
[11] 叶渭渠.雪国的诱惑[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91.
[12] 古丁.关于小松[C]//陈因.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43-50.
[13] 爵青.黄金的窄门前后[J].青年文化,1943(3):84.
[14] 古丁.谭[M].长春:艺文书房,1942:66.
[责任编辑:冯雅]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5)01-0013-08
[收稿日期]2015-03-01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伪满时期中国本土作家研究”(编号:2012JD01)。
[作者简介]刘旸(1984-)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尚一鸥(1978-)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On Several Difficulties in the Studies of GU Ding
LIU Yang1SHANG Yi-ou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
2.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24)
Abstract:The studies of GU Ding is a complex and intricate topic and all the problems,to which are relevant can never be addressed with simple theorie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GU Ding,the great writer of Manchukuo after Japan was defeated,basing on four difficulties: GU Ding’s Creation in post-war era,the category of GU Ding’s literary works,being double-faced and GU Ding’s stand as well as GU Ding’s changing political stand.
Key words:recover;colonial literature;double-faced;change one’s political 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