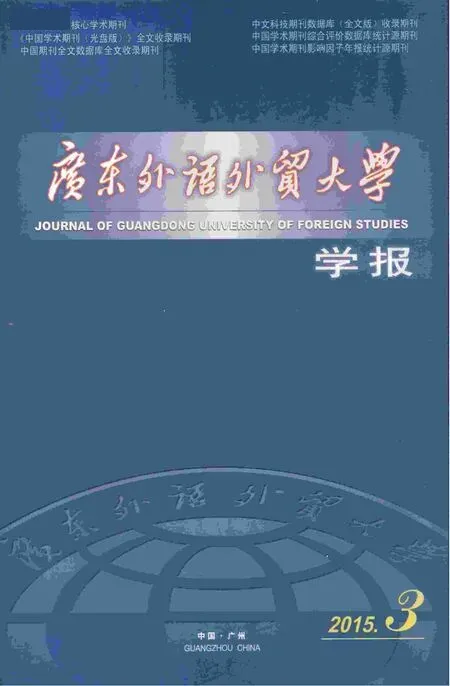麦克尤恩成名短篇主题的诠释与澄明
张平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420)
一、引言
本文采用“拉片子”的方法,即对麦克尤恩三个短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与解析。所谓的“拉片子”,就是“逐格﹑逐句地解读电影和电视剧,通过细致地观摩,全面掌握片中的内容﹑风格与技巧”,是影视编剧艺术的重要方法。(杨健,2008:1)本文借用这一方法细读伊恩·麦克尤恩的三个短篇小说,而非惯常的,以某家或某流派的理论解读。伊恩·麦克尤恩是英国享有盛誉而又深受欢迎的作家,他也被同行誉为“一位真正具有想象力的天才”。大不列颠《时代周刊》对他的作品的评价是“精确,细腻,风趣,妖异,扰人” (O’Neill,2018),其创作为英国小说开辟了新方向。现年66岁的麦克尤恩于1975年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获得声望,并于次年获毛姆奖。(王守仁,2006:217)此后佳作相继问世,迄今已出版十几部小说与小说集,均大受欢迎,荣获过包括布克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有人预测,诺贝尔文学奖最终离他也不会遥远。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麦克尤恩,2010)短篇小说集是麦克尤恩的处女作与成名作,被视为“奇书”。全书共有八个短篇,每篇的主人公均为男性青少年,麦克尤恩借鉴多类写作模式,以意识和潜意识交接地带的经验与事件为叙事对象,以其独有的构思和编排组织素材,赋予平常的故事以非常的思想内涵。每个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但故事性极强,麦克尤恩的写作以精准﹑细腻和充盈的质感征服了文坛。
试将这八个短篇归纳出一个主题是相当困难的,也难以做到准确,事实上麦克尤恩的每篇小说里似乎都有多个主题,理解的角度更是多样,这充分说明了这个天才作家的丰富。本文从短篇小说集里选出《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蝴蝶》、《夏日里的最后一天》三篇放在一起解读,我们发现主题有共通之处,那就是青春的困顿迷茫和现代社会的困境之间的某种共生和同构,以及两者间可能有的因果联系。我们能做的就是仔细地解读,尽可能地发掘作者潜藏的思考,将这个有趣的连线游戏进行下去。很难说这样的主题是作者的独家发现,但麦克尤恩将它推进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由此作品同时具备了所谓人性的深度和社会性的广度。而青春以及与之相连的童年可谓最美好的题材,在这片肥沃的田地里,作者用他创意的种子和出色的技艺种出了奇丽的植物,它们像自然生长出的一样真实,令细察者叹为观止。
二、逾越焦虑——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与小说集同名的小说《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我”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和女友西瑟尔在海边一个四层楼上的房子里度假。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经常听到墙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挠,这怪声响折磨着“我”的神经,最终发现那是一只老鼠。“我”用拨火棍把老鼠打死了,这才发现老鼠怀了孕。“我们”处理了老鼠母子的尸体,决定离开这里去远行。
这是故事的主线,副线是“我”的女友西瑟尔。作者简单交代了她的家世背景,她父母离异,有个十岁的顽皮弟弟阿德里安。阿德里安对姐姐西瑟尔有种过分的依恋,喜欢插在“我”和西瑟尔之间。西瑟尔的父亲不介意女儿和“我”住在一起,还告诉“我”一个赚钱的营生:捉海里的鳗鱼拿到伦敦去卖,于是“我”开始充满希望地不停地做鳗鱼笼—— “我”总要找点事情做。与此同时西瑟尔去工厂打工。最后我只捉到了一条鳗鱼,辛苦做的鳗鱼笼都被冲走了。而在“打老鼠”事件发生之后,“我”把本想留着吃的那条仅有的鳗鱼也放生了,西瑟尔则决定辞去工厂的工作。
小说的高潮是“打老鼠”,作者把这一场面写得惊心动魄。毫无疑问,打老鼠这一行动具有象征意义。怀孕的母鼠在日夜不停地打洞,最终侵犯到人类的空间,走投无路的老鼠对人类发起决绝的“攻击”,最终和未出世的后代一起被“我”打死。小说中的“我”是个敏感的男青年,有着类似母性的创造生命的欲望。“我”会在做爱时幻想生命形成的神秘过程,这让“我”兴奋。而西瑟尔则什么都不想,她总是“任由事情主宰自己”,并且她“从不作评判”。作者没有写“我”多么“爱”西瑟尔,“我们”就这么呆在一起,并不思考。这最初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无因无果。整个夏天,“我”和西瑟尔做爱,却尽力避免创造出生命这一麻烦事。正如许多现代人一样,性是一种享受,一种形而下的消遣,是纯肉体的行为,与灵魂甚至与爱情无涉,而这背离了性是生命的延续这一本质。这是人的异化,这让“我”每每在激情过后有一种隐隐的罪恶感,那老鼠挠墙的声音正象征我心灵深处的不安。
开始的时候一切是那么美好。“从夏日伊始,我们把轻薄的床垫抬到厚重的橡木桌子上,在宽敞的窗户前做爱,直至此举终显无谓。”但这不过是人造的假象,随着时间流逝,无聊的生活显出丑恶的本质。“我”并非想成为父亲,可“我”有着无处发泄的创造的冲动,一种爱和给予的欲望,而它找不到目标。
最后的仪式结束,一切平息下来。“我们把床垫抬到桌子上,在敞开的窗前躺下,像夏日伊始时那样。有一丝清风吹进,带来淡远如烟的秋天气息,“我”感到恬静,无比清澈。西瑟尔说,下午我们先清理房间,然后去远行。“我”把掌心按在她温暖的肚子上说,“好”。“我”和西瑟尔终于找回彼此,在大自然的不可测与荒芜的人的海洋里,我们的床垫像一叶扁舟 (诺亚方舟?)。经过这一个躁动而绝望的暑假,收获的秋天到来了,也许“我”已做好了孕育生命的准备,让这份爱情开花结果。最初的爱情与最后的仪式之后,“我”完成了从一个男孩到男人的成长,而阿德里安也离开了我们。也许我们还有爱的能力?作者给出了乐观的解答。《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揭示了青春期的情欲和浪漫,它却不会长久,即将而又必须走向社会,这给少年带来焦虑和惆怅,这是成长和成熟的必经阶段,回避与拒绝是徒劳的。
三、严肃的悲剧—— 《蝴蝶》
《蝴蝶》的故事则有点耸人听闻,简单说来就是一个青年猥亵女童并将之杀害的故事,因作者貌似站在主人公的立场来写而颇受争议。由此看来,作者只是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为的是更好地揭示人物心理。纵观全文,作者并不是要让人“同情”主人公,而是相对客观地写了一个严肃的悲剧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一个年轻男子星期天早上无事闲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男子的回忆倒叙星期四傍晚发生过的事情。“我”开始回忆星期四。星期四“我”也是这样一个人走着,一个闲极无聊的小女孩跟在了我的身后,她叫简。她就是死者吗?作者没有明说。随着作者的叙述,我们发现事情向着最坏的方向无可遏止地发展了下去,小女孩最终成了“我”的牺牲品,她就是死者,她的确是溺死的,但却是我把她“送进”运河里的。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叙述的调子不疾不徐,“我”是偶然碰到了小女孩,并不是蓄谋犯罪,这不是一篇侦探小说,那么作者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和小女孩一起走的这一段路是小说重点描绘的部分,写得细致逼真,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都很出色。小女孩先是让我给她买玩具,她吊在“我”的胳膊上,“作出贪心的模样”,第一次的接触,“我”是被动的。后来小女孩又要吃冰激淋……转折出现在“我”为小女孩抹掉嘴上的一圈冰激淋,这次“我”产生了性的冲动。接下来“我”变得主动,可以说是“我”“诱拐”小女孩去了荒僻的运河边,“我”说那里有蝴蝶,小女孩信以为真。
作者毫不避讳地写了“我”的生理和心理的全部活动。“我”在一个暗黑的桥洞下拉开裤子,小女孩试图呼救,却被桥上疾驶而过的火车声湮没,然后“我”让小女孩摸我的下身,这就是全部过程。这描写并不色情,甚至有些滑稽,而这是“我”的真实想法。随之而来的是残酷,小女孩吓坏了,她在逃跑时跌倒,头磕到石头昏了过去。于是“我”“悄悄地慢慢地把她放入运河”。“我”就这样平静地杀了人,并没有罪与罚的煎熬跟随其后,“我”这样过了几天,又在星期天的早上出去闲逛了。如此麻木不仁让人想到了加缪的《局外人》,那是一部充满哲学思考的作品,而《蝴蝶》探讨的,更多的也许是社会问题。作者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人。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存在,这样的故事在社会新闻里并不鲜见。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小说中的“我”是极端孤独的。在小女孩央求他买东西时,作者写到:“甚至从我孩提时算起,都从来没有人如此主动地触摸我这么长时间。我只觉得胃里一阵寒战,脚下不稳。”这是一个患“肌肤饥渴症”的人,显然他已经独居很久,因为开头作者提到“我”已经几天没和人说过话。然而孤独不是变态的理由,于是作者又提供了一条,即“我”没有下巴。“我的下巴就是我的脖子,他们不分彼此,滋生怀疑。”这是一个长相怪异的人,于是他的不合群就有了解释。他看到一群孩子在踢球,球滚到他脚边,他只是抬腿跨过,没有加入他们。而紧接着有人向他扔石头,他敏捷地用脚踩住了并得意洋洋。他的母亲也饱受没有下巴之苦,孤独终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尖瘦而乖戾,活像一条小灵犬。”这克制的语调里有“我”对母亲的同情。如果说丑人心灵美,那么我要说这非但不是一条规律而且现实往往相反。难道外貌对人的影响如此巨大吗?莎士比亚在名剧《哈姆莱特》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个人方面也常常是这样,有些人因为身体上长了丑陋的黑痣——这本来是天生的缺陷,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或者生就一种令人侧目的怪癖,虽然他们此外还有许多纯洁优美的品性,可是为了这一个缺点,往往会受到世人的歧视。一点点恶癖往往遮盖了高贵的品性,败坏了一个人的声誉。”
这些条件可以构成犯罪吗?也还不够,还有那条运河。这条河丑陋肮脏,原来有过一个垃圾场,还有个看守的老头,现在都消失了。从“我”对运河的了解可见“我”经常来此散步。“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好奇的是小女孩。她虽然也害怕,但对蝴蝶的渴望战胜了恐惧。她天真地以为臭水沟边会有蝴蝶飞来,还找到了难得一见的花作为佐证。平庸的作者大概要写罪犯被女孩的纯真感化,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罪犯就不是罪犯了。然而,即便我们找了那么多原因,依然找不到那个最根本的“犯罪动机”,也许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从“我”的眼睛看出去,世界是灰色的。你无法找到这整个世界观的构成,它是一点一滴的积累,量变到质变,最终一个细小的念头引起了心灵的蝴蝶效应。“天气炎热,令运河今天的气味更加浓烈。浮渣散发出的不像是化学品的味道,却更似动物的体味。”这是最后的推力。
造成悲剧的还有人性中的恶念。也许“我”本意并不想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然而“我”不知道如何跟这个世界打交道,所遇到的都是冷眼和屈辱,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于是在这一天“我”把这些加倍返还。小女孩是牺牲品,她死得悲惨,她甚至来不及哭,恐惧攫住了她。在她死前,世界丑恶的一面完全暴露在她面前。而对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已经不能说同情,作为一个人他显然是有缺陷的,但他的人性又没有完全泯灭,这就使得他既可怕又可悲。为什么人会被异化成一个幽灵,哪里出了错?那条运河是一个象征,工业文明下人与人的疏离被这个极端的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与人最终的接近方式竟然是互相伤害!
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我”看到了当初向我掷来被我成功踩住的那块石头,“我”开始想象另一种可能性:“我”把滚到脚边的足球踢回去,然后和街角的那群孩子一起踢球。而一切已无可挽回,这另一种选择因不可能而愈显珍贵。“我”现在就要去见女孩的父母,去赴我的“约会”。可以想象,因为那份可疑的证词,“我”此去凶多吉少,也可能我侥幸逃脱了法律制裁,而这些都不重要,因悲剧已经发生。从作者悲伤的叙述中可以读出对边缘人生存境况的深切忧虑。
四、精神世界的疏离—— 《夏日里的最后一天》
《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样也是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所谓最后一天指的是“我”的暑假结束,第二天要去上寄宿学校,而这象征着童年的结束。对整个漫长夏日的描写是小说的主体,主要人物是“我”和一个名叫珍妮的胖姑娘,她比“我”大得多。小说的情境依然是很日常的:“我”的父母亡故后,哥哥将房子变成了出租公寓,“我”每天无所事事地观察那些男男女女的房客,预习着成人世界的种种。“我”十二岁,仍沉浸在丧母之痛中。新来的房客珍妮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母亲的替身,但这只存在于“我”的潜意识。珍妮很胖,笑起来还“发出一种温顺的马儿那样的轻嘶声”,这是紧张引发的不自然的笑,别的房客都听不惯珍妮这样笑,不一定因为难听,只是作为一个进入社会的成年人,紧张羞涩这类“不体面”的情绪早就应该被克服了。而仍是孩子的“我”不介意这些,“我”还没有被社会规范洗脑,“我”的感觉基本都出自本能。可以看出,“我”本能地喜欢珍妮,而其他人则“本能”地排斥她。
这栋房子里全是年轻人,而珍妮虽然和他们差不多大,却好像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年代。珍妮是传统的女性,做得一手好饭,懂得照顾孩子并会为之倾尽全力。住客之一凯特是个未婚妈妈,在珍妮来到之后,她仿佛找到了一个保姆,将自己的小女婴爱丽丝几乎全权托付给了她,像卸下一个包袱。而当珍妮完全赢得了孩子的心,她又有些嫉妒,但很快就释然了,转而和新男友出去约会。瘦削轻盈脸色苍白的凯特是别人眼中最正常不过的都市女郎,她和庞大的粉红色皮肤的珍妮是两个典型,代表了女性审美和“实用”特性的极端分裂。“我”受到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想着以后找女朋友要找凯特那样的。而事实上“我”和珍妮互相需要、相处无间。从小说的叙事中可以感觉到,珍妮是“母性”和“安全感”的化身。现代社会女性的审美“功能”被无限强调,自然属性则被挤压。作者通过珍妮这个具体的形象唤起了我们遥远的记忆与渴望。
房子里的人对珍妮敬而远之,对由她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改善视而不见,他们在社会观念的惯性里,失去了原始和自我的价值判断。他们早已不相信一蔬一饭的平静中的幸福,代之以大麻和寻欢作乐。因此珍妮是孤独的,处于青春期的“我”当然也是,连同还不会说话的小婴儿,“我们”三个是这所房子里的异类和多余人。整个夏天三人经常一起泛舟河上,“我”教珍妮辨认鸟叫,珍妮告诉我她以前在学校当老师时的事情,“我们”的友谊超越了意识形态,甚至语言。夏天快结束时,珍妮带我去城里理发,“剪去了我的整个夏天”,又为我买好了校服。“我们”最后一次到河上去时,船翻了,珍妮和爱丽丝都消失了。
在作者的叙述下这个结尾没有悲剧的沉重,反而有些诡异和说不出的诗意,这种矛盾和张力是作者的注册标签。《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本小说集里的小说风格各异,游走于真实和梦幻两端,每一篇都是两种风格比例不同的调和,而混合两种特质最为平衡的就是这篇《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它极端写实又如梦如幻。这种独特的效果来源于作者对叙述距离的巧妙设置,既切身沉溺又清醒抽离,通篇都是回忆的笔调,隔岸观火,却无比真切。从真实方面看,这是一个悲剧,珍妮和爱丽丝被房客们——社会的“抽样代表”排斥和孤立。母婴的联系以及生息繁衍的正面价值已遭贬抑,现代人反抗自身作为生物链一环的“低级属性”也即拒绝自然。所以她们的生存注定是艰难的。又兼珍妮是胖子,婴儿是私生子,社会的压力将终其一生如影随形。所以最后她们的“投河”不足为奇,虽然看起来她们落水完全是个意外。作者未明写珍妮有自杀的倾向,但她曾唱过一首呼唤耶稣降临的歌。天使一样的珍妮未必不是主动选择了回到上帝身边。
但最重要的不是珍妮而是叙述人“我”的感受。从梦幻的角度理解,珍妮也可以是失去母亲的“我”幻想出的慰藉。这一幻象帮助我渡过了难关,然后消失。“我”接受了母亲离去的现实或者说童年的消逝,进入了学校——社会的象征之一。因此当“我”落水后再水中漂浮甚至快要睡着——紧接着可以想象也是溺死河中——却是“我”即将梦醒的时候。这一段非常精彩:
“我是那么疲惫,闭上了眼,感觉好像是躺在家里的床上,使冬天,妈妈来我房里道晚安。她关掉灯,而我把船溜进了河里。然后我又记起来了,又开始呼喊珍妮和爱丽丝,又望着河水,然后我的眼睛开始合上,妈妈又来我房里关掉灯而我又沉入水中。很长时间我忘了呼喊珍妮和爱丽丝,我只是挂在船沿,漂流而下。”我想回到婴儿时代,母亲的怀抱,但不可能了。夏日的长梦结束了。
三篇小说都提到了河流。《夏日里的最后一天》里告诉我们那条河流向伦敦。毫无疑问河流有着象征的意味,且应和伦敦的象征合起来看。伦敦是弱肉强食的水泥森林,意味着现代化和成人世界。未成年的主人公对未来的岁月有着无限憧憬,但更多的是畏惧。因为“伦敦”难以让人感到亲近,那里离他熟悉的大自然太远,它拒绝童真/贞。所以主人公总在犹豫,要不要就这样顺流而下。《夏日里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段就是这种迷惘和惆怅的形象化:“现在我看到岸上有个地方,很久以前认识的。那里有一小片沙滩和一方草岸,岸边有一个码头。黄斑已沉入水中,我推开小船,任它一路漂去伦敦,而我在黑色的水中慢慢朝码头游去。”
“伦敦是一个我不想让河水知道的很紧要的秘密,它流过我们家时并不知道伦敦。”这个孩子气的拟人的说法揭示了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理和动机。通过这句话,“我”与河水的关系拉近了,同时排斥了伦敦,河水也许可以看成属于我的时间,“我”想挽留它,但更有可能的却是“我”被它裹挟而去。因为它比“我”强大,而且它不仅属于“我”也属于别人,属于伦敦。它绵延不尽,看起来没有变化,但其实一刻不停地在流逝着。“我”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我”想假装伦敦不存在,因为“我”不喜欢,但“我”不能改变河水的流向,伦敦就在属于我的河道里,在下游。
五、结语
胡适在论及现代小说时尝言:“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感觉到满意的文章。”(胡适,1918)麦克尤恩做到了。虽然以上短篇的篇幅有限,但读者却没有感到“扁平化”[Forster,1970:75-77]的俗套,作者呈现给读者是那些短暂的生命旅程,细致的生活肌理和富丽的想象之花。从创作过程看,笔者难以找到证据显示麦克尤恩是在沿着某种路向或理论来进行他的创作,可在故事的舒展形式以及方法与技艺方面确有其独特之处。无疑他是创意性写作的行家里手。也须看到,他对古典音乐的喜爱也在其艺术创作中同样有所表征,如古典音乐中的二重调式与小说构思的两条并行或交替发展的主线与副线。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人物相对集中,故事情节展开自然而简单,但着笔精准,主叙与插曲相互配合,互为表里,略有曲回,便转向叙述的高潮,小说的收尾干净﹑自然。麦克尤恩具有极强的坚守精神,他的创作从不随波逐流,不让层出不穷的文学创作的新潮和手法左右自己,以生活图景为蓝本,关注日常生活空间里人与事,表现其生存的当下状态,他以信达为写作艺术的最高标准,虽然没有华彩,但不乏迷人的艺术魅力。
胡适.1918.论短篇小说[J].新青年(3).
王守仁,等.2006.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健.2008.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M].北京:作家出版社.
伊安·麦克尤恩.2010.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M].潘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Forster E M.1970.Aspects of the Novel[M].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
O'Neill,John.2008-01-05.The 50 Greatest British Writers Since 1945[N].The Times(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