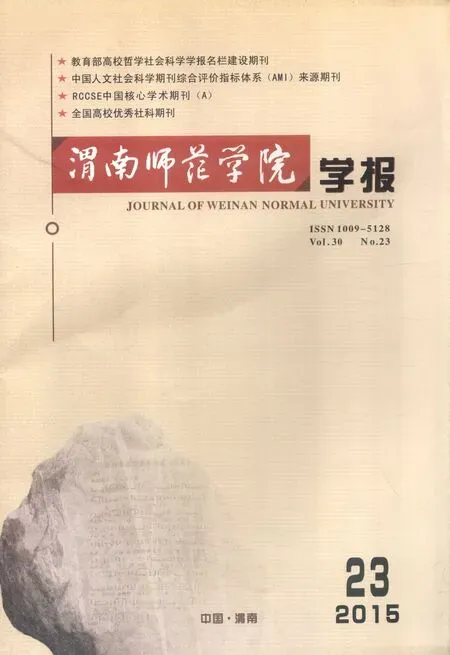从巫史儒之关系传承浅析《史记》的“究天人之际”
张 瑞 芳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巫史儒之关系传承浅析《史记》的“究天人之际”
张 瑞 芳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一。受到巫术神秘思维与儒家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及其《史记》创作,在“究天人之际”方面表现出祖先崇拜、君权神授、天命观等倾向,这与巫、史、儒三者之传承密切相关。“究天人之际”是本出于巫的史官,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继绝地天通之后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梳理。
史记;绝地天通;天人合一;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自述其创作《史记》的宗旨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成为其写作该书的首要目的。史出于巫,“沟通天人”是巫的本职,发展到史官,太史公用“究天人之际”来加以沿承。从“沟通”到“探究”,是汉人对“人”与“天”之关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是人对自身力量以及对人在天地间的位置的重新确认。在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太史公的“探究”,无疑是对当时文化传承与思想转变的一种总结,而居于宗旨之首的“究天人之际”,也成为我们了解太史公写作《史记》的起点与立场的关键。
一、从绝地天通到天人合一——天人关系在时代观念转变下的重新定义
在华夏文化的发展史上,绝地天通是人神分隔、政权意识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绝地天通’是颛顼在传说时代推行的一次事关祭祀、历法的‘神权专制’,在氏族发展成氏族联盟、部落的时代,颛顼命重、黎改变‘家为巫史’、‘民神同位’的状况,将祭祀、历法进行了一次思想和文化层面的统一。帝尧及其后的时代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对后世的王权专制和文化正统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1]I绝地天通之后,天与人的关系开始疏离,沟通天人成为巫师兼部族领袖的特权,成为他们传授神意,进而左右部族事件的重要依凭,政教合一则成为绝地天通之后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国家政权观念的逐步形成,“巫”的神职地位逐渐丧失。频繁的战乱使得人们对于天意的解读与领受更加迷茫,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难以捉摸。汉王朝取代速亡的秦帝国,开创了稳定的大一统局面。在这种背景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逐渐显示出超越诸子理论的优势,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与推崇。他强调天与人之间的相互感应,指出人间的秩序本源于天道,而天道即是人道,强调人自身之行为的影响力与重要性。在董仲舒的理论中,政治清明、个人道德境界的提高与行为举止的符合道义等,即是理想化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并不是简单的天人感应。董仲舒“天人合一”理论的提出,是汉代学者从哲学理论层面对自然、人、社会等相互关系的重新认识。至此,“天人合一”将天意的神秘莫测与人的行为活动联系起来,成为绝地天通之后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进一步拓展与界定。太史公“究天人之际”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二、由巫到史——职业渊源下的认知与探寻
史本出于巫,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2]2732作为史官,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与学识积淀,对其“究天人之际”的写作宗旨有着最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巫的职责即在于沟通天人,借助一定的巫术手段与方式获得上天的旨意,从而在关键事情上替人们决断、解惑,指导人们做事。巫对上天旨意的传达直接关系到部族的繁荣与发展,禹、汤、文王等人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部落首领,也同时是各部族身兼巫职的最高宗教领袖。其身份的合二为一,既是绝地天通之后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出现“政教合一”趋势的一种体现,也是“巫”这一角色随着时代演变而逐渐走上末路的开始。
“古者帝王右史记言,左史记事”[3]4031,在巫所分化出的百工之中,“史”因其重要性,在国家政权中倍受重视,又因其博学与社会现实需要,其“文史星历”的传统职能也一并被保留。由“巫”的沟通天人,到“史”的探究天人关系,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也可视作史官“回归”本职的一种体现。
细察《史记》之结构设定、行文记述等,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阐释也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了这种回归。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自身家学渊源的追溯即从颛顼时代的重黎分治下民开始,将绝地天通为其记述起点: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喜生谈,谈为太史公。[3]3961-3963
又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3]3998-3999自述其父司马谈的学识渊源曰:“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3]3965一再强调史官与“天官”之间的密切联系。其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评价阴阳家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3]3965在承认“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尽管“未必然也”[3]3967,但强调阴阳“序四时之大顺”的意义,将阴阳家列于六家之首。这种出于家学渊源的职业思维与认识,在《史记》的体例编排上更是别具匠心。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对此已有论述:
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下,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3]4031
从张氏所论中,不难看出天文星象历法等知识对《史记》体例编排上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史记》“究天人之际”的意旨是沿承自天官之学的征兆信仰的思维模式,是要借史事来预示未来,是对前兆的一种总结和对占卜预示的一种归纳。
同时,考虑到史官之“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出身,此处之“天”其实还包含有借助天文星象学之观察来审视人事的含义。一般学界都将“天”解释为“自然”或“大道”规律,并进一步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解释为探究自然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但是,结合《史记》的书写,太史公对占星、阴阳术数的重视,多以隐没的方式潜藏在其对历史的记述之中,以富有神秘色彩的预示方式加以注解。因此,对于“究天人之际”的认识,并不应仅仅局限于解释为探究自然与人的关系,“天人之际”本身也包含着具有巫文化色彩的神秘预兆,《史记》在对一些事件与人物的记载中都涉及了此类内容。如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对刘邦赤帝之子这一神秘身份的记述: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3]438-439
以全知视角、借助神秘力量进行预叙,实为史家之惯用手法,并非太史公首创。《史记》沿用了这一手法,用以展示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这在“天人感应”开始日渐盛行的汉代,有特殊的意义。
诚然,观星占卜是史官的重要职责之一,故而有学者据此认为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4]16。对于这样的论断,笔者认为,在认同太史公的天官之学相关学识的同时,并不应过度放大其试图将这些学说用于解释与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用意。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史官的太史公更注重的是借助于大量的史料、史实,为人物立传,为历史寻根,并由此探寻历史发展背后的规律,探讨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学说在武帝时期影响力的逐步增强,“天人合一”思想中对“人”之力量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了理性意识在彼时的抬头,《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努力,也在很多方面展现了“神秘因素”与“理性意识”之间的抗衡。这种抗衡,也反映出儒家学说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来自其内部的承继与突破。绝地天通之后,天人合一的儒家学说,也正借由从巫到礼的转变悄然影响着本出于巫的太史公。
三、从巫到礼——天人合一下的“究天人之际”
儒亦出于巫。《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5]162上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之《要》篇所引孔子言“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儒家所提倡的“礼”,其最初便是由巫之礼仪与规范发展而来。儒家在汉代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推广,得益于董仲舒对于天人感应之说的巧妙转化,儒家对于礼仪规范的尊崇,在董仲舒之天人感应学说中得到贯彻与宣扬。天道、天命、天谴等带有强烈巫术特征的观念与词汇,在新王朝的政治决策中也多被强调。同样,上述这些带有“天人感应”色彩的观念,在太史公借助于史实来“究天人之际”的《史记》写作过程中,也屡次被“重申”与“印证”,成为人们解读太史公命运观的一把钥匙。
第一,从巫到礼,对于祖先的崇拜是巫与儒所共同尊奉的,在天人合一之影响下,《史记》对于民族史、家族史的追根溯源,是人对于自我之重新认知与定位的一种体现。巫术思维下,祖先崇拜对于先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到天人合一下的儒家礼教,同祖共源的记述对于大一统的国家而言同样不容忽视。《史记》记事起于黄帝,并且把黄帝作为华夏以及蛮夷部族共同的祖先,这便在理论层面与事实层面上,为大一统的政权找到了最合理的存在依据。这一方面成为新王朝建国立业的重要根基,另一方面则成为绝地天通之后个人、群体重新确立自身与外在环境之关系的重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天人合一既是个人追根的动力,也成为群体溯源的依据,并最终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将天、祖先与人逐级合一。
第二,受到巫术神秘思维的影响,天人合一下的君权神授观,是《史记》对于王朝更替与人物命运解释的基本出发点,但个人的能力与主观努力,也一再被强调。无论对于时代久远的夏、商、周之更迭,或是对于秦的速亡、汉朝的建立,太史公在行文中对于君权神授始终笃信不疑。这一点,尤以对汉高祖刘邦的描写最为全面,除却《高祖本纪》中对于刘邦神异降生、屡次脱险等经历的记述外,在《淮阴侯列传》中借助韩信之言,说他是“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3]3167;在《项羽本纪》中借范增之言,述其“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3]393;太史公本人也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感叹:“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3]916配合着这种先入为主的君权神授观,个人的才能与努力也同样是太史公表述的重点。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自我评价曰: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3]476
这种清醒的自我认识,恰是刘邦的过人之处,也是他最终打败项羽、登顶问极的关键。相形之下,占尽先机的项羽最终败亡,则更凸显出个人自身能力对命运的影响。太史公的史家眼光也因此跳出了神秘的命定论的局限。
第三,同巫一样,儒家也解释天命,但在天人合一时代背景下,儒家对于天命的解释早已超越巫术的神秘莫测,取而代之的既有顺势而为的主动承担,更有坚韧不屈的积极抗争。无论承担或是抗争,都是太史公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努力完成历史使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一种“天人合一”,也是整部《史记》对于“究天人之际”之主旨最为精彩的阐释。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6]211渴望对命运的认识是儒家命运观的重要内容,其实质亦是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对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3]3974
面对大一统时代的百废待兴,司马迁主动接过父亲遗训,承担起编纂史书的重任。这种继孔子而“何敢让”的豪情,成为他写作《史记》的出发点,从其言辞中不难看出,这种承担,本身就带有极强的天命色彩。而当他遭遇李陵之祸、慨叹“身毁不用”时,对于发愤著书的认识,在“述往事,思来者”的自我勉励中逆流向上、忍辱著述,则成为他不屈从于命运、努力抗争的动力。
就人物个体而言,无论是《史记》中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人物,还是历经祸乱的太史公自己,“天人”之关系更多地成为“天人合一”之天命观的实例。《史记》对于有德者居天下、道义对于战争胜败的衡量、天道循环与王朝兴衰等等的记述,尽管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但对历史趋势的发展和个人的主观努力,司马迁仍是给予了清晰的判断和充分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继于巫术思维、由绝地天通而引出的对未知规律的探寻,成为儒家独尊、天人合一背景下史官对于历史规律探寻把握的起点。“究天人之际”作为《史记》的宗旨之一,恰恰反映了儒学兴起之后,古人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下对于绝地天通的继承,是大一统背景之下巫、史、儒在各自的立场之上对天人关系的探究。
在司马迁的家学渊源、职业传统与学识修养背后,是巫、史、儒三者关系的传承与演进。他借由作史来实现“究天人之际”,是出于巫、受到新兴儒学影响的史官,在大一统背景下对于“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与认识,反映了古人从绝地天通到天人合一的思维变迁。巫职的探求神秘,儒家的崇尚礼法[7],在《史记》的书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究天人之际”,既有字面意义上借助天文星占对应人世变迁,带有神秘色彩的传统内涵,又是史官忠于史事,以古观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以坏之理”[2]2735,试图探究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努力。
[1] 陈冯涛.绝地天通与颛顼的神权专制[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汉]司马迁.史记[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章启群.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9-16.
[5]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李小成.司马迁的礼学思想[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6):12-16.
【责任编辑 朱正平】
See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uman inHistoricalRecordsthrough the Inherit between Witch, Historiographer and Confucianism
ZHANG Rui-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See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d and human was one of the purpos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itchcraft and the theory of witch coming from the Confucianism that Man is an integrated part of Nature,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by Sima Qian reflected the diversified tendencies like ancestors adoration,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fatalism, etc., and it’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witch, historiographer and Confucianism. The historiographer redef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the human after the theory which isol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Historical Records; isol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ted part of Nature; see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d and human
K204
A
1009-5128(2015)23-0069-04
2015-10-21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史记》选本研究(11XZW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史记》所录谣谶及其文学文化研究(14SKYB02)
张瑞芳(1982—),女,山西灵石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唐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