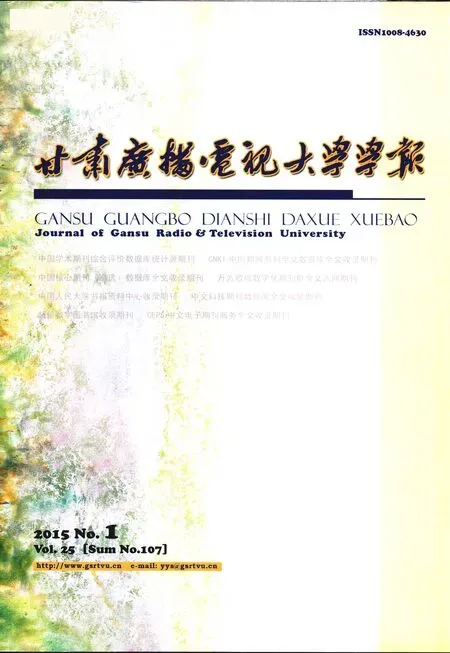大漠回归的灵魂书写
——对话雪漠
朱卫国,雪漠,陈彦瑾,张晓琴,张凡,刘镇伟,等
雪漠专题
大漠回归的灵魂书写
——对话雪漠
朱卫国,雪漠,陈彦瑾,张晓琴,张凡,刘镇伟,等
【丝绸之路文化】栏目开栏语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值此之际,“丝绸之路文化”栏目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也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吧。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并不为大家所陌生,但值此大数据时代,她却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涵义。
自汉代始,中国丝绸便从乡邑流出,穿行于大漠戈壁,远涉重洋,或辗转于中亚、西亚、南亚区间,或直抵地中海及东非沿岸疆域,以其万种风情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时间最久远、路程最漫长、内容最丰富的惊艳之旅。当时中西文化的西传与东渐依附的主要是这条横亘欧亚大陆的通道。朔风中的悠悠文明史最终汇聚成丝绸古道上的一道道风景,驻足于人们的冥思与记忆中,遗响不绝。
两千年后的今日,新的时代悄然来临,古老的丝绸之路也似乎获得了复兴的信念,这或许是历史赋予后继者又一次弥新的契机。时下所提倡的“新丝绸之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文化大走廊”,其厚积薄发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对华夏文明丰富的积淀与内涵进行新的诠释,由此强化沿线广袤区域间更为广泛的互动与共融关系,也为其多元形态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民族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和传统习俗等提供深入的民意基础和地缘优势。
本栏目旨在积淀、发掘、探索和光大丝绸之路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学界人士的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和鲜活独到的语论为内容,以促进其大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弘扬,以博得学术百家的参与与瞩目。温故知新,鉴往知来,这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文化”栏目所意欲显示的一种郁郁勃发、春风欲度玉门关的节奏吧。
[导语]甘肃武威籍作家雪漠的第七部长篇小说《野狐岭》于2014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以解开蒙汉两支驼队消失之谜为线索,以“招魂”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前的中国西部骆驼客的探险故事,把消失了的骆驼客的生活写得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被认为是“激活读者不曾经历的历史”的“重构西部神话”。《野狐岭》是开放式的话题写作,是最能体现雪漠叙事才能的作品,也是2014年长篇小说界的重要收获,它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所说:“雪漠回来了!从《野狐岭》走出来了一个崭新的雪漠。不是一般的重归大漠,重归西部,而是从形式到灵魂都有内在的超越。”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西部作家雪漠,他对故乡的情感记忆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西部凉州贫瘠而辽阔的土地,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都是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正是怀着这种赤子之心,雪漠重回故乡,重温故土,怀着“听真话、听实话”的诚恳心态,应邀前来兰州参加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在2014年12月20日举办的《野狐岭》研讨会。
《野狐岭》;回归;灵魂书写;轮回
时间:2014年19日下午
地点: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310会议室
参加讨论人员: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传媒学院教授朱卫国,著名作家、甘肃作家协会副主席、《野狐岭》作者雪漠,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野狐岭》责任编辑陈彦瑾,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凡,西北师范大学部分教师和研究生。
朱卫国:从“大漠三部曲”到“灵魂三部曲”再到《野狐岭》,您文本中所感知的世界具有继承与超越的特点,那么您在这一过程中的创作心境是怎样的?
雪 漠:其实《大漠祭》之后的所有作品都是文学创作上的喷涌。在《大漠祭》之前和《大漠祭》的写作都是非常痛苦的,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文学功底以及文学素质本身的训练过程。《大漠祭》之后这种训练就没有了,因为文学本身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我的血肉,这时候就像呼吸一样,非常自然,不需要刻意地去打磨和锤炼,《大漠祭》之后的所有作品其实是在流淌着一种灵魂,流淌着不同时期的雪漠的灵魂。《大漠祭》的关注点是老百姓的存在本身,所以《大漠祭》的文本只能用《大漠祭》来展现。严格地说,《猎原》的创作更近了一步,通过牧人、猎人这个意象来写出一种存在,一种心灵“猎原”上的冲突,一种欲望面前的冲突。《白虎关》又近了一步,那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这个时代马上消失了,一群人活着的痛苦,活着的焦虑与纠结,新世纪和旧世纪交替的诸多东西都在《白虎关》中有所体现。之后写《西夏咒》,我觉得存在性的、本体性的东西可以告一段落了,而是追寻一种深层的灵魂的东西,《西夏咒》看来非常难读,但写《西夏咒》的时候完全是喷涌状态,不是常态的,写《西夏咒》的时候停不下来,没有办法阻断这种写作状态。《西夏咒》的呈现,其实是作家创作达到了一种境界,内心世界以及情感达到非常饱满状态的时候,自己就会喷涌出来的东西。
我几乎拒绝各种欲望的东西,因此总能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精神世界,《西夏咒》就是这样的。《西夏的苍狼》写得比较仓促,如写五年就是一个好东西,但我只写了一年,因为当时签约,涉及到时间的问题,里面最好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再说《无死的金刚心》是另外一种风格,好多人认为不是雪漠创作的,事实上我写了一个平凡的人在不断地寻觅、超越过程中成长为智者的故事。《无死的金刚心》和《西夏咒》之后我的读者超出了文学圈,尤其以《无死的金刚心》的读者群最为明显,包括为文化的、为信仰的,等等。他们读得如痴如醉,甚至包括出家人。在文学意义上,作品也许并不是多么重要,但在灵魂意义上,却是很重要的。“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是我创作的不断超越,我感受到了别人没有感受到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理解为精神世界,也可以理解为灵魂世界,很多人读得如痴如醉,文学界很难感兴趣,但是崇尚精神信仰的人却奉为圭臬,奉为心灵的重要食粮。可以说,“灵魂三部曲”里面所有的内容其实是我精神追求的一种归结。
我的《野狐岭》正好就是介于二者之间,既有一种灵魂上的探索,又有回归“大漠”的努力,《野狐岭》的完成是在沙漠里完成了一次类似的招魂。文学是自由的,文学能表达人和人的灵魂。《野狐岭》的创作也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喷涌而出。我的所有的作品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在孕育的过程中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生,但成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出生。写作《野狐岭》的那种喷涌的过程有一种鬼魂附体的感觉,巨大的力量逼着你写。当一个作家到了完全隔绝欲望世界的时候,完全沉迷于精神世界的时候,总有一种饱满的诗意从生命的深处涌动出来,狄更斯和巴金等很多作家就是如此。文字背后有一种奇怪的东西,有一种涌动的力量存在。人与社会、自然达到了一种天衣无缝的浑融,这种写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欲望性写作,我把它称之为智慧性写作。宁静的水面下有很深的世界,流动的河水上找不到这种世界,非常宁静的水面才可以照出整个世界,所以说一个作家的宁静可能更为重要。可以说,我的创作过程更多的是我的成长过程。到一定的时候,作家就可以成为自己笔下的所有人物,能成为大自然,成为骆驼,成为狼。沈从文说自己是贴着人物写,而我是成为人物写,写大漠也是,写戈壁也是,写骆驼也是,写所有的人物都是。为了丰富对于世界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体验,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我经常去深入采访,这个过程就是为我腹内的孩子提供营养,采访的越多,这个孩子就越饱满,所以我的创作过程就是自我成长的过程。
刘镇伟: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您在叙述故事时所选择的叙述方式,是否与您所要表达的主题与文化内涵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雪 漠:明眼人可以看出,我的小说语言有我自己的风格,但是每一本小说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大漠祭》是一种语言,《猎原》是另一种语言,《白虎关》、《西夏咒》、《野狐岭》都不一样,每部作品语言都不一样。事实上,我写作的时候没有语言,但是我笔下的人物有语言,什么样的人物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农民就有农民的语言,凉州人就有凉州人的语言,所以当你进入这个人物的时候,或者你成为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必然会有这种语言,所有人物的语言和他的命运、性格都是有联系的,语言承载着一个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命运。一个人的语言信息和思维信息承载着他的全部信息,一本书也承载着作家的全部信息。就像一个人的细胞,承载着这个人的全部信息,可以复制出这个人,克隆出这个人。语言也是如此,一部书也是。所以有时候,只要作者进入那个人物,成为那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是不用考虑语言的,因为那个人物本身就有语言,这时候你的语言就会成功,就会展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东西,虽然这个人物是你塑造的,但是他具有自己的生命特征,有他的气息,也有雪漠的气息。
其实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挖空心思去考虑语言,只有一种无我的状态,完全融入到描写的对象,人物、景物、实物、场面之中。甚至于这个时候我都没有创作或写作的概念,不考虑语言技巧这些东西,否则心就不宁静了,一般在遣词造句、构思创作的过程中有些东西瞬间就丢掉了。真正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语言的,脑子里没有文字,没有构思,只有一种巨大的诗意力量的涌动。
朱卫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其他的技巧也好、手段也好,对您的创作来说,我认为所有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您的生命写作,或者叫灵魂写作。我们传统的现实主义是讲人物的个性化、语言的个性化的。写农民、工人,小孩、老人就要有符合他们身份的语言,语言就要作为一种外壳,能够看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它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都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但是为什么您的每一部作品的语言特色都不一样,一般的作家,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他的语言是有变化的,但是变化不是太大,作家到一定时候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代表作往往形成这个作家的风格,或者是轻松的、幽默的、或者是凝重的、沉稳的,或者是以短句见长、或者善用长句,或突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或彰显地域乡土特色,等等。为什么雪漠老师的作品从“大漠三部曲”到“灵魂三部曲”到《野狐岭》每一部作品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有雪漠的影子,但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底色。《野狐岭》所谓的神性也好,灵魂也好,这个东西按照唯物主义及无神论观点来说是没有的,但通常被称为“迷信”的东西却在民间大量存在。所以您刚才说“进入了一种状态”,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状态,就是一种境界,更深层说就是完全脱离了世俗,甚至脱离肉体的一种东西,而进入了纯粹的灵魂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因为他已经不是雪漠本人,不是作家本人,写婴儿他就成婴儿、写老人就成老人,包括骆驼的人格化,他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理性世界的作家了。不然就不会有喷涌的感觉和一发而不可收、不吐不快的感觉。理性的东西从文字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有概念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定性定量的分析。但是雪漠老师的作品有时候很难用理智、理性来分析,进入不到作家灵魂创作的境界当中去,进入不到作家那种癫狂状态,你就很难把握作品的底蕴。中外文学史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郭沫若写女神的时候一喷涌他就克制不住,狄更斯等著名作家也都曾有过类似经历与表述。
雪 漠:宁静者没有自己,高度的宁静状态下有一种丰富的诗意,而且它会有一种巨大的快乐,全身的肉也会蹦蹦地跳,这个时候心仍然是非常宁静的。作家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拥有一面大的镜子,它可以照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可以进入任何想进入的人物。
朱卫国:人物之间的这样一种叙述的转换,由这个人说,再到那个人说,或者到骆驼说,有叙说者自己,有作者“我”,还有整个作品叙述的第一人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来平衡?
雪 漠:在境界中观照人物。写《野狐岭》的时候,人物的诉说是最先喷涌而出的,而作者诉说的是完成后加入的。陈亦新和陈彦瑾说必须让读者进去,“我”进入野狐岭的这条线是完成后最后才加进去的。先是作家进入《野狐岭》中每一个人,最后是作家直接进入野狐岭。内心中涌动的力量可以直接化为作家的思维,这里面没有方法,就好像一杯水一倒就出来了,这是大自然某种非常和谐的力量和作家本质的心灵力量达成共振之后奏出的一种乐章。
朱卫国:关于《野狐岭》,许多专家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多方面的评论,既肯定了作品的创新与突破,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没有指出来,诸如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神秘的东西。一个是从他个人来讲,作家之前的作品没有较多的涉及;第二从整个西部文学的创作来讲,有些作品里面确实有一些玄幻、神秘的东西和神性色彩,但是没有像《野狐岭》那样以招魂的形式来书写故事。从题材上来讲,这是西部文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好多作家未必熟悉雪漠老师《野狐岭》里面的驼队,不知道在甘肃武威一带从清代到民国时期,这样一种驼队和驼运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是当时贸易往来、物资交流的重要形式。据历史记载,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驼队所走路线四通八达,遍及大半个中国,东北经北衙门、包头、张家口而至北京、天津;东南经兰州、泾阳而至西安、河南;南经青海而至西藏;西经哈密、乌鲁木齐而至南疆、北疆一带;北至大库列。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委派,民勤人魏永坤作为总领队,带领驼队驼运大批茶叶远赴俄国,曾受到列宁的接见。由此来看《野狐岭》中的驼队传奇、驼客命运及人物的悲剧,何尝不是雪漠在极度尊重历史、尊重那千千万万消失了的驼客原型的基础上,饱蘸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运用与此相适应的艺术手法与独特的叙事方式塑造出来的呢?当然,这也理应成为《野狐岭》成功的重要因素和雪漠回归大漠的重要标志。
对于这个题材,据雪漠说,他在30年前就开始关注,到现在才写。这样的喷涌写作,在其他人身上不会发生。因为没有经历,也没有采访过,包括对这里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各类人物、历史事件,都不甚了解。驼队大部分是昼伏夜行,因为晚上赶路,无牵挂,一门心思去赶路,如果是白天,骆驼看到草就会忍不住去吃,难免有毒草食入。一般一支驼队是11只骆驼,首尾各有一只骆驼戴驼铃,防止走丢。这些都是真实的。没有这样的了解,这种题材就无法去深入挖掘。我想,对作品的深入研究,也需要对背景及其所写题材内容有一些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为什么用这样一种文学形式,特别是招魂的文学形式去写这样一个别人未曾表现过的题材。雪漠讲,不要让这样一种东西逝去。但是再过若干年以后这样的东西也许都会逝去,所以用文学的形式保留着、记录着,甚至再现这样一种历史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
面对这样一种历史题材的小说,雪漠老师没有用传统的手法表现,而是用一种全新的笔法,所谓招魂的写作,我认为这个里面肯定是有玄机的,他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用这种形式能高度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而且把这样一种悬疑、传奇、恩怨、爱恨情仇写得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传统题材的现实主义手法也许不可能做到。
陈彦瑾:雪漠老师是把西部这种神秘文化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招魂在西部其实是一种民间习俗、民间文化,所以雪漠老师故乡的人读《野狐岭》可能会更容易理解,我想这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读者的阅读差异和接受程度的差异。
刘镇伟:在某种程度上,雪漠老师的作品当中磨盘是苦难的象征,木鱼是救赎的象征,那么雪漠老师您是如何看待磨盘与木鱼二者所承载的这种苦难与救赎的文化意象的?
雪 漠:磨坊在西部是非常阴森的意象,很多诡异的事情都发生在磨坊里面。在一个村庄里面最神秘的地方就是磨坊。磨坊也有我童年的记忆,磨盘的磙子叫青龙,也有称作白虎的,磙子是白虎的一种象征。在西部,白虎星是不吉祥的,在《野狐岭》里面的磨盘就是苦难的象征,它像无数的岁月一样把很多东西碾碎了,把许多诗意破坏了,作为苦难的磨盘和作为救赎的木鱼之间其实只有一念之差,就是一个字“爱”。在《野狐岭》里面不自觉地用到这样一个东西,没有爱的时候,木鱼妹就是杀手,每一个人都是杀手。
写作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存在,说不清,有意地拒绝思想,里面有无数的灵魂在喧嚣,在涌动,在叙说,追溯过去往往会有一种生命的感悟。在我的所有小说写作中都有一种力量,但是《野狐岭》没有,不知道这样子是伤害了《野狐岭》,还是提供了《野狐岭》更多的解读性?后来发现很多人读到的《野狐岭》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强烈的企图性、表达性、主题性的东西,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好的小说应该像大地,藏污纳垢,小说不要太干净,太干净的小说它的味道就变了。《野狐岭》其实是很不干净的,也许表现出了一种无意识的生命的存在状态,磨盘和木鱼象征的其实是一个东西,救赎如果没有了爱也就不存在。文学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把大爱放到作品中,用爱去化解苦难和仇恨。
张 凡:阅读当代作家雪漠的小说,有三点与各位分享。第一,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是一种具有雪漠式的乡土叙事,个人化色彩极为浓厚;当人们踏进雪漠的大漠世界,随处可见那种来自底层人的琐碎、嘈杂、无序,那种对生命不经意间的苦楚与淡然,在我看来,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琐碎与嘈杂是极为生活化的,是作家信手拈来的一种自然,雪漠并没有为了迎合某种叙事需要而刻意去处理,这里面交织着一层高过一层的紧张关系。把小说的笔触深深扎进乡土世界的作家,其最初那些对于乡土的体验与领悟是最真挚的,因而写起来也比较任性;对作家而言,对于这种生活的体悟太过刻骨铭心、太过透彻,这种尽显于世人眼中的底层人艰难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乡土视野观照下的底层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来看,不论着眼于乡土的叙事,还是着眼于都市的叙事,从中可以领略到作家们的一种情怀:关注生命的一种焦灼状态。只因生命中太多的不确定让人们深为苦恼,我们阅读雪漠的文字,从中可感觉出他笔下人物深处生活焦灼状态中的那种莫名的疼痛,但你又无法去拯救他们。“大漠三部曲”中各色人物都无法拯救自己,外界的介入也无济于事。贯穿于雪漠“大漠三部曲”和《野狐岭》始终的是雪漠内心深处那种较为成熟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情怀,对于生命世界里的一切报以一种敬畏之心,报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即便那些来自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也是作家写作时必须关注与聚焦之所在。
第二,弗罗斯特曾说过,“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关于雪漠“大漠三部曲”里的方言、民俗等这类叙述,可以说是作家小说中富有地域色彩的认同与表达,或者说这是地域性写作的一种呈现,这些往往是作家从事写作之初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与深谙故土文化的一种任意而为。在某个层面上而言,作家个人的成长成熟也是个需要历练的过程,或许等过了这种比较任意的“地域性”书写阶段后,作家的观照视野就发生改变,逐渐观照起世界来,观照那种普遍的人性。但这些较为原生态的语言呈现与乡俗民情是他生命之初最为熟悉的人生记忆,小说中出现的方言也是在无意识情况下的一种自觉,反映出生命原初的意义及价值,从中可以看到作家之“根”在什么地方。可以说,雪漠的“根”在西部乡土。
第三,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或许这是人的现世焦虑的根源所在。当前,许多作家较为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想方设法逃离自己的世界,但又无法逃离世界本身对他的一种束缚,每个人都渴望摆脱眼前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具有现代性色彩的人的现世焦虑感。《野狐岭》中百年前与百年后这两个时间点的衔接是通过小说中的“我”来实现的,而这个“我”的存在即为一种现代身份,“我”虽进入百年前,但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思维特点却仍具现代特点,跨界的“我”可以跨越灵魂、跨越生命,这或许就是雪漠刚才说的那种流动的力量。
朱卫国:目前《野狐岭》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种独特的文本形式,离不开陈彦瑾女士在当中付出的心血,那么您作为一名编辑,您与雪漠先生沟通交流时是如何平衡自身作为读者与编辑的双重身份的?
陈彦瑾:《野狐岭》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以及自己作为读者和编辑这样一种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书稿到我们手里的时候,作为编辑首先会想读者可能会怎么看这部作品,因此我们会先把自己的“编辑”角色暂时忘掉,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普通读者去看作品。
作为读者,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地特别,在特别之外还有很多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吸引着我,读得很过瘾。我读雪漠老师作品有一个阅读史。我最先读的是《西夏咒》,当时感觉非常地惊艳,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很难读,我觉得很好读,开篇的那首小诗马上就让我进入了一种氛围,我是一气呵成把它读完的,感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然后我才读“大漠三部曲”,好像从一个华彩的乐章进入到一片宁静的大地。接着我读的是《西夏的苍狼》。《西夏的苍狼》是雪漠老师第一次写到都市,故事放在了东莞这样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城市,写都市背景下的一种寻找,开始接触日常琐碎的生活题材。然后是《无死的金刚心》,非常地震撼。这部小说里没有丁点世俗生活的描写,完全是灵魂世界的书写。读完这些,再读《野狐岭》的时候,因为有了前面阅读的积累,感觉《野狐岭》是对之前所有作品的一种综合,在叙事上又有全新的东西,对于阅读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在《野狐岭》中,雪漠老师确实采取的不是普通的讲故事的方式。之前我是想从市场和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诠释这个作品,因此我更多强调的是它的悬疑色彩,这是附加在小说之上的解读,完全是编辑出于市场考虑的结果。但刚才听了朱卫国老师的见解,我发现,这部小说的独特的形式本身,就是西部神秘文化的一种直观呈现。比如说它整体的混沌感,叙事的跳跃性,叙事时间不是线性的时间,而是有错位,像里面的人物说的“颠三倒四”;它的叙事空间也是模糊的,像里面招魂仪式下蜡烛照亮的一圈光晕;它的结构也不是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而是有很多的空白,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因无果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杀手究竟是谁,沙眉虎是谁,等等,都没有明说。所以,《野狐岭》的形式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的内涵,是西部文化思维和西部文化美学的直观呈现。
朱卫国:陈彦瑾女士在《野狐岭》的责编手记中指出,超越作为灵魂对真理的追求,成为了小说的主角,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雪漠先生这种追求的影响和意义的?
陈彦瑾:我读雪漠老师作品,感受非常深的一点便是,小说的叙事总有一个视角是超出世俗层面的,就是总有一个超越的视角。比如说,“大漠三部曲”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超越部分更多的是对苦难生存的感慨和对生命的反思;“灵魂三部曲”则把这种超越的景观放大了,由生存、生命的层面提升到了灵魂的层面,但它是通过寓言、象征等手法来体现的,只要读者能够进入这个世界,就能读懂,和灵魂的超验世界发生一种感应。雪漠老师对灵魂世界的描写是喷涌式的呈现,比如说《无死的金刚心》就是一个极致的典型,它是关于纯粹的灵魂世界的大象征。里面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一种梦境一样的存在,所有的存在都指向对真理的追寻。所以说,在这部作品里,对真理的追寻本身成为了小说的主角。但是到了《野狐岭》,雪漠老师借用了一种招魂的形式,把西部大地上曾经的历史和古老的生活——驼队生活和回顾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时的感悟,以及超越那段历史和生活之上的观照结合在了一起,就出现了一种“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的综合体。作家创作每一部小说的时候,并不一定具有某种目的性,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生命本身走到这一步,他就需要这样一个文本去表达,需要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他这时候的一种生命状态。可能正是这样一些原因,才有了不同作品的不同形态。
朱卫国:在《野狐岭》中雪漠老师通过两种追寻——外层叙事是“我”追寻历史真相,内层叙事是马在波寻找木鱼令、木鱼妹寻找机会复仇、驼队寻找罗刹等,表现出了一个大的轮回主题,在这种轮回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救赎意识,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雪 漠:这个结构我在写之前就有想法,就是轮回的结构。这里面有两个走向,第一个是木鱼妹从岭南走向西部,第二个是驼队从西部走向未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形式,木鱼妹如何从岭南走向西部,然后从这儿走向一个未知的地方,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结构。驼队从民勤出发走向俄罗斯,这个过程是在追寻,只不过后来他们的梦想变了,被欲望所吞噬。木鱼妹从岭南追寻到西部也有一种梦想,她的梦想是复仇,最后被爱转化。他们的梦想既是在追寻又是在被另外一种东西吞噬,这个吞噬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和迷失的过程,迷失中追寻,追寻中迷失。总而言之,这里面有很多类似的结构,大回环式的结构。
朱卫国:雪漠老师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说的超验的、形而上的一些东西,那么您在对您今后小说创作和形式的探索方面有什么打算?
雪 漠:最近回到西部,关注点一直在西部,“灵魂三部曲”其实更多的不是为别人写的,而是为自己写的,写的时候也不在乎什么。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探索,一直在平面式地写“大漠三部曲”意义不大,所以说需要一种纯粹为自己心灵写作的过程。《野狐岭》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可能以后的创作是“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的融合,我准备将文本的构思、灵魂的写实以及境界的超越糅合起来更好地写作。
张晓琴:很多人一直在纠结一个哪些小说好读、哪些小说不好读的问题。其实我个人认为,作品就是作家燃烧灵魂的过程。雪漠在写《野狐岭》的时候,他的灵魂敞开了一个窗口,然后《野狐岭》就从这个窗口里出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的这个窗口就合上了。如果假设作家本人去考虑,《野狐岭》怎样才能让大家接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真正的好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不会去考虑我的读者是谁,我的读者怎么读。比如说今天好多人在读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这是一个普通读者很难进入的小说,但是假设昆德拉把《庆祝无意义》写得特别光滑,去讲一个好故事,那他还是昆德拉吗?肯定不是。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潜在的初衷。《野狐岭》就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写作姿态,一种写作历程,这个东西就像雪漠老师自己说的是比较复杂的,事实上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解读。《野狐岭》在幽魂自述之前,可以说是两个声部。第一会的时候说:“我非常想知道,那个喇嘛认为我的前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是解读《野狐岭》的一个钥匙,第一会虽然字数不多,但却有追问:我到底是谁?这是作家写作时一个重要的密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直停留在“大漠三部曲”,那雪漠还是雪漠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他?所以“灵魂三部曲”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说进入不了“灵魂三部曲”,那就不要进入,这个没有关系,但是《野狐岭》事实上就是一个文学和宗教的结合,而且在这个形式上有许多先锋的东西,此外我还发现您的作品在某些地方和鲁迅的精神是相似的,比如看客的问题,比如精神追问的问题。同时,《野狐岭》也很有电影的场景感,比如拷问陆富机,层层推进。
陈彦瑾:对,有不少评论者都指出这本书里有适合影视化的元素。
张晓琴:那雪漠老师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种影视化的可能?
雪 漠:没有,我的写作都是没有目的性的,一有目的性,小说就不对了,小说的味道就不对了。
朱卫国:您最初应该是有动机的,但是一旦进入创作的时候,就不是了,甚至是面目全非了,反而比原本的思路还要丰富,还要精彩。我觉得《野狐岭》中有好多可以形成画面的东西,有一个独特的西部空间,可以成为影视剧一个很好的脚本,从传播的角度和受众接受的角度更好地让更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和欣赏《野狐岭》这一部具有独特意义的文本,也许这是雪漠老师和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责任编辑 龚 勋]
I247.5
A
1008-4630(2015)01-0001-06
2015-01-06
——评野狐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