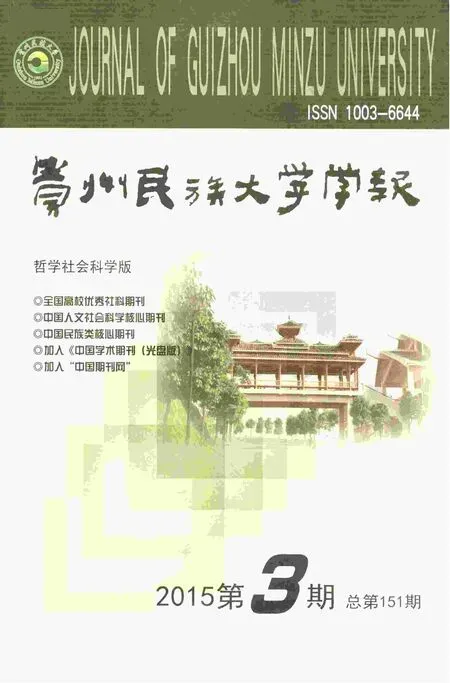论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村庄①
胥永强
(台湾国际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台湾台北 11605)
我国大部分的村庄在经历过“包干到户”所带来的短暂的繁荣之后,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期低迷、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庄组织涣散及公共事务难以开展等一系列原因,社会经济日益凋敝。[1]P13-14这类村庄,成为了中国当前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主要代表。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免除了农业税,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为了进一步促进这类乡村社会经济状况的全面改善,中央政府于2006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中央政府力图解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新农村建设如何具体实施,社会各界缺少共识。从当前大量调查和新闻报道来看,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很高,但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措施与农民的期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一份覆盖17个省(市、自治区)、2 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目前的新农村建设“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典型示范、工程推动的政策,把支持资金集中用于示范点建设,引起了部分村庄的不满”。[2]P46这样星星点点的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未惠及更多的村庄,另一方面还存在行政力量对示范村村民生活的过度甚至非法的干涉。
这背后存在的问题是,当前新农村究竟要建成什么样子,还缺乏深入的思考与共识。也就是说,如何建设新农村,我们首先需要对村庄的理想状态有个设定。这个理想状态的村庄就是我们观察今日村庄的一个理论视野,也就是新农村建设应该瞄向的蓝图。近年来,学界有大量的研究开始关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设定的新农村建设目标过度强调了村庄建设的经济方面,认为应该通过加大经济、物质方面的投入,推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不可否认,对农村过度的剥夺以及公共投入的不足,是导致今日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全面滞后的重要因素。但对于村庄建设,不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在笔者看来,中国农村的独特之处在于,村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它还具有超出了经济领域的更丰富的日常生活方面。与前述经济视角的研究相似,近年来的乡村研究,也过多地关注“比较热闹的甚至是非常态的事件,比如村民自治,上访,集体行动,维权抗争”[3]等,对村庄日常状态的生活或村庄的日常状态关注较少。笔者认为,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村庄生活的本质,我们必须超出单纯的经济视角,也超出新闻报道式的片面视角,而着力关注村庄的日常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针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提出的“生活共同体”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可当作我们的一个出发点。本文的任务,就是参照滕尼斯对共同体概念的论述,对日本学者提出的“生活共同体”概念进行补充,将其建构为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概念,并对这一概念在村庄研究以及村庄建设中的意义做一说明。
一、村庄是共同体
社会学中使用的“共同体”概念来自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共同体(Gemeinschaft)以及社会(Gesellschaft)是滕尼斯抽象出的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类型,这两种生活类型分别建立在人的两种不同的意志上。滕尼斯将人的意志分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人的本质意志表现为本能的中意、习惯和记忆;人的选择意志表现为深思熟虑、心愿和概念,选择意志的这三种表现包括在它的三种总的形式——努力奋斗、深思熟虑和悟性中。[4]Pi-vi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意志之上的,社会是建立在人的选择意志上的。
滕尼斯认为,建立在人的本质意志之上的“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在自然形成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或者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4]Pi-vi滕尼斯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他认为,血缘共同体最为原始,结合最为紧密。血缘共同体进一步发展成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就成为精神共同体,而精神共同体则是心灵的相互关联。[4]P66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建立于人的选择意志之上的“社会”中,虽然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基本上是不结合在一起的,是分离的。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协调,个人预计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会于己有利”。[4]Piii
日本学者最早将“共同体”概念引入到对日本农村的研究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又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农村的研究中。日本学者的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寻找“中国农民中未被西方资本主义思潮辐射的原始的亚细亚式的‘合作共荣’价值”[5]P195-196。不过,当另外一些日本学者在中国华北调查中没有发现理想的“村庄共同体”之后,他们双方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这些争论都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但这也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此后研究中国农村的日本学者长期分为对中国村庄“共同体”性质的肯定派和否定派。[5]P195-196
肯定中国农村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村庄中以庙为中心的“会”以及村民的协同意识。如平野义太郎认为,以庙为中心的“会”与“根据县政府的命令而成立的保甲、邻闾制以及与国家的行政组织单位——行政村截然不同,它是村民的自然的生活共同体。”[6]P153另一学者清水盛光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专制主义支配下的自律的连带”,这个自律的连带依靠的是村民的协同意识,而非实体的组织。[7]
否定中国农村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日本学者主要关注了中国村庄地理边界、公共财产、村民对村干部的认同、村民与村落的结合等。比如,戒能通孝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中国农村没有形成地域固定和稳定的村落集团。福武直指出,公共财产的存在能强化村民共同体意识,而中国的村落缺乏公共财产。对于中国的村干部,这两位学者认为,他们仅仅是为处理官方事务而选举出来的,不为村民谋取福利和服务,而且由地主担任,因此,他们难以获得村民情感上的支持。福武直指出,日本的祖神与土地神是二者合一的,村民家庭与家族的结合,与村庄的结合具有同一性,但在中国并非如此。[7]
对于中国村落究竟是否具有“共同体”性质,笔者认为,争论本身的意义要大于结论。正是因为在“共同体”这一视角下不断地争论,学者对中国村庄的日常生活状态的观察更加深入。但就结论来说,无论是对于传统的中国村庄,还是今日的中国村庄,笔者都肯定其“共同体”的性质。滕尼斯曾明确指出,“共同体”和“社会”这两种人类群体生活的类型都是标准类型,真正的现实的生活是处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对于人类群体生活类型的判断,他认为,“一切结合——既把关系作为整体,也把关系作为团体——,只要它们是基于直接的相互肯定,即本质意志之上的,就此而言,它们是共同体;而只要这种肯定是理性化了的,也就是说,是由选择意志确立的,就此而言,它们是社会”。[4]P42-43基于此,笔者想指出,纯粹的“共同体”或纯粹的“社会”在现实中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因此,也不应以排他性的标准判断现实中的人类群体生活类型。比如,戒能通孝不仅否定中国村落中村民之间的紧密结合,也否定家庭中的紧密结合。他认为,“村落甚至家庭都没有形成紧密的团体结合,而是由松散的个人联合而成的集团,由纯粹的实力关系所支配。”[7]这种对“共同体”的判断标准,明显过高。还有一些学者,一提到“共同体”,就认为其必是温情脉脉,成员高度协同一致等。这种观点在下述两个意义上是片面的:一是将现实中的“共同体”与标准类型的“共同体”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另一是对传统“共同体”做了过分美好的想象。也正是因为过度想象传统“共同体”之美好,也就容易过度强调当前中国农村的“原子化”、“理性化”。
当然,日本学者研究的是七十年前的中国村庄,目前的中国农村,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学者认为,受革命运动、市场经济、传媒以及国家权力的影响,中国的农民正在快速理性化、原子化。村庄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学者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一些因素的出现也在加强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比如,相比解放前农村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得村庄(不管是行政村,还是自然村)之间的边界更加清晰,而明晰的村庄边界是有助于加强村庄凝聚力的。集体林地、集体山地、水源等公共资源的存在,“包干到户”之后集体“机动地”的存在,无疑都会更加促进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及他们的协同行动的能力。而且,当前的村庄内部更加平等,这也有助于村庄的团结。
村民难以合作,这是目前大家有目共睹的现象。这一现象确实与村民的“原子化”密切相关。但是,村民的“原子化”有可能仅仅是缺乏有效的村庄组织的问题,所以也不应将此现象与现代性结合,造成“原子化”现象已是无法阻挡的趋势这一假象。此外,村民的“原子化”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弱化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比如,祠堂庙宇作为村庄共同信仰存在的标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得以重建,信仰活动也同时恢复。[8]而这一过程是与一些学者所强调的村民的“原子化”过程是同步发生的。一些村民可能因工作等原因已不在村庄生活,但是他们对村庄的认同可能从未改变,每逢祭祖、庙会乃至村庄建设之时,他们可能又会返回到村庄中,或者为村庄活动提供捐助。所以,作为一种精神共同体,村庄的结合可能是非常牢固的。
二、村庄是“生活共同体”
“共同体”概念自被引入中国农村研究之后,产生了许多二级概念,如“乡土共同体”、“乡村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村庄共同体”“农村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关系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等。从当前中国学者的文章中看,对“乡土共同体”、“乡村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村庄共同体”和“农村共同体”等几个概念的选择使用,多数是因为学者个人的偏好。这些概念之间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内涵上的差异,也很少被具体界定。
国内学者胡必亮综合西方社会学的多种理论视角以及中国儒家文化的“关系本位”思想,提出了“关系共同体”的概念。不过,他的这一概念将共同体的边界扩大到了“在没有天然的血亲或地缘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方式所构筑出的为自己所需要的新的关系共同体”[9]P14。其实,这一“共同体”概念早已不是滕尼斯所所说的基于人的“本质意志”的共同体,更像是基于“选择意志”的社会。
对于建国之后到“包干到户”之前的中国村庄,一些学者提出了“生产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比如,学者项继权认为,建国后“家族血缘或地缘认同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为以集体产权或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和经济共同体;从一种自然或自发形成的社区共同体转变为由国家权力深度干预和控制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10]这一时期的中国村庄,组织化程度很高,也实现了村庄层面的生产合作。但是,根据张乐天对人民公社时期村庄的研究,村庄高度组织化的背后是村民的普遍离心倾向。[11]P415-419因此,这几个概念也只是分别反映出了这一时期中国村庄某个侧面,村民的离心倾向这一普遍的现实状况就难以在“生产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概念中得到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一些日本学者曾提出过“生活共同体”的概念。日本学者石田浩认为,中国没有欧洲的那种“村落共同体”存在,但却有人们相互间结合的集团,他把这种集团称之为“生活共同体”。[12]否定中国村庄的“共同体”性质的日本学者福武直在分析中国华北农村时认为,尽管华北村庄中的结合不及日本的自然村,但作为一个地缘共同体,毕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活互助关系,而且村落仍然具有对外的封闭性。因此,他将中国华北地区农村的性质定义为“生活共同体”。[7]
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概念。他认为,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基本的贸易和劳务需求。农民对基层市场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状况有充分的了解,他们也常常在这一范围内嫁娶。此外,“各种各样的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如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等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13]P40-49施坚雅对“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论述,实际上是对“生活共同体”论题的一个肯定和补充。只不过,施坚雅将共同体的范围放置在了比村庄更大的地理与社会空间中。
在笔者看来,在众多的有关中国村庄的描述性概念中,“生活共同体”是描述村庄的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概念。首先,“生活共同体”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中国村庄“共同体”性质的两种立场的折衷,这一点从福武直和石田浩等人对概念的使用上可以看出。这一概念,一方面肯定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共同体”并不完善。在笔者看来,不应该对“共同体”做过分美好的想象,不应该以过高的“共同体”标准判断现实中的人类群体生活类型,相对折衷的“生活共同体”概念可能更能描述中国农民群体生活的现实状况。其次,福武直提出“生活共同体”概念,其着眼点是村庄内部的协作、共同事务的开展。换句话说,这一概念的着眼点是村庄的日常生活,而不是维权、上访之类的非常态事件。第三,1978年之后,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收缩,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集生产、经济、政治等于一体的村庄共同体时代结束,村庄的生活、秩序等一定程度上向传统恢复,比如,村庄信仰、人情关系的恢复,由财富决定的秩序重新获得农民认可等。[11]P497-507因此,重提“生活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恰当的做法。
最后,笔者想着重强调的是,“生活共同体”概念可以转化为一个“理想类型”概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任何描述性概念都可以通过某些要素的抽象与重新组合而转化为“理想类型”概念,“生活共同体”概念也不例外。但为什么转化“生活共同体”概念,而不是“村庄共同体”等其他概念,其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共同体”概念有更加明确的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里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哈贝马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4]P7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共同体”强调的是村民私人生活的自主性及公共生活中的相互协作。此外,相比“地缘共同体”、“生产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概念,“生活共同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涵义更加丰富。
三、作为村庄研究视角的“生活共同体”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村庄的观察,笔者认为,“生活共同体”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凝聚力,成员间关系比较亲密,成员共享共同的信仰和规范,具备协同意识,共同体的组织能获得成员情感上的支持的生活单元。共同的信仰、血缘关系、明确的地理边界、公共财产以及道义上的权威中心等的存在有助于加强生活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生活共同体能给成员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它的基本精神是私人领域的自主与公共空间的合作。生活共同体并非天生完善,有序的共同体生活需要一定的力量来维护,这个力量可能来自于生活共同体内部,也可能来自其外部。
上述“生活共同体”概念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要这一概念转化为理想类型概念,事实上很简单。马克斯·韦伯指出,“如果我们把对现象分类的描述转变为对那些现象的解释性或理论性分析”[15]P183,这一转化已经完成。日本学者将在日本农村研究中所得出的“村庄共同体”概念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并对中国村庄是否具有“共同体”性质进行判断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将描述性的“村庄共同体”概念转化为了理想类型概念。所以,当我们带着上述“生活共同体”概念审视村庄的时候,这一描述性概念已经完成了向理想类型概念的转化。创造理想类型概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其分析经验问题。因此,“生活共同体”就成为了观察研究村庄的一个视角。
在笔者看来,“生活共同体”作为一个观察和研究村庄的视角,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这一视角有助于考察村庄凝聚力。村庄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共同的信仰、血缘关系、明确的地理边界、公共财产以及道义上的权威中心等的存在有助于加强其内部的凝聚力。这些要素的缺乏,必然会弱化村庄内部的凝聚力。
第二,“生活共同体”视角有助于发现村庄内在建设动力不足的原因。在村庄中,村民改善道路、用水、村庄环境等的需求是长期客观存在的。村民难以实现合作,不应该用“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之类的观点将原因归咎于农民的本质。从“生活共同体”的角度来说,村庄难以实现合作,原因有二:一是合作基础的缺乏,比如公共财产和道义上的权威中心等的缺乏;二是村庄组织机构缺乏组织集体行动的意愿或能力。对组织机构(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的研究是以“共同体”为视角的村庄研究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比如,村干部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代理人还是村庄共同体的负责人?村干部的角色关系着其是否有意愿组织村民开展公共事务,也关系着其在“生活共同体”中是否有足够的权威来组织村民集体行动。因此,通过村干部角色的分析,可以发现村庄内在建设动力不足的原因。
第三,“生活共同体”视角有助于观察介入到村庄中的国家权力。对于共同体来说,国家权力属于外来的力量。生活共同体并不是不需要外来力量的介入,生活共同体本身并不完善,它的完善需要外来力量的介入。由于“生活共同体”所强调的是私人领域的自主和公共领域的合作,外来力量需要以恰当的方式介入。因此,对于介入村庄中的国家权力,“生活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最后,笔者想指出,“生活共同体”既是村庄研究的一个恰当视角,也是村庄建设的目标。从这个视角出发,不仅可以发现村庄深层次的问题,也可以发现介入村庄的国家权力的局限所在。从完善“生活共同体”的意义上,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权力应该避免对村庄生活的过度干涉,比如,强迫农民上楼等。国家权力应通过加强村庄公共财产、扶持有道义的权威中心等措施加强村庄凝聚力,激发生活共同体内在的建设动力,通过村庄内部的协作来推动村庄基础设施的改善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1]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李剑阁.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3]庄孔韶等.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J].开放时代,2008,(6).
[4][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日]内山雅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J].社会学研究,2005,(6).
[8]朱海滨.民间信仰——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J].江汉论坛,2009,(3).
[9]胡必亮.关系共同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0]项继权.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11]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12][日]田中仁.十年来日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研究[J].祁建民译.历史教学,1993(4).
[13]威廉·施坚雅(美).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5]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