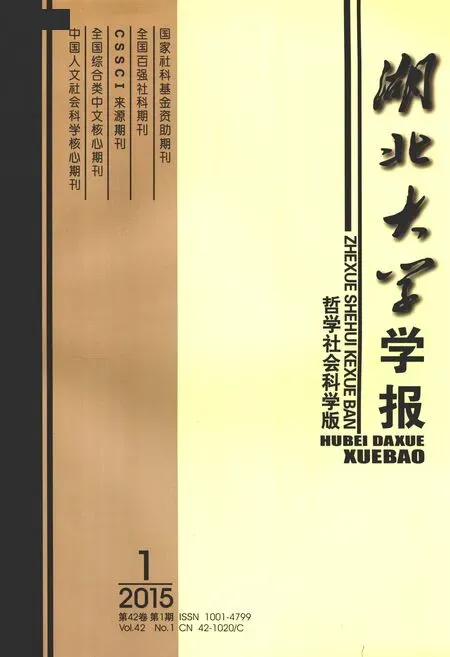新西兰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启示
徐 平,周晗隽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3)
设立环境法院是应对环境危机,解决环境纠纷的通行方法之一。环境法院的两大先驱是澳大利亚南新南威尔士州的土地与环境法院和新西兰的环境法院。目前,国内已经发表了一些国内外学者撰写的研究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的成果,如布莱恩·普雷斯顿等撰写的《环境法庭的运作:新南威尔士土地与环境法院的经验》,丁晓华的《澳大利亚的土地和环境法院》和丁沁怡的《国外环境法院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土地环境法院为例》等。但是国内学界对新西兰的环境法院尚缺乏研究。新西兰环境法院(The Environment Court)是新西兰环境问题处理机制一体化的核心载体。自1991年《资源管理法》颁布以来,新西兰构建了一套完善的争端解决制度,为各国环境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典范。在环境危急频发,环境纠纷层出不穷的当下,研究新西兰的环境法院的设置及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无疑会对中国的环境法院建设及环境纠纷的解决大有裨益。
一、新西兰环境纠纷与环境法院的建立
(一)新西兰《资源管理法》的制定
环境问题在20世纪前期一直困扰着新西兰。在1925年至1965年这40年间,新西兰制定了超过60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然而这并没有遏制环境问题蔓延的趋势[1]26~31。新西兰最早是英国的殖民地,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立法也来源于英国,这也导致了其在自然资源以及环境问题领域单独立法的状况[2]498~519。之所以众多法律的制定并没有有效地改善新西兰的环境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法律之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互动。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首次为世人提供了一个讨论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平台。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专门针对新西兰的环境管理进行了审查,特别指出要对地方性的环境管理问题进行改进。面对环境问题被提上国际议程,以及国内环境治理成效不显的状况,设立一个反映环境管理国际趋势的环境综合管理体系势在必行。因此,新西兰开始逐步对包括《水土保持法》(1967)、《城乡规划法》(1977)、《清洁空气法》(1972)、《噪声控制法》(1982)在内的早期环境领域立法进行审查和修改。
可以说,这次修改是新西兰历史上最大最密集同时也是最昂贵的法律改革项目。在第四届工党政府的指导下,资源管理法律改革(RLMR)由环境部于1988年7月正式启动,旨在建立一部综合性、统领性的《资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来取代现存的环境领域立法。这次改革历时两年共分三个阶段。首先,由核心团队对当时的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领域立法进行缜密分析,形成一篇超过了30页的有关资源管理领域基础性问题的工作报告,并向公众提交了四种可能的改革模式。第二阶段,加大公众参与、核心团队进一步细化改革方案,并提出另一篇阐述这次法律改革的报告性文件。最后,1988年12月,第四届工党政府将这次改革的提议撰写成《资源管理法(提案)》提交至国会。在审议期间,国会特选委员会收到了超过1400份来自公众的建议[3]。由于冗长的审查过程,第四届工党政府未能在1990年10月的大选之前通过该法案,并且在大选中败给了国家党。随后,国家党接下立法的重任,经过进一步的完善与修改,《资源管理法》于1991年7月通过,并于同年10月正式生效。该法案废除了78部环境领域立法,并对其它立法进行了修改,它统一了对全国土地、水和大气的管理[4]。此后,《资源管理法》分别于1993、1994、1996、1997、2003、2005、2009、2013 年进行了修订,其在新西兰环境保护领域的地位不可撼动,可谓新西兰环境保护的宪章[5]。
(二)新西兰环境法院的建立
新西兰环境法院的前身可追溯到根据1953年施行的《城乡规划法》而设立的城乡规划上诉委员会(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ppeal Board),其设立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市规划方案施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设立该委员会的初衷是通过建立一个全职、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专门裁判所的方式,以听证会和证据为基础来解决纠纷,从而在民众与政府之间主持公正[6]。
到了1960年代中期,城乡规划上诉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大量的判例法,包括适用于乡村、住宅、商业区和工业区的规划原则和储备原则等。然而,不断增加的案件量使其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63年新成立了一个临时城乡规划上诉委员会,随着案件量的进一步增加,临时城乡委员会更名为正式委员会,即第二个城乡规划上诉委员会。1969年,又成立了第三个城乡规划上诉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创始人在草创之初便已经意识到,委员会的受案范围将包括对地方政府土地规划和分区政策等决定不服的上诉,这意味着在审判时将有大量技术性问题需要处理。因此,委员会的主席不仅应当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需要对城市规划和地方机构管理的运作模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委员会将从具备专业知识尤其是城市规划方面知识的专业人员中遴选委员。总而言之,委员成员必须兼备法律知识和相关的专业技能。
1977年,新《城乡规划法》施行,基于此法,三个上诉委员会合并成为一个“全面整合审查”的专门法庭,并将级别提升为存卷法庭(Court of Record)。1983年,《城乡规划法修正案》生效后,委员会的主席被重新任命为法庭的法官。1996年施行的《资源管理法修正案》正式将专门法庭重组为环境法院,专门法庭的法官和委员们同样也被重新任命为环境法官和环境委员,同时也将环境法院的级别提升为地区法院。
环境法院成立的历史表明,环境法院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1996年《资源管理法修正案》的改革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在四十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环境法院已经形成了一套开放且细致的听证会程序,以及一套对法官和委员有规范价值的合理裁判程序。
二、环境法院的组织结构
(一)外部结构
《资源管理法》不仅赋予了每个公民享受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而且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环境保护和管理体系。在《资源管理法》体系下,对环境保护事务进行管理、解决环境纠纷的主要机构有以下三类:地方委员会、环境部和环保部、环境法院[7]。
地方委员会是这个三级管理体系中最为基础的一级,其职责是以做出“决定”的方式对那些可能影响邻里、社区、自然环境或者我们自身的行为进行管理,从而减少其对环境的危害。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在做出这些具体决定时,一般需要以相关的地区或区域规划、国家政策声明、国家标准等为依据。而这些规划和政策声明,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委员会在《资源管理法》的框架下制定并通过的。
环境部负责监督《资源管理法》的执行,并就如何更好地适应《资源管理法》,对地方委员会、商业机构和居民社区进行指导。环保部在这个体系下也有一定的职责,即协同地方委员会保护海岸以及其它自然保护区的环境。
而环境法院则负责处理地方委员会在处理具体环境问题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因此,在这个三级管理体系中,环境法院扮演了一个最终仲裁者的角色,它一般并不直接介入具体的环境纠纷。正如当初的城乡规划上诉委员会在设立时所期望的那样“在民众与政府之间主持公正”。
(二)内部结构
1.环境法院级别。新西兰的法院体系由低到高四级: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高等法院(High Court)、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因为新西兰属于英联邦国家,早期,设在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才是新西兰法院体系的最高一级,直到2004年1月1日,颁布了《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最高法院才正式成为新西兰法院体系的最高一级[8]。不过,由于新西兰的上诉法院的判决被上诉到最高法院(形式上的终审法院)的非常少见,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上诉法院的判决在事实上就成了终审判决。此外,还有一些处理专门事务和纠纷的法院,如环境法院、家庭法院、毛利族土地法院等,这些专门法院与地区法院平级,如果对其判决不服,可以上诉至高等法院或者上诉法院。关于环境法院的级别,《资源管理法》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第278条:“在行使民事管辖权时,环境法院拥有和地区法院同等的权力。”第299条:“对环境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上诉至高等法院。”由此可知,环境法院在新西兰法院体系中,是一个处理环境事务的专门法院,与地区法院同级。
2.环境法院的人员构成。环境法院是一所存卷法庭,截止2014年2月,该法院共有9名环境法官、9名候补法官、12名环境委员和5名副环境委员[9]。环境法官一般也兼任地区法院的法官,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官——接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并且终身任职。为了确保环境法院同时也“具备混合知识和专长”,《资源管理法》第253条规定环境法院必须设有非法律专业的环境委员。要想获得环境委员的资格,必须拥有与环境纠纷解决相关的知识和专长,包括商业、经济和地方性政府事务,规划和资源管理,环境科学,工程与建筑,毛利人与《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事务,以及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等。环境委员的任期为五年,在征求环境部长和毛利事务部长意见后,由司法部长任命。环境法院还设有一名首席环境法官,相当于我国的法院院长,负责主持环境法院的各项工作,首席环境法官由总督根据司法部长的推荐而任命。此外,环境法院还包括书记员和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
3.开庭人数。《资源管理法》第265条规定:“一般情况下,审判庭由一名环境法官和一名环境委员共同组成;当第279条或第12章规定的情形发生时(多数是发出声明或者执行令的工作),可以由一名环境法官组成独任庭;当第280条规定的情形发生时,经首席环境法官指派,也可以由一名环境委员组成独任庭。”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案件涉及计划或者资源利用许可,一般会由一名环境法官和两名环境委员共同组成审判庭。在这种情况下,由环境法官主持庭审,但在做出判决时环境委员拥有与法官同等的投票权。总的来说,环境委员更多地工作是参与主持环境纠纷案件的调解,如果未能调解成功,主持调解的环境委员一般不会出现在该案件的审判工作中。
三、新西兰环境法院与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法院的大部分工作都会涉及到与资源管理和环境相关的公共利益问题。在《资源管理法》体系下,法院的职权极为广泛,例如:受理对地方当局基于政策声明或规划做出了的具体决定不服的上诉;对资源利用许可不服的上诉;对减噪通知书不服的上诉;受理发布通知的申请;受理发布执行令的申请等。另外,其它法律也赋予了环境法院一定的管辖权,例如《公共建设法》(1981)中的“对强制征地不服的起诉”;《名胜古迹法》(1993)中的“有关考古遗址的诉讼”;《森林法》(1949)中的“有关砍伐海滩森林的诉讼”;《地方政府法》(1947)中的“对道路停车规划不服的起诉”;以及《新西兰交通法》(1989)中的“与进入受限公路有关的诉讼”。总的来说,在《资源管理法》体系下,环境法院的主要职权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受理上诉
环境法院有权受理对地方委员会之决定不服的上诉。这里的上诉与我国诉讼法对上诉的定义略有不同。上诉(Appeal)在我国是指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判决、裁定或决定不服,提请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活动。依《元照英美法辞典》的解释:“该词被广泛用来指称各种形式的对裁判请求复审的行为。在英国,上诉是指请求上级法院、机构或人员对下级法院、机构或人员就某项正义所作的裁决进行审查,并在其认为合适时,予以改变的行为。”环境法院在《资源管理法》体系中,处在环境保护三级体系的最顶层,而受环境部指导的地方委员会才是直接处理环境纠纷的主体,环境法院在此中的定位只是对地方委员会的决定的纠错者。甚至,在《资源管理法修正案》(2009)第6章及第6AA章施行之前,对环境纠纷的当事人而言,地方委员会的处理还是一个必经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环境法院不直接受理环境纠纷案件。《资源管理法修正案》(2009)施行之后,一些重大项目才被允许绕过地方委员会,直接向环境法院提起诉讼,尽管如此,直接被受理的案件也是少之又少,据新西兰环境法院2013年年报统计,2012至2013年间,环境法院直接受理的纠纷案件仅有5起[10]。因此,我们认为,对地方委员会的决定不服而提起的诉讼应当被称为上诉而不是起诉。在履行其上诉机构职能时,环境法院重新对该决定进行审查,并同地方委员会一样行使权力、承担责任。虽然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可以援引地方委员会提交的证据,但它也可以(而且事实上一般都)收集新的证据。因此,环境法院对大部分提起上诉的案件拥有最终决定权。
具体而言,环境法院可以受理的上诉案件类型有:与区域政策声明、区域和地区规划有关的上诉;与资源利用许可有关的上诉;与设计有关的上诉;与削减通知有关的上诉。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策声明并不在环境法庭的上诉管辖范围内。总之,任何对地方当局基于政策声明或规划做出的具体决定不服的当事人都有权向环境法院提起上诉。
(二)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制度在英美法系中意为法院有权对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尤指法院确认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为违宪而使其无效的权力。由此定义可知,司法审查制度的对象是一切行政行为。尽管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不对抽象、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区分,不过为避免歧义,本文中仍将加以分别。严格说来环境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权力也是一种司法审查权。
环境法院有权对地方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门审查,但是其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范围十分有限。依《资源管理法》附件1中的第14条的规定,只有当事人对地方委员会制定的计划或政策声明中所规定义务之履行不满,并诉至环境法院,法院才有权对该计划或政策声明进行审查。在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公开听证后,环境法院可以维持或者“指导地方当局修改、删除或完善”①参见《资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附件1:第15条,第2款。。地方委员会有义务做出任何必要的修订,以满足环境法院的判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法院同样也是这些规划和政策声明的最终决定者。
与专门审查不同,环境法院所拥有的附带审查权十分的广泛。《资源管理法》第120条赋予了环境法院对上诉案件中大部分地方委员会做出决定的依据进行审查的权力。具体而言,包括区域政策声明、区域和地区规划,资源利用许可等。在《资源管理法》体系下,仅有国家政策声明不在环境法院的审查范围内。
(三)为澄清法律问题而做出的判决
环境法院拥有为澄清《资源管理法》体系中的法律问题而做出判决的权力(Declaration)。该项权力曾被译为“声明权”,虽然简明,却难以用来表明法院或法官运用权力的效果,有失妥当,故笔者采用了《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译法,称其为“判决”而不是“声明权”[11]375。该法第310条规定了其权力范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其范围涵盖《资源管理法》的“任何功能、权力、权利或义务”。这项权力在当事人寻求关于区域和地方委员会的权属划分指导时被行使。同时,它也被用来判定某些行为是否违反《资源管理法》的一般责任,从而避免、纠正或减轻不良的环境影响。另外,环境法院还可以对各种政策声明与规划之间是否一致,或者对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是否违反或可能违反了规划或拟规划的问题做出判决。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做出为澄清法律问题的判决,至于是否做出,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尽管法院一般不愿意对抽象的问题或者没有充分证据的问题做出判决,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法院有时也是很乐意对一些没有争议的法律问题进行澄清。
环境法院澄清法律问题的权力对环境诉讼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使得环境法院可以对一些可能超出其诉讼或审查范围的问题做出判决的进行解释,从而扩大其管辖权。例如,在资源利用许可申请的通知问题上,地方委员会如果决定不通知申请人的,申请人不能对地方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上诉,即使启动了审查程序一般也是归高等法院管辖。但在有些情形中,环境法院已经通过做出判决改变了这种状况:“地方委员会有义务对部分资源许可证申请进行通知”②参见 Foodstuffs(South Otago) v.Christchurch City Council(1992) 2 NZRMA 154(Pl.Trib)(9)。。其次,发表声明以对各部门的权属进行确认,从而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分歧,使得争端在发生之前便得以解决,这将大大降低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四)发出执行令
在《资源管理法》体系下,环境法院也有广泛的发出执行令的权力。《资源管理法》第314条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基于以下理由申请法院发出执行令:(1)为了禁止某人做出违反《资源管理法》的任何条款,任何规章,区域或地区计划中的任何规则,或者任何资源利用许可的行为;(2)为了禁止某人做出任何会或可能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有害、危险、令人反感的行为;(3)要求某人履行作为义务,以符合《资源管理法》的各项规定,或者避免、补救、减轻由其本人或其代理人对环境所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4)为了弥补其他情形下因为避免、纠正或者减轻某人违反《资源管理法》、计划或者资源开发许可证的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此外,第316条规定,地方委员会作为主体也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申请法院发出执行令。
发出执行令这项权力影响深远,它是一套执行法定义务潜在而强大的机制。这一点在《资源管理法》第17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为避免、补救或者减轻对环境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是否发出执行令,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在申请执行令的过程中,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对被申请人做无罪推定。
此外,环境法院的法官还有审理刑事案件的权力,不过涉及环境刑事犯罪的案件应当由具备地区法院法官资格的环境法官在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同时必须遵守包括《刑事诉讼法》(2011)(Criminal Procedure Act 2011)在内的其它刑事方面立法[12]。
四、新西兰环境法院诉讼制度的独特之处
依据《资源管理法》,新西兰环境法院拥有裁决环境管理所有问题的权力。但是,这只是新西兰环境法院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新西兰环境法院区别于其他国家环境保护审判机构的还在于其有特殊之处,这主要表现在环境法院的诉讼是基于重新审查制度以及具有公法性质等特点之上。
(一)重新审查
所谓的“重新审查”(De Novo Standard of Review)是一种司法审查的标准,与传统的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分类有不同之处。传统的形式审查主要考察法律方面的问题,而实质审查则更多地介入案件的事实。但全面重新审查并不止于此,该词来源于拉丁语,意为“重新”。法院按重新的标准审查上诉案件,意味着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受原审法院做出的结论或假设的干扰和限制。简而言之,适用重新审查这个标准,法院可以如同受理初审案件那样收集证据、做出判决。
环境法院在受理对地方委员会做出决定不服的上诉中,正是适用了这种“重新审查”的标准。在审查过程中,法院将不局限于考察地方当局在做出相关决策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法院将会审查任何在它看来适当的证据,并可能传唤任何在它看来会有帮助的证人。法院审查的重点不是地方委员会做出该决定时的审议过程,而是该决定的意义和实质。更重要的是,依据第214条的规定,在行使其审理上诉案件权力时,环境法院“拥有和原决定当局同等的权力、义务和自由裁量权”。除了适用于任何地方当局决定以及《资源管理法》第17条所赋予的“避免、补救、或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具体职责以外,环境法院还拥有“促进可持续管理”这样的一般职责。在履行其职责时,环境法院可以维持、修改或废止任何上诉至法院的决定。
重新审查的权力塑造了环境法院在环境管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使其成为该体系的基石。总而言之,正如环境法院在判例中写道:“法院独立调查取证并认定事实,而且拥有对最终判决的自由裁量权。”①参见 Waitakere Forestry Park Ltd v.Waitakere City Council,[1997]NZRMA 231,234-35(Env.Ct.)。法院可以自由地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使自由裁量权,即使认定的事实与地方委员会所认定的有潜在的不符。当环境法院行使重新审查权时,它成为最终的决策者,并承担实现《资源管理法》目标的全部责任。
(二)环境法院诉讼的公法性质
和所有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纠纷一样,环境法院审理的案件从根本上涉及多数人的利益。它的实质是为了在环境质量方面的公共利益而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因此,环境诉讼是一种公法性质的诉讼,环境法院也在其程序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确保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有利于公共利益。例如,在“蒂阿罗哈空气质量保障诉讼团诉怀卡托地区议会”(Te Aroha Air Quality Protection Appeal Group v.Waikato Regional Council)中,法院允许延长举证期限,尽管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但《资源管理法》体系中的上诉案件的公法重要性远在其他因素之上:“这就是公法性质的诉讼,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有时候可能会超越对私人利益的保护,甚至可能会超越对纯粹公平的追求。”①参见Te Aroha Air Quality Protection Appeal Group v.Waikato Regional Council(No.1)(1993)2 NZRMA 572(Pl.Trib.)。
环境法院诉讼的公法性质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得很明显。例如,提起诉讼或附带审查的当事人一方并不负有严格的举证责任。同时法院并不推定地方当局的决定具有正确性,即上诉人没有推翻这个推定的举证责任。双方当事人仅需提供证明各自立场的证据和论据,并有机会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因此,在目前环境法院的庭审中,抗辩式的法律程序并不像在有关私权的普通诉讼中那样重要,它在这里仅起到甄别证据,以协助法院履行其公法职责的作用②参见 New Zealand Rail Ltd.v.Nelson Marlborough Regional Council,(1992)2 NZMRA 70,76(Pl.Trib.)。。
(三)对环境法院判决不服的上诉审为法律审③参见新西兰的法律属于英美法系,在英美法系国家,上诉审只审查法律问题,而不审查事实问题。这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上诉审是全面审查,既要审查法律问题,也要审查事实问题。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我国的上诉审就是全面审查。
如果对环境法院的判决不服,当事人可以上诉至高等法院。不过,上诉将仅审查法律问题,而不审查事实问题,也就是前文中所说的形式审查。在涉及《资源管理法》体系中的案件时,高等法院并不愿意对地方委员会的政策做过多的实质性评价,这是环境法院的技术性专长,高等法院并不擅长[13]。因此,高等法院在受理此类上诉案件时,严格将其审查范围限制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它的功能是“核实环境法院对区域和地区规划的解读是否妥当……以确保判决没有为不相干的因素所干扰,即环境法庭是以呈堂证供为支撑,并将事实与法律以合理的方式相关联,从而做出合理的判决”④参见 Stark v.Auckland Regional Council,[1994] NZRMA 337,340(High Ct.)。。相比之下,环境法院的工作则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基于其长期经验和丰富专业知识而做出的对地方政策的重新审查。
五、新西兰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环境问题愈渐凸显。中国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中国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妥善处理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纠纷,自1989年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首次尝试设立环保法庭以来,环境司法专门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截至2014年6月24日,全国已有22个省、直辖市共设立各类环保法庭310家,其中设立在高级人民法院的有6家,设立在中级人民法院的有52家,设立在基层人民法院的有252家⑤我国环境审判组织的模式及规模大致如下图。。但是,立案难、案件少的窘境使得大部分环境司法专门化组织形同虚设。例如,2010年,全国环保系统共收到群众来信70.1万件,涉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有关问题的有67.7万件。然而,2010年人民法院审结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9985件,其中,环境污染事故罪仅19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2033件,环保行政案件1894件。从地方情况看,浙江省2011年前三季度涉环保信访数量为4.3万件,而同期环境一审案件仅为261件,相当于0.6%的环境纠纷通过诉讼渠道进入法院[14]。如此大量的司法资源投入以及如此低效的利用率,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存在问题的原因。基于新西兰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成功经验,笔者对于如何改善我国环境司法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陋见:
(一)改变审判模式,设立专门的“环境法院”
当前,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组织的审判模式主要有四种,其中最常见的是环境保护审判庭,其次是环境保护合议庭,两者在现有的环保法庭中所占的比例达到近90%[15]。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一所专门的“环境法院”,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尝试仅停留在“法庭”阶段。环境纠纷一般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诸多特点,这势必要求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整全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否则环境司法将因为人为的制度不匹配而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而我国目前施行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种诉讼形式严格区分的审判模式很难涵盖所有环境纠纷案件,这也导致了一些环境案件久拖不决,甚至不了了之的局面。反观新西兰,环境法院是一个处理环境事务的专门法院,与地区法院同级,同时《资源管理法》还为其运行设立了一套独特的诉讼程序,便于更公正、合理、有效地处理环境纠纷,便于应对突发性环境问题。
我国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已经历时十多年,从草创到试点,发现了诸多问题。如果可以及时总结各地设立的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的经验,并早日突破“环境法庭”阶段并进入“环境法院”阶段,以专业化的制度设置来处理复杂的环境事务,这对我国的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以及整体的环境保护状况势必会大有裨益。
(二)整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环境问题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问题,环境司法只是其中一隅。在新西兰,《资源管理法》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环境保护和管理体系,地方委员会、环境部和环保部、环境法院共同负责可持续管理。地方委员会作为最基础的一层直接管理民众的环境事务;环境部和环保部则负责对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最后才是环境法院,负责对地方委员会具体环境工作进行监督。从大陆法系的角度来观察,新西兰环境法院更偏向于一个行政法院,我国不仅尚未施行行政法院制度,而且就环境审判模式而言,多为“四审合一”或者“三审合一”的集中化模式,纯粹模仿显然是不合适的。
重点在于建立一套整全的环境保护体系。明确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的职能范围,准确落实环境司法的定位,重点加强两者的衔接工作,一改当前环境保护领域行政与司法各自为战的局面。新西兰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中以环境行政为基础管理机构,同时将环境法院作为最终仲裁者的设定,值得我国借鉴。这不仅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避免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的过犹不及,同时也与我国的司法体制定位以及息讼的社会传统相吻合。为加强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的衔接工作,笔者以为至少要遵循以下原则:(1)加强立法,保障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的有效衔接;(2)环境行政执法无效时及时启动司法程序;(3)环境行政执法无力时须加强司法的支持保障[16]。
(三)扩大环境司法受案范围
基于《资源管理法》,新西兰环境法院享有宽泛的管辖权,有权管辖包括区域政策声明、区域和地区规划、资源利用许可在内的各类环境事务。这使得环境法院在新西兰环境保护体系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笔者以为,通过包括立法在内的多种技术手段扩大受案范围,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环境司法机构当前“门可罗雀”甚至无案可审的尴尬局面。通过国内外学者在环境司法领域的有益探索,可以得知环境纠纷往往带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法院及其法官难以妥善处理。只有通过专业性的环境司法体系,才能在最大程度地保持司法公正的同时,整合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扩大环境法院受案范围这一手段,仅仅是我们通过或然的类比方法从新西兰环境法院等成功案例处借鉴而来的表象特征而已,甚至不能将其称为解决“门可罗雀”现状的必要条件。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也大可不必对其效果持过于功利的预期。毕竟,健全环境司法审判机构需要长期、整全的努力。同时我们也切莫因为急于改变我国环保法庭无案可审的尴尬局面,而盲目扩大其受案范围,这只会适得其反。
(四)提高环境纠纷处理效率
我国的环境法院尚处探索阶段。虽然法院数量已经蔚为可观,但是受案量低成为了当前面临的重要窘境之一,其现实原因是大量环境纠纷被拒之门外或者久拖不决,这极大地降低了民众提起环境诉讼的积极性。因此,在赋予了环境法院强有力的权力以及基础后,要想化可能性为现实性,就得在保持公正的前提下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上进行创新和改进。由于环境类案件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是牵涉各方利益且比较复杂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当前的陪审员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遴选环境类案件的专家陪审员,再加上诸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使得目前的陪审员制度对陪审员约束较少,大多数陪审员参审率较低,有的即使参审,也是陪而不审。新西兰的环境法院为我国改革环保案件陪审员制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改革选任制度并加强对专业化技术知识的要求,化特殊性制度为一般性制度,提高专家陪审员的参审人数,将对判决结果的决定权落到实处。另外笔者认为,目前对陪审员的保障有待加强,应实行专家陪审员津贴制度以充分保障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能,将“编外人员”融为环境法院的组成部分。最后,诸如重新审查制度、网络法院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制度都有其合理性并在新西兰环境法院的实证研究中得以证实,应当结合国情有选择性地学习和借鉴。
通过上文的叙述,可以发现新西兰环境法院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环境法律体系的整全性和统一性,以及环境法院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目前,我国的环境法院建设尚处在探索阶段。单从数量上来讲,我国的专门的环境审判组织已经蔚为大观,但是从运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瓶颈,比如案源不足,法官的专业化不够,环境法院的不独立等问题。环境审判制度是镶嵌在我国的整个司法体制中,是其一个环节,环境法院面临的问题有待于整个司法体制的改革,甚至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研究新西兰的环境法院制度,起码给我未来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笔者认为,除了前文中所说的设立专门的“环境法院”、整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扩大环境司法受案范围、提高环境纠纷处理效率之外,新西兰环境诉讼中的重新审查制度、公法性质诉讼制度、环境法庭组成人员的多元化以及调解程序都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
[1]P.Ali Memon.Keeping New Zealand green:recent environmental reforms[M].Dunedin: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 1993.
[2]Oliver M.Implementing Sustainability:New Zealand’s Environment Court Annexed Mediation[C].The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New Delhi: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2007.
[3]Birdsong B C.Adjudicating sustainability:New Zealand’s Environment Court and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M].Ian Axford New Zealand Fellowship in Public Policy,1998.
[4]沈跃东.可持续发展裁决机制的一体化,以新西兰环境法院为考察对象[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5]Past RMA amendments[EB/OL].(2014-06-03).http://www.mfe.govt.nz/rma/central/amendments/index.html.
[6]David Sheppard.Forty Years of Planning Appeals[N].Resource Management News,1995,(5).
[7]Waitaki District Council.An Overview of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EB/OL].www.waitaki.govt.nz/Planning/AnOverview1.pdf.
[8]Supreme Court of New Zealand[EB/OL].(2014-06-03).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Zealand_Supreme_Court.
[9]Judges and Commissioners[EB/OL].(2014-06-03).http://www.justice.govt.nz/courts/environment-court/judges-and-commissioners.
[10]2013 Annual Reports of the Registrar[EB/OL].(2014-06-03).http://www.justice.govt.nz/courts/environment-court/documents/registrar-annualreport-2013.
[11]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Daya Winterbottom,T.New Zealand Environment Court:Evolving Practice[J].(2011)23 ELM.
[13]Briar Gordon,John Hassan,Duncan Laing,Et al.Brookers Resource Management Law Handbook 2014[M].Wellington:Brookers NZ,2014.
[14]袁春湘.2002年—2011年全国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情况分析[J].法制资讯,2012,(12).
[15]杨帆.我国环境审判专门化的探索与发展——基于环保法庭的法律分析[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4,(2).
[16]李清宇,蔡秉坤.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