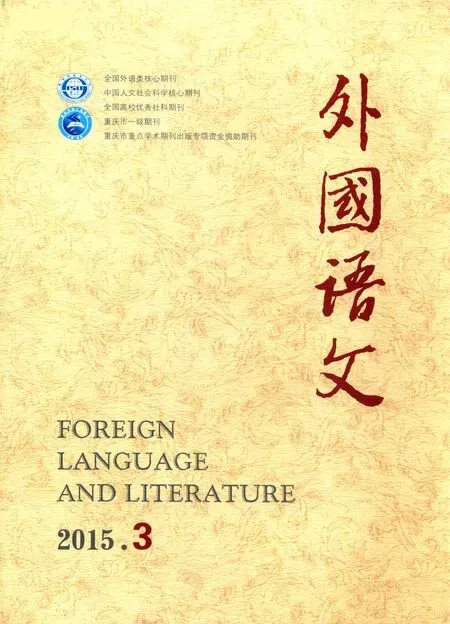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与交流中的译事活动
唐欣玉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65)
1.引言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1938-1945)是一场非正义的法西斯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为了反对法西斯的侵略、保家为国,中国与各个方面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与美国建立了战时合作与交流。在当时,有大量知识界人士投身到中美合作与交流的活动之中,特别是当时有许多人投入到了合作与交流过程中的翻译工作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论文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入手,结合相关史料与翻译史文献资料,对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为了抗击日本而进行的合作与交流中的译事活动进行探源,旨在为进一步研究中美合作与交流中翻译人员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2.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及对翻译的需求
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SACO),全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是抗战时期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背景下建立的抗日军事合作机构,“目的在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用美国物质及技术协同对远东各地之日本海军、日本商船、日本空军及其占领地区内之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之打击”(吴淑凤等,2012a:232)。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培育情报人才、组建游击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支援美国太平洋作战等。抗战胜利后,中美双方遵照协定,于1946年7月1日正式撤销了中美合作所(张霈芝,1999:427)。①国共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利用中美合作所旧址关押、拷打以致屠杀共产党员,其性质发生了变化。
那么,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这次大规模合作,何以能够完成?美方负责人梅乐斯(Milton E.Miles)(1981:171)在《中美合作协定》得到批准后,曾感叹双方在语言、文化背景、军事传统、政治演变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的前提下,竟然能顺利草拟出一个有关联合情报机构的设置方案,殊为不易。至《协定》内容得以有效实施,更是克服了重重障碍。而促成双方合作成功的因素,实有许多,其中译者的居间沟通尤显重要。1942年4月,梅乐斯受美国海军军令部委派来中国商谈合作事宜;1943年4月15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签订;7月1日中美合作所成立。此一洽谈、协商到最后形成共识的过程本身便离不开翻译。且不论会谈期间需要翻译人员传递信息、双方往返电文需做语言转换,单就《协定》的中英文本而言,译者的作用便不可或缺。中美合作抗日,虽系互利共赢,但其中仍牵涉到国家权益、双方义务与责任等问题。在此情势下,翻译时遣词造句便需格外谨慎。根据乔家才的描述,《协定》是先由中文起草,再译成英文;核对、修正后,再由另外一位译员将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翻译后,往往发现不同版本的意思完全不同。而要最终定稿,必须做到译来译去,文字意义完全一致(潘嘉钊、钟敏等,1993:175)。对翻译精准的要求,参与《协定》商谈全过程的原国民党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做了更具体的描述:“(《协定》)由国际科科员王友竹翻译成英文;又经军统英文秘书黄天迈、马佩衡作校订,最后由军统特务、外交部总参议许衾曾来罗家湾做审核。许集中精神一字一句逐条校正译文,而后同梅乐斯交换意见定稿。协定中英文稿拟定、缮写、打字后,报蒋介石核准,1943年年初由梅乐斯携往华盛顿签字。”(潘嘉钊、钟敏,1993:36)《协定》中英文本送到美国后,美方并不信任中方翻译的英文文本,为慎重起见,“先示英文本”,并邀请中国驻美使馆副武官萧勃连日“将中文本逐句逐字口译,麦茲尔(Jeffrey C.Metzel)亲笔记录。结果与国内英文本相符,仅于字句修正。将来仍以国内核对签订为凭”(吴淑凤等,2012a:195)。从以上双方就《协定》反复翻译、斟酌的事实可看出,译员在此次合作中确是担负了重要使命。
而待到美方技术人员、军官陆续抵达重庆,并正式展开各项训练及情报收集工作时,对翻译的需求就更加迫切。为了让来华美方人员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美国陆军部、海军部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本《中国指导手册》(A Pocket Guide to China)。该书内容涉及中国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政治体制、抗战历史、军队组织、抗战策略等等。另外,书中也给出了汉语发音的一些建议、列举了常用汉语词汇和短语及其他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涉及的汉语表达。于那些对中国基本上一无所知的美方人员来说,该书的确有助于他们在短时期内知晓有关中国文化和抗战的粗浅知识、学会简单的汉语会话。然而,《中国指导手册》毕竟不是专门的汉语语言和文化教程,收录的语汇也未涵盖气象、通讯、军事等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而后者恰是合作的重点。如果不配备翻译,美方人员将无计可施,中美合作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类似情形便发生在其时到达中国的美国援华空军身上。1941年,美国空军退役军人陈纳德(Claire Dee Chennault)受中方委托,在美国招募飞行员,组成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到中国支持抗战。之后这支队伍不断扩建,1942改组为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1943年扩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随着每一次改建,来华空军人员便不断增加。而这些初到中国的飞行员,则往往因语言不通、译员缺乏而无法展开工作。时任翻译官王士忠(1945)这样描述:“(民国)三二年春季,大量的美方教官及军火武器源源运到,然因为缺乏通译人员,美方教官无法教练,中国士兵也无法使用新式武器。我们只见美方官兵整日成群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游来游去,又无法工作,不只是浪费了国家金钱,而且会拖延抗战时间。”不过,所幸的是,和援华空军来华时中方尚未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不同,此次中美双方在商谈合作事宜时已大致预见了对翻译人员的大量需求。有关中美情报合作办法纪录中建议,在正式合作机构未成立前,可以先成立一筹备处,其中便需翻译若干人(吴淑凤等,2012a:25)。至协商正式合作机构即中美所组织系统时,“翻译官统计共需二百六十七员(内有两百员系属突击队者)”(吴淑凤等,2012a:84)。军统局还批示“翻译应积极设法罗致,并予训练”(吴淑凤等,2012a:25。中美抗战合作开始后翻译人员被划归到总办公室下设的翻译室和联络组,前者主要负责往来文件的传译;后者则主要担任口头上的翻译与双方人员的联络。正是有了这些翻译官和联络官,中美合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3.译者来源及对译员的要求
在近代中国战争史上,翻译人员通常很难受到信任。如鸦片战争中的译员,基本上都是身份地位极其低下的通事。他们因通“夷语”而为清廷所用,但后者又对其并不信任。战争期间,他们往往被严加看管。战事或谈判结束后,一些人甚至被以“汉奸”罪论处。①相关研究参加王宏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翻译史研究(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2-113.类似情形也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因对日作战的需要,征调了大量美籍日本人担任翻译。尽管这些译员已加入美国籍,并且已是第二代移民,但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同样受到军部质疑②相关研究参见武田珂代子.The Role of Nisei(second generation Japanese American)Linguist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翻译学研究集刊,2013(17):161-174.。那么,发生在中美盟国之间的这次合作,是否也会对翻译人员有特别的要求和限制?
战时合作是中美两国政府授权下的美国海军(签订协议时则以美国战略局的名义)与军事统计局调查委员会之间展开的合作。两个机构的性质已经决定了所有人员必须首先坚守保密原则。这一点在《协定》中也有明确规定。如第四条强调:“本所之工作人员均需宣誓努力打击日本,并对本所之组织与业务及其与本所有关之同盟国单位情形,保守绝对之秘密。”(吴淑凤等,2012a:233)另外,第八条也规定:“在美国训练业已成熟、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同盟国家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处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参加工作。惟此项工作人员在其工作目的地之布置,与其工作之实施,应与本所之主要部门分开,以符秘密工作之原则。”(吴淑凤,2012a:234)而之所以设置如上条款,目的之一便在防止工作人员里通日本。根据来华美国人肯尼斯·布朗(Kenneth Brown)接受访问时回忆,当时中美合作所确有不少投靠日本的通敌者,因此,即便对自己人,双方也都很小心。③本材料源自2011年台湾军事情报局出版的《稻田海军:中美所美方人员口述历史访问纪录》一书,本文转引自http://taiwan.huanqiu.com/taiwan_history/2011-10/2062434_2.html。合作所内部各单位之间设有警戒,不相往来,互相保密(持其内部特制通行证的可以通行)(胡铁城,1985:159-160)。负责沟通工作的翻译官和联络官,自然也应遵守保密原则。
其次,对于此次合作的主导方军统局而言,除需考虑工作人员投靠日本的可能外,还要防止中方人员向美方泄露机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组织双方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人,但如果我们把此一事件置于同时期同盟国在缅甸战场的军事合作及美国对华政策和国民党对美政策这一大背景下观察,就会发现,此次合作并非亲密无间,涉及国家权益时同样存在纷争。根据齐锡生(2012)的研究,中美双方在缅甸战场上冲突不断、蒋介石和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的摩擦不断升级、中国期望美国供应军火及飞机的希望一度落空、计划第二次缅甸战争时美国从承诺中退缩,所有这些矛盾都表明中美合作并非一帆风顺;齐锡生称其为剑拨弩张的盟友关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方对美方人员不可能绝对信任。河南临汝训练班负责人就收到密令,禁止学员和中方官员平日与美方人员接触(仲向白,1981:130)。此外,从当时中美合作所翻译人员的派遣也可看出中方对美方并不完全信任。根据鲍志鸿(2002:56)的叙述,《中美合作协定》拟定,“中美所编译人员,由中方负责聘用,美方不得自行雇用。”这一点也得到了国民党少将黄康永(2005:138)在回忆文章中的证实。尽管我们今天看到的协定并没有纳入此项内容④刘人奎曾谈道,“美方教官在上课时,中方行政负责人员不得进行监视”这一规定系中美双方签订合同时额外的口头协定(刘人奎.中美合作所陕坝训练班和重庆刑警班训练班。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14)· 特工组织(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3)。黄康永和鲍志鸿所讲很可能也属于此类情形。,但从中美合作所三年间的实际运作来看,鲍志鸿和黄康永所讲确也属实。从双方商谈合作开始,到撤销中美合作所为止,所有翻译任务事实上均由中方人员承担。只不过,这一做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必须对中方译员进行严格要求和监督。
最后,国民党还时刻防止着包括译员在内的工作人员通共。即便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共产党也始终是被防范的对象之一。暂时的统一战线掩盖不了双方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军统局时时警惕着共产党力量的渗透和发展。
有了以上三层顾虑,国民党军统局在选用译员时便格外谨慎。考察中美所的译员构成,首要组成是来自外事训练班的学员。该班系军统为建立和加强海外特务组织的需要而创立,学员结业后成绩优异者派往驻外使馆任正副领事或武官,其余则充当翻译人员(江绍贞,2009:103)。中美所成立后,这些军统出身的译员被安排到关键岗位,如刘镇芳担任戴笠与梅乐斯的翻译及中美所翻译室主任;潘景翔充当美国陆军代表魏今生(William C.Wilkin-son)的翻译,任中美所翻译室副主任;潘孚硕、周关锠在中美所总办公室负责译务。1944年秋,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局长长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来华,以扩大对日作战能力名义,签订了中美合作的第二次补充合同。美方愿协助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人员,并答应由军统选派40人分两批赴美留学,为军统培养出一批高级骨干分子。后来赴美留学的,大都是军统中的处长、省站站长。而负责此次翻译任务的便是刘镇芳、周关锠等人,可见他们很受器重。除总办公室外,中美所还下设了诸多训练班。各个班核心层的翻译工作仍由外训班学员担任。如河南临汝训练班的总翻译由外训班第一期高才生、在军统海外区工作多年的常惠卿担任(文闻,2007:282);陕坝训练班的翻译由中校翻译浮春云、少校翻译聂琮、上尉翻译潘然负责(刘毅祥、张少翼等,1984:227);重庆特警班的译员也是从“军统内部有经验和可靠的人中利用”(胡铁城,1985:160)。
然而,随着中美合作所业务不断扩大,需要的翻译人员越来越多,军统自己培训的译员已供不应求。1943年,外事训练班由中美所接办,分别向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各地考选专科以上毕业,并擅长英语之人才,授以翻译常识及专门术语。该班总共办了四期,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内外勤单位担任翻译工作(张霈芝,1999:427)。此外,中美合作所还从当时的重庆译训班征调译员。该班本是为美国援华空军培训翻译人员而设,由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从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征调学生充任译员。这些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后,大部分被分派到航空委、战地医院等机构,也有一部分就分到中美合作所。仅1944年,军统便从重庆译训班征调了100名学员(沈醉,1998:207),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所译员匮乏的压力。不过,与军统自己培养的外训班学员不同的是,来自重庆译训班和1943年后的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思想上较难整齐划一。尽管培训期间官方也特别注重统一思想,每周的政治课以及每周两次(有时候一次)的精神讲话,就是为了向学生宣扬所谓“三民主义、礼义廉耻、效忠党国”等,但此一短期内的灌输实难奏效。军统局自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录用译员时严格把关。其时发生在刘祖烈身上的一件事(左平,2013:170),便能说明译员必须在政治上效忠党国、思想上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刘祖烈是政府征调的军事译员之一。他所学专业为机械制造,因此希望分配到航委会,以便以后可以进入飞机制造部门。但航委会并未录用他,其中原因,在于他被人诬陷与进步学生有接触,外事局要求航委会对他监督使用,航委会则直接拒绝接受刘祖烈。后来事情澄清后,外事局重新将他分派到中美合作所担任翻译。这里所说的“与进步学生有接触”,便指刘祖烈和思想上倾向于共产党的学生有往来。若不是系被诬告,航委会尚且不愿意接受他,更不用说中美合作所了。据绿原(1989:31)自己讲述,他当时也在被抽调的军事译员之列。但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起初被分配到“航委会”,去报到时,却被告知“外事局把你调回去了”。等到了外事局,外事局又对他说:“我们对你是相信的,但是中央团部(三青团)认为你有思想问题,要把你调到中美合作所。”这里所说的“思想问题”,同样指在政治思想上倾向或同情共产党。绿原未到中美合作所担任译员已是定论,但此处他的话似乎存在漏洞。因为从理论上讲,军统局是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还录用一位被认为在思想上与国民党存有异议的译员的。至于实情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察。
最后,除以上两类主要译员外,也还有少量爱国华侨到训练班担任口笔译任务。如分别在雄村训练班和玉壶训练班做过译员的陈德明,便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林体明,2002:308-309)。由于这类译员背景特殊,人数较少,且大都只参加课堂教学的翻译,对中美合作所的情况知之甚少,军统局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限制。
4.译员的职责及贡献
通常说来,战时译员的首要任务及贡献在传译语言。但抗战时期,对译员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也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最高对统帅对译员的职责范围进行明确界定。重庆译训班结业时,学员必须接专门训话。训话首先打破人们对战时译员的惯常认识,强调决不希望译员成为三四十年前的所谓“翻译”或“通事”,单纯作语言文字的传译;接着他将译员的行动纳入中美合作抗日这一背景下进行考量,认为军事译员的首要职责,“在为军队服务;译员应该认识到平时受民众供养,战时受士兵保护,应知感恩图报,多替士兵服务”;而“善尽传译与联络的责任”不过是众多“服务”中的一项。其他使命还包括,促成盟邦与我国的圆满合作,提高我国国家地位,传递、沟通中西文化。具体而言,译员应充分了解双方的优长特点,切实研究盟国官兵生活、行动、精神、思想的特征,并介绍给国军;与此同时,向盟军宣传、介绍中国风俗人情以及立国的精神与主义(蒋介石,1984:58)。也即是说,译员除了传递语言外,还要肩负起文化大使等职责。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中美合作所绝大多数译员的首要任务及贡献仍在语言传译。当然,其中牵涉的具体翻译任务多种多样。首先是中美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往来电文的翻译及会议传译。这一工作主要由中美所翻译室的几位主要翻译人员刘镇芳、潘景翔、周关锠等人担任。他们专门负责梅乐斯等美方负责人与中方军统高层的交涉事宜。另外,萧勃、伍仁硕也经常充任双方会谈时的翻译。其次,情报翻译。《中美合作所协定》第12条规定,中美合作所于重庆、华盛顿两地派驻人员,办理中美两国情报互换事宜(吴淑凤等,2012a:236)。中方转递给美方的情报需由中方事先翻译成英文(吴淑凤等,2012b:371)。时任中美所译员韩金贵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他讲述,当时他的工作便是将各组、室收集到的情报由中文译成英文,送给美国人(邓又平,1988:29)。而整个合作期间,情报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爆破、侦察、布雷、气象、地形地图等军事情报,也有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消息。翻译人员需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方能顺利完成任务。
再者,对敌宣传翻译。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出于对日斗争的需要,设立了宣传组,以对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本占领区内之敌人与人民从事心理战争(吴淑凤等,2012a:236)。具体说来,即“破坏日本国内国外一切战事机构,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机构之士气;在中国各占领区内颠覆日本之傀儡组织;破坏日本威武机构在高丽、台湾及琉球群岛之统治;实施严酷之秘密心理战争,以破坏日本之反宣传,特别是破坏其共存共荣区之谬论;在适当时候鼓励并扶助国内各种以抗日为共同目的之团体”(吴淑凤等,2012b:337-338)。至于实施心理战争的方式,则包括收听日本电台(吴淑凤等,2012a:300);收集日伪书报杂志刊物(吴淑凤等,2012a:307);设立秘密电台以日语等语言公布盟军胜利消息与日本人之弱点及罪行……并以各种文字图画手册以飞机或秘密传递方法传送敌区,以补播音宣传之不足(吴淑凤等,2012a:308)等等。而要完成上述任务,则需要大量日文翻译。然而,在当时,能通日语的人才确实不多。军统在函告邓诺文(William Joseph Donovan)中美合作所与美国战略局的合作情况时便谈到,研究分析(日本电台消息)组因“我方缺乏熟谙日文而具有研究判断之人才,致所获材料未能估定价值”,美方也“屡嫌(材料)来源太不经常,或欠价值之资料”(吴淑凤等,2012b:382)。孟禄也曾向戴笠提及需“谙熟日文之人员”(吴淑凤,2012b:406)。苦于人才难求,戴笠不得已提出调用日本俘虏(吴淑凤,2012b:405),但后者的忠诚度又令人质疑(吴淑凤,2012b:415)。于是,在不是必须任用日文翻译的情况下,中美所往往退而求其次,选派英文翻译完成任务,如威孟斯(Clarence N.Weems Jr.)呈请戴笠委派两名中国学者到研究分析组任职时,要求后者“擅长日文、英文,或仅擅长英文”(吴淑凤,2012b:355),也即懂日文最优,但并不是必备条件。事实上,心理作战组的诸多任务,如编译各种宣传品、收听日本或汉奸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或反宣传等,也大都由英文翻译完成(邓又平,1988:29)。
最后,中美所绝大多数译员最主要的任务及贡献是教学翻译。中美合作所自成立以来,前后创办了20多个训练班,每班数期至数十期不等,每期均配有美方派遣的技术训练指导及负责人。在实时教学中,班部与美教官之间,设立联络组,担任翻译联络。课程分为中国课和美国课,后者包括武器射击、爆破等,每课都配有一位翻译(曹鸿藻,2010)。一切训练,都由美教官负责指导,译员随课翻译(林体明,2002:308)。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译员的付出,中美合作所的通讯人才、气象专家、游击队员等也将很难产生。《军队译员之使命》一文中,要求译员在传递语言时,“要使双方当事人的意思,经过我们的翻译之后,都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使双方都能明了对方的意思,而不致发生误会。”(蒋介石,1984:56)然而,由于战时条件艰苦,整个中美合作期间的翻译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绝大部分又都出在课堂翻译这一环节。梅乐斯曾谈到,语言不通一直是个障碍,在缺乏称职的翻译和地区方言繁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魏斐德,2004:288)。这里先看前者。鉴于原隶属军统局的外事训练班学员受教育程度高,需有大学毕业文凭方能报考(李继星,1993:218),加之他们绝大多数并不负责具体教学的翻译,因此,梅乐斯笔下不称职的译员应大部分来自重庆译训班和纳入中美合作所后的外事训练班。而这些译员之所以很难在美国教官和受训士兵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实有诸多客观原因。比如他们许多大学尚未毕业、绝大部分也并非英语专业学生、军事知识缺乏(仲向白,1981:129)、培训时间短、培训内容粗浅等等。①相关研究参见罗天.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23-249.鉴于此,重庆译训班学员到中美所时,军统又成立了一个临时的训练班,即军统重庆训练班译训队,用一个月的时间向学员们讲述中美所的业务和统一翻译名称等工作(沈醉,1998:207)。可即便如此,译员的英语水平及专业知识仍很难在短期内跟上需要,实际翻译过程中不能胜任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至于地区方言的问题,中美所训练班的学员来源广泛,操持各种方言的士兵和译员之间确是难以沟通。这也就连带出另一个梅乐斯未谈及的问题,士兵素质及受教育程度低下同样给翻译造成困难。各个训练班“训练之对象应遵规定之条件遴选,宁缺毋滥,俾能适合部队之性能,达成任务……使为劲旅”(吴淑凤等,2012a:405)。其中对士兵知识水平的规定为“粗通文字、能做简单报告者”(吴淑凤等,2012b:42)。在后来实际接受训练的士兵如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人员中,“粗通文字”体现为大多为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翁养正,2001:417)。除此之外,受训人员中也不乏从沦陷区挑选出来的苦工、农民以及小业主等(魏斐德,2004:287)。学员受教育程度如此低下,自然很难用普通话进行表达,更不容易听懂翻译人员转述的军事专业知识,由此也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无可厚非,沟通产生障碍,译员负有一定责任,但不应忽视的是,这也是多方面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因此便否定了译员们为此次合作做出的重大贡献。
除语言传译外,中美所译员也还担负了其他职责,如负责中美双方人员的日常联络、沟通与交流;高层翻译人员能部分起到居间调停作用。②如梅乐斯刚到重庆时,戴笠提出为他安排住处,但梅乐斯告知翻译刘镇芳不希望戴笠插手此事。刘立马否决,并主动决定由他来处理此事。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梅乐斯自行其是的话,则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戴笠的信任。刘镇芳也因颇能揣摩戴笠和梅乐斯双方意图、商谈问题时很少弄成僵局,颇受双方器重(沈醉,1979:66)。此外,大多数译员还随军队参与了敌后游击战争。美方人员归国后,戏称自己在中国的身份为“稻田海军”③相关著述有Linda Kush.The Rice Paddy Navy:U.S.Sailors Undercover in China.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12;Roy Olin Stratton.SACO-The Rice Paddy Navy.New York:C.S.Palmer Publishing Company,1950.,因为他们虽为海军,但服役作战的地点不在海上舰艇,而是在中国的稻田间。而那些跟随美方人员一同出生入死、共同抗日的翻译官,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稻田译者”。
5.结语
抗战胜利后,多数译员被解散。离职之时,他们分别获得中美双方颁发的离职证明书,后者极好地呈现了双方对译员的不同态度。美方高度认可译员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具体表述如下:“在你们结束美国驻中国军队翻译官之职责时,美国驻中国军队感谢你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如果没有你们,美国驻华军队的使命将受到严重阻碍。你们的辛勤工作帮助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加强了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希望你们将来继续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国家。”(Kwan&Kwan,2009:61)④此处中文为笔者翻译,原文是:On the termination of your duty as an Interpreting Offic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the Commanding General,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China decides to thank you for a splendid job well done.Without Interpreting Officers the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China would have been seriously hampered.The hard work done by the Interpreting officers has materially aided in accomplishing this mission,and has helped to cement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It is hoped that you will continue your good work in the future as in the past,and help to build China into the great nation it deserves to be.中国译员战时的杰出表现及付出的辛劳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为抗日战争和促进中美友谊所做的重要贡献受到称赞。而此证书由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亲自授意签发,更是彰显了美方对译员的重视。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方颁发的证书上仅标注了译员工作的起止年限等信息,如“查何士平于卅四年八月三日,奉派担任三级翻译官工作。至卅四年九月十三日,因抗战胜利,任务完成,合行发给离职证明书,以资证明”,丝毫不见任何正面的评价。更令人唏嘘的是,二战后,美国政府为表彰同盟各国对美国对日作战的支持,授予有突出功绩的人士以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82名享有此荣誉的中国人中,翻译官占了56名(梅祖彦,2004:62)。
[1]Kwan,Stanlney S.K.& Nicole Kwan.The Dragon and the Crown:Hong Kong Memoirs[M].Hongkong:Hongkong Univeristy Press,2009.
[2]鲍志鸿.抗战期间的中美特务合作[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4)·特工组织(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曹鸿藻.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琐忆[N].新华每日电讯,2010-10-29.
[4]邓又平.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J].美国研究,1988(3):26-39.
[5]何署.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J].书屋,2002(7):72-76;关于“中美合作所”的一个误解[N].北京日报· 理论周刊,2006-12-18.
[6]洪小夏.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7(3):59-87.
[7]胡铁城.重庆“中美合作所”记忆拾零[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磴口县委员会编.磴口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5.
[8]黄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38.
[9]江绍贞.戴笠和军统[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
[10]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11]李继星(主编).戴笠传[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
[12]林体明.我所知道的玉壶训练班[G].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精选集(2)(1924-1945).温州文史资料(第16辑),2002.
[13]刘毅祥、张少翼等.陕坝的中美合作所[G]//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辑).巴彦淖尔史料(第4辑).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地方志编修办公室,1984.
[14]绿原.胡风和我[J].新文学史料,1989(3):29-78.
[15]梅乐斯.神龙·飞虎·间谍战(又名《另一种战争》)(上册)[M].新生报,译.台北:新生报出版部,1981.
[16]梅祖彦.晚年随笔[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7]潘嘉钊、钟敏.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
[18]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上、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9]任中原.戴笠全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20]沈醉.沈醉回忆作品全集[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
[21]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M].北京:群众出版社,1979.
[22]王士忠.报告翻译官[J].西风,1945(80):147.
[23]魏斐德(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M].梁禾,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4]文闻.抗战胜利后受降与接收秘档[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25]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G].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杭州文史丛编(政治军事卷)(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
[26]吴淑凤等.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成立[G].台北:国史馆,2012a.
[27]吴淑凤等.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业务[G].台北:国史馆,2012b.
[28]张霈芝.戴笠与抗战[M].台北:国史馆,1999.
[29]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临汝训练班[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
[30]左平.抗战时期盟军的中国译员[J].社会科学研究,2013(1):16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