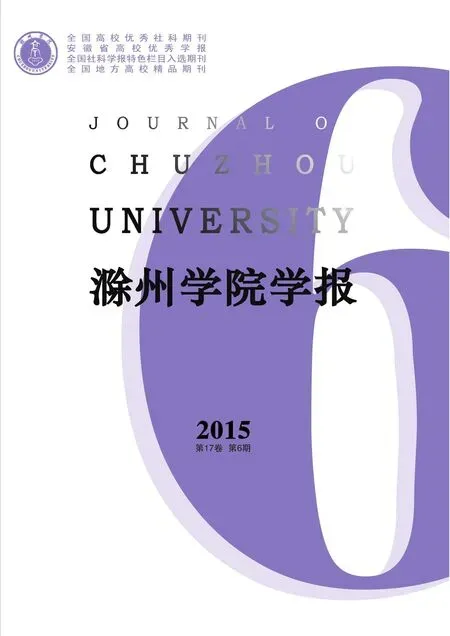旅行叙事下的“他者”群像——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远航》
夏侯勤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几经易稿,于1915年3月在英国首次发表。小说女主人公雷切尔·温雷克早年丧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与外界几乎隔绝,使她在二十四岁时仍然对社会、政治、两性关系等都一无所知。在舅母海伦·安布罗斯的帮助下,雷切尔登上了“欧佛洛绪涅”号,开启了从英国到南美州之旅。在与各色人等的交往过程中,她经历了一次次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在结识有志成为作家的英国男青年特伦斯·黑韦特后,他们坠入爱河并很快订婚。而成长起来的雷切尔却逐渐走上了一条与传统规范决裂的不归之路,最后在幸福唾手可得的时刻居然染上热病而英年早逝。学界对于《远航》的评论不多,一般都认为它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评论认为“《远航》描述了少女雷切尔·温雷克的成长过程,是部典型的成长小说”。[1]59本文旨在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解读《远航》所彰显出的菲勒斯文化或父权文化对女性、西方中心主义对殖民地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环境的非生态正义,揭示小说反映出的后殖民观和生态女性意识。
一、缄默“他者”的觉醒与颠覆:菲勒斯文化对女性的非生态正义
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底层人能说话吗?》中指出“臣属妇女处在父权制传统文化和父权制帝国文化的夹缝中,失去了言说的权力”。[2]135身处“臣属”地位的妇女受父权制传统文化的压迫而屈身于失声的“他者”。“后殖民生态批评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和自然界的压迫,呼吁关注妇女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聆听属下妇女真实的声音”。[3]25在菲勒斯文化的压制下,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权利还是两性关系,女性都依附于男性,无法真正获得话语权。这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她们的自省意识,以至于奋起反抗。《远航》女主人公雷切尔是个来自大英帝国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孩,作为帝国女性深受宗主国父权文化的压制,总是“被观看、被言说、被处置,处于‘他者’地位”。[1]61在登上“欧佛洛绪涅”号航行之初,二十四岁的雷切尔单纯善良,天真到只会弹钢琴。她的舅母海伦·安布罗斯认为这种惊人的天真无邪是她过去所受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雷切尔早年丧母,她的父亲威洛比只爱他的生意。雷切尔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过于狭窄的生存空间限制了她的全面发展,以至于在社交场合中她常常显得无知、刻板、不知所措。在旅行途中,雷切尔离开了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更多地了解了自己和同类,接触了不同的人与文明,直接暴露在“冰冷”的人生中。“现象世界的繁杂超出了她的理性认知能力,生存的帝国性、动物性让纯白的她无所适从,对自我的认知也因而不能完成……不仅是她自我认知的未完成,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她象征性地成为了自然和殖民历史的献祭品、统治逻辑的牺牲品”。[4]84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屈身为“房子里的天使”,被迫依附于男性世界,隐忍失声。雷切尔突破传统,追求自我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伍尔夫以雷切尔之死解构了传统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更是对菲勒斯文化之殇的无情鞭挞。
在《远航》中,伍尔夫以嘲讽的笔触展现出男性世界的统治欲望和男权观念,折射出在菲勒斯文化的压迫下,女性被迫屈身为缄默失声的“他者”。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由于男性在经济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妇女被迫成为男人的附属物,被制约在家庭的樊篱中,失去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以及其他诸多权利。女性不被男人当回事,她们都变成了“可怜的人儿,只能喂兔子。”①正是基于菲勒斯文化的压迫,女主人公雷切尔一直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她的恋人黑韦特深信男人对女人“拥有某种控制力,就像对马的控制力一样”(第237页)。也正是男权观念作祟,他认为“男人观念构成的世界多么奇妙…我们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第238页)《远航》折射出来的菲勒斯文化对女性的压迫还表现为男性对女性政治权利的蔑视与剥夺。临时上船的自命不凡的理查德·达洛维就是男权价值观念的坚定推崇者。他傲慢地说“在英格兰要是女人能投票,还不如让我先死了!我就是这个态度”(第40页)。在海上风暴来临之时,其对雷切尔的“强吻行为”更是暴露出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逻辑。
伍尔夫在《远航》中竭力塑造一位意欲寻求自我,逃脱男权观念樊篱的女性个体,旨在完成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解构。雷切尔因教育缺失,认知能力受限,很多情况下她只能寄情于钢琴,以此作为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最佳途径。在与特伦斯订婚后,当被问及对于恋人特伦斯作品的意见,她沉默不语,而是专注于弹琴。当被问及对罗马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看法时,雷切尔遭到了大男子主义者赫斯特的无情讥讽。盛怒之下的雷切尔以钢琴为武器,为自我辩护。至此,“弹琴”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寓意。钢琴此时已幻化为女主人公宣泄情感,表达自我内心声音的工具,演变为自我救赎的工具,体现出雷切尔意欲摆脱男权压制的女性意识的极度膨胀。通过“弹钢琴”这一非语言方式,雷切尔向父权文化体制发出质疑与挑战,试图以此消解父权制话语霸权,彰显其文化性存在,实现自我救赎,颠覆男权压制下的女性受压迫的被动性质,击碎以“家中天使”为核心的男性乌托邦。至此作品为读者生动呈现出菲勒斯文化语境下被称为异己的沉默“他者”迈向主动发声的“他者”的嬗变历程。
二、帝国霸权统治逻辑下的殖民主题:西方中心主义对殖民地的非生态正义
殖民主题体现了伍尔夫对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美学视角的使用和展现。通过这一视角可管窥西方中心主义对殖民地的非生态正义。“18世纪的理性主义确立了理性与感性、文明与野蛮、人与动物之间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主宰地位,成为殖民扩张和征服的理论基础”。[5]27西方殖民者将自身定义为“理性”与“文明”,在他们眼中殖民地世界就是“荒野”与“野蛮”。他们从自身视角看待西方以外的世界,认为西方世界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远航》中,特伦斯、伊夫林和珀罗特“把自己想象成为殖民世界的伟大船长”(第302页)。理查德发出了“一个人要不是英国人可怎么活得下去”(第51页)的感慨。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英国人似乎,从总体上说,比多数人更明白事理,他们的历史更干净”(第68页)。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压制殖民地世界的价值观。非西方的第三世界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演化为非西方的“他者”。“由于帝国主义在知识、社会和学科中深嵌的暴力,这个欧洲的主体试图生产一个能巩固一种内在的东西,即通过把殖民地限定为他者并为其编码,欧洲自我的构造便凌驾于这多种自我表现模式之上,这些模式在帝国主义征服者的文化中被重新组装起来,并以被置换的形式在西方准则和价值与普遍的思维形式相并存的一种文化霸权中持续下来,第一世界的知识主体的任务是拒斥和批判经过‘同化’的第三世界”。[3]29
身处“他者”地位的殖民地遭受殖民者在意识形态、经济活动等多重领域的剥削。《远航》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了英国曾经染指但并未全然统治的南美洲。小说呈现的殖民地贸易活动体现出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的占有与剥削。雷切尔的父亲威洛比一直从事从美洲贩运山羊到英国牟取暴利。他告诫雷切尔说“要是没有山羊,也就没有音乐……音乐要靠山羊”(第16页)。殖民贸易的不公平性可见一斑,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劫掠。英国殖民者凭着“钢筋般的肌肉,贪婪的毒牙和渴望黄金的利爪”(第97页)在殖民地“搜罗女人,生养孩子”(第97页),活脱脱地表现出殖民者的帝国意识。殖民地人民被他们视为草芥,成了他们的手中玩物。殖民者从殖民地敲骨吸髓般疯狂掠夺资源,他们从殖民地“带走了大批银块、亚麻、香柏木材”(第97页),加剧了广大殖民地经济的持续落后。而他们自己却“被这神奇土地上的水果撑得肥头大耳”(第97页)。小说呈现的殖民地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诠释出帝国主义扩张的原始动力就是对殖民地经济的占有与剥削。殖民帝国的崛起与殖民掠夺密不可分,殖民掠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西方殖民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他们在广大殖民地大肆疯狂掠夺,促成宗主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美国学者布劳特甚至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大发现后对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的残酷殖民掠夺与盘剥,是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和美洲地的贵金属及种植园造就了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6]20正是凭借广大殖民地出产丰盛的“水果”,殖民者才变得“肥头大耳”。“在殖民时期,宗主国的经济依赖于海外的领土控制,经济剥削和社会文化的观念。没有这些,家园的稳定与繁荣是不可能的”。[7]78
《远航》借助旅行叙事模式讲述了女主人公雷切尔随舅母海伦·安布罗斯从伦敦出发航行至南美洲直至病逝的经历。“欧佛洛绪涅”号满载猎奇观光的英国游客,他们将去南美旅行视为一种“时尚”。旅行所带来的异国情调及剥削式的行为给当地造成了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巨大负面冲击。英国游客眼中的南美洲“时尚”之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他们以资本主义价值观,审视当地的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远航》中提到在旅行过程中,古老的庙宇很快变成了宾馆;一些著名的汽船为了便利旅行者而改变了航向。从“庙宇”到“宾馆”的蜕变凸显出西方殖民者对当地人文景观传承的漠视,更是殖民者在殖民地为所欲为的殖民霸权的最好注脚。享乐主义作祟下的西方游客在殖民地旅行目的地大行其道,不厌其烦大兴土木,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世界“需要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一个临时避难所或精神藉慰地。至于他者是否需要、是否愿意被维持不变 (如更舒适的生活标准和发达的设施等)这样的问题,则已降至次要地位,暴露出霸权与支配的面目”。[8]201因此《远航》的旅行主题也氤氲着西方中心主义对殖民地的非生态正义,对于揭示当下生态旅游的生态帝国主义性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生存困境下的伦理责任: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环境的非生态正义
小说也刻画了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环境的非生态正义。赫斯特说“这些树扰乱了人的神经—它们都是那么疯狂。上帝无疑也疯了。健全的人会如何看待这荒凉之地,这只有无尾猿和短尾鳄的地方?如果我住在这里,我准会发疯—妄想狂”(第313页)。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将自然与动物视作为外在于人类需要的“他者”。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话题。它们之间的矛盾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发展日益凸显并迅速激化。在人与自然环境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人类将自身定义为理性,自然界被看成是与人完全对立的存在物。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赋予了自身与上帝相同的含义,把自己想象成为能动的造物主与征服者。自然环境演变成为可以随意征服和利用的对象。随着人类控制欲望的极度膨胀,理性膨胀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进而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美国20世纪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人类既要维护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也必须承担起保护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动物和其他生物的个体义务”。[9]7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人对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说人对自然有义务,那么这种义务被视为只是对人的义务的间接表达。这样,人类中心主义就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10]15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西方殖民者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人就是宇宙中心,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自然及其它存在物都是工具,人可以随意处置对待。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生态的操控者,将自然景观与生物殖民化。至此,西方殖民者的帝国霸权统治逻辑表露无遗。以美国哲学家保罗·W·泰勒为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人类和其他物种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每一种生物的生存和福利的损益不仅决定于其环境的物理条件,而且决定于它与其他生物的关系;所有的机体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因此每一种生物都是以其自己的方式追寻其自身的好的惟一个体;人类并非天生就优于其他生物”。[11]35泰勒通过反对人类优等论,他认为生物都是平等的,所有生物都拥有同等的固有价值,都应当受到同等的道德关怀。“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征服与压迫与殖民者对于殖民地非人物种的清除与毁灭两者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5]26依据这样的价值观念,人类陶醉于征服自然的成就,却逃避了对其活动负效应的自责和所应承担的责任,忽视了人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透过这一视角,《远航》在一定程度上呼吁人类履行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
[注 释]
① 本文所引用的小说中文译文全部引自黄宜思译本《远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文中其它引自该小说的译文参照这一版本,将不再单独注明出处,仅标出页码。
[1]段艳丽.《远航》:建构自我之旅[J].世界文学评论,2007(1):59-62.
[2]祁亚平.双重“他者”的压迫与颠覆——《舞动卢纳萨节》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2(3):134-142.
[3]唐晓忠.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生态批评解析[J].当代外国文学,2012(3):25-32.
[4]吕洪灵.双重的统治逻辑《远航》中的自然与殖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2):81-84.
[5]朱新福,张慧荣.后殖民生态批评述略[J].当代外国文学,2011(4):24-30.
[6]韦宗友.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J].国际展望,2013(6):13-26.
[7]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左晓斯.乡村旅游批判---基于社会学的视角[J].广东社会科学,2013(3):196-205.
[9]李巧慧.环境·动物·女性·殖民地---欧美生态文学的他者形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0]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11]徐春.以人为本与人类中心主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33-38.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