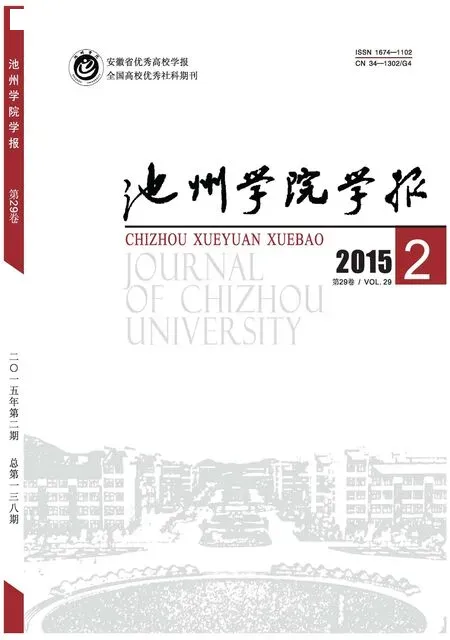时代特征下催生的中国近代教育——以铜陵近代教育为论述对象
王 娟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铜陵在明清时期,儒学教育达到巅峰。明朝时,即“在县治东设铜陵县学”[1],这是铜陵官学的典型代表。私学则分为书院、私塾、义学、社学等。近代以前,铜陵官学和私学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儒学为主。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半殖民地化程度两加深,封建传统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已担负不起拯救国家的重担,新式教育的开启是必然的。本文以近代铜陵教育为对象,论述其变化与发展,期以窥探时代特征催生的中国近代教育。
1 近代铜陵教育的基本概况
铜陵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属长江之滨,同时它拥有丰富的铜矿石,占据着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铜陵大通作为“寄航港”对外开放,从而开始了铜陵近代化的历程”[2],但铜陵教育的近代化并没有开始。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施行“癸卯学制”,正式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1904年,明伦学堂附设的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标志着铜陵近代化教育随之启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三十余年间,是近代铜陵教育发展的主要时期,其基本概论如下:
1.1 学校状况和存在的相关问题
清末“新政”时期的学堂教育:清末“新政”,文化教育改革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颁布新学制,逐步从为科举服务的教育迈向学堂模式的新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铜陵先后设立三所小学堂,另和悦洲(原名“荷叶洲”,属于大通镇)设立一所半日制私立小学。这4所小学都是施行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分为初等小学堂,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制。初等小学堂设有经学、中国文学、算数、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课程。而高等小学堂增加了图画课,同时将“历史”改为“中国历史”。宣统元年(1909年),明伦堂附设的高等小学堂改为官立两等小学,经费收支两抵,而其余三所则是入不敷出,“其余三所学堂经费岁入2395元,岁出4307元,蚀1912元”[3]2。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铜陵当时作为一个县级单位,在教育上得到了较大的革新,西方的科学教育被正式纳入教学内容当中,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忠于朝廷且懂得西学的候补官员,指导思想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当时铜陵的学堂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一,学堂数量较少,清政府重视不够。整个铜陵县,只有四所小学堂。其中,只有一所官立小学堂,即1904年成立的县立高等小学堂,其他三所,两所是绅士设立,一所私人性质的。其二,教学内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陈旧的内容,“中国传统修身、读经之类课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份量颇重”[4]53。其三,教育经费不足。三所学堂只有一所是收支两抵,其它三所则是负债状态;且从其经费来源看,教育经费多是盐捐、捐助义款等,“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县立高等小学以书院田租积兴存款及盐肉串票为常年经费”[5]500,政府并没有拨发专门的教育经费。
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颁布壬子学制,癸卯学制废止,学堂改称学校,初小改为四年,高小改为三年。同年,铜陵就在城内积谷仓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民国十二年(1923年)进而施行壬戌学制(民国十一年公布),初小改为四年制,高小改为二年制。在这两个学制的指导下,铜陵出现了兴办近代教育的高潮。“据民国18年(1929年)安徽省教育厅统计,铜陵县共有各级小学44所”[3]3,44所学校中有2所女子学校,1所少数民族学校——回部私立穆德初级小学。其中38所学校教职员148人;学生人数有1610名;年经费18020元。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据《安徽省概况统计》记载,铜陵县的小学(初小、高小)共有38所,其中初级小学28所,高级小学10所,教员113人,学生有1990名。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九年(1920年),铜陵县在县立女子小学设立幼稚班,这便是铜陵幼儿教育的开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很大程度的摧毁。“民国27年(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县境后,全县大多数小学被迫停办,仅存私立完小(初、高级)1所,短期小学10所”[3]3。其后,大通、城关等乡镇的小学虽相继恢复,但失学儿童仍占大多数。
和清末“新政”时期相比,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铜陵的近代教育确实是得到进一步发展。从上文可看出,这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日本侵占县境前)的教育从学校数量、教员人数、学生人数到教学经费,都有很大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铜陵的幼儿教育发展较早。“幼稚园分为县立、区立、私立三种形式”[5]481。但民国时期,铜陵的教育仍有很多困难和不足,尤其是受战争影响大。如军阀倪嗣冲独霸安徽时,拿教育经费充当军费,“为了军事理由也不惜牺牲教育”[4]538。因此,“民国时期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产租息、捐税附加”[5]500。其次是日本侵华以后,学校数量锐减,“抗战期间,全县中小学几乎被迫相继停办”[3]3。
乡村民众教育:民众学校前身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设的民众问字处,据铜陵文史资料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县民众委员会开办,时有2所,后增至10所。民国三十年(1941年),小学设民教部。翌年,全县4所中心小学和30所保国民小学(以保甲制度为基础,乡设的中心国民学校)共设有民教部班级42个,学员2520人。在乡村推行的民众教育“就公民现有之程度与实际生活施以文字、公民、生计、健康、家事、艺术(娱乐)等六项内容,以消除文盲、训练运用四权,养成健全农民,增加生产,增进健康,改良家庭,提倡正当娱乐”[6]。由此可见,民众教育为铜陵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不少的指引和乐趣。
1.2 学生状况
从清末“新政”到抗战前期,铜陵的近代教育经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受教人数明显增多。例如,清末“新政”时期,铜陵县三所学堂(不包括和悦洲的半日制私立学堂),学员只有98名。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时38所学校已有学员1990名。当然,在这一时期,铜陵的近代教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学生数男多女少、学生受教内容仍大量保留传统儒家教育内容、旧的私塾教育没有被打破等问题。
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和儒家理学的影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女子的受教权利往往被忽略。民国十八年(1929年)安徽省教育厅统计的数据中44所学校虽有2所女子学校,但女生入学数量极少。如民国元年(1912年)创办的县城第一所女子小学,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只有女学生70名。44所学校中38所学校男女学生共有1610名,而女生有409名,不到1/4。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铜陵县初、高级学校共38所,“初级小学有学生970名(其中女生270名);高级小学有学生1020名(其中女生220名)”[3]2。女子的低入学率,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入学总人数,降低了整个铜陵县的教育水平。
关于学生受教内容,铜陵的近代教育虽有发展,但传统的儒家教育仍根深蒂固。首先,学堂教育仍开设修身、读经讲经这些课程,且课时量不少。更有甚者,清末和民国年间铜陵县的学堂和学校教育兴起,但私塾仍然大量存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全县尚有私塾53所,就读学生2076人,塾师143人[3]4。私塾仍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授教内容,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接受新思想、新生活方面明显不如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
1.3 教师状况
教育乃兴国安邦的大事,教育的三要素(学校、教师、学生)中,教师在传播思想文化、培养人才的环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代铜陵的师资力量与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征有关。清末民初是铜陵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教师多为私塾老师。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与此同时,教师队伍无论在数量和素质上,还是在待遇上都有较大的提高。
安徽省自办幼儿教育始便面临着专业的幼儿教师奇缺的问题,大多数的幼儿教师由塾师或是小学教师代替。“1931年,全省的幼稚园教师只有63人”[7]32,其中铜陵有4人,这在全省范围内对比来看,铜陵的幼儿教师数量尚属足够。1931年,铜陵县的小学教师共有111人,专科以上学历有87人,其中专业类师范院校毕业生有33人,约占30%[7]38。1943年,全县小学教师有106人,专科以上学历有37人,其中师范类学校毕业生有27人,约占25%[5]486。两年对比,再次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时期铜陵教育的发展受到影响。清末民初,“高等小学堂教员年奉平均为180千文”[5]499。1934年,铜陵县的小学教员的工资大多集中在5元到20元不等。
2 近代铜陵教育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
2.1 教育难以发展
从清末“新政”到抗日战争时期,近代中国的教育是显著的,这无论从教育体制还是教学规模都是能看出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教育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息息相关的。近代铜陵教育虽有发展,但它的发展仍是缓慢的,经济落后,社会战乱,致使教育难以发展。
经济的落后对教育的主要影响就是教育经费的不足。根据铜陵市的文史资料记载,1904年成立的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书院田租。1906年在大通余氏祠堂成立的公立两等小学堂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盐捐和义款。教育经费没有专门款项,有时依靠义款。学校经费困难,儿童书物、体育用具非常缺乏,教师待遇过低,校舍极其简陋。民国十八年的38所学校“常年经费18020元(其中县立第一经费为2520元)”[3]12,而学生共有1610名,平摊下来少之甚少。经济的落后,对教育的直接影响就是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从民国时代的教育部门调查报告中,我们可看出,经费不足、教育设备不齐全、校舍狭小简陋、师资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教育是反映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像,教育发展迟缓的背后隐藏的正是当时经济发展的落后。
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16年间,先后有倪嗣冲、张文生、马联甲、王普等军阀先后驻扎在安徽主事,尤以倪嗣冲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军阀倪嗣冲独霸安徽时,他曾“力主停办全国学校”[4]538。1916年5月,“倪嗣冲通令各县停办学务”[8],将教育经费用作军费,甚至私吞。“根据民国7年的一项统计,各种中学共12所,学生仅1607人,无论学校或学生人数,均不及清末半数”[9]31。另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动乱,学校因战争时常停办,“马路第一完全小学,屡被驻军,兵师驻通时,颇受损失”[10]。尽管这样,铜陵的近代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日军侵占铜陵后教育对事业的破坏。一方面,日军摧毁铜陵原有的教育,或是因动乱,学校停办。另一方面,日本占领铜陵后便开始推行奴化教育,试图培养亲日汉奸,摧毁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日本占领铜陵县以后,全县仅存一所私立小学(初、高级),临时性的短期小学也只有10所。1938年11月,日伪政权建立后,大通、顺安等乡镇的小学虽相继恢复,但入学人数却相对减少很多,众多学龄儿童没有入学,“民国29年(1940年),全县共有学龄儿童1.51万人,入学者仅3480人,失学者1.16万人,占76.82%”[5]3。又如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统计,铜陵县共有20个乡镇,合287个保,乡镇中心国民小学只有4所,也就是说,5个乡镇才有一所小学,教育总经费仅8640元。在此期间,众多学校被毁,如明伦堂小学,“城关在日军铁蹄下百业凋敝······明伦堂小学随之名存实亡”[3]8。广储学堂“抗战期间,虽有主持人,但名存实亡”[3]12。
2.2 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策略
近代中国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风雨飘摇的时代,外有众多列强欺凌,国际地位低下,内有顽固的封建腐朽统治和专制残酷的军阀统治,社会动乱,人民苦不堪言。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强烈地激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政治界兴起各种救国运动,商界则倡导“实业救国”,教育界则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现状,倡行爱国主义教育。铜陵县在教育近代化历程中也体现了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特征,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新式人才。
在清末新政时期,铜陵县设立的高等初级学堂,将历史改为“中国历史”这一课程,为的是让同学们牢记历史,增强民族认同感,意识到民族危机感。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也在冲击着铜陵,有识之士陈春圃“认为欲要民主救国,只有兴办新文化教育,以唤起国人的觉醒,才是有效的途径”[3]9。1919年中秋,陈春圃先生在九榔庙开办了“铜陵县九榔高级育才小学校”。这所学校完全是陈先生个人办学,其办学思想强调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民主救国、民族解放培养人才。陈先生办学得力,入学者免费,培养一批人才,有参加革命的、考取大学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培棠先生四处奔走才得以创办铜陵临时中学,也是铜陵县历史上第一所中学,该校的教学宗旨是“培养学生成为抗日人才”[3]16,带领全校学生动员全民抗战,为铜陵县的抗日作出巨大贡献。坐落于铜陵狮子山的皖江第二联立中学,当时不仅开设常规的语文、数学课程,还开设了政治时事常识和中国革命运动史两门课程。
2.3 教育发展不平衡
大通镇作为著名的港口,它发挥着铜陵县对外交流的主要的作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中规定大通为“寄航港”,标志着大通近代化的起航。大通作为“寄航港”的开通,给大通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轮船、教会、邮局等都是由大通进入铜陵,它是铜陵近代化发展的前沿。首先,近代经济的发展,外资经济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起来。其次则是社会观念的转变,西方人带着西方文化闯入后,人们对于外来文化从陌生、仇视到潜移默化地接受,大通的近代化走在铜陵其他地区的前面。正因为此,大通的教育发展也比县内其它地区要快。
清末“新政”时期,铜陵县共创办四所学堂,其中有三所是在大通,即“(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公立两等(初小、高小)小学先后在大通镇佘氏祠堂、和悦洲同仁局设立”,另外和悦洲设立一所半日制小学,属私人制。另有创办于清朝光绪末期的“广储学堂”,校址在和悦洲,是为六年制小学。这所小学虽历经沧桑,但它代表了大通近代教育的高水平,学校最兴时达到300多人,“是铜陵县最知名的学府”[3]10。另外,当时整个铜陵县只有两所女子小学,其中一所便是在大通和悦洲建立的“大通女子小学”,该小学建于1920年左右,教师皆为女性,学生最多时有200余人,并设幼稚园。女子小学的建立无疑是它的兴办教育独到之处,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提高了女子的社会地位。同时,随着大通“开埠”,西方文化不断冲击本土文化,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时便创办教会学校,如民国二十年(1931年),圣公会基督教徒在县内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即在和悦洲,后又有“大通福音堂小学”。教会学校的授课内容不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反而更多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文化,适应了时代要求。根据1929年铜陵县教育局五月份的工作报告所记载,当时城乡各地学校已是经费不足,无以为继,而作为“寄航港”的大通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镇立小学,办理颇见精神……屡破外界攻击,尚能毅力维持”[9]30。
大通教育的优先发展,反映出了近代铜陵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其背后原因的分析,笔者发现,大通在被动开放的前提下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近代铜陵教育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大通教育的优先发展和其他地区的滞后,早在1904年之前大通的教育近代发展便已是铜陵的先锋,“堪称铜陵县的教育中心”[3]12,且在多次的教育改革中都积极办学。反观铜陵其他地区,如顺安、董店、城关等地,虽办学却在质量和数量上远不如大通。在清末新政时期,这些地区并未办新式学堂,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县境内迎来办学高潮,但日本侵华后,学校大多被毁且无力恢复之前。正是因为这种不均衡性更加拉开了大通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与铜陵其它地区的差距,同时也影响了近代铜陵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3 结语
近代铜陵教育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在时代特征的催生下产生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近代化教育。因此,近代铜陵教育的发展是带有时代特征的,与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差异。但现实是历史的延续,铜陵近代教育的发展为其现代教育发展打下根基,其不足和优点成为后世的经验教训。近代铜陵的教育发展抓住时代契机,适应了近代人才培养的需求。当今中国之教育,人才培养成为教育的重要任务,如何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和符合时代特征的人才是解决中国发展中问题的重要环节,近代铜陵教育的发展虽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缩影,但确为当今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启发。
[1]陈贤忠,程艺.安徽教育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22.
[2]姚雪梅.皖江城市铜陵的近代[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2.
[3]政协铜陵县委员会.铜陵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G].内部印制,2002:1-30.
[4]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530-540.
[5]安徽省铜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陵县志[M].合肥:黄山出版社,1993:481-500.
[6]高阳.乡村建设方案[M]//田晓明.高阳教育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54.
[7]刘强.1927-1931年安徽省教师群体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1.
[8]翁飞.安徽近代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416.
[9]铜陵县教育局.铜陵县教育局五月份工作报告[J].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29(22):30-32.
[10]皖省教育之新调查[J].环球,1917,2(1):180.
——上汽大通D90……虞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