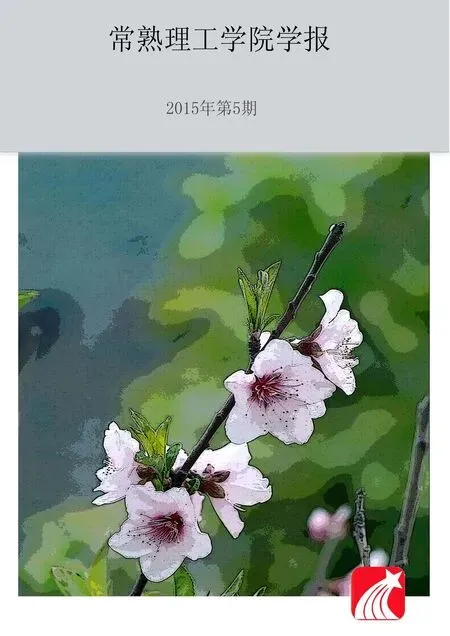三种马克思与共产主义
——浅论巴迪欧《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46)
2012年,德国哲学家,著名的帕萨根·弗拉格(Passagen Verlag)出版社的总编彼得·恩格尔曼(Pe⁃ter Engelmann)在德国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关于马克思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对话,这次对话最后以《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Philosophie und die Idee des Kommu⁃nismus)①这本书的原初版本为德文版,2015年,此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才相继出版。为名在恩格尔曼自己的出版社里出版了。实际上,恩格尔曼是一位黑格尔研究的专家,也是著名的出版商,他翻译出版了德里达、勒维纳斯、鲍德里亚、朗西埃、维希留、齐泽克等人的大量著作,巴迪欧谈阿拉伯之春的著作《历史的重生》德文版也是在他手中出版的。恩格尔曼和巴迪欧的对话发生在2012年的3月23-24日,共持续了两天,两人讨论的话题极广,从阿拉伯之春、古希腊金融危机到今天的中国,从纳粹德国到斯大林模式,从当下的政治事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假设,从数学革命到美学的变革……当然,在全书中,实际上贯穿着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马克思,也涉及后来的苏联和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萨特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和发展;另一个是共产主义,尤其是关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假设或观念在今天的世界政治和革命运动中是否还具有价值,这种共产主义假设或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具有关系等,都是这本小册子中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一
熟悉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作品的读者,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尽管巴迪欧以左派自居,尤其被世界左翼运动和政治视为当代激进政治思想的旗帜性人物,但是,1982年撰写完《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之后的巴迪欧很少直接去涉及马克思,更少直接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评价。我们如果对巴迪欧的思想进行分期的话,1982年的《主体理论》和1985年的《我们能思考政治吗?》(Peut-on penser la politique?)绝对是巴迪欧的整个思想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巴迪欧是一个典型的阿尔都塞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受到了毛主义的影响,巴迪欧仍然对马克思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这种评价是经过他的恩师阿尔都塞折射的。在他最早期的著作中,他会提及并引述马克思的原话,如他的第一篇作品《辩证唯物主义的(再)开始》,以及在七十年代出版的《矛盾理论》(Théorie de la contradiction)和《论意识形态》(De l’idéologie),即便在《主体理论》和《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中,也经常谈到马克思。而在1988年出版了他最主要的著作《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②准确来说,《存在与事件》并不是没有谈到马克思,马克思仅仅只是在沉思9的时候被提到,而沉思9主要讨论的是恩格斯的国家论,恩格斯的国家论被巴迪欧拿来与他对情势状态(état de la situation)的分析作对比。之后,他对马克思的思想的讨论实际上很少,几乎到了避而不谈的地步。相对于马克思,巴迪欧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更愿意谈的是巴黎公社③巴迪欧对巴黎公社的讨论肯定会涉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不过在巴迪欧专门讨论巴黎公社的著作《共产主义假设》(L’Hypothèse communiste)中,也很少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他所引述的材料更多的是丽莎佳蕾(Lissagaray)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而且巴迪欧对恩格斯后来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撰写的序言持批评态度。、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及他的革命战友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 Lararus)的政治实践。因此,在2013年出版,并于2015年翻译为英文和法文的《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一书中,巴迪欧直接对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分类的评价就显得格外特别。
《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一书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巴迪欧对马克思著作的关注。尽管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之后,提及马克思的相对较少,而且巴迪欧对马克思著作的关心,主要集中在被巴迪欧命名的马克思的“政治”作品上,如《共产党宣言》《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等,他并不像一些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会谈及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而这本小书,似乎是巴迪欧在八十年代转向之后,比较系统地集中面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最经典的领域,而此前,他对这些著作都是避而不谈的。
现在的问题是,巴迪欧不愿多谈马克思或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像一些巴迪欧思想的诠释者,如阿尔贝托·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和布鲁诺·波斯蒂尔斯(Bruno Bosteels)所解释那样,巴迪欧已经在这个阶段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后康托尔集合论-拉康精神分析结合下的事件哲学——彻底取代和超越了马克思的哲学和思想,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已经被巴迪欧所超越和扬弃,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已经在巴迪欧那里不名一文了?在读完《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这本小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解读完全是对巴迪欧的思想的误读,最重要的是,正如巴迪欧所说,马克思一直是他整个哲学思考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他一直用他的著作在向马克思这位大师致敬,尽管他并没有太多地谈及马克思及其文本。
不过,关于巴迪欧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我们绝对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他是支持马克思还是反对马克思的问题。对于当代的西方左翼学者来说,这样的问题都不会有十分简单的答案。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的是,巴迪欧对马克思的阅读和理解经验是从何而来的?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现成的答案——阿尔都塞。但实质上,正如巴迪欧自己回忆所说,在成为一个阿尔都塞主义者之前,他是一个萨特的信徒;而在萨特之前,对巴迪欧影响更大的是巴黎高师的老校长伊波利特。我们知道,科耶夫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讲座和伊波利特翻译的法文版《精神现象学》(尽管这个译本遭到很多诟病)①在巴迪欧的《小万神殿》中,巴迪欧著作的德文译者于尔根·弗兰克尔对巴迪欧说过,伊波利特译的《精神现象学》的法文译本完全是“伊波利特自己的书”,而巴迪欧的评价是:“当我年轻的时候,传闻说伊波利特的德语非常差劲,他的翻译是一种哲学工作,即在这种工作中,语言是为译者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翻译背后的动力。有人说,这个早上,伊波利特构建了一个法国的黑格尔……幸好后来于尔根·布兰克尔跟我讲了许多,他告诉我正确理解那本书的方式,主要是仅仅用法文来理解黑格尔。”参看阿兰·巴迪欧《小万神殿》,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是二战以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诞生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科耶夫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主奴辩证法逻辑,而伊波利特则进一步将这个逻辑存在主义化,即让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时代,必然充满着苦难。因此,对于伊波利特,以及受到科耶夫主奴辩证法讲座影响的一代人——如萨特、米歇尔·亨利、梅洛-庞蒂等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去思考一个主体,去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去解放这个世界。因此,萨特十分关注主体问题,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主体,是一个背负着这个世界责任和苦难的主体,而不是康德式的那种信守绝对道德律令的主体②这个主体一般被视为大写主体,一个给人类本身的行为立法的主体。实际上,巴迪欧曾表述过,他非常厌恶康德,尤其是伦理和实践理性中的康德,在巴迪欧的后期代表著《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中,他曾说道:“康德是另一个我完全无法亲近的人。他的一切我都会感到恶心,尤其是他的律令论。”Alain Badiou,Logiques des Mondes,Paris:Seuil,2006,p.561.。显然,让巴迪欧信服的也是萨特自己的主体学说,尤其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提及的那个主体学说。巴迪欧说:“基本上,萨特试图维护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一个历史主体,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大众主体。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似乎发展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形式逻辑,这个逻辑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更加清晰。”[1]31这样的萨特,会让巴迪欧对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不那么排斥,这是他与最坚定的阿尔都塞派别之间的分歧所在。阿尔都塞坚持了存在着一个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的观点,而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作品,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视为残留有黑格尔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痕迹的不成熟作品,因此,阿尔都塞的内部圈子,乃至法国共产党内部,都禁止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青年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相反,巴迪欧并不认为以一个非科学的标记,就可以轻易打发掉那个青年马克思与后来的马克思的关联,其中的主体理论的线索,被巴迪欧认为是马克思青年到成熟时期思想发展的一根主要的线索,而在阿尔都塞的解读中,这完全被湮没掉了。
这样,我们可以再来看看阿尔都塞阶段的巴迪欧所受到的训练。早期的巴迪欧十分信奉阿尔都塞的科学与哲学之分,而阿尔都塞的科学与哲学的区分标准,也被巴迪欧坚持了下来。在1967-1968年期间,巴迪欧协助阿尔都塞为科学家们开设哲学课,并在课堂上为科学家们讲了一个学期的课程。他的讲课笔记后来被整理出来,以《模式的概念》(Le Concept de modèle)为名出版,并获得了阿尔都塞的好评。阿尔都塞强调阅读的文本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尤其是《资本论》,巴迪欧尽管没有赶上阿尔都塞主持的“读《资本论》”小组的活动,但是,他仍然向阿尔都塞提交了一篇谈阅读《资本论》感受的文章,这篇文章,据巴迪欧自己所讲,已经散佚,不过他将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概括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辩证唯物主义的(再)开始》之中①对于巴迪欧和《资本论》,以及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小组的关系的详细内容,可以参看我的《巴迪欧版“读资本论”》,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不过,在这篇文章中,巴迪欧提出的是在《资本论》中寻找一种让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科学的科学基础。实际上,巴迪欧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更大的价值,即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理性形式”,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好是在这个“新的理性形式”基础上,发现了作为社会形态发展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属于科学,而辩证唯物主义是所有科学的科学性的根基,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只是一种科学,即社会形态发展的科学,它的科学性,在巴迪欧看来,也必须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巴迪欧比阿尔都塞走得更极端,他宣称:“事实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达,即对作为客观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的因果关系类型的理论,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而阿尔都塞讨论统治结构,讨论《资本论》对象的基本文本,也不可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2]152很明显,在巴迪欧的逻辑框架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提供了马克思的决定性的模式,并让马克思真正与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断裂。
尽管在《存在与事件》之后的巴迪欧再没有涉及过更具体的对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的讨论,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一些著作中以只言片语的形式,零星地引述着马克思。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做出判断,巴迪欧在这个时期已经抛弃了马克思的基本框架,而创立了以数学集合论和拉康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新的哲学体系。这种说法显然有点操之过急。很明显,巴迪欧和恩格尔曼的《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一书从正面解释了巴迪欧对马克思的态度,正如巴迪欧所强调的那样,他没有抛弃马克思,而且一直在坚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观念和假设。倘若如此,我们应当从什么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巴迪欧对马克思的坚持?我们是只有一种马克思,还是多个马克思?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解读巴迪欧为什么要谈三个马克思。
二
巴迪欧在《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一书中,最为精彩的对马克思的探讨,源于他认为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马克思。在巴迪欧看来,之所以有人误解他“超越”了马克思或抛弃了马克思,原因正是在于,这些评价者是拿他们心中自己的马克思来对比巴迪欧的哲学中对马克思理解。显然,在巴迪欧的绝大多数内容中,我们几乎不会看到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也几乎看不到他会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同马克思,正如巴迪欧的研究者尼克·休利特(Nick Hewlett)指出,巴迪欧很明显地带有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轻视,“马克思对巴迪欧著作的主要影响在于他不断地将哲学与物质世界直接关联起来,但很奇怪的是,政治经济学在巴迪欧物的图示中毫无地位。看起来似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哲学的上层建筑没有丝毫影响”。[3]33而这两个领域常常被我们直接视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最重要的两个武器。与之相反,巴迪欧更珍视的是他自己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②必须指出的是,巴迪欧所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这既不是正统的列宁-斯大林体系的解释,也不是卢卡奇、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巴迪欧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作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奠基的基础理论,也就是说,巴迪欧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或者具有科学性的力量,恰恰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利特继续说道:马克思真正影响巴迪欧的是他的解放政治学。
在这个基础上,在《元政治学概述》(Abrégé de métapolitique)中,巴迪欧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曾存在”[4]67。巴迪欧之所以这样说,正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根本不能视为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这个并不是后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或者哲学家、思想家对马克思有着不同的阐述,而是马克思自己的文本就表现出一种断裂性的症候,一种不能用一以贯之的逻辑将他的所有文本全部贯穿起来的碎裂性状态。因此,为了理解马克思,我们不能采用单一的符号来简化马克思的思想和文本。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是单数的(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出多个马克思;至少,在这里,巴迪欧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马克思。
在对三种马克思进行详细阐释之前,还必须强调一点,巴迪欧的三种马克思的划分,其实并不同于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区分。阿尔都塞坚持的是两个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在《保卫马克思》中,“这种‘认识论的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式‘意识形态’的阶段,1845 年断裂后的‘科学’阶段”[5]14。可以说,阿尔都塞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马克思文本中存在异质性断裂的因素,这些因素并不能用简单的单一线索来贯穿马克思的文本始终;但是阿尔都塞采用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将马克思的1845年之后的作品绝对凌驾于之前的作品之上,也就是说,以成熟的马克思绝对地排斥青年马克思。他之所以排斥的理由也十分简单,之前的青年马克思尚处在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与后来的“科学”的马克思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因此,他以科学的名义,绝对地将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划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之外。阿尔都塞的这个做法自然引起了诸多争议,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这种做法是将蕴含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的断裂问题,简单地还原为一个历史分期问题,即这种思想和文本上的不连贯性,恰恰是1845年马克思的“顿悟”事件造成的。这种绝对的划分,让我们无法真正面对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和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作品中本身的不连贯性问题。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否只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的逻辑?或者说《手稿》就是一个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下诞生的不成熟的文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被阿尔都塞誉为成熟马克思的代表性作品的《资本论》是否就是一个真正符合科学连贯一致性标准的作品呢?估计阿尔都塞自己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就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小组中,围绕着文本的阅读,就发现了马克思的文本中的诸多症候。例如,朗西埃后来对阿尔都塞的发难,很有可能肇始于其在读《资本论》小组时期的不同思考,而这些不同思考当然不能仅仅从阿尔都塞和朗西埃的不同视角来解读①阿尔都塞后来在《学生问题》中专门谈到了这一问题,但阿尔都塞坚持认为,知识教育不能与政治混同,老师在知识教育上相对于学生具有绝对的优势,而这番言论,自然引发了朗西埃的不服。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看Louis Althusser,‘Students Problems’,Radical Philosophy 170,2011和Jacques Rancière,Althusser’s Lesson,Emiliano Battista trans.,London:Continuum,2011.,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就呈现出异质性断裂的症候。而阿尔都塞后来强调的症候式阅读,也应该是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断裂性症候提出的一个特有的阅读方法。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多种马克思的可能性,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共时性断裂,而不是阿尔都塞的在时间线索上的断裂。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经历的阅读背景和知识的断裂性,导致了他完成的文本映射出他在知识和思想上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虽然马克思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变化和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却不是基于时间的,而是基于马克思本身的分裂性。在文本中,我们遭遇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与我们在知识象征层面和我们的个体想象层面构筑的马克思都有所差别,我们的象征性语言无法真正再现出这个处于真实界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本身就是分裂的,我们唯一可以触及他的方法就是从复数的元素来触及马克思的本真,这些复数的马克思,如巴迪欧所说:“这三个马克思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6]27。但是,我们不能像阿尔都塞一样,简单地声称成熟的马克思是“科学”的,并借助这种“科学”排斥了其他马克思的可能性。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做法当然是一种蒙昧的野蛮作风,因此,巴迪欧的三个马克思的指认,我们可以视为他在与阿尔都塞分道扬镳之后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再思考,尽管巴迪欧迄今为止并没有以真正文本的形式来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巴迪欧列举的第一种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被阿尔都塞指责为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影响之下,并未真正摆脱意识形态襁褓的马克思。巴迪欧显然承认了这种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联,巴迪欧说:
首先有一种带有黑格尔哲学遗产的辩证的马克思,这种辩证法主要被视为客观性的辩证法,即矛盾运动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构建了历史哲学的马克思,实际上,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历史运动……这就是第一种马克思,即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一种带有广阔的历史视野的马克思。[6]27
这种马克思的特点是,它试图从一个宏大的历史脉络中来把握历史的辩证法,即真正历史进步的科学。显然,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或许已经摆脱了从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来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尽管这种历史哲学在后来的许多解释中,被视为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头脚倒置的颠倒。尽管马克思强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他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7]73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将历史发展的基础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Geist)还原为现实中的真实的历史(Geschichte),但是这并没有真正摆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阴霾,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甚至更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个历史仍然以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在起作用。简言之,我们不能否定,马克思在一开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带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去发现一种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科学,因为他从黑格尔那里承袭而来的正是这个大历史的观念,相信有一个历史的脉络可以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所有线索和事实全部贯穿起来①应该说,马克思的这种对大历史科学的或者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追求,甚至一直延续到他自己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相关著作的研读上,而他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研读使他确信了线性的历史观的脉络,而他所需要做的正是,验证在前现代社会,从原始的人类文明,到古代和封建社会中的实证性拓展,这种拓展是否延续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也体现了对黑格尔的大历史哲学观的承袭。。用张异宾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在超越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科学的历史辩证法的创立,即任何人类生活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现实生存,一切外部对象也都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被历史地呈现出来。”[8]443换言之,我们虽然驱除了观念和绝对精神的魔咒,但是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历史范畴的笼罩之下,在这个大历史的范畴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历史自身的变化。
巴迪欧很敏锐地观察到,这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带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痕迹。历史不是线性的运动,而是辩证的运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释了所谓的历史科学的辩证运动,在其中,马克思对历史的构想,仍然基于黑格尔式的思辨之上,即便这个思辨的辩证法根基已经被替换成为现实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但是历史辩证的逻辑仍然以一种宏观的线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演变运作。当然,对巴迪欧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残存着某种影响,就彻底抛弃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痕迹的思想,恰恰相反,正如巴迪欧后来所分析的那样,马克思的哲学必然带有黑格尔的思辨色彩,而这种思辨的辩证法,恰恰处在马克思的基底部分,不是简单用一个悬搁和抛弃就能完全消除其影响的。因此,即便在1845年之后的著作中,黑格尔的思辨和历史哲学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呈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个部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碎片,被马克思巧夺天工地编织到他的后来的思想和文本之中。
巴迪欧随后谈到了第二种马克思,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大量地阅读了英国国民经济学的著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已经造诣颇深,这个时期,他对于穆勒、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如数家珍。但是,巴迪欧也很明确地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述的内容影响了马克思,而且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在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放弃了从单纯的大历史角度来思考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逐渐明白,他需要从市民社会内部来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在这种背景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放置于次要地位,相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方法逐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显露出来。
正因为如此,巴迪欧很明确地谈道: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真的按照真正的社会功能理论,来构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正如他自己说过,这个理论不是起源于历史哲学,而是起源于英国政治经济学。不是来自于黑格尔,而是来自于李嘉图。众所周知,马克思几乎毕其一生来写作《资本论》,这本书并没有写完,此外,这本书建立在非常详细,非常精致的分析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这本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处于次要地位。我并不是说,辩证法在其中完全消失了,而是说,它不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剩余价值及其分配机制的分析。[6]28
在这里,巴迪欧区分的十分明确,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以及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再是单纯的大历史的内在逻辑,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基本现实而运作的“功能逻辑”。也就是说,与之前那种如何概括出历史的脉络、如何看到历史的总体发展规律不同,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前提下,马克思更关心的是细致入微地分析资本主义机制本身所包含的秘密,这种奥秘不可能通过历史的内在逻辑分析得出,因此只能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概念上(应该说,经过马克思的科学改造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来思考。如果没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以及明确的数理逻辑的推理分析,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在其中精准地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因此,巴迪欧说:“马克思所发现的是资本如何起作用的规律,以及对资本的规律进行了分析性评价。我并不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完全是辩证法的马克思,而是一个分析性的马克思。毫无疑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受到了科学理想的驱动,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想的驱动。”[6]29
不过,巴迪欧在这里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地展现了出来。在巴迪欧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一致的。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某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使马克思可以鞭辟入里地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内在肌理中去观察,但是,马克思的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却被巴迪欧有意忽视了;即马克思的方法根本上是服务于他的批判,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著作的表象,在这个表象下面,马克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拜物教式的颠倒,即我们将历史内在逻辑的结果(表象)直接当成了原因,并以这种颠倒的图像构造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揭露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深层次的颠倒,而不仅仅只是从社会功能分析上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巴迪欧和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一样,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解读停留在一个历史现象的理解上,而忽视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等作品时的基本辩证关系,即张一兵教授所说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基于现实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而对现实的表象与本质的颠倒进行批判。
三
实质上,巴迪欧谈论第一种马克思和第二种马克思,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出他所主张的第三种马克思。这并不是说,巴迪欧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马克思是错误的和有偏颇的;而是说,在以往的马克思的研究中,更多的人重视从历史哲学(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第三种马克思或多或少被马克思的研究者所遗忘或边缘化。
什么是第三种马克思,巴迪欧很明确地指出,第三种马克思就是“政治的马克思”,对于这种马克思和前两种马克思的关系,巴迪欧说道:
还有第三个马克思,即作为一个政治人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立者,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大声宣告,赌上一切,同无政府主义者,同普鲁东等人进行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旦有必要,这个马克思会援引另外两个马克思,一旦需要,他会援用历史哲学。很自然,他也会援用对经济科学的讨论,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却是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目的提供的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框架,第二种类型的目的是对当代社会运作机制,进行极其精细的分析,第三种类型则创造了一种革命工具,某种可以积极地用于颠覆既已确立的秩序的工具。毕竟是马克思开始了德国的革命。[6]30-31
对于巴迪欧的这段文字,我们要先注意两点:
首先,巴迪欧强调的这种政治的马克思,不能与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的一个经典划分相互混淆。我们经常会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而这三个来源对应于他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把前两者等同于巴迪欧所说的前两种马克思的话,那么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第三种马克思,即巴迪欧所说的政治的马克思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巴迪欧和马克思一样,都十分重视现实的政治,但是巴迪欧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对于马克思的政治性的思考,基本上也源于他的哲学思考。
其次,巴迪欧基本上不会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他更喜欢使用的词是共产主义。在他之前的《共产主义假设》一书中,他就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主义观念的价值与意义。巴迪欧说:“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处在那个时代,1847年,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起草完毕,我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在穷苦的劳工大众之中进行的新型的政治进程,它试图在现实中寻找所有让共产主义观念成为可能的方式。”[9]20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巴迪欧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够从前面的历史哲学的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出一个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我们所具有的仅仅只是一个观念,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假设。我们可以援引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来说明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的观念,不能被还原为历史辩证法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巴迪欧指出:
共产主义观念就是观念的典型的范例,其用处就是对真实运动的形式化。正是这个观念,可以让你们去判断具体情势或真实运动的政治价值,并判断他的一般方向是否与观念相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尺度,它既不是辩证的,也不是分析的。如果将共产主义列于哲学史之中,如果你说共产主义是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历史发展运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目标,一个不可避免的目的,如果共产主义被理解为历史哲学的一个范畴,它就是辩证的。但如果你说共产主义是必然的实证性的结果,它是资本主义自身逐渐创造出来的结果,在那里,要么进入共产主义,要么陷入野蛮与蒙昧(要么成为人的生命的浩劫,要么进入共产主义),你就将共产主义与分析性要素衔接起来,你将之关联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是用来形式化真正运动的东西,它表明,真正的运动就是朝着共产主义的观念运转的。你不必在分析与辩证之间做出抉择: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优点所在。[6]41-42
由此可见,第三种马克思,即政治的马克思是一种裂变的马克思,在这里,巴迪欧并不需要我们从历史哲学(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的角度去论证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也不能像一些理论家(如哈特和奈格里)一样等待资本主义自己陷入危机中,并最终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我们不能等待在理论上完整地论证清楚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或者等到资本主义社会自动地腐朽没落之后,再去实现共产主义。对于巴迪欧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绝对的中断,一个不能用当下的知识逻辑来言说的东西,它不能被阐明。在一定意义上,共产主义对于当下的语言和知识体系来说,是一个绝对的空,一个绝对不可辨识的东西;那么自然,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绝对不能从之前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中得出。
所以,对于巴迪欧来说,第三种马克思的可贵之处,不是等待合理论证的出现,而是将一个仅仅只有名字的观念推出来,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事件的方式,让一个全新的政治程序在其中运作起来。马克思早就已经说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7]87共产主义不是直接具有规定内容的概念,相反,它是相对于当下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绝对漂浮的东西。我们面对共产主义观念,重点不在于共产主义是什么,而是在于,共产主义何以可能,正如巴迪欧所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共产主义一词并非关键性的操作项,它仅仅是一个点,从这一点开始,分析运算只能在国家生产、阶级等的层面上运行;同样,辩证运算只能说明在这些层面上的否定性是如何运作的,矛盾各方如何彼此冲突。此外,共产主义一词的优点和力量在于,它十分清楚并十分详尽地代表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一种完全不同社会的架构是可能的。”[6]45-46
不过,当共产主义成为一个可能的观念的时候,这个政治程序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还缺少一个直接的现实环节,即可以将共产主义道成肉身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主体。主体是巴迪欧哲学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没有主体对于共产主义观念的忠诚,共产主义观念就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上。正如前文说过,巴迪欧的主体观念受到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大众主体的概念影响很大,这不是一个个体的主体,或者说,不是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主体。在革命运动和事件中,只有那些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观念的个体才能合体为主体,这是面对真理的主体,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力量。在巴迪欧看来,马克思不仅仅书写了一个叫作《共产党宣言》的文本,更为重要的是,他创立了第一国际,将一个本不存在的观念,变成了一种现实化的运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号召下,欧洲的无产者和穷人联合起来,合体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主体,并开创了德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
也唯有如此,那个投身于具体的革命运动的马克思,那个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并点燃了1848年的革命风暴的马克思,才是巴迪欧心目中最不可或缺的马克思。对于巴迪欧来说,他并不强调以这种政治的马克思来取代前两种马克思,巴迪欧反复强调,前两种马克思,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巴迪欧谈论的重点是,这个直接投身于革命的马克思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马克思。的确,巴迪欧看到,欧美的左翼和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将马克思本身变成了一种玄学,用极其佶屈聱牙的词汇,言说着普通大众根本看不懂的文字。对于巴迪欧来说,真正需要的不是从新学理上彻底论证清楚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工作需要,但不是最必要的;最必要的工作仍然是从忠诚的主体的角度,坚持共产主义的维度,让共产主义仍然作为漂浮不定的幽灵,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徘徊。
[1]阿兰·巴迪欧.小万神殿[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Alain Badiou.The(Re)commenceme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M]//The Adventure of French Philosophy.Bruno Bo⁃steels trans.London:Verso,2012.
[3]Nick Hewlett,Badiou.Ranciere,Balibar:Re-thinking Eman⁃cipation[M].London:Continuum,2007.
[4]Alain Badiou.Abrégé de métapolitique[M].Paris:Seuil,1998.
[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Alain Badiou,Peter Engelmann.Philosophy and the Idea of Communism[M].Susan Spitzer trans.Cambridge:Polity,201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9]Alain Badiou.Circonstances,5.L'Hypothèse communiste[M].Paris:Ligne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