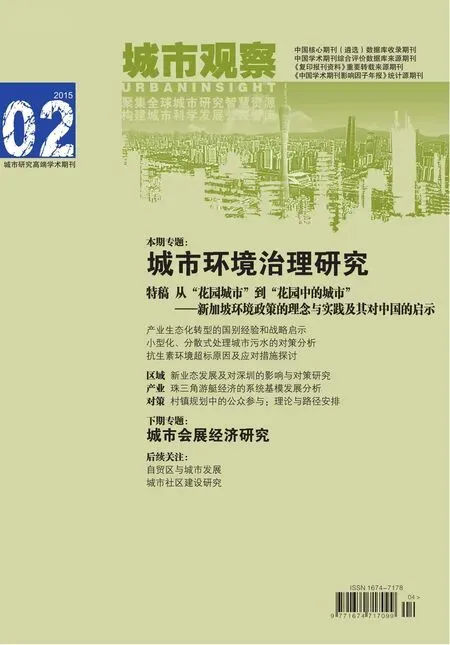城市、城市化与中国研究——兼论“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
◎ 罗 东
一、引言
当下,“以中国为对象”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或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在西方学术界已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六十年历史。尽管它的研究史不比汉学(sinology)那样悠久,但在这大半个世纪里,中国研究从边缘渐次走向了主流,正在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学术事业。这特别体现在,过去的三十年以来,中国研究在以下诸多方面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1)研究领域得到了扩展;(2)参与进来的学科在增加;(3)此外,从研究主体来看,中国学者的不断加入也正在改变西方(以及日本等)学术界的霸权局面①。但这三十年间,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共同展开的对中国研究的集体性反思——寻找主体性[1]。在西方学者那里,他们继续反思从事中国研究的范式和立场,从前三十年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和“国家—社会”(state-society)模式到对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批判,以及中国中心论的崛起等[2][3][4]。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问题则要复杂一些,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首要困境是如何审视或理解中国研究这一目前仍由西方学术界主导的社会科学场域,另一方面,则如周晓虹先生在他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一书中倡导的中国研究未来走向,即同西方学者共同致力于中国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1]。
差不多与这些反思同时展开的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中国自上而下对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诉求与实践。它们都由改革开放的触发而来。从三十年来的建设史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先后两个重大阶段:在前期体现为工业化,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则全面转向于城市化,正是由此,中国驶入了邢幼田指出的“城市大转变”(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时代[5]。中国正在因城市化而发生巨变,这还不仅在于人口学意义的城市人口规模性增加,而更在于城市化之下城市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拆迁,以及动迁户和业主等社会成员发起的维权行动,两方力量之间的张力正在重构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但令人感到十分诧异的是,城市又特别是城市化建设或运动在中国研究的议题中,即使不是绝对(如邢幼田等极少数学者)但也基本是不在场的、被遗忘的。追根溯源,中国研究的对象从来是单一性的中国,即乡土中国,而不是城市中国(Urban China)。同时,本是应作为理解当下中国城市化最关键的理论框架——“国家—社会”关系——在西方学术界的范式反思与重构中,面临被质疑乃至遗弃的危险。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在笔者看来,城市中国被悬置背后的话语逻辑,仍然是西方以及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霸权,即将中国置于“先进的现代西方—落后的乡土中国”二分体系之下。在此意义之上,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集体性反思都算不得是彻底的。
二、单一性的中国及其学理机制
可以说,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开创的海外中国研究既以汉学为基础,又超越了汉学,把对中国的研究从古典文籍的人文学研究中抽离出来,建立了这么一门基于综合性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这是他对这门学科不可磨灭的丰碑性贡献。此后,中国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范式反思与重构。但在这些反思中,我们极少见到城市(化)或城市中国的影子,中国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单一性的乡土中国。
在这些反思中,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被学术界认为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反思最为激进的,也是最为尖锐的[1]。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在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在他看来,不论是前面提到的“冲击—回应”,还是“传统—现代”抑或“帝国主义”等研究模式,莫不是置西方于中心的。鉴于此,他首先提出了“中国中心论”。具体来说,他倡导通过四项研究技术或策略来实现“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的目标,也即:(1)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不仅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经历的,衡量它们的标准也应是中国而非西方(美国)的;(2)在横向上,将中国从空间上分为较小的、易于掌握的单位来研究;(3)在纵向上,将中国社会按不同层次(统治人物、文化名人及底层等)来研究;(4)以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而不仅是历史学来做中国研究[6]。尽管周晓虹等学者指出,柯文在他的中国研究中并未真正做到或实现将中国置于研究的中心,同时还牵扯到对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冲击这一事实的间接性忽略[1],但笔者还是认为,一方面,他对以往研究范式的批评以及这四项倡议都是弥足珍贵的,另一方面,他真正的局限在于对中国的单一性解读。城市中国是不在场的。当然了,柯文的研究对象是近代中国的转变——他认为中国内部已蕴含了向现代性迈进的自身因素——有关中国在建国之后凸显出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他的关注焦点,但问题仍然在于,即使是在他的批判与倡议中,同样不见城市的影子。特别是在(2)和(3)中,他考虑到了将中国区域化(内陆与沿海的差异)、分层化研究,但遗憾地忘记了对城市—农村的区别研究。如果说在改革开放早期,城市化还并不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题,那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已替代工业化成为城市政府及国家(执政党及中央政府)追求政绩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事实上,城市(化)在中国研究中仍是缺位的,相关的研究屈指可数。即使是周晓虹先生站在全球化的立场,在那本对中国研究做出综合性评述与研究的专著中,同样不见城市中国。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十年的中国研究中,绝不是没有任何城市相关的研究(如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7]等),但笔者这里提的城市或城市中国,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含义,一是在文化上指中国的城市性(同乡土性相对应),二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城市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运动。鉴于此,像魏昂德(Andrew G.Walder)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8]中对城市单位(danwei)的研究便不属于笔者这里所谓的城市中国研究,这在于,他们是将城市作为挖掘材料的场所或田野(field)而不是直接的研究对象。有趣的是,魏昂德在研究中发现的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庇护”关系常常被认为是同城市性相违背的。另外,在九十年代,戴慕珍(Jean Oi)对乡镇企业的观察,富有创见地揭示了中国地方的“政治—经济”逻辑,即地方国家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9],尽管他的研究几近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与实践,但关注点在于工业化而不是城市化。无可厚非的是,这自然是同他本人将中国农村作为研究方向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遗憾所在,海外特别是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如果关注的是区域(而不是组织或社会运动等),那么他们的研究对象不约而同的都是乡土中国,如欧博文(Kevin O’Brien)以及戴慕珍等西方学者②。同样,回到包括大陆、港澳台等中国学术界,近年来致力于对中国研究反思的学者,仍以乡土中国的研究主体为多,如吕德文[10]等华中乡土学派的青年学者,以及王铭铭[11]等人类学者。他们对中国研究的贡献或努力,是不可低估的,但反过来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事于中国研究的城市研究或将城市研究置于中国研究框架之下的学者还极为缺乏。中国研究的对象是单一性的乡土中国。
但为什么是乡土中国?或者说,从接受学或知识考古学来看,将中国概化为乡土性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首先回到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这一社会学经典中: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如果以传统社会学的二元对比来看,乡土性集中体现在中国的熟悉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及血缘关系等社会结构[12]。但事实上,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将这一乡土性提升到对中国的整体性描述,这不仅体现于书中,他本人在不同的场合(讲座、访谈等)也表示过乡土中国描绘的是乡村,或“乡土社会”。这一点不可置疑。既然是这样,那乡土中国这一概念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认识机制被确立为整体中国的?近年来致力于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的陈映芳在《城市中国的逻辑》一书中做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讨论。陈映芳将“乡土中国=中国”这样的机制归因于两大学科的学理机制: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这在于:在社会学那里,“现代的西方—传统的中国”根植于古典社会学对“现代—传统”的二元认识结构,同时在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寻求对现代的实践,将罗列和清算中国社会内部的传统性视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使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则又“以农村社区为田野,以村落小团体的个案来描述中国社会”,在发现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3]。她进而阐释了这一误读为当下理解中国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后果,特别是将中国的困境一味地寄托于乡土性,将现代性归结为西方输送的结果而对之排斥。她的反思令人深思。
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讨论还可以进一步得到补充。尽管陈映芳提及了来自西方视野(即西方将东方视为落后的、传统的)的因素,但事实上,她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中国社会学者。从事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同样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他们早期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迹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体现在将中国视为西方视野之下落后或传统的国度,另一方面则是将近代中国的转型归因于西方国家的冲击,这样的中心主义影响至今。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学术界经历了若干次反思但仍未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因素。除了学理上的因素,笔者认为,农村社会占中国主要地位的这一长期的事实同样不失为一个原因。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农村是生活资源以及统治者合法性资料最重要的生产地,到了当下,伴随大量民工外出而又出现了农村发展和治理的困境。长期以来,这些都吸引了学术界致力于农村研究(rural studies)并形成路径依赖。但问题或许在于,当下农村问题根植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特别是农村在土地征收和外出务工人员等方面遭受到的不平等或剥削。因而,对于二者的绝对二元化研究不利于对中国问题的全面认识。
同农村中国受到的学术关注度相比较,城市中国出现的诸如城市开发带来的拆迁、产权纠纷、业主维权等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重视。
三、城市化的两幅中国图景
那么,城市中国正在或发生了什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执政党将现代化的中心移到了经济建设,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纲领。具体来说,经济的现代化又经历了先后两个阶段,一是八十到九十中期的工业化,二是此后到当下的城市化。它们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于一九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于第一个阶段的工业化,中央政府为了激活和动员地方的建设活力,财政上推行包干制,允许地方享有一定的自由权限,同时只对最后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做出要求,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和兴办乡镇企业获得了包括灰色收入等大量的收益。这时期的现代化得到了戴慕珍等中国研究学者的关注。但财政包干制给中央政府造成了财政困难,地方的财税出现了混乱,鉴于此,分税制及其改革最终在九四年被确定了下来[14][15]。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九四年的分税制重塑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的地方财税受到了限制,被压缩了兴办企业的利润空间,这时的地方政府将财政空间转向了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农业税;二是城市的土地开发。农民负担的加重,进入到学术界的关注视野,这才出现了后来李昌平上书的三农问题③。同时,城市土地带来的出让金、房地产税等大量的利益,构成了地方城市政府的财政主要收入,城市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得以轰轰烈烈地进行,一系列的城市问题由此产生④。但对于这阶段的城市问题,照样未进入到中国研究的主要视野。
(一)城市拆迁与土地征收
目前的土地制度之下,土地被规定为城市用地(即国有土地)和农业用地(即集体所有以及少量的自留地)两大类。城市开发中,针对后者是将土地征收为国有性质,对于前者则是通过房屋拆迁以实现对使用权的国家收回。它的基本逻辑是,城市政府完成对土地的征用后,再以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给开发商,从中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不需上缴中央财政)以及房地产开发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地方占百分之六十)[15]。为了尽量压低土地征收或城市拆迁的经济成本,城市政府同动迁户展开了一场利益博弈。如此一来,就有了当下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冲突事件。对于城市政府来说,如何在维持合法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成了它们的首要考虑之项。从实践来看,它们除了动用利益补偿、劝说等软性手段外,更为常见的是,将动迁工程以市场交易的形式交给拆迁公司或拆迁队来做,以威胁、暴力等强拆手段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开发运动。从近年来的新闻报道来看,不乏流血冲突乃至人员伤亡等事件。对于动迁户来说,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争取更大的权利保障,是一个需要策略或技术的艰难历程。他们不仅在动迁之时,通过“守房”等不得已的途径来对抗拆迁人员,在遭遇强拆之后,又通过信访、诉讼等途径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但事实上,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应的制度措施,现实生活中的维权之路,对于他们而言仍是举步维艰。对于此,邢幼田在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城市大转变》)一书中给予了关注[5],这也是目前中国研究中直接以城市为对象的极少数成果之一。在书中,邢幼田以空间研究为框架,详细地阐述了中心城区(urban core)、城郊(metropolitan region)和边缘农村(rural fringe)等三个空间之下的土地政治,将城市政府、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动迁户(城市中的私房主、城中村及农村的动迁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巧妙地概化为以土地为中心的领地化(territoriality)。但遗憾的是,因她的学术旨趣在于对城市化的整体性解释,较少触及到具体过程中的拆迁策略,以及动迁户的维权或抵抗策略。
(二)城市业主及其行动的兴起
城市化运动中第二个问题,牵涉到一个新兴群体的出现,学术界称之为“业主阶层”或“有房阶级”。尽管国家在《宪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明文规定,即土地征收需要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到了实际运行中,城市政府将土地的开发主要用于商业用途,商品房则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但商品房以及业主的兴起,同九十年代的住房改革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单位的福利房成为了历史,房屋成为一件商品走上了交易市场。从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发展来看,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问题在于,在各大城市,有关业主维权、抗议等行动不断受到了舆论的关注。这是因为,伴随房屋的市场化,城市政府在治理上并未做出及时的跟进,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等经济集团的利益矛盾显现了出来。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郭于华等学者主持的城市业主调查与研究来看,业主维权集中在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抵抗。他们的成果汇集在《居住的政治》[16],该书向我们呈现出了,物业公司在服务、公共产权(如公园、走廊、电梯等)等方面对业主的不平等对话。业主的权益遭受了损失,但个体又构不成对抗物业公司的力量。他们选择依法成立业主代表大会,力争自主决定对物业公司的聘用,但尽管在城市政府部门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项努力来得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首先要通过居委会的许可,再到房管部门备案、登记,最终能成功者屈指可数。这一图景,不仅体现了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市场关系,深层次地,还映射了业主同房管部门等城市政府,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社会管制之间的张力。
城市中国的土地正在演变为波兰尼在《巨变》中批判的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17]。但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有关城市化的议题并不限于这两大类,另外还如国家经租房及私房主在城市化之下的问题,以及都市环保主义的兴起等。不一列举。
四、作为理解中国城市化的“国家—社会”框架
无可置疑,这一场城市化运动正在改变或重构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
在传统中国,“国家—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费孝通与吴晗两位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论及的天子与乡绅(宋以前为贵族—地主),广袤的农村地区享有一定的社会自治权[18]。相反,国家则建构为“简约型国家”,皇权的触角往下延伸到县一级便停止了。关于这一点,从那时的国家财政税收中可见一斑[19]。到了近代,“乡绅—地主”这一群体或阶层在早期城市化和科举制的终结中被淘汰[18],共和国建立之后,同时又作为旧势力遭到打压,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空间被挤压至不复存在。笔者这里提的社会,在概念上可追溯至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具体来说,它主要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相对于国家提出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20]。社会在农村被合作社、生产大队等挤压,在城市则集中被单位挤压,社会在该阶段不再存在。整个中国表现为总体性结构。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下的市场经济建设,合作社、生产大队及单位逐渐被历史遗弃,社会的空间被重新释放出来。但尽管如此,社会却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它需要人们发挥主动性,调整同国家的关系以完成社会的生产(making society)[20]。
城市化运动之下,社会面临着被生产出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在城市土地征收或拆迁中,动迁户在维权实践中,生产出了相应的公民权(citizenship)与公民的勇气,另一方面,业主通过建立业主代表大会来维权,同样预示着社会在中国的再次兴起。社会的另一端,是正在做出回应、调整治理技术的国家(以及市场),城市中国下的城市化运动正在改变或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但正如笔者在前文提出的,回到中国研究,“国家—社会”这一关系框架在西方学术界的范式反思中是被集体性遗弃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研究中,兴盛于二十世纪的五十至八十年代。按照周晓虹先生的说法,西方的学者围绕这一关系构成了两种不同的亚模式:一是冲突模式,或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或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抗拒,代表学者如苏尔曼(Franz Schurmann)、傅高义(Ezra Vogel)等;二是互动模式,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妥协、渗透和共存,代表学者如怀特(Martin Whyte)等[1]。但随后,这种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遭到了反思,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并不适用于对中国研究,这是因为,中国是否存在市民或公民社会是一个值得质疑的议题。他们转而将这里的反思提升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以柯文为首要代表的中国中心论随之兴起。但事实上,西方学术界这一反思建立于建国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那段时期的确是一个社会受到压缩的中国。他们的反思不无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们放下这一范式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催生了(公民或人民)社会的诞生,社会将可能被生产出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被改变或重构。这是令从事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始料未及的。
这里,笔者将指出的是,将城市中国同中国研究联系起来,不仅在于再次发现和理解一个完整的中国,还在于方法论的反思与提升。对于中国研究来说,对中国单一性的理解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缺失,对于城市中国来说,将它置于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之下,有助于学术界对城市及城市化的深刻理解。这是因为,正像学术界已经认识到的,尽管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上存在一些偏差或不便,但他们同样具有摆脱制度等约束的先天性条件,中国学者同他们一道,以周晓虹说的“主客体并置”这一出路来完成对城市中国的理解[1]。到那时,中国研究将可能摆脱“他者”(other)的西方中心主义,同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海内外学者将可能实现胡塞尔(Edmuud Husserl)所谓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次,相对于已形成研究路径依赖的西方学者来说,中国学者对于城市中国在学术上更敏感,将是找回中国研究主体性的一次机遇。
注释:
①这些中国学者中,早期是在美的华人学者,如林南、赵鼎新、周雪光、李静君、邢幼田(Youtien Hsing)、彭玉生等,近十年来,还先后加入了王铭铭、周晓虹等活跃的大陆学者。
②这一时期,以城市作为观察田野的研究成果,还有Kellee S.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Andrew G.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101(2): 263-301.等。
③关于李昌平向国务院领导反映 “三农问题”的前后,可参考《江苏农村经济》2001年第6期文章《说句真话不容易——给国务院领导写信的前前后后》等。
④值得一提的是,戴维·哈维在他的近作《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中,对中国城市化运动评价到,它帮助中国解决了资本投资和农民工就业问题,以此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强大的免疫力。参考: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9-67。
[1]周晓虹.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6-47.
[2]周晓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2,(3):227-236.
[3]黄宗智.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J].开放时代,2005,(4):43-62.
[4]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J].社会,2007,(6):89-101.
[5]Hsing You-tien.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29.
[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3-23.
[7]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1.
[8]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2-5.
[9]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1992,45(1): 99-126.
[10]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社会,2007,(6):80-101.
[11]王铭铭.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中国社会科学,1997,(5):106-120.
[1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3:1-7.
[13]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413-431.
[14]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6):100-115.
[15]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2007,(1):49-82.
[16]沈原等主编.居住的政治——当代都市的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53-225.
[17]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
[18]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长沙:岳麓书社,2012:1-6.
[19]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北京:三联书店,2001:23-47.
[20]沈原.社会的生产.社会,2007,(2):17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