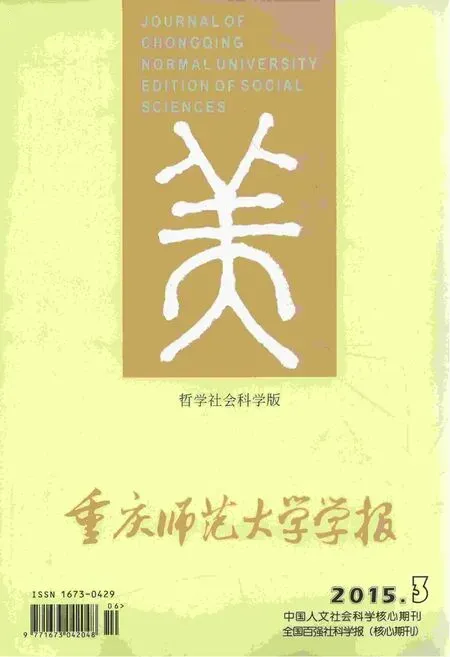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述论
喻学忠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宋朝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也就是文彦博说的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士大夫即为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之优劣,关系到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乃至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而,士风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非常值得关注。本文欲对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作一初步研究。本文“变节”,主要指改变原来的节操或品行,丧失原有的气节,而不论是否屈服投降敌方。
一、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的诸多表现
晚宋时期,蒙元对南宋构成亡国威胁,一大批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大多渎职或临难脱逃,或于宋亡前投降蒙元,或在宋亡后积极仕元,从而形成晚宋士大夫的变节之风,完全脱离了“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的初衷。
第一,临难逃避之士大夫。
此有二类。首先是战争期间临难逃避的各地郡守知州等重臣。他们各自亡命自保,不敢组织抵抗,丧失了各自应尽的职责。
早在晚宋时期的宋与金战争期间,临难逃避的各地郡守知州一大批,如地方守臣有程松、黄炎孙、应谦之、杨克家、刘昌祖、罗仲甲、侯颐、雷云、李文子、赵希昔、董居谊、何大节、尚震午[1]卷9,15,16等等。
而在宋蒙(元)战争期间,临难逃避之郡守知州等重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多不敢抵抗元军之兵锋。略举不同时期的代表,如端平三年(1236)十一月,蒙古口温不花入淮西蕲、舒、光州,守臣皆遁。[2]1047理宗景定三年(1262)六月,朝廷闻知李璮受围,给银五万两,下益都府犒军,遣青阳留梦炎帅师援之,梦炎至山东,不敢进而还。[2]1124德祐元年(1275)正月,元兵逼近江州,知安东州陈岩夜遁。二月,元兵进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逸。三月,知江阴军郑濡道遁。元军攻下平江府,守臣潜说友逃遁。江上诸城,或降或遁,无一重臣坚守者。鼎州、澧州、常德府、寿昌军并降。元兵攻至抚州,时制置使黄万石开阃抚州,闻元兵至而遁。十月二十三日,元兵破独木关,留梦炎遁。十二月元兵屯驻平江府,京师戒严,留梦炎、陈文龙、黄镛、刘黼并遁。次年正月,元兵攻入临江军,权守滕岩瞻遁。[3]卷8德祐元年七月,沿江制置使赵溍与张世杰会兵与元军决战,大战前遁走,次年赵溍入广州,元军来攻前夕,于十二月弃广州遁走。
其二,在晚宋时期发生兵变之时,有地方守臣临难逃避,并没有认真组织平定兵变。如嘉定年间,溃兵张军煽动士兵作乱,“太守林(仲虎)弃城遁”[4]卷5。嘉定十二年(1219)三月,兴元军士权兴等作乱,进犯巴州,守臣秦季槱弃城而去。夏四月,兴元军士张福作乱攻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聂子述遁逸。五月张福叛兵迫近遂宁府,潼川路转运判官权府事程遇孙弃城去。五月,张福攻入普州,守臣张已之弃城去。[1]卷15,16
第二,南宋灭亡前争相逃避或降元之士大夫。
在宋(蒙)元战争的后期,南宋朝廷岌岌可危,一大批士大夫不思报国,为国尽忠,反而争相逃避或降元。上至朝廷重臣,中至地方官吏,下至三学士子,变节之人比比皆是,形成晚宋时期的变节逆流。
首先是临安陷落前夕逃避的朝廷士大夫。德祐元年正月,朝臣不顾京师戒严,接踵宵遁。当时数十重臣并遁,朝中为之空疏。谢太后任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在慈元殿“宣麻”时,文臣只来了六位,场面极为凄凉。可见当时士大夫们临难逃跑人数之多!二月二十六日,左丞相王爚遁去。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鉴遁逸。[3]卷7有人评论王爚“具位平章,在朝无所建明,不顾君父之颠危,退为保身存家之计,鄙哉!”[3]卷8同年十二月,京师戒严,留梦炎、陈文龙、黄镛、刘黼并遁。德祐二年正月十五日壬午,在朝臣一时俱逸。[5]卷17除了朝廷中的京官逃遁外,各地守臣,眼见大势已去,亦纷纷弃职逃走。明朝学者张溥对宋末大臣纷纷弃职逃走曾悲叹曰:“德祐元年之春,左丞相章鉴闻元兵日迫,托故迳去,既而临安戒严,曾渊子、潘文卿、季可、许自、王霖龙、陈坚、何梦桂、曾希颜、文及翁、倪普等数十人,相率并遁,太皇太后诏榜朝堂,厉词申责,势不能禁,及留梦炎降唆都,陈宜中入占城,身为大臣,行同犬豕,飘蓬翩反,亦曷法乎?”[6]德祐二年,元兵进逼南宋小朝廷,丞相陈宜中“是岁大军至,陈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7]121,参知政事常楙弃职离开临安,隐于民间。可见在朝廷危急时刻,士大夫们只顾自身逃跑,哪里还顾得上朝廷?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并不是所有临难逃避之士大夫都是降元或仕元的,其有三类,一类是先临难逃避而后降元的,如黄万石。一类是先临难逃避而后做遗民的,如陈宜中。一类是先临难逃避而后成为忠义之士的,如陈文龙。因此临难逃避的士大夫只有一部分后来降元或仕元。
另外,除了士大夫们的临难逃避之外,当时朝廷重臣还形成一股降元逆流,此在元军进入临安前后表现尤为突出。参知政事陈岩于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降元。留梦炎,身为宰相,“状元曾受宋朝恩”[7]153,也于德祐二年(1276)投降元朝做官二十年。元兵进入临安府,北使请三宫北迁。福王赵与芮,参政谢堂、高应松,驸马都尉杨镇,台谏阮登炳、邹珙、陈秀伯,知临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数千人皆在遣中。[3]卷8北上充祈请使的五位大臣中,除家铉翁外,吴坚、贾余庆、刘岊、谢堂都降元。
士人出身的地方官吏与守臣之降元者,其人数之众,则又远远超过了朝廷之重臣。号称开庆六君子之一的黄镛(时知卢陵)、曾唯,在元军进攻前夕,“如黄、如曾数公,皆相继卖降”[7]135。省元李澌泉,“为从官,为督府参谋”,宋亡前也是投降元朝。[7]175而地方官吏与守臣之降元者,又以德祐年间及随后几年为最盛,伯颜入临安后,“阿里海涯传檄诸郡,繇是袁、连、衡、永、郴、全、道、桂阳、武冈皆降。”[2]1166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官吏与守臣是蹇材望、洪起畏与方回。湖州倅蹇材望在元兵进攻之前,以忠臣自许,“毅然自誓必死”,“且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北军入城时,蹇已不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发现蹇材望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降元,遂得任命为本州同知。[7]139-140类似的还有知京口洪起畏,他在元军入境之初,曾经大书揭榜四境曰:“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7]181-182但其后却举郡以降。知严州方回,元军将至时,方回倡言死封疆之说极其雄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7]251此三人前后行径各相对比,有异曲同工,临难前都是极尽豪言壮语殉国之能事,事实上却都是争相降元,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实际是当时官吏内心的普遍写照。
还有三学士人之降元。德祐元年正月,“大兵入临安府。三宫北迁之时,太学宗学生数百人,皆在遣中。”[3]卷8“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文学二人,武学二人。”[7]173他们被授与路学教授的官职。积极归附的士人还有刘裒然、陆威中等。可见宋亡前,有很多士子归附元朝。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诏北行之士人是否算是降元?主动降元与从诏北行至元朝是有区别的。从诏北行尽管是被迫的,但从本质上说,从诏北行归附仍是仕元的,应为宋亡前降元。原因有三:一是当时就有士人在从诏北行时不愿归附而为国尽忠的。如德祐元年二月,太学生徐应镳,誓不北走而殉国。[8]13277二是即使在从诏北行后,仍有士人不愿意归附。如德祐元年,北上的高应松亦不食卒。[9]卷183还有北上的祈请使家铉翁亦不愿归附。其三,时人即认为当时北上的士人就是投降。如文天祥说:“我立二王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帝愍而北者非忠臣,从元帝为忠臣,从徽宗、钦宗而北者非忠臣,从高宗为忠臣。”[10]也就是说,文天祥认为当时从诏北上之士人非忠臣,这些士人是“公卿北去共低眉”[5]卷13。在文天祥眼中,不论是强迫还是自愿北上的士大夫与士人其实就是降元。今人史卫民也认为太学生中多数是从诏北行降元。[11]94当然,也有一部分太学生悄悄地溜出临安,逃到偏远的州郡暂避风头。
第三,南宋灭亡后入世仕元之士大夫。
南宋灭亡后,有一批士人,或不甘寂寞,或追求名利,或出于贫困等原因,纷纷出仕元朝。这一批士人的表现虽然各异,不论是主动仕元还是被动仕元,但其本质却是变节。其表现有以下几类。
宋亡时归隐,后被征召出仕之士大夫。如:郑滁孙,南宋景定年间进士,“知温州乐清县,累历宗正丞、礼部郞官”,宋亡后不仕。元朝至元三十年,受到他人举荐,“世祖召见,授集贤直学士,寻升侍讲学士、学士。乞致仕,归田里”。其弟郑陶孙,“亦登进士第,监西岳祠,升应奉翰林文字,后为江西儒学提举。”[12]4338胡长孺,南宋咸淳年间入蜀铨试第一名,“授迪功郎、监重庆府酒务”,不久“兼总领湖广军马钱粮所佥厅,与高彭、李湜、梅应春等,号南中八士。已而复拜福宁州倅之命,会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元朝下诏求贤,有司强起举荐胡长孺,至京师,待诏集贤院。延祐元年,转两浙都转运盐使司长山场盐司丞,阶将仕郎,未上,以病辞。不复仕,隐杭之虎林山以终。[12]4331-4332牟应龙,咸淳年间进士,后被“沿海置司辟为属,未几以心疾乞告归养”,而后宋亡。入元后,因为家贫,“稍起教授溧阳州,遂以上元县主簿致仕。”[13]879郭隚,初为太学生,宋亡时居乡教授,“至元中,以遗逸起家,三为郡文学”[14]文集卷3。程矩夫下江南求遗逸时,叶李、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孔洙、曾仲子、凌叶中、包铸、王泰来等二十余人皆入仕元朝,“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12]4016。
宋亡后直接变节仕元之士大夫。如:文天祥之弟文璧在宋亡之后,“以宗祀不绝如线,皇皇无所于归,遂以城附。”[5]卷18曾希颜曾为南宋御史,为兵部侍郎,为江西安抚使,积官朝奉大夫,归附元朝后“授承务郎、湖南儒学提举。”[13]922臧梦解,宋末为进士,未及为官而宋亡。至元十三年,“从其乡郡守将内附降元,授奉训大夫、婺州路军民人匠提举,后以亚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12]4129-4130曾冲,仕宋为南安守,降元后为“佥福建闽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议大夫致仕”[13]432-433。戴表元,咸淳辛未进士,“善策论,失仕归里,力从诸先生,能古文”,后仕元为金陵教授。[15]卷33谢昌元,淳祐甲辰四川类试第一,以著作郎迁秘书少监,后仕元为礼部尚书。[16]卷5仕元为尚书之士人除了留梦炎、谢昌元外,还有王虎臣。另外,宋甲戌状元王龙泽仕元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12]4334时人汪元量即对晚宋士大夫的降元逆流有深刻的批判:“满朝朱紫尽降臣”,“满目故人皆厚禄”[17]16,130,形象地讽刺了这种不良之风!
二、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形成主要原因
分析晚宋时期士大夫群体普遍盛行的变节之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晚宋士大夫穷奢极欲,志于享乐。
南宋定都临安后,宋金之间和平居多而战争较少,士大夫们习惯于穷奢极欲、安于享乐的生活,加上本来杭州就具有奢靡的风气[18]卷4,更是加剧了士大夫生活奢靡腐化。晚宋时人的诸多文献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吴自牧怒斥曰:“今钱塘驻跸之久,骄奢淫逸长,此安穷人欲炽而天理灭矣。……然自曩时有纳声色以固宠位者,而后举天下成诲淫之风,至今观光上国之士,自一命以至班,改粉白黛绿,群载后车,其势已不容不贪黩。”[19]卷3袁燮感叹道:“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风也。末习之好而去本浸远也。富者竞为骄夸,贫者倾赀效之,歆艳以成俗,侈靡以相高,旦旦伐之,而本真微矣。”“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宫室藻绘之饰,器用雕镂之巧,被服文繍之丽,极侈穷奢,荡心骇目。公卿大夫之家,妇人首饰,动至数万,燕豆之设,备极珍羞,其侈汰如此。”“故近岁以来,都邑之侈,偏于列郡,而达于穷乡,此岂小故而可不正哉?”[20]卷2《代武冈林守进治要札子》王迈讽刺道:“今天下之风俗侈矣。宫室高华,僭侈无度,昔尝禁矣,今僭儗之。习连甍而相望也。销金翠羽,蠹耗不赀。昔尝戢之矣,今销毁之家,列肆而争利也。士夫一饮之费,至靡十金之产,不惟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21]卷1宋末黄幹甚至这样揭露时弊说:“世间以仕为乐者,以其富贵也。”[22]卷14今人周良霄即认为: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社会里,除了抢劫、偷盗,作官是暴富的唯一途径。[23]314
由于士大夫只顾自己的享乐,欣赏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24]241-242。以至时人批判高宗不建都建康而建都杭州是大为失策,因为“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3]卷1当时之士大夫“但知为富贵之图,不复为根本之虑,托献羡之名,以盖其贪酷之迹”[25]卷64。宋末张端义也抨击道:“今之士大夫甚至闻讣,仕宦冒荣自若。衰绖有不曾著者,食稻衣锦,汝安则为之,圣门之训,天理灭绝,去禽兽几希。”[26]卷下当襄樊被元军围困之时,天下大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仍然“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8]12474-12475
故而一旦国家形势危急,士大夫在为国捐躯或逃避隐逸或乞降自保的多重选择时,只有变节乞降才能继续保持荣华富贵而又享乐腐化的生活,而其他选择则无法满足此类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士大夫穷奢极欲,志于享乐无疑促进了变节之风的形成。
第二,晚宋士大夫贪恋权势,志于爵禄。
贪恋权势,志于爵禄,这是晚宋时期士大夫积极入仕的重要原因,即时人所说的“贪位慕禄趋事赴功”[25]卷59。皇帝与权相也以此为手段,“以爵禄笼天下士”[27]卷168,真德秀感叹道:“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者有年矣。”[28]卷2许应龙向皇帝进呈抑奔竞故事时阐述道:“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曰奔竞。”指出了当时许多士大夫致力于跑官要官的现象。他又进一步批判奔竞“其弊已极”,指出士大夫“未履仕而求辟,无寸功而冒赏,舍法用例,宛转扳援,趋权附势,妄图荣进,承乏则冀,即真未满,则思内擢图近。次则攘人之阙而勒令改替,百计营求,不进不止”,奔竞成功者“必不肯以徼幸自名”,其不成功者“必以沉沦为叹”,究其原因,“虽起于在下者有所求,而亦基于在上者,有以遂其求。惟不待求而自予,有所求而不予,兹实救弊之要术也”。他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革其弊,因而建议,“求者之多也,诚使两造吾门者抑之,以戒贪进。安于静退者,荐之以厚风俗,则伺侯于王公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者,必皆闻风敛迹,恐为清议之所指目,况敢冒然而求进乎。”“苟皆知不当得者不容妄求,则奔竞之风不患其难矣。”[25]卷117甚至宋末皇帝在降元表中也承认:“自贾似道丧师后至今十余月,国事危急,将士离心,士大夫陈乞差遣,士人觊觎恩例,一筹不画,及是束手无措。”[3]卷8在国家将亡之际,士大夫及士人不仅未操心如何替国家效力,却仍在“陈乞差遗”、“觊觎恩例”,这实际是士大夫贪恋权势、志于爵禄赤裸裸的写照。如贾余庆、刘岊相继降元后,对元朝权贵奴颜卑膝,百般逢迎讨好,文天祥即怒斥贾余庆“甘心卖国罪滔天,酒后猖狂诈作颠。把酒逢迎酋长笑,从头骂坐数时贤”,讽刺刘岊云“落得称呼浪子刘,樽前百媚佞旃裘。当年鲍老不如此,留远亭前犬也羞”。[5]卷18
相反,元朝在攻灭南宋时,非常注意笼络或利用降元之士大夫或将领,给他们封官加爵,实行若干恩惠或优待政策。如唆都等既入闽,李珏、王积翁降之,被封为福建宣抚招讨使。文天祥之弟文璧奉守衢州,降元后被封为广西宣慰使。这类政策,非常符合晚宋士大夫贪恋权势、志于爵禄的心态,于是他们更多地是选择与元朝合作,“大臣方且为固位持禄之计,孰与任社稷存亡之忧”[29]卷6,变节降元则成为此类人不二的选择,从汪元量的“满朝朱紫尽降臣”“满目故人皆厚禄”等诗句可以看见,元朝实施此政策的效果非常成功。当然,这类政策对于忠义之士而言,则是无效的。如元朝曾以宰相之高位来劝降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则被严辞拒绝而失败。
第三,晚宋时期理学的负面影响。
理学在晚宋时期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地位,这也是晚宋时期的特征之一。理学对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晚宋理学家徐侨说:“比年(朱)熹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求其专精笃实,能得其所言者盖鲜。”[8]12615应该说,对于那些假理学家来说,理学是他们的进身之阶,依靠理学可达到自己的私心与利欲,获取功名利禄。因此有学者认为:“参与道学最终成为一个获取声名的方式,并且当同情道学的学者控制了科举,道学还成了及第的便捷之路。”[30]343也有学者指出,南宋统治者提倡的理学,主要是空谈“心、性、理”,务虚言而不切实际,议论多而成功少。[31]也就是说,理学本身有空疏不实的弊病,对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的形成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有学者指出:随着理学此后逐渐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士大夫在愚忠观念的钳制下,日渐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乃至作为人的尊严和灵魂。如果说汉代以来在“儒表法里”的统治体制中士大夫经历着一个“儒的吏化”过程,那么,自南宋以后绝大多数士大夫经历的是“儒的奴化”过程。这不是士大夫阶层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民族的悲哀![32]对于那些假理学家来说,信奉理学,其目的只不过是把理学作为仕途晋升之阶。晚宋朝廷将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士大夫们的功利性很强,难免会吸取理学中空疏不实的内容。所以元人总结道:“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文儒轻介胄,高科厌州县,清流耻钱谷,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至于宋之季极矣!”[33]卷14
历史实际表明,理学家们专讲道德修养的心性之学,不仅于世道人心无补,而且亦于个体自律无益。宋明两朝的历史表明,一旦抹杀了儒学的经世取向,所谓“内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堕落到空谈误国的无底深渊中去。[32]这些士大夫虽然受理学的影响,但既没吸收到理学的精华,又没吸取儒家的忠孝观,更没吸收和弘扬朱熹教育思想中最宝贵的精髓,即德育思想和爱国思想。所以时人感叹:“呜呼!自夷狄乱华。南北分裂,而‘畏虏’二字,遂为士大夫膏肓骨髓之病。”[27]卷138因此,当时一大批理学家或受到理学教育的士大夫构成的变节之风,自然是受到理学的负面影响。
第四,晚宋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
宋代士人普遍受到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应该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信念,这类官员自然不是南宋所特有,但是宋代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兴盛,应该强化了官员的此类信念。实际上,晚宋时期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以致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总结道:“在有宋一代,特别是在13世纪,在官僚阶层中有明显的堕落现象。”[34]45这是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有的表现为轻道义、重功利,这在时人文献中比比皆是。如士大夫“道义之念常轻,而功利之念常重。静退之习常少,而躁进之习常多”[35]卷2;士大夫“惟知财利之可贵,岂知仁义之可尊”?而“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心之趋利。举世之人皆趋于利,则知有已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国”;[28]卷18“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之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25]卷100,士大夫中的“谀谄阿附之徒侥幸获用,而孤立独行之士,无自而进矣”“好趋进者以昵己而亟用,乐安恬者以疏己而见遗。权力多助者不能沮止,孤寒寡援者不能荐进”[36]卷9;士大夫“惟其私而不惟其公,志于利而不志于义”[25]卷62;士大夫们“逐逐然惟利禄之计”[37]卷7;士大夫“但知为身计,为子孙计,为门户计,不知凶于而国,则害于而家”[38];“好利之蠹,则剥蚀士大夫之良心为甚,此殆不可以沈痼之,日为受病之始也”[39]卷29;士大夫“好善之名,不足以掩恶直之实,尽公之念,不足以胜为私之情。一身之廉,不足以盖一家之贪。”[29]卷6这种晚宋文献的详细记载,说明轻道义、重功利的道德观念,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所以受到正直士人的重点关注与批判。
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有的表现为寡廉鲜耻,心术大坏。时人对此多有揭露:士大夫“正道不行,而人心坏。人心坏而吏治坏,舍义趋利,假公售私,朘民自封,一孔不贷”[40]卷29;士大夫“心术之坏,胚胎于进身之苟贱,养成于居官之苟容,败露于临难之苟免,积是三坏心术之正无几矣。方为小吏,无心远器,以贿为缔交之媒,以货为生死之地”“向者,西蜀之变,抗义而死者,尚见于闾巷之细夫、闺门之女子,而缙绅大夫能守死而不变者,百仅一二焉。是何某为臭秽之生而不愿为芬芳之死如此也。比日以来,诺诺者盈庭,而谔谔者卷舌,容容者接武,而皎皎者遁行。”[21]卷1知澧州曹彦约曾上奏批判道:“十五年来,士大夫之心术坏矣”“惟是廉耻道丧,风俗不美”。[25]卷59理宗皇帝也曾下诏,指责士大夫“鲜廉寡耻,相师成风,背公营私,恬不知省”“因循苟且,玩岁愒日,由内而外,靡然同流”。[41]卷32到了度宗时,黄震仍然在批判士大夫“廉耻道绝,货赂公行”“希指求进者,虽杀人于货,亦所忍为”。[28]卷2可见这种普遍性的道德败坏一直在延续。“羞恶之心,谁独无之,何至泯没如是?……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体陛下之心,而各自以其心为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25]卷64;“比年以来,羞恶不立,廉耻尽已,皆由士大夫急于富贵,不自知其失口失色,以至此极也。”[25]卷117由于无羞恶之心,则他们所作所为就不会受到道德的束缚与制约。
时人在分析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时,大多认为这是长期形成的,是很普遍的现象。刘克庄认为士大夫“内无定见,外无定力。利欲之所诱怵,世故之所驱,使有亟改者,有渐改者,有终身屡改而未已者”[27]卷100。徐鹿卿也指出:“士大夫德望之伟,特非一日而成,而风节之衰颓,并非一日而坏。”[42]卷2黄震认为晚宋士大夫道德沦丧是流俗渐变的,“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兼跨彼此两间,自以和平为得计,而不知几成西汉之风矣。苏轼有言:平居既无犯颜敢谏之士,临难必无捐躯狥义之人。风俗至此,最为可悲!”[43]卷69学者陈得芝即认为“和平”,指的是气节消靡,圆滑杜世,以保其美官厚禄,不能激切直言指摘弊政。[44]
至于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途径,则有多种形式。有认为是科举制度导致的,时人姚勉揭露士大夫“逐逐然惟利禄之计,则科举之法有以坏之也”[37]卷7。清人顾炎武亦指出宋代士人,“自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而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45]卷13今人陈得芝认为:至于科举,则庸夫俗子率皆俯首诵习所谓“黄策子”者,家以此教子弟,国以此造公卿,士人从小学习这一套,但能应付三日课试之文,则青紫之望盈于前,廉耻、义命皆所不顾。[44]有认为是教官失职造成的,“教官失职,学无宗师,廉耻道丧,士习日卑,夫上有缉熙问学之君,而下无明师硕儒以推广德意”[46]卷3。有认为是流俗造成的,如文天祥坦承:“(士)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人?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5]卷3有认为是漕试不当造成的,如曹彦约说:“惟是漕试之弊,积习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诈,恬不为怪,坏士子心术,莫甚于此。”[47]卷11
尽管晚宋时期众多志士仁人对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严厉批判,但基本未扭转士大夫普遍性道德败坏的思想与行为,因而在生死攸关之际,投降变节即为理所当然之举了。
三、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的后果及影响
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因为士大夫为宋朝的执政阶层,“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寄于士大夫之人品高下,即与世道为重轻”[48]卷13,“古今国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盗贼,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24]168
晚宋时期士大夫“一旦临利害得丧、死生祸福之际,鲜有不颠沛错乱、震惧陨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节,弭大变,撑住乾坤,昭洗日月乎!”[24]239这些士大夫大多降元或仕元,形成变节之风气,导致南宋没有足够多的可倚仗之忠义士大夫。
尽管当时有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忠义之士,但若与变节之士大夫相比,则仍属极少数。连文天祥自己也曾悲叹道:“甲戌(1274年)冬诏天下勤王,予守赣,首应诏,意同志者当接踵而奋,已而竟无应者,予遂以孤军赴阙,世事不济殆由于此,哀哉!”[5]卷16而当时以制置使之职坚持抗战到底的文官仅李庭芝。据研究,南宋中期至后期的兵制演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制置使之类的差遣基本上由文臣担任。[49]183-184由此表明,晚宋时期担任制置使一类之士大夫,绝大多数应该是变节的。时人刘一清在姚訔为国捐躯后呼吁道:“使北兵渡江之后,一州州有守臣如姚訔者,忠于国家而死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转移耶?”[3]卷7邵焕在陈炤为国捐躯后即感叹道:“宋之亡,守藩方环甲胄而死国难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仓猝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13]850今人陈得芝指出:留梦炎、方回,一为中朝重臣,一为州郡长吏,代表了宋季相当多士大夫的趋向。[44]这也表明当时降元或仕元为绝大多数士大夫之选择。
那些积极降元或仕元之士大夫,为了表达对元朝的忠心,立即变身为灭宋急先锋。赵淇,以大臣子免铨试,后为刑部侍郎,降元后,“江淮宿将既内附,以公为言。”[13]1072他们一旦降元后,“金城汤池,社稷寄之,一朝反戈,鱼羊食人,入寇招叛,为虏前驱,吕文福、昝万寿等纷起效尤,乱莫制矣。”[2]935元军进入京城后,贾余庆迎逢卖国,令学士降诏,俾天下州县归附,又各州付一省札。[5]卷18而受此变节之风的影响,南宋各地守臣纷纷望风而降。前述,伯颜入临安之后,“阿里海涯传檄诸郡,繇是袁、连、衡、永、郴、全、道、桂阳、武冈皆降”,传檄即归降,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湖南全境。可见,变节之风加速了元朝攻灭南宋的进程。
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还似乎对元朝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宋朝政治是士大夫政治、文官政治。而早在宋亡前,袁甫即上疏曰:“国家平日以礼义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仗节死义之风。”他非常悲观,认为士大夫“乃无一足仗者”“但知迎合取宠,而曷尝以宗社生灵为念,一朝有变,其能尽忠竭节为国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46]卷2历史实际证明,他的奏疏不幸而言中。德祐元年,京官和各地守臣,眼见大势已去,纷纷弃职逃走。谢太后恼怒焦急,命人贴榜于朝堂之上。榜上写着:“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8]8659虽然两宋厚待士大夫、养士,但士大夫只知避难偷生甚至降元仕元,形成变节之风,根本不足倚仗。这对元朝的统治应当带来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仕元做了高官,绝大多数降元或仕元之士大夫仕途并不得意。正如有学者指出:临安旧有一班词臣名士“不甘寂寞,不免纷纷北来。这些高人一等的不过放在词馆史院,任他们消磨岁月;低一点的只有奔走权贵,做新兴贵族的弄儿。”[50]202似乎元朝并不十分信赖并重用这些降元之士大夫。元代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重吏贱儒政策,并不太重视文治,当是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防范。元人苏天爵说:“我国家之用人也,内而公卿大夫,外则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进。”[51]卷17中、下级官僚中,出身吏员占了压倒性优势。而昔日学而优则仕的儒士集团则受到冷遇,即使针对儒士的科举选官考试,也是时兴时废,因此儒士在元朝官僚机构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很难有入仕为官的机会。元诗曾反映此等现象:“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52]初集卷50受此影响,儒士在元朝地位并不高,“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53]卷2元朝这种重吏贱儒政策,自然有宋末士大夫变节之风的影响。
[1]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O].北京:中华书局,1995.
[2]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O].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刘一清.钱塘遗事[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岳珂.桯史[O].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O]//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6]冯琦原编,陈邦瞻纂辑,张溥论正.宋史纪事本末[O]//万有文库.
[7]周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脱脱.宋史[O]北京:中华书局,1977.
[9]毕沅.续资治通鉴[O].北京:中华书局,1957.
[10]郑思肖.心史[O]//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11]史卫民.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4.
[12]宋濂.元史[O].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3]虞集著,王颋点校.虞集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14]揭傒斯.揭傒斯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85.
[15]袁桷.清容居士集[O]//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16]袁桷.延祐四明志[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7]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8]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19]徐元杰.梅野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0]袁燮.絜斋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1]王迈.臞轩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2]黄幹.勉斋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3]周良霄.皇帝与皇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4]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6]张端义.贵耳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O]//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2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O]//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29]杜范.清献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0][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1]关履权.论北宋初年的集权统一[C]//两宋史论.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32]葛金芳.宋代儒学的伦理学转向及其对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影响[C]//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3]程矩夫.雪楼集·送黄济川序[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4][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5]孙梦观.雪窗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6]卫泾.后乐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7]姚勉.雪坡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8]俞文豹.吹剑录外集[G]//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39]吴泳.鹤林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0]洪咨夔.平斋文集[O]//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41]佚名.宋史全文[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2]徐鹿卿.清正存稿[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3]黄震.黄氏日抄[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4]陈得芝.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J].南京大学学报,1997,(2).
[4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O]//四部备要.
[46]袁甫.蒙斋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7]曹彦约.昌谷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8]欧阳守道.巽斋文集[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49]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0]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M].台北:中华书局,1968.
[51]苏天爵.滋溪文稿[G]//适园丛书.
[52]顾嗣立.元诗选[O]//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3]谢枋得.叠山集[O]//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