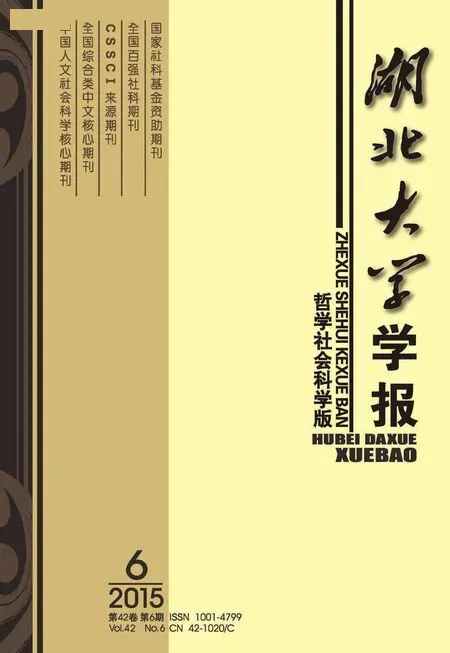审美现代性批评理论症候及其批判——兼评当下一种文学史观
袁苏宁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审美现代性批评理论症候及其批判——兼评当下一种文学史观
袁苏宁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审美现代性”及其变体“晚清现代性”理论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应警觉这一理论症候的发散性效应,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模式,并泛化为一种别样的文化审美理论趣味和意识形态立场。一切唯“现代审美性”论,“用个体的审美感性去反抗现代性对人性的异化”作为其文学史理论纲要,将百年中国文学叙事视为一部抗拒历史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个体审美叙事史,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动因和历史文化品格的改写与颠覆。“审美现代性”先天性的理论缺陷和中国叙事批评的错位移植和过度阐释,将对建构科学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带来危害。“晚清现代性”论者的所谓“现代性危机”及其叙事,对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变革而言,是一个虚拟的“伪命题”。唯有以“历史结构意识”呈现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境遇及不同层面,确立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史学正义”和“诗学正义”,才真正有可能“重整”汉语文学谱系。
[关键词]审美现代性;晚清现代性;历史诗学
一
当今中国文学叙事批评语境里,“审美现代性”极具理论魔力。挟席卷全球现代性反思风潮之余威,持西方现代及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和“颓废”之感性审美立场,既有新锐的理论品格,又有批判历史并指向现实的实践意含。“审美”且“现代”,这一语词的组合似乎天然生成和获得了一种文化批判的伦理优势和美学的终极裁判权。“用审美的个体感性去反抗现代性对人性的异化”,是对“审美现代性”理论的简约和最佳的理解及陈述。中国当代学界对这一新的理论话语的急切和热烈的回应,造成了一种新的理论话语范式和文化精神流向。这既是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视角和审美立场,也体现了一种别样的社会历史态度和意识形态色彩。举凡一切异于或逆于历史主潮的个体呢喃和另类想象,一切边缘的弱伦理趣味抒情和叙事,都在“审美现代性”的光照下,赢得了叙事的合法性乃至伦理与审美的双重优越性。翻旧以为新,倒俗以为雅,以边缘颠覆中心,以逆流翻转主流,是“审美现代性”论者的基本理路和批评策略。一种泛化的“审美现代性”理论的症候群似已形成,某些论者的理论操作已如此纯熟自如,得心应手,悉数现当代作家,解析作品,臧否人物,皆唯“审美现代性”论。耽美,颓废,历史之恶下的个体呻吟,现代化进程下的人性异化与病相,都在这一理论的光照下被艺术化和审美化了。在“后启蒙”时代,还有哪一种思想武器,能比“审美现代性”更具统摄性,更具降佛伏魔无边法力呢?更有文学史论家,欲以此论“重整汉语文学谱系”,将百年华语文学史纳入“审美现代性”理论纬度,再度“重写文学史”,来建构和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叙事线索。近年来声势甚大的“晚清现代性”理论即为滥觞,虽来自海外学者之倡言,却在国内引发广泛呼应,附声蜂起,各种阐发、引申、附会,演化为“晚清文学”热,由此激发的中国文学史批评理论角度和方法的转换,为近年来一大理论批评景观。
“审美现代性”批评且行且远,其理论内涵及边际日渐扩展延伸。有论者提出,由于它对中国20世纪文学具有巨大的阐释能力,将超越和消融影响深远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革命左翼文学”叙事两大文学史观,独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风潮。笔者不认同此论,相反却认为,面对这一理论的发散性效应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颠覆性书写立场,应保持足够的理论警觉和置疑。无论从批评方法论还是理论话语的
社会历史内涵及意识形态立场上,“审美现代性”批评理论都有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其流弊也将对建构和发展中国当代科学健康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危害。
“审美现代性”是“审美主义”的别称而已。“审美主义”是一种生发于现代西方的拒斥历史理念和理性主体,以满足个体心性需求和生命解脱的文化审美潮流。晚近的西方文化学者,遭遇了“现代性危机”的历史境遇,用“审美主义”的立场,参与反思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运动,既是西方人文知识分子介入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方式,同时也赋予了“审美主义”新的历史内涵。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中,较早提出美学现代性问题,明确指出其对抗传统和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文化秉性。“审美现代性”是“审美主义”在现代性知识合法性危机的历史境遇下的理论批评话语。韦伯关于现代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裂带来的社会灾难性后果的揭示,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解构政治学批判,利奥塔对启蒙叙事及其一切现代知识性话语的反思与置疑,都将西方现代以来的“进步”的历史观及其“现代化工程”的历史实践置于审美批判的席位上,将其视为一种强大的异化人性的压制性社会机制,一种历史之恶。现代个人无力抗拒“历史”,个体的感性呻吟和内心的情欲流泻及分裂的精神症候,是现代性压抑机制下的生命哀音。唯有对这一审美体验的抒情和叙事,通过语言解放或话语游戏才能实现个体生命的救赎和解脱。它虽无法颠覆历史,却可以浸染和颠覆语言及文化精神结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和审美救赎之道,“审美现代性”理论具有某种社会批判的革命性精神意向,然仍不脱文化批判静观、反思的致思窠臼,带有非历史主义的局限性和虚幻性。
“审美现代性”理论进入中国文学批评领界大约在新世纪之交前后,引发学术新潮并延续至今。由海外学者李欧梵、王德威首倡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现代性”批评学派的领军人物。“晚清现代性”及其“想象中国的方法”不仅是中国文学史叙事的新命题,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更新。然而这一新的理论路向是推进了中国文学史学科研究的深化,还是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和分裂?试图重新整合中国文学史多向思想路线的统摄性“审美现代性”理论视角,是否会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迷津和谬误?迄今所有的探讨性研究,都将“问题”推向矛盾重重的境地,所衍生和激发的有关中国现代性历史认知和审美判断,反而使得中国文学史叙事潜在的理论冲突和矛盾更为尖锐和剧烈。
所谓“对20世纪中国文学巨大的阐释能力”,是“审美现代性”理论的魔力所在。将文学批评视作一种理论逻辑的推演,迷恋一种普适的超越历史和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理论法则,而无视审美体验的独特的历史内涵和社会认识经验,无视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独有的“中国式境遇问题”,将会产生怎样的历史语境错位和理论的悖论与谬误呢?唯“审美现代性”论,对中国百年的历时性文学叙事,皆置于“现代性危机与反思”这一西方当代共时性理论命题下并作过度阐释,其实是将复杂的文化审美问题简单化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审美,中国与西方,是一个交织多重话语和思想印记的场域,也是一个充满了互渗共生、矛盾对立的悖论式的演进过程和形态。“矛盾式的思考矛盾”,应是理论批评应有的学理智慧和基本的思维方式。唯有以“历史结构意识”诠释百年中国文学,呈现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境遇及不同层面,才真正有可能“重整”汉语文学谱系。笔者忧虑的是,当“审美现代性”形成一种理论症候,一种批评话语模式和霸权,并泛化为一种审美文化趣味和社会历史立场,对当代中国叙事伦理的重建,其负面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二
“晚清现代性”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批评的一次逻辑推演和话语操练,也是当下中国“审美现代性”批评诸多观念的汇集和发散源头。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似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叙事纲纽。王德威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点评的着力和用心,便是刻意用声色艳情等私人领域来对抗公众领域,用风花雪月来对抗国家大事,认为正是这些无“行”文人的寓教于恶,真正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潜在动力,从而翻转五四新派批评家对鸳蝴派腐俗的文化界定和伦理评判。由此推伸开来,“我以晚清的四个文类——狭邪、公案小说、谴责、科幻——来说明彼时文人丰沛的创造力。而这个文类其实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1] 16。“晚清现代性”论者的理论热情始终瞩目于那些“对欲望意外的欲望,对正义实践的辨正,对价值流动的
注目,对真理与知识的疑惑”[1] 16的另类叙事文本,而对晚清维新及革命诗文表示不屑或置于不顾。崇“晚清”而贬抑“五四”,不只是将20世纪文学史的源头向前移置了,重新界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更重要的是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文化逻辑,颠覆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内涵和审美精神品格,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动因和审美历史品格的双重改写。于是“晚清鸳蝴派小说”、“邪狭小说”寄托闲情、娱人娱己的文字,恰是小说世俗本性的回归,是对梁启超们“小说界革命”主潮的抗拒和消解,而这一边缘姿态及批判性思考,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动因。同理,五四文学的典范意义,不是启蒙理性精神和“感时忧国”,而是对启蒙主义的置疑和批判。近年来不断推出的鲁迅的“现代性”解读新论,即为例证。“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有资格成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代言人,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作品见证了传统的阴影下,书写现代性的风险与暧昧”[2] 27。所谓“被压抑的现代性,泛指五四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2] 11。此处所谓“主流”,自然是指启蒙理性精神、革命与救亡、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叙事”。一场始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伟大现代化历史社会变革实践及其为之“呐喊”呼应的历史叙事,在“审美现代性”论者看来,不再具有“史学正义”或“诗学正义”,相反,恰恰是对历史暴力——所谓“现代性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与心理机制加诸国人身上的规范和训戒”的抗辩,才真正体现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审美精神。
“晚清现代性”论者仿袭他们的现代西方精神先导们的学术姿态和精神立场,寻找和建构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现代性异化”力量,展开中国的“现代性反思”文化批判运动。问题并非在于能否对外来思想理论借鉴和移用,也不仅在于中西历史语境的差异而导致的理论误用和偏差,而在于“审美现代性”批判的某种先天理论缺陷和中国“晚清现代性”论者学理上的失范。视历史理性为一种历史之恶,一种异化人性的压抑性社会机制,惟有个体之耽美或滑落现代文明之外的“颓废”,才体现现代个人的救赎之道或心性关怀,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现代或后现代文化人本主义批评立场。“晚清现代性”将这一理论普泛化,套用和移植到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百年历史叙事语境,名其曰“全球化现代性反思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叙事”。也许偏差和误读永远是“理论移植”的某种基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挥散不去的理论迷雾中一直浮现着现代西方理论的“幽灵”。一如西方各种现代文化批判思潮共同的理论特质和思维方法,将“现代性危机”及其“人性异化”视作“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并抽象为一种普泛的文化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历史主义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历史活动只能是人的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因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揭示和批判着力于制度和实践层面,简言之,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造成了现代性的异化与危机,资本原则及其物化逻辑,作为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制下的社会机制,直接造成了人的精神异化和人与社会的对立。将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对之展开文化反思批判和个人主体的审美内省,是“审美现代性”理论的理论特质,其虚幻性和理论限度是显然的。文化批判和审美心性超越,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统治法理,也无法建构现代个人主体,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中国20世纪现代化历史进程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思想文化脉络。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先进性”的理性精神和“革命”的思想理念始终充当变革现实的时代先锋的角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演变发展而来的由中国革命先进政党引领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在对传统的变革中,始终贯穿着对殖民主义的抵抗和对资本主义弊端的警醒和批判,如汪晖所言,带有鲜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征[3]。而这一革命先进政党的“思想纲领”,到21世纪的当代中国,依然是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路线。它的革命性和先锋性精神及其历史实践与“人的解放”是高度统一的,“个人解放”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始终是相互依存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主体导向是现实主义的历史情怀。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潮流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期,都未能获得广泛的回响和呼应。这是由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文化特性所决定的“中国叙事学”。“晚清现代性”论者的所谓“现代性危机”对中国文化变革和发展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一个虚拟的文化叙事。“晚清现代性”论者放大中国文学叙事中的个体感性情愫,刻意寻找和制造个体和历史的紧张对立关系,并赋予它们对抗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审美精神。这既是对现代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移用,偷换了“现代性”概念的理论内涵,也反映了论者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
晚清审美现代性批评散发着一种“恶”质的美学品质。颓废,病象,衰朽,情色,涕泪飘零,末世魅影,既是20世纪文学史叙事中幽幽叙说的审美情感意象,也是抗辩中国现代性历史的精神力量。“这些憧憬解放的学说被神圣化,竟成为压抑主体及主体的最佳借口”[2] 11。王德威在一段访谈中陈言,这些图腾与禁忌既奉现代之名,在技术层面上往往能更有效率,也更“合理”地制约我们的言行。因此所带来的身心伤害,较诸传统社会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鲁迅只剩下了对“疾病与诡奇的偏好,以及他对梦境、非理性死亡的痴迷”,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落寞,张爱玲的逃离和海外飘零,颂歌诗人闻捷在文革中的自杀,乃至顾城和海子的自绝弃世,都成为现代“历史之恶”下的个人命运的叙事和抒情象征。本文此处无意辨析个体命运与历史运动间复杂的纠葛及根源,但例举文学史上某类作家的个人悲剧,并一概归结为“现代历史暴力”对审美个体的戕害和异化,既失偏颇也缺乏论辩的力量。个中就里,既有历史前行中的偏差,也有作家既有艺术风格在新时代的困惑和不适。至于鲁迅,何只只有对“非理性和死亡的痴迷”?显然这只是论者刻意展示和理论包装的鲁迅。海子卧轨山海关,有论者问道,是源于对现实的绝望还是来自诗人内心的黑暗?我们无从知晓,但指其为“殉诗”,对诗人“自杀”的圣化也不厚道。中国现代历史及叙事,当然要比“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呈现出单一面相要丰富和复杂得多,亿万中国人的现代历史大合唱,既有个人的单音独鸣,更有众声合一的激越昂扬的主调,“战地黄花分外香”,“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革命浪漫主义和响彻云天的乐观主义人民文学抒情,何曾不是一种最“现代的”审美精神品格的表达。《小二黑结婚》里人民政府反封除霸运动下一队新人的喜庆大团圆,《创业史》中梁生宝们解放后渴望集体致富的劳动大生产,无不是现代主体性解放欲望释放的审美叙事。将“革命”升华为一种审美精神体验,将个人解放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的变革中,是中国20世纪文学最为独特,也是最为精彩的现代审美叙事精神。
三
“审美现代性”及其“晚清现代性”理论批评尽可凭空凌虚展开它的逻辑推演,以一贯之纵论百年中国文学叙事,但终究还是要面临和回归到一切审美文学理论的基点,一个缠绕所有中外文论家的理论玄思上。即“历史与审美的”关系问题,诸如二者之间孰为本体或优先性,它们之间复杂的关联及其表述,以及各自持守的疆域,份际和限度,即所谓“历史诗学”理论。中外形形色色的文论都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答案和结论,然而这些结论和答案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致相互之间无法通约,所以至今仍是审美批评理论上的“无底之迷”。晚近出现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试图调和、折中历史性和叙事性复杂的矛盾对立,但依旧陷在“表述优先”的历史的文本性理论泥淖中,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和审美主义理论的两大话语体系的分野,并未消融。命题虽然古老,理论话语形态却俱时翻新。“审美现代性”和“晚清现代性”理论与审美主义精神传统的理论亲缘关系自不待言,偏倚文学的“虚拟架空”性质,坚持审美的超越性立场,但又带上了“后现代”诸学的理论色彩,尤其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转向”及历史的叙事本性理论,福科的权力话语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化批评。因而“晚清现代性”批评的理论资源和特征,显得尤其复杂、矛盾和含混,也使得这一理论阵营的思想特征和意识形态立场可疑难辨。
“后现代”文化审美批评在传统审美主义的基点之上,再度引入了“历史性”因素,对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和理论热情,是不同的“后现代”理论派别文化批判共同的旨趣所在。然而“历史”的再度回归,是在历经了“语言论”文化哲学思潮洗礼之后的回归,历史被视为一种拥有自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附着语言的特性、想象的虚拟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历史性”和“审美性”关联被强调了,但“语言论”下的调和和折中也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模糊了,乃至取消了二者之间的所指界定。批评家可以在历史和审美之间随意游走,不断变换历史学家和诗人的文化身份,既可以用历史因素索解作家精神困境,也可用叙事文本的人物命运坐证和指实“历史的暴力”。王德威们的理论操弄如此得心应手,在历史性和审美性之间左右逢缘。他们可以在左翼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读出女性青年革命者最终对革命虚幻本质的彻悟,用文学叙事性消解了革命历史性,又用沈从文50年代的个人落寞,指证一个时代的衰败,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叙事因素。这里的问题是,“晚清现代性”批评理论究竟是一种历史学,还是一种历史诗学?
着力于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体现了现代审美文化批评介入社会现实的理论热情,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唯美主义划清了界限。但文本中历史与审美的繁复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叙事伦理。有自身的疆域和限度,文本想象的历史“象征”和“寓言”特征,并不能简单等同类比非语言叙事的“历史”。在历史的信史和小说叙事的虚幻之间穿越,在二者的繁复往来中相互印证,取舍之间,极易言之凿凿,却谬之千里。“晚清现代性”论者将百年中国文学史视作抗拒历史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个体审美叙事历程,视作一部政治乌托邦想象瓦解的寓言,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另类书写。然令人起疑的是,中国20世纪革命实践的“历史之恶”或“现代性之病相”到底是论者的审美判断还是对历史本质特性的政治论断?如果是前者,只是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的历史诗学而已,若是后者,就有跨界僭越之嫌。王德威们并没有打算恪守审美精神的领地和小说的语言叙事自足系统,而是屡屡侵入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历史时空。在消解五四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背后,更是直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叙事”的政治立场。因而“晚清现代性”批评的“审美主义”或“审美现代性”理论不仅是一种“历史诗学”,也是一种“历史学”,所谓对中国20世纪文学“诗学正义”和“史学正义”的解构和置疑,便显示了这一理论话语的某种僭越。这种僭越,是源于论者的解构理论热情及其逻辑,还是源于批评者的某种偏狭的意识形态立场?
何谓“史学正义”?“诗学正义”何为?在后现代语境下何人或何种史学理论竟然能有史学正义的自信?用西方现代解构主义史观来匡正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和脉动,怎敢用“正义”的概念来标榜和自许?所谓“全球化现代性反思语境下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叙事”及“用审美的个体感性去反抗现代性对人性的异化”,既非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历史动因和精神品格,也不是20世纪主流的“中国叙事学”和“历史诗学”。视“启蒙理性”和“革命理念”为一种“历史之恶”,一种异化的压制性的现代性思想霸权,是中西语境错置的“反历史”的认知,一种典型的“解构主义”的后现代的西方语境和文化逻辑。启蒙理性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理念,也是最具时代特征的超越性的审美意向,启蒙主义文学叙事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先导和主潮。“左翼革命文学叙事”是启蒙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它将人的个性解放推升到人的社会解放,并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批判。革命理念、革命精神的先锋性和审美性的热烈想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激越、最华美的乐章。“与西方不同,中国‘现代’的动力基础是中国式的政党实践”[4]。政治与审美的关联,是中国文学演变的现代性境遇,因而“革命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变革及历史叙事最重要的特质。坚持“启蒙主义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的关联性、统一性,坚持“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革命现代性文学叙事”的主流地位和合法性,是重整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谱系应有的原则和立场。“晚清现代性”理论当然无从体现所谓“史学”或“诗学”的正义,反是自曝其学理上的悖谬和意识形态的虚妄。在中国百年来的滔滔现代化历史洪流前,一切唯现代西方是尚的高蹈的宏论,都将显露自身的苍白虚弱。中国现代史的“正义”是由中国先进政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所书写的,其发展方向也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宏图的展现所确证。正是这一“史学正义”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和先进文化精神及其“诗学正义”。百年中国的文学叙事,是波澜壮阔的史诗和几代人前行的呐喊,还原和重建百年中国“宏大叙事”,建构中国现代先进文化,才是文学史书写“想象中国的方法”和应有的“诗学正义”。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
[4]张志忠.现代性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J].文艺争鸣,2009,(1).
[责任编辑:熊显长]
[作者简介]袁苏宁(1958-),男,湖北嘉鱼人,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12-15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5)06-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