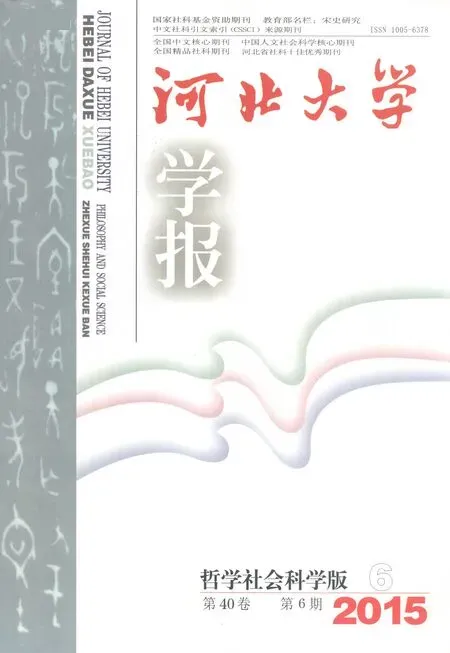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双构性叙事策略
郭晶晶,岳爱华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承德 067000)
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双构性叙事策略
郭晶晶,岳爱华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承德 067000)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通过对衣、食、住、行等显在之“技”的表层叙述与刻画,揭示了小说深层的潜在之“道”,即生之文明、活之滋味、居之情调、行之守真。在双构性叙事策略中“技”与“道”相互生发与推进,彰显出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所包涵的文化底蕴。
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双构性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满族女作家叶广芩以“家族系列”和“京剧系列”等满族题材小说,展现了她对自己簪缨家族及其所属民族的独特认识和感悟。邓友梅评价其小说“叙事写人如数家珍,起承转合不温不燥,举手投足流露出闺秀遗风、文化底蕴”[1]4。的确,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文本的角度细读,我们可以感受到八旗子弟的生活气息、没落贵族的苍凉身世、历史变迁的世事无常;从叙事的角度观照,这些小说运用了结构之技和结构之道的双构性叙事策略,即在小说叙事中采取一明一暗的双结构线索。明,即显在的“技”的层面;暗,即潜在的“道”的层面。通过“衣、食、住、行”等显在之“技”的铺叙与刻画,揭示出潜在之“道”即生之文明、活之滋味、居之情调、行之守真。“结构之道用以笼罩全文,结构之技用以疏通文理,二者的功能是具有统摄和具现之别的”[2]。正是在这种明暗相互生发、道技相互撞击之中产生出文化底蕴的升华。
一、衣之技与生之道
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最鲜明、最直接、最惹眼的区别是人讲究穿戴而动物不然,因此,“衣”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人类生存的文明境界。在这里,“衣”指广义的穿戴,既包括穿在身上的衣帽鞋袜等衣物,也包括戴在身上的配饰。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通过对满族人穿戴之物的色彩、款式、质地、大小的精细刻画与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满族人生存的文明境界。
在《梦也何曾到谢桥》[3]251-265中,叶广芩描写了旗人的服饰,一件水绿绲边缎旗袍,低领连袖圆摆样式,古朴典雅、清丽流畅。这是一件极其惹眼又内蕴故事的旗袍,是小说的引子。文章开头便写到这件垂挂在衣架上的,样式、材质、做工都无可挑剔的,处处都透着不凡的旗袍,仿佛在静静地与我对视一般。这件神秘的旗袍勾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之后叶广芩才将旗袍所引出的家族往事娓娓道来。“我”的父亲是世袭的“镇国将军”,家有三位太太、十四个儿女,但出于对早逝六哥的怀念和大宅门里森严秩序的厌恶,父亲又在雀儿胡同包养了一个宫廷裁缝的遗孀谢娘,因为谢娘有一个和我六哥同龄同名的儿子,父亲经常以年幼的我为幌子去谢娘家,并告诉我六儿就是我的六哥。在谢娘家,我看到了一个与平时不一样的父亲,会舒坦地喝“高沫儿”、会吃杂合面条就大蒜、会光着膀子和泥修房子,我缠着手巧的六儿给我做小布人身上的水缎绿旗袍,六儿却用碎布给我做了个灰耗子,我发现其实六儿并不喜欢富贵的我和父亲介入他的家。最后,谢娘在我母亲的撮合下再婚了,六儿在谢娘死后杳无音讯。直到四十四年以后,我找到了雀儿胡同,看到满头白发、眼睛浑浊的老人六儿,隔着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当年的“王八丫丫”与六儿终于能心平气和了,六儿告诉“我”其实自己与金家没有丝毫血缘关系,我一片茫然地收到了“六哥”做的水绿缎子旗袍。叶广芩通过一件旗袍,勾勒出满清皇亲贵胄之家的隐秘。旗袍的两次出现,讲述了一个从垂髫到白发的沧桑故事,将三代人的历史时空紧密相连。父亲的执着和六儿的倔强,共同讲述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的人生大道。
在《豆汁记》中,莫姜的一根梳两把头用的翠绿扁方,晶莹剔透、温润可爱,却有黑色的微瑕。《雨也潇潇》里,慈禧赏给“我”祖母的一枚金镶珠石云蝠帽饰,精美绝伦,当年只有皇亲显贵才有资格佩戴,可这样贵重的饰品,却时刻提醒着二格格嫁给商人子的耻辱,被她的儿子还给金家。从这些饰品的故事中,娓娓道出了大羹必有淡味,大巧必有小拙,白璧必有微瑕的人生哲理,简单而又深刻。
服饰具有实用、审美和象征的功能。一件满族女性服饰在它所属的家族甚至是历经数十年依旧具有它的基本功能,通过对服饰的描绘与刻画,体现出叶广芩对往昔岁月贵族精神气质和生活品味的眷恋与认同,既于字里行间营造出一种怀旧的氛围,又在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关注这种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处境与变动,并对其在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不断挤压下逐渐走向没落的境遇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与无奈。这种复杂的情感使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表现出一种诗意的温情和沉重的反思,于眷恋中有批判,于批判中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情怀。
二、食之技与活之道
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是要命的事情,可有了吃的,吃什么和怎么吃就要看人的用心了。饮食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饮食讲究的是通过烹饪者的调制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记载 :“凡味之一,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之变,人为之纪……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5]在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中,饮食之技所承载的大道,就是人通过饮食的全部细节来品尝、感受生而为人的满足与幸福,感悟人活着的滋味与乐趣。
在《曲罢一声长叹》中[3]289-300,七哥舜铨做的糖醋白菜,菱形的白菜心,梅花状的胡萝卜,吃时佐以鲜绿香菜,酸甜适中,好吃好看。冬至祭祀时要吃白肉,纪念祖先艰苦的征战生活。白肉晶莹透明、肥瘦相间,醇香美味。在《风也萧萧》中,母亲在立春时节烙的春饼,烫面混合香油,吃的时候卷上酱肉肘子、小肚丝儿、豆芽菜等等,再佐以甜面酱、大葱丝儿,真是满口留香。特别是在《豆汁记》中,从复杂的松肠、醋焖肉、鸽肉包、熟鱼活吃,到平凡的窝窝头、豆汁、麻豆腐,美食的制作过程令人眼花缭乱。厨艺最精的是身世坎坷的莫姜,她心灵手巧、品性高洁,美食因她而变得“赏心悦目”,绽放异彩。叶广芩在对美食烹饪不厌其烦的叙述中渗入了丰富的情感内涵和复杂的人生感悟。烹饪者要使五味调和,就要耐心运用“调”的本领,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享受生活,体验活着的滋味的过程。继而让人悟出“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6]103,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最珍贵的亘古真理,人伦日用、食色性也,于饮食之中洋溢着生之欢乐。
叶广芩通过表象的饮食叙述生发出对“活着”的大道的体悟,在道与技的推进中,饱含着她对旗人民俗的怀旧情绪,表达了她对传统的由“土地”带来的稳定生活和安全感逐渐消失及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日渐失落的深切关怀,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彰显出一种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
三、住之技与居之道
住,就是人们在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劳动手段建造的具有挡风、遮阳、避雨功能的可供人们栖身、活动的实体空间里栖息。但是居之道,远远不止于人的肉体归宿和世俗之家,而是人在居住中体现出的文化精神,显示出人的气质与品位。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通过对满族建筑的刻画,彰显出满族人居住之气派与情调。
在《谁知乐府凄凉曲》中,描写了爱唱戏的金家美伦美奂的戏楼 :“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7]135这样的建筑,是为了玩乐,却又不仅仅是为了玩乐,而是透着高雅、专业和认真,体现出主人优雅的生活情调。在《瘦尽灯花又一宵》中,年幼的“我”好奇于舅爷高大的府第过年却贴着白底镶蓝边的春联,一问才知其中大有讲究,清朝只有王爷的府第才有资格贴白联,他们才是高高在上的皇亲宗室,全北京能贴白联的人家没有几户,都是很有脸面的人家。贴白春联彰显的其实是一个家族的矜贵身份和显贵气派。
在《不知何事萦怀抱》中,建筑学家廖世基阐述了自己对东直门的看法,说它是通正气之穴,有息库之异……震位属木,五季占春,五色为青,五气为风,五化为生,是座最有朝气的城楼。体现出中国建筑的气运,中国建筑的气势。这里包含了很多对建筑历史的回顾和对建筑艺术精神、文化精神的阐释,“太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8],建筑和人相同,皆是生死悠悠,一气系之。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之大道。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通过对传统建筑和居住环境的描写,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充满世俗美感和彰显文化精神的家园,使人物的灵魂从浮躁的尘世中得到涤荡与升华。正是通过精细描摹满族人的居住环境,展示出居之文化底蕴,带有一定的文化寻根意味。
四、行之技与真之道
行在这里专指人的举止行动,指人在日常行为中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在活动,真指遵从人性的本然、自然和应然的规律。人在日常行为中遵从了人性的天然与本真,才能避免矫情、雕琢、违心,才能欣赏、体验到真正的美。《庄子·渔父》中曾提到法天贵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9]。取法于天,就是说人在行为上应该效法自然,不要过多地束缚压抑自己。在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中,满族人在日常行为中体现出他们回归人情人性本源的大道追求。
在《状元媒》[10]21中,叶广芩描写了消失的行当“锔碗”,“锔碗的拿出一张小弓……在裂缝的两边钻出对称的两排细孔……用大小合适的铜锔子将裂缝铆上,抹一层白瓷膏就算齐活了,修好的碗跟新的一样”。对传统行当的描写、对精湛技艺的刻画,展现了旧时代老百姓生存的艰难,但困窘并非消沉,反而激发了他们对待生活的智慧,朴实而又温暖。
在《大登殿》中[7]93,刻画了母亲(盘儿)的形象,敢于抗争、独立自主,极富人格魅力。母亲是下层旗人的后代,居住在朝阳门外以贫穷杂乱著称的南营房一带。父母去世后,为了抚养年幼的弟弟,漂亮的母亲坚持不嫁人,直到成了三十岁的老姑娘。后来无意中被贵族后裔的父亲相中,成了父亲的填房。洞房花烛之夜,母亲才知道父亲并非比自己大六岁,而是十八岁,并且家里还有一位多病的如夫人。无所畏惧、刚强不屈而又极重名分的母亲不满被欺骗,大闹洞房。甚至为了讨个公道,抛下荣华富贵,带着弟弟远走天津去找状元媒人理论。作为一个出身贫寒、地位低下的弱女子,母亲为了尊严几经周折,显示出一种独立的人格和可贵的气节。母亲的到来给陈腐的金家大宅门带来了鲜活的市井气息,与父亲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的落寞贵族气不同,母亲的性格是豪爽泼辣的。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家中一有难事一定是母亲出头露面,儿女在外闯祸受气,父亲连大声说话都觉得有辱斯文,只有母亲与人较真,为自家孩子打抱不平;日本宪兵队来家里检查,父亲吓得在西院侧着耳朵听动静,母亲却在前院抵挡周旋,保护家人的安危。母亲出身于社会底层,却充满高贵与尊严,她是儿女的避风港,是金家的主心骨,母亲以生命树立起的坚定信念体现出民族文化精神的可贵之处。叶广芩笔下的女性,坚强而又善良、忠贞而又自尊,无论是出身尊贵还是地位低下,都表现出贵族精神中最稳定的内质,正是这样的女性,用柔弱的臂膀承担起了传承民族文化、拯救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闪耀着可歌可泣、可钦可敬的人性光辉。
学者赵园认为,北京人多礼,缘于满族文化。文化塑造人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化环境使然,礼仪进入了最日常的思想行为,成为满族旗人的“本能”。在《风也萧萧》中,刚进家门的舜錤,抢上前去、规规矩矩地给老母亲请安,问候了家中一切,然后落座,接受妹妹的敬茶和弟弟的问候。在《雨也萧萧》中,早年被撵出家门的二格格舜镅,听说母亲病危,跪在雨地里泪流满面地不住磕头,以尽自己的一点孝心。在《曲罢一声长叹》中,以“儒”来概括老七舜铨的一生,老七舜铨眉宇间透着祥和之气,居心宜直、用情宜厚、表里如一。他是事亲至孝的儿子,为了遵从母愿,他放弃了与柳四咪的真挚爱情;为了让病入膏肓的母亲高兴,他娶了各方面都与自己不相配的织袜女工;为了赡养母亲,他坚持住在破败不堪的老宅。他是和蔼可亲的兄长,经常带着小妹妹出去玩,给妹妹买乳酪、素丸子汤、奶油炸糕,对妹妹细心关照、宠爱有加,名为兄妹实则情似父女。他是温良恭谦的君子,面对有着夺爱之恨的大哥舜铻,他仍然畅叙亲情、毫不记仇。晚年的舜铨,在纷乱的时代安居家中、疏离社会,恪守家族的贵族气质和儒家的文化传统,以孱弱的病体和孤独的灵魂寄情于琴箫、沉湎于书画,坚持自己的人格操守。当礼仪内化为生命活动的自然节奏,就形成一种人格、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
满清旗人有“铁杆庄稼”的特权、有教育的优势,所以他们虽不劳动却温饱无虞,虽无职业却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极其讲究闲雅、精致的生活情调。在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中,遛鸟、斗蟋蟀、赏古玩、练书画成为人们惯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京剧的喜好,更是达到江山社稷可以丢弃、民族权威可以无视,唯有京剧需常伴相随的地步。在《谁知乐府凄凉曲》中,讲述了大格格戏人合一的人生,写大格格优美的唱腔,“忽而如冲天白鹤,天高阔远;有时低如絮语,柔肠百转……”[7]173这样的人生是高雅的,这样的爱好是执着的,也只有在这样的娱乐活动中,平时严格的规矩、礼仪、等级、秩序才能被打破,没有尊卑、亲昵接触、出乖露丑,演戏看戏成了狂欢式的生活,甚至是“翻了个儿的生活”,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追求。王元化先生谈到京剧时说,“近两百年来京剧在民间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7]7。《逍遥津》中的男旦钮青雨终日沉迷于京剧之中,活在戏里、活在旗人优裕洒脱的贵族心态里,甚至迫于淫威,成为日本人玩乐的工具,为人所不耻,但最后他却以枪杀日本要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慷慨悲壮。可见,传统京剧中蕴含的忠孝信义的精神、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就是在这经久不绝地浅吟低唱中潜移默化,成为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参照。
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通过对满族人日常行为的书写,生发出对人情人性守真之大道的深情呼唤,可谓是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
纵观历史,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双构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叶广芩的满族题材小说,使其表现出一种结构的双重性。它以结构之技呼应着结构之道,又以结构之形暗示着结构之神,或者说它的结构本身也是带有表里呼应的双构性的,以浅层的技巧性结构蕴涵着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呼唤着、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叶广芩通过她的满族题材小说,让人领悟到平凡人脚踏实地的世俗生活本身就具有一种坚韧之美、顽强之力。此外,面对逐渐消逝的满族语言、满族服饰、满族饮食、满足职业、满族礼仪、满族娱乐甚至是满族精神,叶广芩用她的满族题材小说,复活了民族的古老记忆、连通了民族的文化之根,保护了民族之神韵、传承了民族之精魂,为满族文化作传、传统文化作传、为中国文化作传。正如叶广芩自己所言 :“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337”。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2]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3) :28-30.
[3]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9.
[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 :中华书局,1990:26.
[5]伊仲容.吕氏春秋校译[M].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8 :13.
[6]陈宏谋.养正遗规[M].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7]叶广芩.黄连·厚朴[M].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3.
[8]高诱. 淮南子注[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35.
[9]庄周.庄子集注[M].沙少海,注释.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331.
[10]叶广芩.状元媒[M].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1]王元化.清园谈戏录[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2]周燕芬.文学观察与史性阐述[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侯翠环】
Double Constitutive Narrative Strategy of Ye Guangqin’s Manchu Novels
GUO Jing-jing,YUE Ai-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Ye Guangqin’s Manchu theme novels,describes and characterize the surface of the “technology” from clothing, food,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and then reveal the deep potential of the novel “Tao”,namely the civilization of life,the taste of life,living in a mood,and acting according to nature. “Technology” and “tao” in Ye Guangqin’s Manchu novels mutually rely on and propel each other, revealing the deep cultural deposits of Ye Guangqin’s Manchu theme novels.
Ye Guangqin; Manchu novels; double constitutive narrative
2015-06-20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研究》(HB14WX017);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叶广芩满族题材小说的民俗学研究》(201322)
郭晶晶(1982—),女,辽宁省黑山县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
A
1005-6378(2015)06-0075-05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