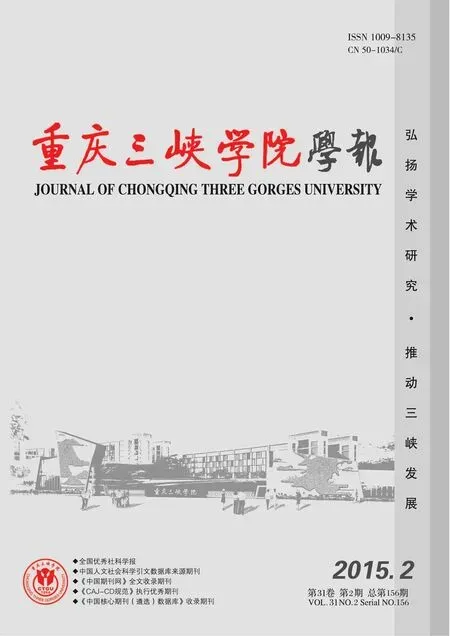浅析汪野亭与邓碧珊瓷板画创作异同
凌江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汪野亭研究
浅析汪野亭与邓碧珊瓷板画创作异同
凌江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汪野亭与邓碧珊是新粉彩文人瓷板画的典型代表,前者主要创作山水瓷板画,后者开了文人鱼藻瓷板画的先河,对文人瓷板画的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通过比较汪、邓两人在诗书画印的和谐统一的共同追求以及在绘画中对待“形”与“意”的不同侧重,可以看出汪野亭和邓碧珊都高度重视瓷板画的雅致,但对瓷板画的“形”与“意”的侧重不同,显现了绘画上的“以形显神”和“以神统形”两种不同的绘画观念。
汪野亭;邓碧珊;诗书画印;形与意
主持人:黄念然
主持人语:“珠山八友”全面地继承了浅绛彩文人瓷艺家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旨趣,并通过粉彩这一艺术形式弘扬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瓷器制作工艺。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诗、书、画三位一体的美学特征和瓷艺装饰与瓷画并存的审美特征,同时在风格上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本期研究中,我们主要研究汪野亭同邓碧珊及程意亭在瓷绘创作方面的审美异同。一篇通过对汪、邓两人在诗书画印的和谐统一的共同追求以及他们在绘画中对待“形”与“意”的不同的侧重的比较,分析了汪、邓二人对瓷板画的雅趣的高度重视,也分析了他们基于瓷板画的“形”与“意”的不同侧重而显现出的绘画上的“以形显神”和“以神统形”两种不同的绘画观念。另一篇则从生存哲学的视角剖析了汪野亭山水画与程意亭花鸟画在求得心灵安顿的绘艺创作中所呈现的不同哲学思考与审美旨趣。
珠山八友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景德镇的一个瓷画流派,他们是一群有着友谊关系,又有着相同的艺术追求的一批瓷画艺术家。他们承继和发展了浅绛彩文人山水瓷画,并发展成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新粉彩山水瓷画。珠山八友走的是继承创新的道路,在“浅绛彩文人山水瓷画”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创造性地将文人画应用到了粉彩瓷画艺术中。山水、花鸟、人物是他们常用的意象。汪野亭与邓碧珊是珠山八友的代表人物,前者主要创作山水画,是汪派山水瓷画的创始人,后者主要创作鱼藻,开了文人鱼藻瓷画的先河。
虽然说汪野亭和邓碧珊在绘画的内容选材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对于瓷板画的形与意的侧重也有不同,但是由于两人都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他们对瓷板画的雅致,对瓷板画诗书画印的和谐统一,有着共同的追求。本文将从汪野亭和邓碧珊在对瓷板画的诗书画印的书卷气的共同追求以及他们对于瓷板绘画的“形”与“意”的不同的侧重来探讨汪野亭与邓碧珊文人粉彩瓷画的异同。
一、“诗书画印协调统一”的共同追求
文人画的显著特点是对诗、书、画、印的重视。在画上题字作诗,以诗文直接来配合绘画,使得诗画融合为一体,通过诗文来突出画面的意蕴,来增强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是文人画艺术家们的共同追求。汪野亭与邓碧珊都是文人瓷板画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创作不受成法的约束,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水墨渲染的水墨画的范畴。汪野亭和邓碧珊创作文人瓷板画时,都很注重文人画特色的显现,注重书卷气的流露,特别注意题诗,书法入画。
从两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方面来说,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促使其文人与画工的双重身份在两人身上有了明显的体现。汪野亭出身在江西乐平,在去景德镇之前,他跟随名师学习画花鸟。后来去景德镇,在瓷板画的创作方面,他起初学浅绛彩,后转到粉彩山水,他具有画工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在艺术修养与文化修养方面有很大的优势。邓碧珊早些年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因此他的文学底蕴深厚,除此之外,书法也是他所擅长的。他也没有像一般的绘瓷艺人经历的师传学艺经历,因此,他的作品一出现就有着浓厚的书卷气,个性鲜明。因此两人对于瓷板画中诗书画印的和谐有着本能的追求。
从汪、邓两人的作品来看,作为文人瓷板画创作中的主要代表的汪野亭瓷板画,诗、书、画、印的融会贯通的审美特点必然就是其主要特性,诗书画印的因素在汪野亭的大多画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就汪野瓷板画的具体作品来说,汪野亭创作的作品均有画中题诗或落款的惯例,具有很浓厚的书卷气,如汪野亭的瓷板山水画便有题诗“谁将笔墨写秋山,点缀烟霞尺幅间。预访高人在何许,寒林渺渺水潺潺”这一题诗使得诗与瓷画浑然为一体,增加了瓷画的写意性,获得逼真的结果。除此之外,汪野亭还特别注意书法的特征与瓷板画的合作。“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1]28,从董其昌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认为绘画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运用不同的书法,如隶书,行书,草书,已达到绘画的要求。汪野亭在瓷板画中的追求正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诠释,使得他的瓷板画具有文人画气质,有很浓的书卷气。
邓碧珊所绘的粉彩瓷板画多数题有行草诗文,所题的诗不仅与画融为一体,并且极其高雅。邓碧珊的瓷板画中有题诗:“弄萍攫破镜花秋,掉尾扬鳍得自由。最怕碧峰岩下影,风藤如线月如钩。[2]”不但与画相得益彰,并且读来意味无穷。此外,邓碧珊的书法有苍劲的气势。正是对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才体现出其鲜明的个性以及浓厚的书卷气。
通过上面的对比发现,虽说汪野亭和邓碧珊对于绘画内容题材等方面有不同的追求,但是汪、邓两人对于诗书画印的结合方面是有共同的追求的,在这一方面达到了和谐统一,形成了他们具有书卷气的特色。
二、“形”与“意”的不同偏重
王履谈为什么创作《华山图》时说过:“图传神,记志事,诗道性情,此三者所以不能已于太华之游也。……常而可以不图者,……然其不谓之神会心得矣夫。[3]”
在这段话里王履主张的绘画观念是侧重于对“形”的描绘,把“以形显神”作为绘画的取舍标准。除此之外,在这里他还反对为了达到写意性放弃对于形的描绘的绘画观念。不过他即主张对于“形”的描绘,同时也认识到了意的重要性,他认为“形”的描绘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意”的表达。不过形也很重要,没有了形似,“意”的表达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形”与“意”二者的关系中,他注重的是二者的统一,而不是把二者看成是对立的。
汪野亭与邓碧珊两人都是文人瓷画的代表,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在两人身上表现都很明显。他们在新粉彩瓷画的创作上,都着意寻求文人画的意境美,所谓意境美,便是讲求心与物,情与景的协调统一。但是汪野亭与邓碧珊在对如何达到这种境界时是重“形”还是重“意”有着不同的侧重。
汪野亭的瓷板画作品总的来说更具有文人画“写”的特色,虽说汪野亭在早期绘画中也注意瓷画中形象的描绘,采用工笔的手法,但是汪野亭主要还是重视画的写意性,用“逸笔草草”来形容是最贴切的,他的绘画观总的来说可以用“以神统形”。然而邓碧珊虽说也接受了中国传统的绘画观念,他的绘画观念却与汪野亭明显不同。邓碧珊受到过很系统的文化知识的教育,他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并且邓碧珊醉心于书法,他也没有像一般的绘瓷艺人经历师传学艺,因而,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具有着浓厚的书卷气,个性突出。可是他的瓷板画作品却并没有走向以写意为主要的目标,而是在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与西方艺术思想及绘画理论产生碰撞的时期,选择了积极的吸取西方艺术理论以及日本的东洋的绘画观念,并把这些思想运用于瓷板画的创作中,这在当时比较闭塞的景德镇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新。在重“形”还是重“意”这一问题上,邓碧珊的主张可以用“以形显神”这四个字来概括。
在具体的瓷板画创作方面,汪野亭的瓷板画创作风格经历了前、中、后三个不同的时期,其整体的风格从开始的兼工带写渐转至因神显形。汪野亭的风格经过了“师古”“师造化”然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性的发展。
汪野亭初期的创作大致是20世纪的初期,在这一时期,他既学习继承了浅绛彩瓷画艺术家们对于把文人画风格运用于瓷画的不懈努力,侧重对于文人画的书卷气风格的追求,同时又受到董其昌“师心不师古,在意不在迹”的绘画观点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形成了汪野亭初期既注重绘画的写实,也注重绘画对于个人志趣的表达。他即对瓷板画作品的写实性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以便达到雅俗共赏的标准,对于作品经济价值的实现提供便利,同时他也注重瓷板画作品中个人的志趣的追求,以便满足文人画特点的追求。
在经历了早期的学习古人的阶段后,汪野亭在其创作中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师造化”成为了他在中期的绘画的重心。在石涛的绘画观念的影响下,对于自然的美的重视成为了他瓷板画创作的重点。石涛认为绘画要想达到传神的标准就必须要经历一个“搜尽奇峰打草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3],只有经过了这一过程的洗礼,作者对于所要描绘的物体有了亲身的体验,自身的情感才能够与山水达到情景交融,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在作品中表现出个人特别的审美情趣,达到董其昌说的“胸中脱去尘垢,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2]”
在汪野亭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对于佛家思想的痴迷,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占据了主要的方面。他的这种思想以及对于人生的态度的转变成为了其晚期风格转变的关键点。他的创作特点从青山绿水向墨彩山水转变,创作过程中不在注重画的色彩的明亮,绘画中常表现出的是清幽肃穆的景色,胸中的山水天地以绘画的墨色的变化来体现。他把幽山寒泉、古木枯枝作为其常用的绘画题材,在黑白二色之中展现清幽静穆的气息。此外,汪野亭在绘画中着重表现自己的个人审美趣味,枯藤、老树、孤村、落叶、阴云等一系列意象成为了他的瓷板画中的常用意象,这些意象的运用使得绘画达到了诗画浑然一体的效果,无限诗意跃然画中。这时期的瓷板画创作已转变为“以神统形”的风格特色。例如汪野亭晚期的作品《茅亭秋思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其绘画不讲求对景物的工笔描绘,其主要以写意为上,寥寥几笔,表现出引人遐想的无限诗意。
与此同时邓碧珊却有了不同的变化,由于受到这些思想风格的影响,邓碧珊把中西方的绘画理论进行了结合,形成了一种十分注重写实的风格。在画鱼藻时,同样也讲究形神兼备,这正是邓碧珊的一大特色。邓碧珊正是以擅画水中鱼而闻名,看起来没有画水,但鱼鳞的疏密排列,明暗关系以及鱼的尾、鲤、鳍都会做到写实而生动传神。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提到:中国画的美学特色“其核心是强调要在‘形似’的基础上表达出自然对象的生命”。[4]174他的这句话指出了一个艺术家要有生活经历的丰富性以及亲历性,只有有了深刻细致的观察,所绘的物才能够表达出个人的情感。绘画要反映我们的生活就离不开生活的形,古人同样也有“因物象形”、“以形写形”[5]的主张。
邓碧珊的鱼藻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这种思想的极好表现,来源于他对自然与鱼类的细致的观察。著名的产鱼区余干是他的家乡,河流流环绕着他的少年时代。少年时代,跟着父兄下河捕鱼成为了他的日常活动,各种鱼活动的特点以及鱼的生活习性开始在他心中留下印象。冬天在门前晒太阳,他也会仔细观察鱼的特性,在那里认真作画。后来他自己从事教学的闲暇时间也常去垂钓,垂钓成为了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有时他邀请三五个好友,有时独自一人乘船游湖,一面游湖,一面写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其观察也就愈深,对鱼的形象也就更加清楚,绘画中就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形成了形神兼备的特点。邓碧珊为了达到绘画的形似做出了极大地的努力,从一段对邓碧珊关于鱼与鱼草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鲤鱼的鳞,从头到尾大致是三十六片;鳜鱼的鳍,一般平年十二根,闰年则有十三根。他掌握了什么鱼栖什么草,急水中的鱼草是粗壮大叶的,也只有粗草才挡得起风浪冲击;静水中的草萍,茎细叶小,常有条鱼栖戏,金鱼则爱狮子草。”[6]这些丰富的生活经历和细致的观察,让他笔下的鱼非常“形似”。
例如邓碧珊的一幅《游鱼戏藻图》,他为了达到“以形显神”的效果,着重刻画了鱼的头部。通过对头部的细致的刻画,来突出鱼的神韵。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邓碧珊虽说着重于写实,他的绘画也不是完全遵照事物的本来样子,他的绘画和真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他注重的是通过对形的深入细致的描绘来表现其中的神。
这里所说的汪野亭与邓碧珊对于“形”与“意”的不同偏重,是相对而言的,他们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影响,对于绘画需要传达个人的思想情感都很重视。汪、邓两人的不同侧重在于要传达个人的情感时,是着重用写意的方法还是强调对于形似的要求来显示其神采。汪野亭受到更多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在绘画中注重主观之意的表达,因此,其在绘画中坚持的是“夫画,从于心也”的绘画观念,绘画中随意性比较大,对形的精细刻画较少。然而邓碧珊结合了中西以及东洋画的技法,在绘画中更加注重对于绘画物的形的深入细致的刻画,以细致入微的细节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
三、小 结
汪野亭与邓碧珊同属珠山八友中的成员,他们的粉彩瓷画创作都遵循文人画的绘画观点,没有超出文人画的范畴。他们在对文人画的诗书画印的结合方面拥有着共同的追求,都追求绘画的书卷气。
虽说汪野亭与邓碧珊两人在对待“形”与“意”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的不同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汪、邓二人对瓷板画绘画中的形与意的要求是努力做到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对这两方面都比较关注。这里说的他们对于形与意的不同侧重是比较两人的绘画倾向得出的结果。这种不同倾向的形成,与汪、邓二人对于不同的技法继承与创新有着紧密关系。在汪野亭的瓷板画创作过程中,主要追求的是“师古”“师造化”[8],最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特有风格。他的主要倾向是从传统国画中寻求笔法、风格的借鉴,因此形成了“以神统形”的风格特点。而邓碧珊除了学习中国传统的笔法风格之外,他还学习西方以及东洋画的风格,更加注重写实,形成了“以形显神”的风格。
汪野亭、邓碧珊在浅绛彩文人瓷画衰败的时代,继承并发展了浅绛彩文人瓷画,从而形成了凸显艺术家个人情感的粉彩文人瓷画,使瓷板画既具有商品性又具有艺术性,使粉彩文人瓷画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1]董其昌.画旨[M].毛建波,校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2]肖振松.邓碧珊的艺术生涯[J].景德镇陶瓷,2004(1):20.
[3]肖鹰.形与身的突出——明代前期画论的美学转向[J].清华大学学报,2012(6):59-66.
[4]夏斯翔.浅析汪野亭瓷板画艺术的风格特征[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6):66-70.
[5]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09.
[6]张红.石涛对张大千山水画创作的影响[D].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萃原,曲立氏.近水知鱼性·邓碧珊[J].陶瓷研究,2006(2):12.
[8]郑依晴.汪野亭与刘雨岑瓷板画创作异同探赜[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6):67-70.
(责任编辑:郑宗荣)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s between Deng Bishas and Wang Yeting
LING Jiang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Wang Yeting and Deng Bishan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w famille rose porcelain plate literati painting, and the former drew mainly landscape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s, while the latter was the pioneer of literati fish algae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s. Both had indelibl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an porcelain plate painting. This paper, by comparing Wang and Deng in terms of common pursuits of harmony and unity in poem,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seal and their different emphasis on either shape or meaning, reveals two different painting notions of either “revealing charm with form” or “govern form with charm”.
Wang Yeting; Deng Bishan; poem,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seal; form and meaning
I206.6
A
1009-8135(2015)02-0050-04
2014-12-13
凌江华(1989-),男,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