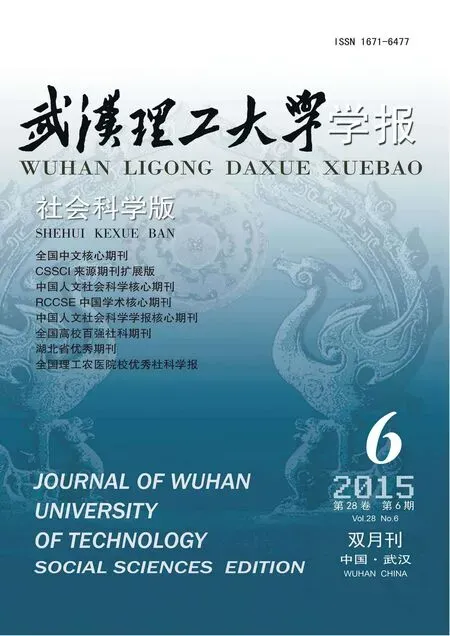生态整体主义的三重困境*
——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局限
马 草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75)
生态整体主义的三重困境*
——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局限
马 草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75)
生态整体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对于人类重新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然而生态整体主义并非尽美尽善,而是存在着相当的疏漏,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悖论,生态事实上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与价值判断和责任主体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形成了悖论;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误解,仅从生物性存在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才是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的关键;三是个体维度的缺失,过度强调整体的地位与作用,而忽视了个体的合法权利与重要性。
生态整体主义;困境;反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关系;个体维度
生态整体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对于人类重新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生态整体主义的兴起、发展有其现实背景,它结合现代生态学,以生态整体性来衡量和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了关于二者关系的新认识。生态整体主义突破了传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对于正确理解和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以及推动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态整体主义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美学等领域影响巨大。从诞生之日起,生态整体主义就一直伴随着争议,人们对其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本文认为,作为现代哲学思潮,生态整体主义有其贡献与可取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生态整体主义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疏漏,这主要表现在自身存在的三重困境上。
一、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悖论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卑微。在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二者都享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生态系统内的每一个个体存在都拥有得以展现和实现自我的权利,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去损害其他存在物的发展。这是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观的核心观点,带有非常强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与其他自然存在物都处于生态系统的链条中,都有着各自不同却独特的功能与地位。不过它所主张的平等是一种生命价值上的平等,但生态系统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绝对的平等,而是存在着众多不平等现象。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各不相同,由此而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生物链。生物链所遵循的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中便含有大量的不平等现象,例如捕食与被捕食以及物种的被淘汰,等等。如果生命真的平等,那么这诸种现象又作何解释呢?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观并不能反映生态事实,它是以人类的主观判断为依据,是人类基于自我内心的情感体验而得出的一种准则。这种平等观是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平等或价值论的平等,是一种泛道德主义,它以生命的比拟性为基础。赵奎英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拟人论”思维,在这种思维中,“自然是‘像’人一样的、有生命感觉、有目的意志的存在,人与自然在人的生命感觉的基础上得以统一起来。而这种‘拟人论’思维,恰恰就是一种来自人类早期的以人类自我的生命感觉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由于在这一视野中,人类是比照人的形象、从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人类兴趣的投射’,所以它也被归入更宽泛的‘人类中心论’的行列。”[1]生态整体主义代表人物奈斯认为,要想真正做到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必须依赖于自我实现原则。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类应当在生命共同体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缩小自我与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将其视为自我,并最终走向大我,即生态自我。自我实现原则试图通过发掘人类内心的善,激发人类的道德良知,引导人类自觉地保护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自我实现原则所依赖的主体仍然是人类,途径仍然是人类主观心灵的领悟。它企图依靠人类的认识与领悟来达到生态平等,这就为人类预留了中心位置。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反人类中心的目标,仍然把中心地位留给了人类。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自然最了解自己,只要是自然的就是最好的。它暗含了这样一种意识:人类应该像自然那样地生活。但是自然并不能言明哪种状态是最自然的,人类也无法真正站在自然的角度去思考。人类只能依靠自身的经验去判断某种状态或行为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在此之下人类被推向中心,成为整个生态系统的评判者。生态整体主义主张一切自然物都有内在价值,也即固有价值。它不是以对人类的有用性来衡量的,而是建立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自然与人类一样都具有内在价值,那么人类应当尊重自然。“大地伦理使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为普通的成员和公民。它蕴含着对它的同道的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生命共同体的尊重。”[2]194出于对生命共同体的尊重,人类必须保护它不受伤害。因此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以保护自然为先,应以是否有利于生态平衡为标准。“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时,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2]233-234史怀泽也认为“善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就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3]在这些表述中,人类从一名普通成员被推向了前台,成为了自然的评判者与保护者。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什么才是善或恶;为了能保护一种生命而去伤害另一种生命是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生态整体自身并不能作出判定,只能由人类代其作出判定。因而生态整体主义所依赖的这些判断标准都是人类制定的,其判断主体是人类。况且正误、善恶、伦理、价值等概念本身就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设置的原则,而非客观的自然规律。生态整体主义把人类置于价值判断中心,将人类的主观判断当作了客观标准。从表面上看,人类是作为生态整体的普通一员而负有保持生态平衡责任的;但从深层来看,由于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主体性的成员,那么保持生态平衡的责任只能也必须由人类来承担。换言之,人类天生不是生态系统的中心,但天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中心。生态整体主义总是对人类抱有强烈的自信,它暗藏着这样的意识:人类能在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真正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他们可以采取正确的发展方式,最终拯救自然,拯救世界,达到生态的平衡。在此,其所暗含的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信乃至自负。“因此,即便是最为激进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也总是基于对人的信任,基于人的言说而言说的,它永远不可能代替没有嘴巴的自然来说话。”[4]
生态整体主义表面是反人类中心主义,但在深层里仍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它在生态事实和立场上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在价值判断和责任主体上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力图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中走出,但经过一番努力后却发现又重回到了这个泥潭。它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目标总是落空,最终在客观上又重回到人类中心主义之中,生态整体主义陷入了悖论之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在于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主体性的误解。不可否认,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人类主体性的过度膨胀与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所导致的,但这不能作为否定人类主体性的依据。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就消解了人之为人的存在根基,就无法认识和改造世界,生态整体主义也就无从谈起。生态整体主义所反对的应是人类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及由此产生的不合理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作为人类之类特征的主体性。从哲学维度或实践维度而言,人类的主体性是作为类存在的人类的本质属性,这是无法反掉的。因此生态整体主义必须面对而且承认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主体性,将之作为生态整体之中的人类的根本特征。同时生态整体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人类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坚决反对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及其导致的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也就是说,生态整体主义既要承认人类的主体性,又要警惕人类主体性的缺陷。而它所提出的生态维度,无疑是对人类主体性的新认识及其缺陷的弥补。只有做到了自然性与主体性、生态维度与人文维度的有机统一,生态整体主义才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泥潭,正确认识和理解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一些学者所提倡的“生态人文主义”或许指出了并非唯一但无疑是正确的道路与方向。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误解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共同组成了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名普通成员。人类既非自然的中心,也非自然的主宰,它只是自己的中心与主宰。生态整体主义借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生态事实,以此向外推衍,从哲学上重新确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整体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对于人类重新审视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但生态整体主义过分强调了人从属于自然这一生态事实,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二者构成的生态整体关系并不能正确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生态学现象,这就为其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困境。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最普通的一员。从生态学的角度而言,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只是生态事实,也即自然事实。它只是一种现象事实,而非本质事实。仅仅强调人是自然的普通一员这一事实,无法说明为什么这一普通成员却能从根本上威胁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仅能够在生态学上成立,却不能在人本学上成立。生态整体主义若不能说明人的本质,就无法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5]80。人类不只是一种生物性存在,还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5]107人类有两种存在,一是自然存在物,即种的存在物或生物性存在;一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是自为的存在物,这是人与自然的本质性区别。类属性或社会属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正是建立于此的。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而言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5]83。因此要想真正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必须从人的社会本质出发,也只有理解了人的社会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环境的关系总是要以人类相互的社会关系为中介、并通过它们来界定这一事实。”[6]但生态整体主义却消解了人的社会属性,只强调人的生物性存在,只强调在此基础上的二者的统一,却忽视了二者的差别。因此“当生态整体主义伦理学将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时,就产生了生物还原主义倾向,消解了人之为人的存在。”[7]生态整体主义过分地降低了人类的尊严与主体性,把人降低到与动植物同等的地位,也就无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生态整体主义仅把人类当作生物性存在时,那么它试图从伦理、价值等角度确证生态整体的努力也将落空。因为伦理、价值等范畴只适用于有意识的主体,而作为生物性存在的人与自然是不适用这些范畴的。人类作为类存在物的最根本特征恰恰是具有主体性,能够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57,但这却被生态整体主义所忽视。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危机是由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类所导致的,而非生物性存在的人类所导致的。“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5]107当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不能有机统一,即人的社会属性压过了生物属性,仅把自然视作生活资料或生产工具时,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然而生态整体主义却消解人的社会属性与主体性,仅把人类视作与动植物一样的生态物种,消解了其主体性,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整体主义没有正确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整体之中的各部分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在此关系中,对立包含着统一,统一也包含着对立。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但生态整体主义只看到了人与自然之同,却忽视了二者之异。它试图以生物性存在统一自然与人,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是根本区别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只看到了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却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作用;它只注意到了人从属自然这一事实,却无法说明人之于自然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忽视人的社会属性,过度打压人的主体性,也就否定了人类之于自然的作用与价值。生态整体主义只看到了自然包含人类,却忽视了人类也包含着自然。人与自然构成了生态整体关系,在此之下人无疑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类也包含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意识的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总体来看,生态整体主义切断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仅仅描绘了一种单向或单一的关系。它用统一掩盖了对立,用单一消弭了相互。这无法正确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种片面的、机械的解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诉求来看,它存在着企图以自然压迫人类,甚至取代人类的倾向,无怪乎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生态法西斯主义”。
生态整体关系关注的重点在于人类如何统一于自然,而非人类与自然如何统一成一个有机整体。它所揭示的只是生态层面的物质能量循环关系,而非人本学层面上的对象性关系。生态整体主义误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地解开二者关系的实质。生态整体主义过度局限于生态学视野,这就制约了其理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如果跳出生态学,那么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或许能够得以正确地说明。马克思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5]106。任何事物都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5]106-107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对象性关系,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人类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要以其他存在物作为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即以自然存在物来表现自己的本质;一方面人类也是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是自然用来表现自己生命本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的关系之中,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此关系之下,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二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二者也是统一的,“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为一个整体,自然世界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8]44。“对立双方各自蕴含着对方的本质,潜在的就是对方。自然世界本身是人本质的对象化,是对象性的人,而人本身则是表现自然界本质的对象,人本身是被自然化了的人。”[8]45这里的对象性关系并非主客对立式的,而是存在论、生成论式的。对象性关系既避免了自然沦为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料工具,也避免了自然对人类的过度压迫,使二者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真正统一起来。对象性关系从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性界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的论述,对生态整体主义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生态整体主义应当吸收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合理成分,在生态整体的基础上建构起人与自然的新型的对象性关系。这或许在哲学层面上更符合对人与自然关系实质的描述,更有利于生态整体主义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三、个体维度的缺失
生态整体主义企图用生态整体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提出的生态整体关系是关于二者宏观关系的深刻认识。但生态整体关系并不是指向事物的内部,它虽然决定了事物在生态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它不构成某一事物或现象的内部规定性,即它不是形成某一事物的自主性成分。我们说某一事物是处于生态中的,却难以说明它就是生态或者生态整体。因为后者所指的关系,是一种事物之间的关系。生态整体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关系,它虽是生物的本质属性,但是它却不能构成事物的实体,即不构成事物的实在性。关系虽然有本质性的地位,但它还不是构成事物本质的全部。它只是说明了构成事物的一部分,研究事物除了探究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外,也需要在这种关系下深入探究其内部,尤其是组成整体的各个实体部分,而这恰是生态整体主义所缺乏的。
进一步而言,这就导致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另外一个困境:个体维度的缺失。生态整体主义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这是其巨大的功绩之所在,但却也过度强调了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忽视了个体和个体的创造。生态整体主义存在着这样一个倾向: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只能由生态系统来赋予和确认,而非它们本身所拥有的。这就会形成一个疑问:既然个体没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那么由个体所构成的生态整体的价值又是从何而来?我们承认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作为部分的个体的存在又有什么样价值和意义呢?生态整体主义并不能回答这种质疑,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生态整体主义中个体维度的缺失。生态整体主义向我们展示和强调了整体的重要性,却无法向我们指明生态整体中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个体的价值与意义是由整体赋予的,而非自身拥有的;个体的价值与意义是指向整体的,而非指向个体的自身存在。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语境中,个体的存在并非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生态整体。生态整体有权决定个体的存在与否,是最高的主宰者。这就意味着个体必须服从生态整体的利益,否则生态整体有权决定此个体是否继续存在。但如果一味服从整体利益,那么势必就会出现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体的现象,正如贾丁斯所说的那样,“对土地伦理整体主义最严厉的伦理学批判是认为它牺牲个体的利益而满足整体的利益。如果我们用生物群落来定义好与坏,似乎有可能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如个体的人。比如,利奥波德好像对杀死个体动物以保持生态群体的整体性与稳定性表示谅解,但由于他还把人类描述为群落中的‘平等’的成员,似乎他允许杀死一些人,这样做会保持其群体的整体性、稳定性及美。”[9]由于过度重视整体,生态整体主义忽视了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权利。然而每一个体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是由生态整体所赋予的,还是由其自身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体不符合生态整体的利益就轻率地削弱或取消它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况且生态价值只是事物众多存在维度中的一维,我们不能因为此一维度而去否定其他的维度。否则,生态整体主义对于个体而言就不再是最终归属,反而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
生态整体主义并没有正确理解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它过度强调了整体的价值与意义,而忽视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它过度强调了整体对个体的影响与作用,却忽视了个体对整体的影响与作用。在我们看来,整体与个体处于辩证关系之中。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没有整体便没有个体,没有个体也就没有整体;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作用,整体决定个体,但是个体也会影响整体,尤其是某些关键个体还会对整体产生决定作用。否定了个体,整体的大厦也必将崩塌。与整体相比,个体并非不重要,而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价值。这是由其内在的价值所决定的,它以此为基础影响和改变整体。“作为个体的个别微小元素不单是不允许被忽略的,它还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目前的观照行为本身,改变整个世界。”[10]我们在此强调个体并非是维护个体私利,而是尊重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权利。我们必须避免一谈论个体就联系到私利的思维定式,而是谈论如何维持和保护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权利。我们承认整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但也强烈反对以整体而否定个体的行为。过度倾向于整体的决定作用,那么整体会借此消灭一切与自己不统一的个体,势必会产生“法西斯主义”倾向。对于生态整体而言,它是以个体为基础和为依托的,它的存在与发展最终是通过个体体现出来的。如果忽视或否定个体,那么整体又如何存在?生态整体对个体固然具有决定的作用,但是个体对生态整体也会产生影响,尤其是作为拥有主体性的类个体的人类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态整体的健康发展。因此,生态整体主义必须正确处理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重视个体的地位、作用及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其合理性,并发挥其理论的有效性。
生态整体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是现代生态学,但仔细审视生态整体主义对生态学的借鉴和吸收,就会发现,生态学对于生态整体主义或许有启发作用,但并没有给其注入真正的或正确的科学内涵。现代生态学虽然强调整体和联系,重视个体对整体的依赖关系,但也强调个体,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考察以及对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价值的审视。但生态整体主义在利用生态学资源时却有意地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意在借此以达到一种理论上的深刻性和警醒性。与此相关的“互利共生”与“竞争捕食”关系,生态整体主义也只是强调前一点而忽视后一点。由此可以看出,生态整体主义并没有正确使用生态学知识,而是进行了有意识的取舍。这种取舍却从根本上违背了生态学的科学精神,使其背离了科学依据。人文科学固然不能改变自然科学的真理性,但是也不应该全盘移植自然科学知识。理论上的深刻性并不在于其片面的深刻性,而在于系统的深刻性。生态整体主义只做到了前一点,而止步于后一点。麦利考特曾对生态整体主义作了如下评论:“深层生态学也许是深沉的,却不是生态学的。生态学也许启发了深层生态学,但它并未使深层生态学变得更有智慧。深层生态学那种粗糙的形而上的整体论更是难以通过诉诸生态科学来加以证明。”[11]162生态整体主义并未真正领悟到生态学的科学精神,其理论体系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雷毅指出了这一点:“如果深层生态学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生态科学,那么,其理论说服力会因此大大削弱。”[11]162
四、结 语
生态整体主义的困境并非只有这三个方面,它还存在着诸如生态至上主义倾向、生态正义失衡等方面的缺陷。因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进行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生态整体主义无疑有着极具冲击力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视野,它对于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反思与确定人类的发展路线,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但它自身存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这在根本上制约着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说服力与实践操作性。生态整体主义必须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断进行修正,逐步走向完善。惟其如此,生态整体主义才能获得当今社会的认同,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为当今社会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1]赵奎英.论生态美学的困境与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8-34.
[2]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候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史怀哲.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9.
[4]蒋 磊.生态批评的困境与生活论视角[J].文艺争鸣,2010(11):16-19.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修订版[M].韩立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2006:74.
[7]曹孟勤.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人与自然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整体[J].伦理学研究,2010(1):63-68.
[8]曹孟勤.生态整体主义自然观的困境与出路[M]//环境哲学:理论与实践(第二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第三版)[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0.
[10]王耘.复杂性生态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11.
[11]雷 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文 格)
On the Treble Predicament of Ecological Holism: the Limitations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Aesthetics
MA Cao
(SchoolofPhilosophy,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375,China)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ecological holism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owever, ecological holism has not reached the degree of perfection because of some omissions.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of the predicament: First, the anti-anthropocentric paradox,ecologically factual anti-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value judgment and the subject of liability on the doctrine of human centre form a paradox; Seco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e.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logical 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hile ignoring that the social nature of human existence i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ird, the lack of individual dimension, or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whole, while ignor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vidual.
ecological ho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ti-anthropocentr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dividual dimension
2015-06-19
马 草(1987-),男,山东省新泰市人,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及生态美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3YJC720033)
B151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