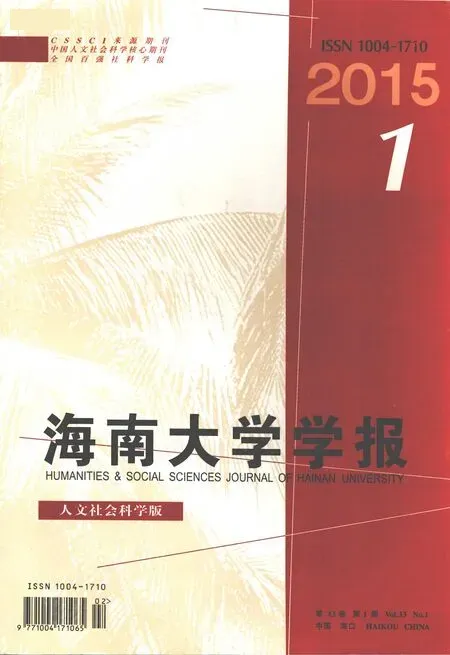君子之道的仁义抱负与文教起点——试论介于质教与文教之间的儒家诗教
李 旭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07)
中国的博雅教育,其本土源头是孔子开启的教化传统。孔子教学因材施教、发挥学生性之所长、纠补学生性之所偏,也有通贯的教育理想——造就君子。据《论语》记载,孔子对何谓君子有多种多样的教诲,基本上都指向德性成就。那么,何为君子的质,何为君子的文?大要言之,仁义是君子之质,礼乐是君子之文。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礼乐为君子之文,可考之于孔子的原话。《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此处“成人”指才德完全之人,与孔子“君子不器”的教诲相近,“君子”与“成人”异名同指,也可见君子的“成德”并非仅仅是外在道德规范的塑造,而是来自内在性情的成长,这一成长需要礼乐之文,最终的实现就是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就是以仁义为质,以礼乐为文。因此,从教化的角度讲,儒家的君子之道可分为质教和文教两层,二者兼备,才能造就文质彬彬的君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即是文教;忠-信,即是质教;行,则是君子之质的彰显,让文得以充实的实行。
从质教和文教的不同层次来看,君子之道有不同的起点。孟子以扩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四端为养成仁、义、礼、智四德的功夫,着重于君子之道的质教起点。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说的是君子之道的文教次第。有子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发挥了孔子行仁由孝友始的思想。“孝悌”是质教与文教之间“行”的起点,孝悌一方面是践行仁义的起点,另一方面也是生成礼乐之文的根本①孟子讲:“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见《孟子·离娄上》。。就义理而言,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四端是孝悌之行的种子,更是礼乐之文的根本,君子之道的质教似乎比文教更基本。但从历史的发生看,诗书礼乐的文教其实先于孟子仁义礼智的质教,孔子“文、行、忠、信”四教也以文教为先。孔子之教文质并重而以文教为先,是要以承载了先王之道的“文”,来引导、涵养人心的仁义美质,让这美质不滋蔓、不偏斜地成长为卓然自立的大树,结出德盛仁熟的佳果——文质彬彬的君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以文教涵养美质的君子成德之教。
那么,为什么诗教居于文教之首?
一、温柔敦厚与忠孝仁义——诗教培养君子抱负的性情教育
马一浮先生认为诗教主仁,并认为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这个解释明显偏重于诗的质教。就笔者所知,古代的诗教论述中很少概要地将诗教的功能定位于仁德或其他某一种德行的养成上。孔子对诗教大旨最精要的概括是“思无邪”,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为“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程子说“‘思无邪’者,诚也”。无论“性情之正”还是“诚”,都不是指某一种德性,而是德行的总体特征。将诗教的功效确定为某一类性情和德性,最著名的是《礼记·经解》中的讲法:“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温柔敦厚”与“仁”是不是一回事?孔颖达疏解“温”为“颜色温润”,“柔”为“性情和柔”。性情和柔是能感,颜色温润是能爱;冷漠刚硬,对苦乐忧欢无所感,则近于不仁。但是“敦厚”很难仅仅从当下化的“感”出发理解,“厚”意味着时间、历史的层积,需要超出当下之感的记忆和想象。《论语·学而》中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是一种超出当下需求的追念,能够追念父母先祖,丧尽其礼,祭尽其诚,“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可见“敦厚”需要超出当下现实感的追念范畴和能力,如果把“仁”解释为心灵的感觉、感通能力,要么温柔敦厚就不只是仁者的性情,“敦厚”还包含着超出“仁”的某种品质,即仁者的感不仅是当下的,而包含着追念与希望的时间和历史感。从儒家以孝悌为仁之本的一贯思想看,仁显然不只是一种当下的感觉,而包含着慎终追远的敦厚性情,温柔敦厚即是仁。马一浮“《诗》教主仁”之说与《经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之旨是内在一贯的①“温柔敦厚”作为“仁”的性情特征也可以找到文本依据,如《经解》篇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主旨,同时说“诗之失,愚”,则可见温柔敦厚有可能失之愚,而《论语》中孔子也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但必须明辨仁者的“感”不只是审美的感官感觉,而是敏于当下同时思接古今、有时间和历史厚度的“感”。
仁作为温柔敦厚性情所包含的生命厚度,体现在孝悌忠信的伦理操行中,其中最为基本的是孝悌,从孝悌中建立并推广仁,是儒家的仁爱区别于墨子兼爱、佛教慈悲和基督教博爱的特色,这其中包含儒家对人的生命时间性、历史性深度的体认与坚守。孟子虽然以普遍的恻隐之心来作为仁之端,但也没有放弃从“亲亲”之孝来讲仁的儒家本有思路。孝是人应有的对自己生命本源的感念——人最直接的生命来源是父母,奉养孝敬父母是最朴素的孝,由此继续扩大,孝可以上升为敬事祖宗(追远)、感恩天地和君师,这就是荀子说的礼之三本——父母祖宗为血缘之本,天地为衣食之本,君师为政教之本。礼之三本,在后世形成了对中国民间宗法社会影响深远的“天地君亲师”的祭拜秩序,其根本则在于孝,在于从孝生发的仁。但“仁”的发用不只在感念生命本源的“孝”,也包含关怀未来生命的“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是完整的仁。相对而言“慈”是比“孝”更为天然的伦理德性,是在动物的孵卵和哺乳行为中就已具端倪的德性。现代人更多地倾向于把仁往“仁慈”而不是“仁孝”的方向去理解,说明相信进化论的现代人在德性的理解方面却让自己向动物方向退化。作为生命时间伦理的孝与慈,两个维度都不可缺失,真正的孝要求达于父母之心,以父母之心为心,孝内在地也要求慈。孝相对具有本能色彩的慈来说更需要心灵的自觉,更多地是教化的结果,更具有超越性。君子的仁德作为慈的扩充远远超出了生物繁衍后代之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君子的仁德主要以“为民父母”和得君行道的方式实现。君子要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者抱负,主要的途径就是出仕从政。就此而言,出仕的君臣之义,乃是实现“为民父母”之仁的一个中介,反过来也可以说事君的本分之忠(忠义),也需要并体现为为君分忧的“为民父母”之仁。对“抱负”二字的分析可知,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的仁孝乃是君子之担负,而“少者怀之”为民父母的仁慈与事君尽忠的节义则是君子的怀抱。具体展开为孝悌忠信的仁义抱负,是君子之质。
这一切与诗教是什么关系?诗教如何能涵养孝悌忠信的君子品质?君子的仁义抱负为何需要诗教的兴发?
显然,并非所有的诗都堪为教化之资,儒家“诗教”概念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虽然现存的《诗经》305篇是否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由孔子删定学界颇多争议,但“诗三百”肯定经过删述,并非三代以来产生过的诗歌总数,以尧舜以来时代之久远、有周一代文化之发达,“古者诗三千余篇”未必是妄说。“诗三百”即便不是孔子删定,也一定经过孔子之前采编者披沙拣金般的择取。删定、择取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不只是、甚至也主要不是审美价值,也未必是狭义的道德或意识形态目的。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朱子认为“学诗之法,此章尽之”[2]210,其实这句话何尝不可看做“诗三百”编订的大体宗旨,今人编选诗歌、文学的集子,也未尝不可参照这一标准。从这句话看,孔子的诗教旨趣非常宽广,并未限制于狭义的道德教化,相比《经解》篇中的“温柔敦厚”涵摄要广。清代持性灵说的诗论家袁枚更认取“兴观群怨”说而贬抑“温柔敦厚”说,认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3]。
“诗三百”中有事父、事君之道,可以达于人伦、政事①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讲得很明白,验之《诗经》与《左传》,也可知不是虚言。事父、事君的忠孝仁义②其实不仅在事父之孝事君之忠的伦理里面有仁义,即是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中也未尝没有仁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只是知识上的广见闻,也是感性地体认“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地生生之德。鸟兽草木比之父、君虽远,而孝子忠臣贤妇良友比兴拟意往往寄托其间,不只是修辞寓意的需要,也是触物起情的兴发之机。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是此处诗教大义。与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是什么关系?对这4个字朱子的注释与汉儒有明显的差别。朱子注:兴,感发志意;观,考见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何宴《论语集解》集汉儒的注则是:“孔曰:‘兴,引譬连类。’郑曰:‘观风俗之盛衰。’孔曰:‘群居相切磋’。怨,刺上政。”[4]1212相比汉儒的注,朱子对兴、观、群、怨的解释明显偏重诗教的性情和道德的效用,是从质教的角度解释兴观群怨,而汉儒的注解则关注诗教的言语、政教意义,偏重文教③朱子的解释偏重质教,一方面是理学解经的特点使然,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在朱子的时代“文”的意义已经主要由礼乐之文转变为文辞之文、文人之文,因此理学家有强烈的贬黜文辞的倾向。。如对“兴”的解释,朱子的“感发志意”着眼性情,汉儒的“引譬连类”着眼言语,与《诗经》六义“风赋比兴雅颂”中的“兴”意思更接近;对“群”和“怨”的解释,朱子的“和而不流”与“怨而不怒”着眼于操持中道的品格修养,汉儒的“群居相切磋”与“刺上政”,则着眼言语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刺上政”如《诗大序》中讲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其中也有事君之道。从朱子的解释方向看,“和而不流”、“怨而不怒”接近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④温柔则平和能群,敦厚有持守则不流。。汉儒对兴、观、群、怨的注释看起来伦理道德义涵不强,但如果联系“引譬连类”的“兴”来理解“群居相切磋”、联系“主文而谲谏”来理解“刺上政”,其中亦有温柔敦厚的大义。
“诗三百”中包含的事父事君之道等伦常意蕴并非抽象的教义,而是具体地体现在言语和行事中。如体现了孝道之精微的“色难”、“事父母几谏”就通于诗教的温柔敦厚,是忠信仁义的君子品格既需要诗教兴发、也需要诗教涵养的道理所在。对儒家而言,诗教不是针对不识字、理解力低下的民众而设的感性化教育。那种为传播教义而针对民众的感性化教育——如基督教的圣像膜拜、佛教的方便之门——对君子而言流于浅显。中世纪早期为圣像画辩护的格里高利教皇说:“文章对识字的人能起什么作用,绘画就能对文盲起什么作用。”[5]言下之意,教堂中的圣像画对不识字的基督徒是有用的,对能阅读《圣经》的基督徒则不然。诗礼乐的儒家文教对于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而言是必需的,因为孝悌忠信并非超感性的教义或绝对命令,而是需要扎根于敦厚性情、表现为温柔辞气的德行;君子抱负的成就并不在彼岸天国,而是在“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王道历史使命中。正因为如此,宋代以后偏重于质教的《四书》并不能取代文质兼备的五经、六艺,而只能作为进入更古老的六艺文教的前奏,无论是君子自修的内圣功夫,还是淑世的外王治道,都离不开诗书礼乐的文教。孔子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文教次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二、诗教之兴的道德担当
探讨孔子文质兼备的诗教,离不开对“兴”的理解。孔子把诗教的功能概括为兴、观、群、怨,兴是第一位的,相对于礼、乐,他又把“兴”单独标举出来作为诗特有的功用。要准确、深入地理解诗教的“兴”,就不能停留于将“兴”看做与“赋”和“比”并列的修辞手法。就本论题而言,需要探讨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兴”如何兼具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其二,诗教的“兴”如何与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性相关联。先看其一。
犹如《论语》中记载的诸多夫子之言,“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也是恁地腾空而出,它并非孔子针对弟子发问的作答,也没有呼召某个特定的弟子对言,这句话甚至连主语都不明朗。谁、什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夫子没说,主语空置,能把捉的实在之物只是诗、礼、乐,而兴、立、成这三重势态,就依凭于被给予的诗、礼、乐。即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现实活动之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主体。这样一个凭借诗、礼、乐的先王之道而兴、而立、而成的“主体”生成过程,就是学与教。着眼于“学”或“教”,这句话可以填充两类主语。首先,如果孔子这句话是对学习、成长中的弟子说的,它的主语就可以是学道的君子或君子的德性,这是内圣的解释思路;其次,如果这句话是孔子对已经学道有成将要出仕从政的弟子或当时的为政者所说,其主语则可以是王道教化,因为教化乃是王道政治的要义,这是外王的解释思路。传统注家基本上也可以分为这两路,而以前者为主。
《论语集解》中汉代学者包咸注“兴于诗”:“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立于礼”:“礼者,所以立身也”;“成于乐”:“乐所以成性”[4]529。包注看起来有一个缺点,就是兴、立、成的主语稍不一致,兴和立的主体都是“身”,乐所成的却是“性”。不过这个不一致却可能隐含某种深意,“乐所以成性”,从《中庸》“致中和”的成己成物思想看,孔子所讲的“成于乐”不仅是成己之性,也是成物之性,因此不只是“成身”,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至上和乐。朱子的《四书集注》统一把这句话的主语解释为“学者”。皇侃的《论语义疏》引王弼的解释则认为这里讲的是“为政之次序”[4]530,这个解释虽然有点舍内而求外的嫌疑,但儒家为政以教为本,教化之道与修身之道不二,所以也讲得通①如孔子认为学诗可通于为政(《论语﹒子路》),颜渊问为邦答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孔子的政治思想重在诗、礼、乐的文教。。综合起来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内圣外王之道的次第——诗是内圣外王之道兴发的起点,礼是内圣外王挺立的主干,乐则是内圣外王的大成境界。对儒家君子来说,内圣自修是更为根本的,《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所以可以构成为政之次序,首先因为它是修身之次序。儒家修身之道的目标是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因此首先须理解为什么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性要“兴于诗”。
《论语集解》的解释非常简单:“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汉儒从修身之道来理解诗教的起首地位,着眼点是诗教之文。“修身”固然是儒者都注重的,但在孔门弟子中尤为注重修身的首推曾子,讲“以修身为本”的《大学》,宋儒就以为是曾子所作。从文本看,在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前面,记载的恰好是曾子的言行,而且多与修身有关,如疑是曾子临终时的话有:“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曾子的学问,在孔子诸弟子中介于文、质之间,如其著名的“日三省吾身”、以“忠恕”解释孔子之道的“一以贯之”等,均着力于君子之“质”,从曾子得到的“参也鲁”的评价来看,曾子的学问和为人也偏于质鲁。但从曾子的重视礼来看,其为学为人又未尝缺乏君子之文,不过曾子所重的是修身之礼——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都关乎修身——而不是治国之礼。着眼于修身,则诗教首先体现为言语之教,孔子告其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曾子的“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都是修身当学诗的旁证。但是汉儒并没有解释修身当“先”学诗的理由,因此“兴”的起先义也不甚了了。
朱子的解释进一步穷究了“兴于诗”之所以然,体现了格物穷理的理学注经特点:“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2]121。对“兴”字的解释,朱子与包咸一致:“兴,起也”,他进一步从言语和性情特征解释了诗教的起先地位,即为言易知和本乎性情的感人易入。不过朱子并没有采纳汉儒以“修身”解释诗教之“兴”的注释,而是着眼《大学》八条目中的“正心诚意”解释诗教之“兴”——“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2]121。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即是“正心”,此心之“不能自已”,即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诚意”。以“正心诚意”解释诗教之“兴”,倒合于“思无邪”的“得其性情之正”(朱子)与“诚”(程子)。相对《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正心诚意”偏于质教。君子之质主要是仁义,朱子此处所谓“好善恶恶”,具体地说,是好仁恶不仁,好义恶不义。好仁义(好德)恶不仁不义如“好好色恶恶臭”一样本乎性情而不能已,即“兴于诗”的道德效能。如此看来,诗教中竟有成就“好德如好色”的大义,夫子慨叹其当世未见如此君子,难道诗教大用在孔子当时已隐蔽不彰?更大的疑问是,如果诗教既已能兴起学者好善恶恶之心,为何还需接着“立于礼”和“成于乐”?
在兴于诗之后还须立于礼、成于乐,说明仅仅凭借诗教还不足以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就仁义之为君子的核心品德而言,如果说诗教兴发志意的核心是“志于仁”①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那么志于仁的“学者”为什么还需要立于礼?据《论语》可知孔子对颜回讲的是“克己复礼为仁”,这要求对诗教之“兴”做深入的理解,不能满足于把“兴”理解为起首、起先之“起”。对于诗三百传统的“兴”,历代学者的论说丰富多样,从诗的创作和接受两个方面看,“兴”大致可分为创作的“兴”和解释的“兴”两个层面,《毛诗》在解诗过程中基本上都着眼于创作的“兴”,把“兴”看做与“比”不同的隐喻,而且往往有美刺寓意。《论语》中孔子讲到的“兴”则大都着眼于诗之用,不涉及创作中与赋、比相并列的兴。实际上对于诵诗与用诗者来说,诗中的赋、比、兴都是可以兴发的,领会诗的整个方式都可以是“兴”。如果说在创作的“触物以起情”中兴起诗人之情的是“物”,那么在后来者的诵诗、用诗的兴起中,诗本身就成了让学者兴起之物。诵诗、用诗的“兴”既包括“引譬连类”的言语方式、“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领会方式,也包括兴寄、兴致的性情感应方式。朱子解诗教之“兴”为“兴起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侧重“兴”的情志层面。这与审美主义、美育是否很接近?
历史上对“兴”的性情化、审美化解释代不乏人,著名的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兴趣”说②值得注意的是,在兴致、兴趣这些具有审美色彩的词语中,“兴”都念去声。[6]134、钟嵘的《诗品》解“兴”为“文有尽而意有余”说③彭锋从美学角度认为钟嵘对“兴”的解释跳出了汉代经学家的窠臼,“完全是从新的时代精神出发的”,认为钟嵘对兴的这种崭新解说经过严羽的发挥在诗学领域中被广泛认可。《诗可以兴——对古代宗教、伦理与哲学的美学解释》,第116页以下。客观地看,以“言有尽而意有余”解诗之“兴”是深有见地的,儒家诗教当然不是无涉道德的审美趣味,但诗也毕竟不是道理说教,不是寓道理于形象之中的寓言,诗之“兴”里面有溢出言说者之“意”的多余者,这是“兴”和“比”不一样的地方。孔子其实也没有完全把诗教的效能限定在人伦道德范围内,所以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之后还留了一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余地。。彻底的审美主义有摒弃道德的超善恶倾向,无论是“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还是寓理念于感性显现的美育也好,都有太强的目的性、规定性,都不是“有余”的“意”,若以审美主义眼光看来都未得“兴”之究竟。在现代一些美学家的眼里,魏晋六朝名士的生活才是典型的审美生活,是最有“兴”味的生活。其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世说新语》所载山阴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然而,“兴于诗”决然不只是这个意义上的随兴之兴,君子的修身与好善恶恶之心决然不能随兴而起、兴尽既去,事父之孝、事君之忠、夫妇之义、交友之信,是君子的本分担当,不是取决于个人高兴与否的审美趣味。仁义道德实质上具有担负的性质,并非起伏不定的情感判断。如何理解道德的负担性与诗教之兴的关系?
“孔子的伟大贡献正是把周初强制性的伦理规范转化成了自觉的伦理要求。在孔子那里,礼不再是禁忌对象,而是君子们主动追求、学习、爱好和发自内心的喜悦的东西”[6]212。周礼对孔子而言当然不只是禁忌对象,而是“郁郁乎文哉”的先王之道,但是不是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呢?对孔子而言行礼是不是轻轻松松没有重负的事情?道德生活是不是完全与恐惧无关的自由理想的表现?从儒家文献看,并非如此,保持“戒慎恐惧”④《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恰恰是君子修身的一个基本方面。“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修身本就和戒慎恐惧相关,人有所忌惮,才会收回放肆、狂妄的心思与手脚,回向成己成物的生命大道①朱子集注此章引尹氏言:“三畏者,修己之诚当然也。小人不务修身诚己,则何畏之有?”。
重修身的曾子在其生命情态中表现了这种“戒慎恐惧”,《论语·泰伯》云:“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与那种对“兴”的审美式体验极为不同,在慎终追远的曾子这里,由诗所兴发的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慎恐惧,更难以理解的是,曾子临终引诗所表白的恐惧只是一手一足的身体保全,颇不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者气象。需要明辨的是,让曾子战战兢兢的手足保全,不同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个体生命之自保,“盖此身髪,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千字文》),这种包含在修身中的身体保全意识,乃是君子对自身生命本源的感念。与那种对个体生命的原子式设想不同,古代儒者认识到人的生命不只“属己”,也是属于成全着自己生命的伦理本源的②那种以自保为人的本质规定的原子式看法其实混淆了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的差异,人类社会的自杀现象就是对这种原子论的反驳。但基于对人的生命的伦理历史归属的认识,儒家虽然肯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却反对自杀。。其中首先就是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的生命中存有父母祖先的血脉;不仅如此,人身人形并非动物的躯体,其中承载着“四大五常”,蕴涵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要求,修身就是“践形”(《孟子·尽心上》),不过仁义礼智的德性未必如孟子所认定的天性固有,而是需要王道政教所玉成的。是自觉地承负起位天地、育万物的先王之道,是君子之志,君子的生命承负着父母师长之望、先王之道、天地生生之德,正是这份重量让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君子藉以维系父母师长之望、先王之道和天地生生之德于不坠的,正是“克己复礼”之要义。礼,对于孔子和儒者而言,既是美好、文理粲然的,也是沉甸甸、需要战战兢兢地持守的。“克己复礼”之“仁”因此就不只是一念之间的恻隐之心,而是需要“死而后已”地肩负的重任③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曾子这句话正载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前面。。
三、教之兴的礼乐归宿
回到前面的问题,“仁”之重任与诗教之“兴”是什么关系?需要诗教的兴起才可能成就肩重任行远道的弘毅之士④耐人寻思的是,曾子在这句话里呼召的是“士”,而非“君子”,这也许暗示曾子的出发点是较为质朴、谦逊的,但质朴中有宽博,谦逊中有坚毅。吗?联系前后两个问题看,不妨推测“兴”的主体是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弘毅之士。在此诗教之“兴”如何承负仁之重任?需要进一步探问、体会这个“兴”字。按照对“兴”的情趣化解释,诗兴恰恰是一种摒绝事务负担的轻松宽快,任事之重与诗情画意的轻松简直是相反的⑤如《文镜秘府论》认为作诗要“江山满怀,合而生兴,须摒绝事务,专任情兴”,“如此,若有制作,皆奇逸”。[6]115。也许与后来对“兴”的这种解释不同,在“诗三百”以致更早的时代,“兴”是可以负重的,但这种负重和在恐惧中承受“禁忌体系的重负”并不一样,其中是否仍有某种轻?也许在后世官僚政治的“案牍之劳形”和商贾熙熙攘攘的逐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事务,即虽严肃庄重却不乏诗意的事务?
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兴”字在甲骨文中已有,是象形字,像众手托盘而起舞之形。后世释“兴”为“起”,倒也没有脱离“兴”在甲骨文中的原义。对于甲骨文中的众手托盘之形,古文字学家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盘是重物,“兴”是实际劳作中的举起重物,因为只有重物才需要众手托举;另一种认为盘是轻物,“兴”是摹拟性表演活动中情感的上举、升腾。对轻物盘为什么需要众手托举,彭锋给出了一个很妙的解释:
盘虽轻但仍需众手共举,这当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要,而是因为表演的需要。除了这种表演上的需要外,还有宗教、道德情感上的原因。盘的质量虽轻,但在诸如宗教祭祀之类的歌舞活动中,因为敬重、尊重而仍需共举。正如现代汉语词汇所显示的那样,重不仅因为重量而重,而且也因为尊重而重。[6]57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中,乐舞的身心升腾上举之“兴”与祭祀礼仪的庄重性之间的内在同一。也说明了这种“兴”的原始礼仪,并非如卡西尔所讲的那样是纯然靠恐惧维系的禁忌体系之重负,而是原始诗、礼、乐未分的一体浑然,这种原始祭祀歌舞中的“兴”是一种起而承负的姿态。所承负的东西虽然在物理上也许是轻的,可能只是盛着果实或玉器的盘,但在意义上却是重的,是丰收节庆中天地的丰厚馈赠,或是献给祖先神灵、关系家国福祉的美好牺牲。这种举轻若重的恭敬慎重姿态,也是后世行礼活动中的基本情态,如清代的《弟子规》里就有“执虚器,如执盈”的教导。就儒家诗教的“兴”作为一种起而承负的兴起而言,它具有兴发仁心襄成礼乐的内在方向,学诗之兴指向“仁以为己任”的弘大抱负,方不失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宗旨。纬书《诗含神雾》训“诗”为“承负之义”,以“诗”、“持”互训,若合符节地承续了甲骨文中“兴”的众手托盘、起而承负之义:
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8]
虽然原始祭仪中的“兴”具有举轻若重的承负特点,但它与西学禁忌体系的重负并不一样,其或多或少有着感应的自觉,肃穆中仍有欢欣鼓舞。若没有了“兴”,那么礼仪活动中的繁文缛节就可能真的成了禁忌体系的重负,只能靠恐惧维系,一旦外在权威松懈,人们就可能抛弃这些规矩而寻求任意妄为的轻松。这也许是讲克己复礼的孔子在“立于礼”之前,要先“兴于诗”的原故。简言之,礼之文主要不是悦人耳目的审美形式,而是承载着伦理重负的仪轨,若没有本于性情的诗教之质兴发、充实,就可能流变为不堪其重的繁文或竟求奢华的虚文,“文胜质则史”大概就有这方面的意义。礼之重,需要风一般轻举而有力的诗之兴,才能成为士君子可以肩任且行远的重。与此相关,可发现孔子对仁的解释也兼有本乎性情的“易”与克己复礼的“难”,“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始乎孝悌,这是仁心可以兴的一面,孟子的“恻隐之心”发挥了这一面;“仁者先难而后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这是仁德难成的一面,是为什么在“兴于诗”之后还要接着“立于礼,成于乐”的原因。颜回能够“三月不违仁”,最接近于仁德的成就,而孔子称赞可与言诗的子贡和子夏却至多是“日月至焉而已矣”,子夏甚至还被孔子告诫“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也许就是因为子贡、子夏尚未能深造于礼乐,而颜回能够笃行克己复礼的功夫至于“不改其乐”的境地吧。
仁德的成就为何还需要礼乐之教,为何温柔敦厚的诗教还不够?朱子的注解是:
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2]121
学者凭借礼而能卓然自立,不为任何身外事物所摇夺。如果说诗教的感兴启迪学者之心,开启君子的弘大心志,那么礼教的敬让之道与节文度数则引导、约束学者的行,强化君子的坚毅持守。温柔敦厚的善感性情,需要礼教节文度数的约束,才能“和而不流”(《中庸》)、“强立而不反”(《学记》);引譬连类的微言雅语,需要落实在行礼的践履中,才不是巧言令色的华而不实之辞。士之弘毅、士之能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仅需要诗教的兴,还需要礼教的立。礼是天人、古今、人我之间交会的节文度数,即是节文度数,就需要身心的约束,同时也是彼此的相与并立和通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的心志需要在礼的节文中落实,仁在礼之中的落实,也就是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中和乐境地。朱子解“成于乐”为“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侧重在君子的内圣成德,意思虽较明确,却不如包注的“乐所以成性”可兼成己成物、内圣外王涵摄广。当然,内圣与外王体用不二,君子的内圣成德之道与外王政教之道是可以一贯的。以“义精仁熟”解释“成于乐”颇有深意,暗示了礼乐之文之于仁义之质,犹如花果之于种子的关系,君子之文并非外在人为的修饰,而是“然而日章”(《中庸》)的日新盛德与富有大业,是由洗心革面而来的虎变与豹变(《周易·革卦》)。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成就之道。这个质,是从志于仁、质直而好义到义精仁熟的仁义美质,而并非食色之性的质;这个文,是感发、引导、约束和成全仁义美质的礼乐之文,而并非文人修饰与自我表现之文,是行于天人、古今、人我之际的节文,而不是用来娱人和观赏的审美之文。诗教,既是言语之教,也是性情之教,介于文教与质教之间,既能让仁义美质有涵养的土壤,不致于流失为抽象的概念,又能让礼乐文章有性情的根本,不致于异化成奢华的虚文与僵硬的制度,因此,诗教是涵养文质彬彬君子品格的关键环节。故而,诗教是兴发士人温柔敦厚的心志、承负起成己成物、礼乐治道的文教起点。重温这一儒家文教的起点,是否能在儒家的质教与文教、内圣与外王之道皆有待重新兴起的世运下,重拾当今士君子的重任?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37.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6.
[4]程树德.论语集释: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135.
[6]彭锋.诗可以兴——对古代宗教、伦理与哲学的美学解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7]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2:285.
[8]刘小枫.德语诗学文选:编者前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