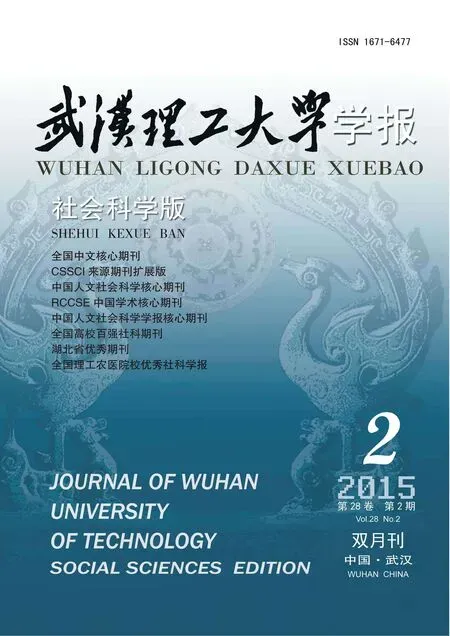冲破冤错案积弊的藩篱*
——由刑事冤错案件引发的思考
李 涛
(西南政法大学 刑事侦查学院, 重庆 401120)
冲破冤错案积弊的藩篱*
——由刑事冤错案件引发的思考
李 涛
(西南政法大学 刑事侦查学院, 重庆 401120)
冤错案件的频发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司法公信力,同时暴露出诸多方面的原因。人权观念淡薄、留有余地的审判方式以及诸多不合理的审理制度深入的积弊难返都难逃其咎。为冲破这一系列“藩篱”的禁锢,还原司法的公平正义“脸谱”,则需要立足于原因——对策分析路径,从观念改革、实践变革到制度勾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解答,如此方能有效遏制刑事冤错案件的发生。
冤错案件;留有余地;司法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10年前,因为被害人的“死而复生”,佘祥林在忍受了11年牢狱之苦后,终于卸下了那副“耻辱”的枷锁; 5年前,同样是因为被(杀)害人的“突然回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赵作海并没有“悲剧般”地把“牢底坐穿”。如果说佘祥林与赵作海是幸运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已经被枪毙的聂树斌在黄泉路上想必永远也不会瞑目。随着杀人真凶张书金的落网,聂树斌案重回大众的视野,聂树斌的冤屈也终将得以昭雪。当迟来的正义最终到来之时,佘祥林、赵作海们都留下了无言的泪水,这并非痛苦的泪,也非激动的泪,而更多的是冤屈、无奈的泪。面对如此情形,我们不得不追问,抛开公权人员不负责任行使权力的简单说辞,冤错案件的发生是否具有深层次的原因?是否我们的现有司法观念、制度设置等方面已经与民主、文明社会对司法的要求有所背离或者偏差?如果这些假定成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冲出这些“藩篱”,为已经逝去的冤魂祭奠一首挽歌或者对那些险些逝去的人们送去安慰,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具有安全感。为此,本文将遵循原因—对策分析路径,从观念改革、实践变革到制度勾画等方面进行解答,以期未来的司法审判能全面有效地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
二、求医把脉:冤错案件的发生原因
冤错案件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司法现象,任何偶然性中都蕴藏着必然。“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时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他从历史上消失的。只要人类的功利主义还在作祟,只要冤案存在的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那么冤案便不可避免。”[1]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冤错案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既然冤错案件不可能完全根除,我们就需要寻找它产生的根源,从而有的放矢地使其发生率降到最低,以此来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形象。
(一)观念上:人权观念淡薄,“司法口号”压力巨大
在论及冤错案件形成原因的诸多文献中,刑讯逼供、司法人员业务素质低下成为众多学者口诛笔伐的对象。诚然,上述因素毫无疑问是冤错案件形成的因素之一。然而,这只是表面的、浅层的原因,仔细深入分析则会发现,在目前我国司法体制下,刑讯逼供的产生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人权观念的淡漠是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所确立的两大根本任务,也是刑事审判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两个根本理念。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刑事司法中,如何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均衡,便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对此,一条总的原则是:既要坚持有罪的人必须依法受到追诉,也要坚持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当然,在二者无法平衡的前提下,必须更加注重人权保障。坚持人权保障理念,体现在刑事实体法上,就是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落实到刑事程序法上,则必须要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但是,长期以来,深受传统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障”,“重定罪、轻量刑”等思维惯习在一部分刑事司法工作者中仍然存在,而“刑讯逼供”、“疑罪从轻”等宁枉不纵的错误做法在个别地方仍然屡禁不止。可以说,人权保障观念的淡薄,是导致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冤假错案频发的罪魁祸首。这在“赵作海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案的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严重的“先入为主”的办案倾向,以至于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一错再错:一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了尽快破案,不惜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证人的言词证据;二是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公诉机关对赵作海所控诉的被刑讯逼供的事实置若罔闻,以致该案失去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三是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院仅为被告人象征性地指定一名律所实习生担任如此重大案件的辩护人,以致无罪辩护言微力乏。
其次,在“司法口号”压力下,刑讯逼供沦为案件侦破的不二法门。“口号文化”在中国司法史上历史悠久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被强大舆论支持着的“口号”往往会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法律意识形态,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然而,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口号文化则极易异化为办案指标,甚至突破法律规范,冤错案件的出现就在所难免。比如,在公安机关中常常作为军令状出现的“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的口号,则成为司法人员考核的指标之一。为了实现该口号,即完成考核指标以求得晋升与加薪,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在注重效率与结果的影响下,通常会放弃或忽视程序的要求,以至非常规手段——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则成为必然,同时也埋下了冤错案件形成的祸根。
(二)实践中:“留有余地”的判决盛行
事实上,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发生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为中国法院长期坚持的司法裁判逻辑,那就是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3]。根据陈瑞华教授的研究,留有余地的判决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现实中的“留有余地”,即指所谓的疑罪从轻的裁判方式;另一种是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即指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尚无法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的,法院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应当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3]不可否认,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即对量刑存在疑问的案件作出宽大处理是正当合理的,而现实中的“留有余地”由于违反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则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但问题是,这两种意义上的“留有余地”能都有完全、清晰的界分吗?答案是否定的。在目前我国的审判体制下,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并非截然分离,而是交错进行的。如此,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不可能仅仅考虑定罪证据或量刑证据,而都必须将二者交互适用。那么“强调量刑证据存在疑问时可以慎用死刑,势必在实践中走向在定罪证据存在疑问时也可以‘留有余地’,所谓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很容易直接滑向现实中的‘留有余地’。从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一系列刑事误判案件的情况来看,中国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留有余地’裁判,那就是在案件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尚存明显疑点的情况下,法院没有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是宣告被告人构成犯罪,但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量刑上‘留有余地’,选择死缓或者更为轻缓的自由刑”[3]。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人员错误地将“留有余地”偷换了概念,从而使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成为司法人员做而不谈的潜规则。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裁判方式并不因其广泛存在而具备合理性。申言之,因为其与无罪推定原则的直接背离,将可能直接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因而,应当坚决地予以摒弃。
(三)制度上:不合理的审判制度积弊难返
冤错案件的发生何以如此频繁,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必定有着制度上的缺陷。因为只有现行的不合理的审判制度才能使冤错案件的生产过程披上“合法”的外衣,才能使冤错案件的发生屡禁不止。因此,深入探讨这些不合理的审判制度包含哪些方面的因素就显得极其重要且十分必要。
其一是不合理的地方政法委制度。在我国,作为党政机关存在的地方政法委,在理论上具有积极的存在意义。“要保证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得以有效运行,就需要地方政法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协调功效;此外,地方政法委通过对刑事案件进行协调处理也可以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4]但是,现实中,这种协调常常因公检法机关由于具体刑事案件中各自间的利益纠葛而演变为“利益协调”,从而使协调异化为不当干预,尤其是在重大刑事案件中,这种不当干预可谓贻害无穷,赵作海案、佘祥林案都是政法委协调(干预)下的结果。除此之外,地方政法委干预、协调还严重损害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原则。在此制度下,审判独立已被架空。当法律不再成为案件审理的唯一根据时,冤错案件的发生就只是时间问题。
其二是利弊参半的审委会制度。审委会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审判制度,其产生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在法律不健全、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为求得公正的处理结果而设立的。时至今日,在迈向法治轨道的今天,无论是司法规范的设置,还是司法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都已今非昔比,但审委会制度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在充满人情关系的中国社会,一个案件的审理,尤其是主审法官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他除了要依照法律规范之外,还要协调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而审委会的存在,无疑可以屏蔽掉案外的诸多无形压力,使法官分流人情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确保了审判结果的公正。然而,审委会制度的天生缺陷也使其有产生冤错案件的风险。如审委会的成员主要来自院长、副院长及主要部门负责人,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直接参加庭审,也不可能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陈述与证言;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并非全部都精通刑事审判业务,这就造成了法院内部“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审判分离”的尴尬局面。事实上,每一个冤错案件的发生,都是在审委会的“把关”、“审议”之下发生的。
其三是滥用的发回重审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5条规定,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二审法院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而在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改判的情况少之又少,只是反复地、无休止地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以佘祥林案件为例,湖北高院在发现证据漏洞百出、难以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并没有作出无罪判决,而是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这一系列行为背后其实隐藏着司法机关已深入骨髓的有罪推定意识。而且作为级别相对较低的下级法院,在对抗行政干预方面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力量和能力,因此,发回重审的结果通常还是坚持原审判决,冤错案件的发生并不能得以纠正。
其四是公、检、法机关的利益联姻架空了相互间的监督、制约职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三个机构之间的利益关联,“三家变一家”似乎已成为潜规则。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定罪方面存有疑点的案件,法院如果作出无罪判决,将会使公诉机关受到极为负面的评价,使公诉人受到严重的负面考核结果;检察机关一旦作出不起诉、不批捕的决定,也会使侦查人员甚至负责侦查监督的检察官受到负面的考核结果。”[3]而此类考核直接与公检法机关的年终综合评分以及具体办案人员的晋升与奖金挂钩。简而言之,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或法院的无罪判决对其相关下级机构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政法委的协调、下级机构的阻挠就成为必然。公、检、法之间的制约机制也被虚化甚至架空,在利益的驱动下,缺少制约的司法机关最终酿成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冤错案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症下药:防范冤错案件发生的具体对策
幸运的是,无论我国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已发现了冤错案件产生的症结所在,具体而言,抛开司法腐败,观念落后、权力干预、非法举证等问题都是起因。那么,以此为切入点,也将拉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序幕。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提出三点建议。
(一)破除“口号文化”,树立人权保障理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宪法的修订也拉动了程序的进一步完善,与此相对应,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刑事诉讼法》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确立了该原则,目的在于更好地平衡犯罪打击与人权保护。为此,转变司法观念,牢固树立人权保障理念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表示,不要苛求“命案必破”。这体现出最高司法机关对“口号文化”的摒弃,也体现出倡导层面的所谓口号被转化为制度层面的硬性指标在司法实践中成为某种“规则”,进而对刑事司法已经造成相当大负的面影响。由此可见,树立人权保障观念与破除口号文化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只有树立人权保障观念,才能遵循法律规定探求案件事实而非按照“口号”要求“另辟蹊径”;只有杜绝非理性“口号”,才能真正做到保障人权。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刑事审判工作中牢固树立以下人权保障理念:一是坚持程序正义。实质正义固然重要,但要实现它并非易事。只有保证审判的每一个步骤公平正义,最后的结果才有可能公平正义。实体正义不应依靠、也不可能依靠非正义的程序来获得。二是坚持程序优先。虽然单凭程序正义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正义,但正义的程序可以最大化地减少人为的错误。因为个体作恶被枉纵较之于制度作恶冤枉无辜要轻,故“两害相权取其轻”,程序与实体冲突之时,程序必须优先。三是坚持罪刑法定。刑法必须使得国民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否则个人的自由无法保障。因此,在定罪量刑中必须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四是坚持无罪推定。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必须推定其无罪。
(二)严格执行证据规则,完善律师辩护制度
留有余地的判决的逻辑起点是疑罪从轻,尽管对疑罪从轻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但是,这仍然构成了对无罪推定这一基本原则的根本背离。众所周知,无罪推定原则是宪法“尊重与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根本体现,也是刑事诉讼中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可能会放纵个别罪犯,而坚持疑罪从轻则可能会冤枉个别好人。在纵与枉的两难选择中,作为以公正为终极价值取向的法律必然会作出价值选择。而纵与枉其实暗含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守与进,纵即是在守的思想指导下的结果,枉则是在进的思想指导下可能产生的结果。法律从来不积极地指导人们如何行为,只是消极地告诉人们哪些行为不该实施,即法律的总体思想是以守为进的。那么,权衡这两者,择纵而弃枉就是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是与法律的基本精神暗合的。任何原则都是抽象的,必须以相应的规则加以落实,而无罪推定原则要落到实处,就必须严格遵守证据规则以此防范刑讯逼供。其理由不难理解,因为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刑事证据的“成色”如何,直接影响定罪量刑,影响办案质量,影响人权保障。凡冤错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证据瑕疵——不是证据内容证明不了事实,就是取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前者,要解决的是证据内容的证明力问题;对于后者,要解决的是取证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有鉴于此,新《刑事诉讼法》对此作出了明确的修改,不仅“证据”一章的条文从8条增加到16条,还新增了两种证据类型,更重要的是新刑诉法在吸收五部门“两个证据规定”内容的基础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和职责。对于非法言词证据,要坚决适用绝对排除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要正确适用相对排除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方法违反法律规定从而致使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必须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对该实物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外,还强化了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并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这充分体现了新刑诉法不断强化的司法要求是“对证据的疑点一个都不放过”,也是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得以贯彻的重要手段。因此,无论是在刑事侦查阶段、检查起诉阶段还是法庭审理阶段,严把证据关,摒弃留有余地判决,坚持将无罪推定原则进行到底,才能为防范冤错案件打下实践基础。
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形成辩护权与侦查权制衡的良性循环,形成公权力之外的监督,就更利于防范冤错案件。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事实上是被隔离于刑事侦查程序的,具言之,侦查阶段的律师作用仅仅被定位为从事法律帮助的人员,会见权受到极大限制且无取证的资格。而通过辩护权制约侦查权是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手段。实践中,长期困扰律师办案的问题无非是会见难、阅卷难和取证难。而这些恰恰就是辩护权无法制约侦查权的表现。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可以看出这一方面取得的进步。该次修订明确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受委托的律师在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和案卷材料。尽管这些修订对辩护权的设定进行了细化并扩大了律师的部分权力,但作为同一个法律共同体中的成员,律师的权限依旧非常有限且受制于公权力。如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试行)》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该规定体现出公权力对律师的一种姿态表达——要听取律师意见,但从刑事诉讼整个程序来讲,律师的声音太微弱。且不说在侦查阶段律师无法介入、监督侦查活动,即使偶有听闻律师介入也无法收集成详尽的书面材料加以呈送。此外,检察人员对与当事人有关的材料都应当认真审查,无关乎是否为律师提出的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材料,以形成律师有效监督诉讼程序的局面。
(三)完善司法职业化、独立化和行业自律制度
近年来,司法独立命题在学界硕果颇丰,我国政府高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了“保障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明确说法,因此本文不打算跟风论证司法独立这个宏大命题。但就防范冤错案件而言,司法独立问题又具有一些独有特色。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并没有完全做到司法独立是客观事实。而在冤错案件发生的诸多原因中,司法不独立绝对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然,我们相信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司法独立目标会逐渐实现。但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地不再让因司法机构受命于人的原因造成冤错案就值得我们思考。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尽早实现司法职业化,这也是现阶段体制能够逐渐解决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试图改革或者废除政法委制度,因为地方政法委很多时候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冤错案件的发生,而推动司法职业化的好处在于让一个司法外行“免开尊口”,即让政法委很难对他不擅长的问题随意干涉。这既保留了现有机构设置,又巧妙地回避了其不当干涉。另一方面就是推动法院、检察院的去地方化、行政化。通常而言,更高级的统治机构关注的是统治秩序的巩固而较少关注社会公平,而下级机构和官员则更多地表现出向上级表达忠诚和能力。于是,一旦出现问题,地方机构往往喜欢隐藏而对外对上表达出公平正义的信号,这导致地方法院、检察院被被动捆绑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战车上,从而出现背离法律的情况。当前,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所体现的“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原则的提出,司法去地方化正随着地方司法机构被统一纳入省级财政而开启了逐步试点。当司法机关不再唯地方党政马首是瞻时,就会免除动辄以 “维护地方和谐大局”的名义而湮灭对案件的规范化处理。去行政化则应当坚持“庭审中心主义”,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精简审委会成员人数,与此同时将少数业务能力较强、审判经验丰富但非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纳入审委会,确保案件审理的效率与公正;二是坚持审判长负责制并对发回重审的适用进行适当限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改革发回重审制度的重点是将其适用范围限制缩小。笔者认为,对于刑事案件中证据明显不足、存在合理怀疑或者经两次发回重审仍然证据不足的案件,上级法院应当表现出足够的担当与勇气,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坚决、果断地直接作出判决,不得为延迟诉讼而滥用发回重审权。
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形式上通常是由公、检、法三机构合力完成的(贪污渎职等犯罪例外),整个完整程序无法缺少其中一个机构而独立存在,那么,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机构的不正当火星都可能最终蔓延成冤假错案的熊熊大火。因此,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参与人员都必须要将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依据。而我们也知道,冤错案件的发生除了外在干扰外,司法腐败也是重要成因。换言之,任何一个在司法过程中存在司法腐败的人都有可能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但在专业领域,骗骗外行很容易,但忽悠同行就需要费很多功夫,因此必要的行业自律是系统内部自查的重要举措,是将害群之马踢出的最好办法,也是维护整个法律共同体公信力的积极手段。“给法官一个紧箍咒,谁用权就要负责一辈子。”[5]这是某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长的话,是法院欲把审判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具体表现。这不仅适用于法官,也适用于参与刑事司法程序的所有公职人员。而错案追究制度(不同机构可能有不同称谓)是行业自律的具体办法。因为在审查一系列冤错案时通常就发现个别人员业务素质低下、责任意识淡薄甚至以权谋私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因此,这种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参与刑事诉讼的公职人员如果出现错案则会受到相应的惩处,这将促使他们侍更加廉洁和谨慎地行使好手中的权力,为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树立一道重要屏障。当然,刑事诉讼的“错案”必须有严格的标准,既要防止司法公职人员恣意枉法办错案,又要充分维护侦查人员、公诉人员依法产生的“司法前见”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四、结 语
时至今日,在我们畅谈自由与公正、法治与理想时,冤错案件可能正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慢慢发酵。“人们都希望在公正而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判决有罪的证据既有压倒性优势,又显示出比被告人的无罪主张更可信。但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刑事司法程序的每个阶段如何费尽心机,错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6]既然如此,分析其成因,使冤错案件的发生率降为最低就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我们相信,从观念、实践及制度三方面出发,构筑防范冤错案件发生的有效机制,形成多层面、立体式防控体系,就可以有效减少冤错案件的实际发生率。
“法律秩序所关注的是,人类不必像哨兵那样两眼不停地四处巡视,而是要能使他们经常无忧无虑地仰望星空和放眼繁茂的草木,举目所及,乃实在的必然和美好,不间断的自我保存的呼救声至少有一段时间沉寂,以使良心的轻语终能为人们所闻。”[7]而当冤错案件的发生不再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当不幸成为被告的那些人在审讯时可以合法地保持沉默,当法律真正成为审判时的唯一依据,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司法机关开始自我省思时,拉德布鲁赫所展望的这种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才可能真正实现。如今,我国司法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是我们对冤错案件发起的有力“挑战”!
[1]刘宪权.克减冤错案件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J].法学,2013(5):61-68.
[2]郭敬波.冤假错案背后的“口号”成因[N].人民法院报,2013-05-12(02).
[3]陈瑞华.留有余地的判决:一种值得反思的司法裁判方式[J].法学论坛,2010(4):26-32.
[4]曾 军,师亮亮.地方政法委协调处理刑事案件的制度考察及分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2):65-72.
[5]双 瑞,黎华玲,李亚楠.严防冤假错案,中国强化法官责任追究[EB/OL].(2013-07-10)[2014-03-05].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7/10/c_132527900.htm.
[6]克莱夫·沃克.司法不公与纠错[M].姚永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56.
[7]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 健,朱 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69.
(责任编辑 江海波)
Breaking the Barriers of the Maladies of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s Generation:Reflection on Criminal Injustice and Wrong Cases
LI Tao
(SchoolofCriminalInvestigation,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Injustice and misjudged cases occurring frequently impact the fragile justice, and expose many reasons such as weak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flexible verdicts, the unreasonable trail system. In order to break these barriers, restore the face of judicial justice,we should 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ause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and give an all round answer from concept, practice to system.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event effectively these cases.
injustice and misjudged cases; flexible verdicts; judicial reform
2014-11-20
李 涛(1984-),男,河南省焦作市人,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法学、犯罪学研究。
重庆高校物证技术创新团队(KJTD201301)
D912.6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28